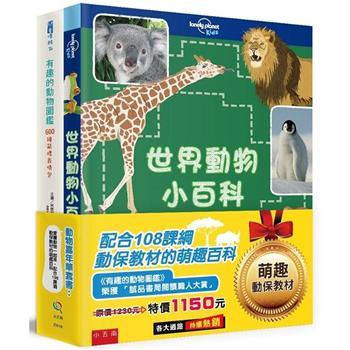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傻門春秋(精)-三民文庫077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三民網路書店 評分:
圖書名稱:傻門春秋(精)-三民文庫077
- 圖書簡介
「呆人好做,低路好行!」際茲社會生活競爭激烈,為減少人際間的磨擦,這句話益發有道理。朱耘樵女士這部集子:散文三十一篇,是作者個人生活的部份回憶。題材新穎,文字簡潔;貫串全書的是:一片樂觀向上的精神。書中有許多「吉光片羽」, 在現實生活中是夠實用的。作者很懂得生活趣味,尤其是夫唱婦隨的那種情趣。正在學校中的青年讀者,正在恩愛中的家庭夫婦,可把本書當作「生活指南」。
- 作者簡介
幼柏
1923年生瀋陽巿人國立重慶女師學院畢業現任中學教師 - 序
「傻門春秋」序 孫如陵
幼柏女士連來兩封信,約我為她寫序,已經好幾天了,拿不定主意,還不能答覆她。寫吧,一時分不開身;欲待不寫,又好像這篇序,非我寫不可。原來我們同學之間,別有一段因緣,趁便一述,現在倒是一個機會。朱女士在我們西康分校讀書期間,我在重慶已經畢業,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以致我們有同學之誼,而無一面之雅。來臺以後,只因她講課之餘,喜讀中央副刊,久而技癢,乃執筆投稿。她的作品寄到,夾置其他稿件中,該用的用了,該退的退了,處理並無差異。幾年下來,偶有書信往返,岔出題外,才理出我們曾經同學的根來。雖是如此,她仍在新竹教她的書,我仍在臺北編我的報,各安所業,兩不相照,所以我們的友誼,開始是什麼檨子,今天還是什麼樣子。她的文學有根柢,她的氣質很純樸,她的生活富於情趣,讀了她幾篇作品,我就慫恿她寫作。不過,慫恿她寫作的是我,退她的稿子退得最勇猛的也是我。她其所以有成就,完全在她能以國文教師之尊,折節磨鍊,頻頻承受退稿的衝搫,而且是在「投中」之後飽受挫折,積數年之久,沒有埋怨過,沒有沮喪過,沒有停頓過。我於寫作一事,認為成敗的關鍵,不在天分高不高,而在意志強不強。朱女士的「傻門春秋」,足以證明我從事實紬繹的結論不假,因此,我樂意將這段不愉快的過程,率直道出,用來反襯這個美滿的成果,得來不易!更願藉此轉告有志寫作的朋友,誰能堅持到底,誰就穩操勝算,像朱女士一樣!五十八年九月八日於涼風送爽中 - 目次
傻門春秋
菩 薩 心
香煙與我
也是藝術
灰 色 襖
各據一方
水 晶 婚
情繫「宇宙鋒」
似聾似盲
漸入佳境
長遠的約會
他的娛樂
無弦的琴
物我同在
重見光明
何必曾相識
尷 尬
特別節目
我在湖州
打箭爐之憶
北國水寒
山
風陵夜渡
鄉音鄉情
雌雄莫辨
不勝今昔
我的軍訓生活
願再誕生一次
上夜課‧談往事
沸騰的水
人生似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