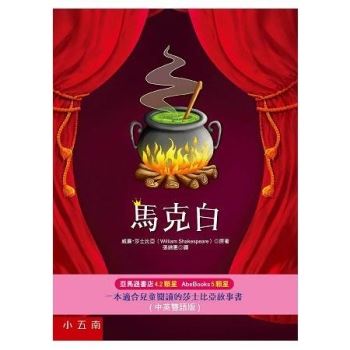那天,在一個宴會上,一位美麗的女士忽然對我說:「你們寫故事的人真好,好像可以認識各種各樣的古怪人物,甚麼人都可以在你們筆下出現。」
我笑而不答,對一個珠光寶氣、體態因為不肯在食用上稍為犧牲一點而變得肥胖、有進一步的趨勢變為臃腫的女士,很難解釋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或許她的智慧十分高,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太過優裕的生活,使她沒有多動腦筋的機會,所以自然會變得不甚靈敏。
我這樣說,絕對沒有輕視這類女士的意思,只不過指出事實。
而事實的另一點是,那位美麗的女士,真是十分美貌,她的美貌,遠在她身上所佩戴的過量的名貴飾物之上,可是她自己卻顯然不知道,因為她正以一切可能的動作,有意無意地在炫耀她手上的一隻極大的翡翠戒指,而忽略了她那帶著三分稚氣的動人的笑容。
我沒有說甚麼,在座的一位男士卻代我反駁:「其實,衛先生筆下的人物,也只不過是普通人。只不過他在一個普通人身上,發掘出古怪的事情來。」
那位美麗的女士不服氣:「普通?他連神仙都認識。還說普通?」
那位男士顯然知道對方所指的「神仙」是甚麼人,所以立即回答:「你是說賈玉珍?當衛先生認識賈玉珍的時候,他並不是神仙,只不過是一個古董商人,如果當時衛先生以低價把那扇屏風賣給了他,那麼以後再有甚麼事發生,自然和衛先生也不發生任何關聯。」
美麗的女士顯然是她說甚麼人家就一定附和她的意見慣了,所以一旦遇到了反駁,神情就相當不自在,她揚了揚手:「是嗎?那就是說,衛先生就算遇上了一個最平凡的人,也可以在他身上發掘出一個奇特的故事?」
我對於這種爭論,不是十分喜歡,一面喝著酒,一面道:「我倒有點像日俄戰爭時的中國。」
那位男士笑了起來,他聽懂我的話,可是那位女士卻睜大了眼,分明不懂,我也懶得解釋,要告訴她日本和俄國打仗,戰場卻是在中國,看來相當吃力,可是那位女士卻還不肯就此干休:「衛先生,我看你就不能在我先生身上,發掘出甚麼奇特的故事來。」
我微笑道:「恐怕不能。」
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這位美麗華貴的女士的先生幹甚麼,連她是甚麼人,我也不知道,我順口這樣說,是根本不想把這個話題持續下去。
而那位女士卻連這樣的暗示都不明白,神情像是一個勝利者:「看,是不是?」
那位男士有意惡作劇。要令這位女士繼續出醜,他問:「你先生是……」
美麗的女士的口部,立刻成了一個誇張的圓圈。彷彿人家不知道她丈夫是誰,是一種極度的無知。
席中另有一個看來相當溫文的長者,在這時道:「溫太太是溫家的三少奶奶。」
我和那位男士,不禁一起笑了起來,「溫家三少奶奶」又是甚麼玩意兒?這似乎是一些人的通病,自己以為有了點錢,全世界就該知道他們是甚麼人。當然,真到了奧納西斯、侯活嘵士或洛克斐勒,自然有權這樣,可是一些小商人,真是,請原諒他們。但是笑還是忍不住。
我和那男士一面笑,一面互相舉了舉杯表示我們都明白各自笑的是甚麼。
那位老者又道:「溫家開的,是溫餘慶堂。」
我眨了眨眼睛:「聽起來,像是一間中藥店。」
那男士也學我眨了眨眼睛:「多半還發售甚麼諸葛行軍散之類,百病可治的獨步單方成藥。」
那位男士說著,放肆無禮地哈哈大笑,抱著我:「中藥店的掌櫃,衛先生,我承認,只怕你也不能從蟬蛻、桔梗、防風之中,發掘出甚麼奇特的故事了,算我說得不對吧!」
那位男士在他的言語之中,表現了明顯的輕視,令得闔座失色,那位美麗的女士,更是一陣青一陣白,下不了臺。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衛斯理傳奇之犀照【精品集3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57 |
推理科幻 |
$ 169 |
小說/文學 |
$ 175 |
奇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衛斯理傳奇之犀照【精品集31】
※衛斯理的傳奇,也是科幻小說的傳奇!倪匡巔峰代表作嶄新出版!
※本系列多本著作曾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精彩可期!
※倪匡現已宣布封筆,要想一窺大師名作,此系列作品為入門最佳選擇。
※其餘倪匡相關作品,請參考風雲時代官方部落格(http://eastbooks.pixnet.net/blog)!
本書包含〈犀照〉、〈再來一次〉兩個故事。
※犀照
衛斯理的好友張堅從南極寄來了三塊小冰塊要求化驗,而負責化驗的胡懷玉博士突然之間性情大變而且行為怪異,難道這些冰塊暗藏著什麼玄機?還是他遭到什麼不知名的生物侵入?
※再來一次
你可知道生物進化中的有一種「返祖現象」?而且這種現象竟然是返到了幾億年之前?一個原本生命已經結束的老人竟然又得到了新的生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作者簡介:
倪匡,本名倪聰,字亦明。浙江鎮海人,1935年生於上海。1957年移居香港。學問皆靠自修而來。在偶然的機會下,他開始用筆名「岳川」為《真報》寫武俠小說,並逐漸由業餘寫作轉為職業寫作。後轉為《新報》寫稿。後來又以「岳川」、「倪匡」、「沙翁」等筆名為《明報》寫武俠小說和雜文。六十年代初,在金庸的鼓勵下,他開始用筆名「衛斯理」寫科幻小說。第一篇小說名為《鑽石花》,在《明報》副刊連載,從[此開始他的寫作生涯。倪匡寫作範圍極廣,包括武俠、科幻、奇情、偵探、神怪、推理、文藝等皆有涉獵,自稱是全世界寫漢字最多的人。現處於封筆狀態。
章節試閱
那天,在一個宴會上,一位美麗的女士忽然對我說:「你們寫故事的人真好,好像可以認識各種各樣的古怪人物,甚麼人都可以在你們筆下出現。」
我笑而不答,對一個珠光寶氣、體態因為不肯在食用上稍為犧牲一點而變得肥胖、有進一步的趨勢變為臃腫的女士,很難解釋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或許她的智慧十分高,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太過優裕的生活,使她沒有多動腦筋的機會,所以自然會變得不甚靈敏。
我這樣說,絕對沒有輕視這類女士的意思,只不過指出事實。
而事實的另一點是,那位美麗的女士,真是十分美貌,她的美貌,遠在她身上所佩戴的過量...
我笑而不答,對一個珠光寶氣、體態因為不肯在食用上稍為犧牲一點而變得肥胖、有進一步的趨勢變為臃腫的女士,很難解釋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或許她的智慧十分高,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太過優裕的生活,使她沒有多動腦筋的機會,所以自然會變得不甚靈敏。
我這樣說,絕對沒有輕視這類女士的意思,只不過指出事實。
而事實的另一點是,那位美麗的女士,真是十分美貌,她的美貌,遠在她身上所佩戴的過量...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倪匡
- 出版社: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5-23 ISBN/ISSN:978986146773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6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