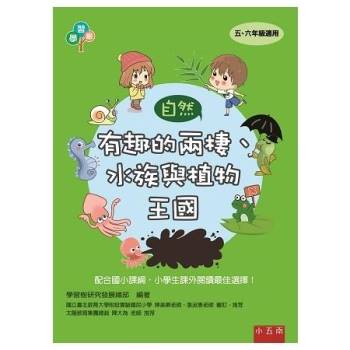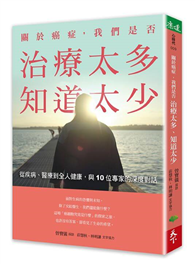第一章
話說北宋徽宗宣和年間,東京汴梁城的虎翼營內住著一戶姓陳的人家,主母早逝,只有陳老爹帶著兩個兒子過活。
陳老爹年五十許,身子骨倒還硬朗,任殿前太尉之職。長子名字喚作陳行義,在禁軍中做個教頭。小兒子年方十九,名喚陳從善,一年前中了三甲進士,御筆欽點到廣東,任的是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
且說這陳從善赴任一年以來,於公務上甚是謹慎幹練,很得上司南雄府尹張老爺的賞識。南雄府尹張老爺本是陳老爹的舊交,見陳從善生得俊美,年紀雖輕,但頗有才學,又為人正直,雖說性子稍嫌冷漠了些,但正因如此,反而顯出些難得的少年老成的沉穩來,便頗對這後生青眼有加。恰巧自己有個女兒,小字如春,與陳從善年貌相當,便有心結這一門親家,當下尋了街坊王媒婆登門一說。陳從善年已十九,正是該當娶親的年紀,想著如春小姐家世清白,又是父親世交之女,雖未見過面,但嘗聞如春小姐賢德之名,此時府尹大人紆尊降貴先來提親,如何不應?此番親事,便再無不成的道理。
陳從善既應了這門婚事,自然要寫家信稟告父親,又尋思著在這南蠻瘴癘之地,高堂不在身邊,如此草草完婚,未免委屈了張家的姑娘;恰又接到父親的回信,教他將新娘子接回東京汴梁,再熱熱鬧鬧的操辦婚事,便稟告了未來的岳丈,要將張小姐接回京中成婚。張府尹聽了,亦是十分贊同,連誇陳從善辦事妥當得體,又捨不下獨生的女兒,便幫忙打點了不少行李,只待陳從善將衙門裡的事務交割完畢,便要同他們一起上路回京了。
這日正是三月十五,第二日便是上好的吉日,正好成行。陳從善在街上逛逛,尋思著再採買些特產之類,也好帶回京城分送親友。
沙角鎮上三月十五有個不小的廟會,左近村鎮的貨郎、打把式賣藝的都彙集到了沙角鎮南邊的集市上,陳從善走在街上,滿眼均是塵埃煙火氣,世俗的快樂。
他在街角微微笑了笑,一回頭,卻被不知哪裡冒出來的一個算命老兒拉住了衣袖。
大羅仙界,觀塵池邊。
大羅仙界的觀塵池,水面如鏡,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池內亙古開著白、粉、藍、紅、金五色蓮花,其中以金色最為稀有,歷五百劫才得見一次。
這日,紫陽真君一陣仙夢沉酣醒來後,隔著重重的碧玉樓臺,翡翠欄杆,遠遠望見那觀塵池中金光一閃,登時忘記了寶相之莊嚴肅穆,光著腳便跳將起來,衝到了池邊。
果然是金蓮花盛放。紫陽真君急著叫仙童來,吩咐下去,命將玉清元始天尊、上清靈寶道君、南極仙翁、清虛道德真君、玉鼎真人、赤精子、廣成子等一眾仙友速速請來,共賞金蓮花。
紫陽真君這廂吩咐完畢,回頭看時,卻見那不斷變換景象的池中正映著一個黑衣少年的身影,少年站在街頭微微一笑,容顏之明媚,竟使那無比絢爛的金蓮花都稍失了幾分色彩。
紫陽真君朝那少年看了一眼,微覺面熟,恍然記起,這少年幾百年前,與自己曾有一段善緣,今番再見,眼前這人已長成如此風致的翩翩少年,不覺感慨;又見這少年容顏雖是明媚俊美,但眉宇間似是縈繞著一縷黑霾,顯見是不祥之兆。
紫陽真君皺皺眉頭,掐指一算,原來是命中應有之劫數,雖說天機不可擅自洩漏,但今番得見故人,不若幻化下界去,略加提點。若此人有造化,悟了他的仙機,或可避過此劫也未可知;若他沒造化,那也是命中注定的,這劫雖來勢洶洶,其中更有萬般苦楚,但亦非闖不過的。
思及此處,紫陽真君便呵出一口仙氣,幻化出一頂破破爛爛的青唐方巾,一領百衲水田直裰兒,左手在空中一撈,便撈出一柄布幡,上書「鐵口直斷」四個大字,抹抹臉,隱去了流光溢彩的真容,只一彈指間,便立在了沙角鎮廟會的街頭,伸手拉住了陳從善的衣袖。
「這位小哥兒,你且住一住。」紫陽真君涎著張老臉,一雙枯樹皮般髒兮兮的老手死死拉住陳從善的淨絲黑袍。
陳從善略略愕然,回頭道:「老人家,你叫我何事?」
紫陽真君見他待人和氣有禮,不由心中又讚了兩聲,當下不露聲色,只管胡纏:「這位小哥兒,小老兒見你印堂發黑,面帶晦澀且烏雲蓋頂,可要小老兒為你算上一卦,以逢凶化吉、趨利避害?」
陳從善乃三代將門之後,自小又跟隨先生讀書多年,最不信這怪力亂神一說,但看著紫陽一身行頭著實可憐,便從腰間的褡褳內摸了一塊碎銀子出來,擱到紫陽手中,溫言道:「老人家,這銀子給你,卦卻不必起了,我是素來不信這些的。」
紫陽收了銀子,正色道:「小哥兒近日不要出遠門,否則便是大大的不吉啊,你若執意上路,便有千日之災。」
陳從善聽了,並未當真,只微笑道:「多謝老丈提點。」略一拱手,便朝著最近的乾貨攤子去了。
紫陽見話已帶到,命定之劫數,乃是天機,亦不便說得太多,言盡於此,陳從善是信也罷,不信也罷,便要看他的造化了。當下便幻化成一道清氣,回那大羅仙界,同眾仙友賞金蓮花去了。
一個月後。
梅嶺。
吳地的梅嶺風光旖旎,故一向有「小廬山」之稱,谷壑幽深,峰巒秀麗,水碧山青,讓陳從善一行人留連不已,故而因貪看山間景色,錯過了宿頭,眼見著天色漸黑,陳從善不由得有些發急。
催馬緊走,可眼前層巒疊嶂,一架山一架坡,哪裡有半個人煙?
話說這梅嶺上有個獅子峰,獅子峰上有座洞府,名叫「十二洞天」,洞內住著個修陰陽和合道的地仙,大號喚作申陽。
這申陽本是個山中的魈,修煉已有千餘年,道行深厚,且修的又是事半功倍的陰陽和合道,雖說不大體面,但修此道者,不易犯什麼天規,因此闖過九十九次天劫之後,便算是修成正果,可以稱為地仙了,但若要位列天庭的仙班,卻還是遙遠得緊,不知還要再過幾世幾劫了。
不過地仙自有地仙的逍遙,跳脫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又沒有天庭的清規戒律來束縛,是以申陽終日吟風嘯月,蝶舞花叢,端的不愧這逍遙二字。
這日申陽正在洞府中閒坐發悶,一眾姬妾孌寵,紅偎翠繞的過來湊趣,申陽摸摸這個,親親那個,正玩兒得沒興頭間,忽有小妖兒來報,說是一隊人馬進了獅子峰下,看是個送親的樣子。
申陽起了興頭,催動目力,果見山下來了一隊人馬,當中兩乘小轎,前頭那個轎內,坐著個花白鬍子的老頭兒,申陽頗嫌晦氣的啐了一口;又觀那第二頂小轎兒,赫然一個年方二八的妙齡少女在內,容貌雖說不上豔麗,但別有一番清麗靈動之意,當下心中一蕩,便要下山捉了她來。
心中這一蕩不要緊,連眼神也跟著蕩上了三分,眼角便瞄見一個黑衣少年端坐馬上,那少年回頭跟身邊的伴當說了句什麼,眼波流轉間,一張明媚的臉便如一根釘子般打進了申陽眼中,再拔不出來。
此時再反觀那轎中的少女,姿容更見平常,連一雙眼睛,都顯得黯淡無光起來。
申陽坐在洞中只歎了一聲:「月是少年明啊!」便倏忽不見蹤影。
這梅嶺中照例是有山神土地的,這山神土地照例是廟小龕破難以棲身、香火不濟缺少供奉的,是以他們照例是聽命於盤踞此山的妖魔鬼怪申陽的。申陽未成仙前是如此,成了仙後,山神土地更是對其俯首帖耳,唯命是從。
只消一個訣,申陽便喚了這二神出來,如此這般吩咐下去,不過一盞茶的工夫,一家小小齊整的客棧便立在了陳從善一行人必經的山路旁。
陳從善等人正焦急間,忽然山路回轉間,露出小小一方酒幌,玄黑的底子,上面月牙白的一個「酒」字,待看去時,卻是一座齊整的二層青磚小樓,大門敞開,內中散坐著幾個食客。
眾人見了大喜,紛紛下馬下轎,自有一干丫鬟養娘簇擁著如春的轎子,伺候姑娘下轎。
陳從善為人十分守禮,況且本就性子冷淡,此刻與如春小姐雖已訂親,但因著男未婚、女未嫁,男女授受不親之故,在如春面前向來是目不斜視,亦絕不多說一個字,多行一步路,生恐唐突了人家一向養在深閨的女孩兒。是以此刻只到張府尹轎前,先躬身叫了一聲「世伯」,扶了張府尹下轎。
堂內早有土地老兒幻化的店夥迎了出來,胳膊上搭著雪白的手巾把子,俐落的一抖,擺開笑臉道:「客官裡面請!」將一干人等接了進去。
如春的丫鬟嬤嬤等人先是將小姐扶到角落的一張桌邊,鋪設了錦褥腳踏等物,攙扶了坐下,又從行李車上抬下了一架屏風,遮得嚴實了,方才出來招呼茶水點心等物。
如春這般的排場,陳從善一路上見得多了,當下見怪不怪,只那夥計吃驚得張大嘴巴,陳從善望著他道:「小二哥,可有甚湯水菜蔬?」
那小二低聲嘀咕道:「好傢伙,比我這神仙的排場都大。」
陳從善沒有聽清:「什麼?」
「啊哈啊哈哈,沒什麼沒什麼,這位客官,小店有祕製的滷牛肉、野筍子燒鵝、老鴨湯,另外今兒還有新鮮的爛煮黃精,山陰板栗,客官可要嘗嘗?」心中則暗道:「你不知幾世修來的福,讓個神仙伺候你點菜。」
陳從善先低聲詢問了張府尹的意思,再向小二道:「就這樣吧,每樣都上一個,那邊桌上也依此例就好。」
店小二領命而去,不一刻布了菜來,一一鋪排妥當,那菜香氣撲鼻,別有一種山野風味,一眾十幾個人是早已餓得狠了,風捲殘雲的吃了,便有山神幻化的掌櫃出來,問可要住店。
店自然是要住的,但這客棧甚小,二樓的客房安排了張府尹和幾個姨太太並通房大丫頭、上炕老媽子、如春小姐等等女眷之後,便再無空房,陳從善便和伴當僕役們在一樓的堂內排開了鋪蓋。
本來這一路行來已有一個月,陳從善饒是年輕體健,卻依舊免不了疲憊不堪,誰知今日累雖累極,但卻偏生睡不著。他在被內輾轉了數十圈,愈加覺得渾身上下不痛快,見那店門只是虛掩,並未上鎖,便爬將起來,欲到外面略散一散。
這日正是四月十六日,有句俗話說得好,十五不圓十六圓,此刻正是一輪明月高懸,月光便如潑銀一般,映得這山間的月色更是清雅。
陳從善信步走著,轉過一叢竹林,眼前豁然開朗,竟是一池碧清可愛的小潭。他走到潭邊,只見水面上正絲絲縷縷冒出些熱氣,伸手一試,那水竟是溫熱的。
陳從善生性愛潔,上路這一個月來,舟車勞頓,早已是渾身塵土,此刻見了這溫泉,看看四下無人,便脫了衣裳,慢慢走進水中,頓時舒坦得長歎了一口氣。那熱水將他渾身的肌肉泡得鬆弛舒服,加之熱氣一熏,竟模模糊糊的靠著潭邊的石壁睡去了。
不知睡了多久,陳從善在睡夢之中似是聽到了些「嘩嘩」的水聲,那聲音先是似有似無般的聽不真切,過了一會兒,漸漸大了起來,似是有人在近旁撩著水盥洗一般。陳從善迷糊間張眼一望,但見清澈如銀波玉暈的月光之下,一人正在潭中,全身赤裸,水沒到腰際,雙手掬起一捧潭水,自頭上澆落,凝結了的水珠順著那人黑緞一般的長髮滾落到胸口的皮膚上,那肌膚細膩如鴿腹上潔白的柔羽。那人回過頭來,對著陳從善微微一笑,面色皎潔如月,眼瞳如點星子,長髮似流雲,淡雅絕俗。
陳從善一瞬間覺得周圍的一切都暗了下來,眼前僅只那渾身披滿亮銀月光的人是唯一的亮色,不由得呆住了。
端的是人間仙景。
此人正是申陽。
申陽早已覺察到陳從善醒來,當下強自按捺住胸中翻滾的春意,只不動聲色的轉過頭來,對靠在潭邊瞪大眼睛的少年微微笑了笑,臉上的表情,三分笑意,六分慵懶,一分挑逗,火候拿捏得剛剛好。
陳從善怔愣了半晌,方才覺出自己眼下的尷尬處境--自己赤身裸體不說,還盯著一個素不相識人的裸體看個不住,簡直是--失禮之至。當下臉便憋得通紅,結結巴巴道:「這位--兄臺?我我我--在下--這個……」
申陽見陳從善一張臉都紅得透了,越發的可愛,恨不能當下便將他壓在潭邊弄個興盡,但申陽一向自詡風流,總是誘得他人心甘情願雌伏於自己身下,這等強人所難之事,是從不屑做的。當下不露聲色,站在池間深深一揖:「在下便是此間客棧的主人,姓申。這位小哥兒可是今兒個來投宿的客人?」
「這個,正是……」陳從善從池中立起身來,手忙腳亂的在草叢裡撿了衣服穿上,「我冒昧來此地,這個--實在是失禮了,申兄莫怪、莫怪。」
申陽笑道:「這潭溫泉乃是天然在此,也不知有幾千幾萬年了,又不是我一人私有,人人都可來得,又怎有失禮一說呢?」
說著,慢慢踱到池邊,抬腳便要上岸。陳從善見狀,連忙將臉低到不能再低,大氣也不敢出一聲。
申陽暗暗好笑,故意磨磨蹭蹭的穿衣,穿好之後,揚長而去。
這邊廂陳從善又足足在池邊發了一炷香工夫的呆,這才悄悄啐了自己一聲,輕手輕腳摸回客棧大堂,鑽進了被內,胸口內一顆心兀自跳得如擂鼓一般,是再睡不著的了。
輾轉了又幾十遍,忽的那客棧大門「吱呀」一聲被拉開了,先是一片月光流了進來,繼而被一道黑影遮住,那黑影停了片刻,腳步窸窸窣窣的走到陳從善近前,一陣淡淡的冷香自那人身上氤氳而出。陳從善閉目裝睡,那人輕笑一聲,如翠玉相扣般柔和悅耳,俯身問道:「兄臺可是睡不著?」
「是申兄啊……不知?」
「兄臺可願隨我到山中一遊?」
陳從善便如被蠱惑了一般,說不出半個「不」字,雖是略有遲疑,仍道:「……好。」
申陽輕輕的笑了笑,他一向不做那等霸王硬上弓之事,有傷風月情調不說,淫人妻女乃是大罪,是犯天條的,但若是兩廂情願,便是玉帝老兒管得再寬,也管不到人家夫妻的炕頭上來,此時見陳從善早已被自己迷得三魂七魄只剩其一,便得意一笑,伸手在他面上一揮,陳從善便睡得熟了,再不做一聲。
陳從善再睜眼時,似是在空中馭風而行般,耳邊有風聲獵獵作響,自己正趴伏在一人背上,以極快的速度在半空中縱躍。
陳從善大驚失色,劇烈的掙扎起來。他本是三代將門之後,從小習得文武藝,身手也著實了得,這一掙之下,背他那人險些脫手。
陳從善邊掙邊叫道:「你是誰?」
那人緊了緊雙手,腳下未停,只悠閒回頭一笑,赫然是那客棧中的小二哥。那小二哥道:「客官莫急,且隨小神到申陽公子洞府之中小坐,此刻萬萬動不得,你看看腳下。」
陳從善低頭一望,頓時叫了一聲「苦也」──但見明月清輝之下,四下皆是一片萬丈深淵,黑魆魆的深不見底。
陳從善問道:「你到底是何人?」
小二哥道:「小神乃是這梅嶺的土地,那申陽公子,便是此地修煉得道的妖仙。」
「什麼!」
「公子少安毋躁,待到了十二洞天,便一切知曉。」說畢幾個起縱,如風馳電掣一般,不一刻,到了一座地勢峭拔險峻的孤峰峰頂,眼前是一扇青石大門,上書四個古拙蒼勁的大字--「十二洞天」。
那土地將陳從善放下,道:「申陽公子這洞天福地,小神是不得進的,客官你自進吧,小神去也。」說畢,走到崖邊,縱身一躍,竟不知去向了。
陳從善其時兀自懵懂未解,四下一望,均是一片黑魆魆的深淵,此時退是無路了。暗恨自己鬼迷心竅,竟應了個素不相識之人的邀約,枉費了往日的沉著幹練,竟被迷了個神魂顛倒。也不知這申陽到底是人是仙,是妖是怪,左思右想,萬般無法,只得走上前去叩那青石大門上的門環。豈料手剛剛觸到那門板,門便「吱呀」一聲應聲而開,那洞中透出一縷清澈至極的乳白色光暈來,更兼有仙樂自內裊裊而出。
陳從善站在洞口躊躇片刻,退路已無,只有進洞,況他本就不是膽小的鼠輩,當下仗劍而入,且先看看這申陽到底要耍什麼把戲。
進了那洞,便是一道幽深的隧道,四周的石壁竟是乳白色的玉石雕就,隱隱散發著柔和的光暈,洞內氣息清新,似是有微風徐徐。走得幾步,眼前豁然開朗,一座山谷內,竟是個極大的庭院,其間月光花鳥,潺潺流水,一如洞外風光,有詩為證:
樓臺高峻,庭院清幽。山疊岷峨怪石,花栽閬苑奇葩。水閣遙通行塢,風軒斜透松寮。回塘曲檻,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嶂層巒,點點蒼苔鋪翡翠。牡丹亭畔,孔雀雙棲;芍藥欄邊,仙禽對舞。紫紆松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岐,紅豔叢中喬木聳。 煙迷翠黛,意淡如無;雨洗青螺,色濃似染。木蘭舟蕩漾芙蓉水際,鞦韆架搖曳垂楊影裡。朱檻畫欄相掩映,湘帝繡幕兩交輝。(註一)
陳從善尋思,這申陽莫不成是個真仙?洞中竟有風光如斯,端的不負這「洞天」二字。
「冒昧請公子前來,是申陽失禮了。」一道清澈的聲音自假山後轉將出來,但見那花陰月下,緩緩走來一人,只見那人:
唇紅齒白,眼秀眉清;秋水以為神,瓊玉以為骨;淡似煙霞,潔若秋霜。
正是申陽。
陳從善見這等景觀,又見申陽如此人物,便是自來不信怪力亂神之說,亦早覺察申陽不是尋常凡夫,便不是神仙,也當是個皇孫貴胄,隱居於此;又見他言行謙遜有禮,溫和瀟灑,當下還了一禮,道:「公子言重了。」
申陽走近前來,攜起陳從善的手道:「在下略備了幾杯薄酒,公子若不嫌棄,且請移步廳上,共飲一杯何如?」
陳從善回禮道:「承蒙不棄,請。」
二人便相攜入席,一時間席開玳瑁,宴設芙蓉,更有無數美童秀婢在旁服侍,另有樂姬數人,調弄琴弦,未幾,宮商迭奏,絲竹並呈。
席上自然是炮龍烹鳳,珍饈羅列,更兼這申陽修煉千餘年,一向談玄論道,此刻將往日所得略略談了一二分,便令陳從善欽佩不已,直贊申陽乃是天縱奇才,遂問道:「以兄之才,因何不居廟堂、坐高位,反在這山野之中隱居呢?」
申陽一笑,道:「在下一向自認才學不凡,卻屢屢科場失意,做的文章,等閒入不得考官的法眼。這等名利之心,遂也斷了。似如今這般,與些文人墨客、隱士高僧,無論是談玄論道,亦或是詩酒放曠,更是快哉!又何必去自尋煩惱,到那爾虞我詐的官場呢?」
一席話聽罷,陳從善點頭讚歎,道:「兄乃真名士真高人,當浮一大白。」
二人相談甚歡,陳從善不勝酒力,先自醉了。申陽按捺住急色之心,本要慢慢磨轉得陳從善心甘情願雌伏於己,但又看著眼前這少年端的是秀色可餐,加之美人微醺,更添豔色,便有些耐不住了。
陳從善只道申陽乃世外高潔之人,哪裡知道他腹內轉的齷齪念頭?酒意湧上來,便放心醉倒。申陽見了,揮手叫眾人退下,輕輕撈起陳從善的身子,進了內堂。
*註一;此段詩文引自《醒世恆言》第二十九卷〈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定風波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7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定風波
陳從善從沒想到,自己堂堂一個男兒身,竟會被妖怪搶親?!
而對方口口聲稱他才沒搶,是他自己答應的?
這這這……分明就是妖魅惑人啊──
自看見陳從善後,申陽的心中就只有他的身影了。
雖是男兒身,但那身形容貌,卻是比女人更為清麗。
施了點小法術,誘得他開口同意後。
自然是展現出他的妖怪本色──搶回山啦!
「妖孽!還不快放開我!」
呵,怎麼可能放?
這輩子甚至是下輩子,他都不可能放手的!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話說北宋徽宗宣和年間,東京汴梁城的虎翼營內住著一戶姓陳的人家,主母早逝,只有陳老爹帶著兩個兒子過活。
陳老爹年五十許,身子骨倒還硬朗,任殿前太尉之職。長子名字喚作陳行義,在禁軍中做個教頭。小兒子年方十九,名喚陳從善,一年前中了三甲進士,御筆欽點到廣東,任的是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
且說這陳從善赴任一年以來,於公務上甚是謹慎幹練,很得上司南雄府尹張老爺的賞識。南雄府尹張老爺本是陳老爹的舊交,見陳從善生得俊美,年紀雖輕,但頗有才學,又為人正直,雖說性子稍嫌冷漠了些,但正因如此,反而顯出些...
話說北宋徽宗宣和年間,東京汴梁城的虎翼營內住著一戶姓陳的人家,主母早逝,只有陳老爹帶著兩個兒子過活。
陳老爹年五十許,身子骨倒還硬朗,任殿前太尉之職。長子名字喚作陳行義,在禁軍中做個教頭。小兒子年方十九,名喚陳從善,一年前中了三甲進士,御筆欽點到廣東,任的是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
且說這陳從善赴任一年以來,於公務上甚是謹慎幹練,很得上司南雄府尹張老爺的賞識。南雄府尹張老爺本是陳老爹的舊交,見陳從善生得俊美,年紀雖輕,但頗有才學,又為人正直,雖說性子稍嫌冷漠了些,但正因如此,反而顯出些...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伽藍雨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9-22 ISBN/ISSN:978986206518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90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