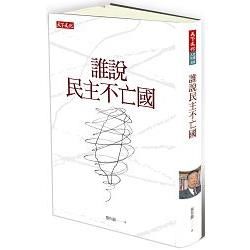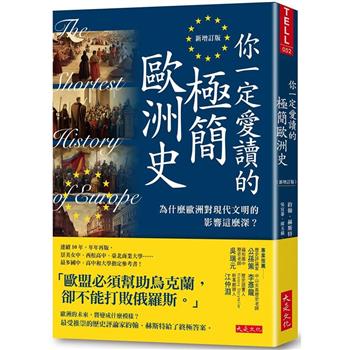自序
國家不幸記者幸?──略陳「感時篇」選集的出版經過
張作錦
寫了二十七年的《感時篇》,於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結束,我撰《「感時篇」的最後一篇:向讀者告別》,坦承耕耘小小一方土地的老農,「此刻放下鋤頭,走過田埂,然猶屢屢回頭張望也。」依依之情,不避人見之。
世事無常,人生有限。有些事是自己能力做不到的,或者做不完的,在適當的時候,都要放手。稍有留連或為人情之常,拖住不放則屬自戀過甚。
倒是讀者諸君子的反應,使我感動,也使我受寵若驚。他們或來信,或來電話,肯定我過去發言的誠懇,不欺世,也未流於放言高論。他們對我的擱筆感到遺憾,認為台灣前途未卜,少一個說實話的人,就是少一分促使國家社會進步的力量。
他們的鼓勵與督責,都使我點滴在心。事實上,我在「告別讀者」文中已先招認了:「台灣處境艱難,國人望治心切,而筆者力薄能鮮,專欄雖云『感時』,但文章未能『濟世』,辜負了讀者的期許。」若來日尚有機緣,自當努力回報。
「感時篇」連載一結束,「天下文化」負責人高希均教授和王力行小姐就告訴我,要我選出若干篇章來,由「天下文化」出版兩本選集。他們兩位的好意,曾使我略有躊躇,蓋時論散文的大敵,就是時過境遷的變化。二十七年多少事,這些小文還有否時效上的意義?
但是偏安一隅的台灣,這些年來,耽於內鬥,怯於開拓,有些內在外在的問題,竟然「歷久彌新」,「感時篇」所言所論,有些仍有「溫故知新」的作用。不敢說記錄時代,視之為前後參證可也。
清代詩人趙翼在《題元遺山集》中有句云:「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台灣的種種坎坷,使我輩記者能有機會「直攄血性為文章」,這樣的「幸」,何其「不幸」啊!
三年前筆者就有意停寫「感時篇」,但我的同事與好友聯合晚報發行人兼聯合報總主筆黃年先生,曉之以義,動之以理,使我又勉力續寫了好幾年。
自「感時篇」開篇以來,同事賀玉鳳小姐就和我一同照顧這個專欄,她出身中文系,替我整理文稿,改正疏漏,打字和存檔,二十多年同甘共苦,我感激不盡。
聯合報編輯部學養和文字都屬一流的沈珮君小姐,對這兩本選集,協助甄選文稿,組合排列,並在系統和邏輯上提供不少建議。
尤其要感謝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教授。對許院士,我一向以師視之,但他不以學問傲人,以朋友待我,平常就給我很多指導與鼓勵。「感時篇」結束,他寄「聯合副刊」一文《等待接力長跑的下一棒》,對台灣的現狀與未來的發展,有剴切的評論與殷勤的祝望。我請求把此文當作「選集」的序文,也蒙他見允,目的不僅在為本書增色,也希望國人有更多的機會讀到許院士的醒世箴言也。
「聯副」歷任主編瘂弦、陳義芝和鄭瑜雯諸朋友,以及「天下文化」負責規劃和編輯本書的吳佩穎和賴仕豪兩先生與吳毓珍小姐,都要在此感謝他們的辛勞。
另外,為了稍稍豐富選集的內容,有少數篇章並非出自「感時篇」,而是發表在《遠見》或《聯合報》其他版面上,也納入選集,謹此一併說明。
2015年3月于台北市
推薦序
「好人」有「好報」─張作錦對時局的五大觀察
高希均
(一)「好人有好報」新解
大多數人相信:好人有好報;如果「好報」尚未出現,那麼「時間還沒到」。
這篇評述張作錦先生兩本新著的標題:「好人有好報」另有新解:
(1)「好」的「人」才能辦出「好」的「報紙」。
(2)好人辦報會有「好報」:辦出好的「報紙」,也會得到好的「報應」。
(3)惡人辦報有「惡報」:辦出惡的「報紙」,也會得到惡的「報應」。
一九七○年代我常利用暑假回台參與李國鼎先生主持的經濟發展研究,偶有機會投稿《聯合報》,認識了當時的張總編輯,立刻變成了理念接近的朋友,展開了我們四十多年的莫逆之交。
作錦兄在一九六四年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即投身《聯合報》,從高雄特派記者起步,四十三歲即升為總編輯(一九七五~八一),然後赴美進修,並調任《世界日報》紐約總社總編輯(一九八一~九○),九○年再回到台北,先後擔任《聯合晚報》、《香港聯合報》、《聯合報》社長等職。在《聯合報》系全盛時期擁有五千多位同事,作錦兄是極少數能擔任這麼多重要職位的人。
創辦人王惕吾愛才惜才,作錦兄以全方位的聰敏才智,熱情奉獻。對一份報紙,最大的貢獻是要來自新聞內容及編採;這正是作錦兄的最大強項:找新聞、編報紙、寫評論以及發掘及培植優秀記者是一生最愛,也是他一生最大的貢獻。
不僅他有敏銳的新聞感,更有深厚的文史底蘊及廣闊世界觀。他日以繼夜的投入,參與打造了《聯合報》系輝煌的歷史,成為全球頂尖的華人報業。《聯合報》系是他一生唯一獻身的工作機構。
(二)提出五項大觀察
作錦兄在聯副「感時篇」專欄寫了二十七年(一九八七~二○一四),風靡海內外。他做為天下文化的創辦人之一,自然要由我們出版這兩本選集。一本為《誰說民主不亡國》(共九十六篇);另一本《江山勿留後人愁》(共一一○篇)。在過去二十多年,我們曾出版他九本著作,從一九八八年的《牛肉在哪裡》,到二○一二年的《誰與斯人慷慨同》。
這兩本新書所跨越的二十七年,正是兩岸經濟起飛與民主發展的關鍵歲月。台灣這邊,民主浪潮席捲一切,兩岸關係從李陳的「兩國論」到馬英九的「不統、不獨、不武」;大陸那邊,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推波助瀾之下,快速成長,已在全球經濟棋盤上舉足輕重;美國則在外交受挫內政受阻下陷入「相對衰退」(relative decline)。
兩本書中彙集的兩百篇文章,是以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歷史等主題為評論焦點;以兩岸關係,大陸崛起,美國政情等做為背景比較。現就第一本書稍做評述。它分成五部,每部所定的標題,正反映出作者思維的大脈絡,可稱之為「對兩岸時局的五項大觀察」:
第一項觀察:台灣,成於民主,敗於民主?
其中〈請外省政治人物全數退出政壇〉,〈請王金平離開立法院〉都是充滿道德勇氣,傳誦一時的評論。
第二項觀察:政客收買選票,百姓零售國家
評論指出:台灣應當要有「執不執政的黨,都必須是負責任的黨」,事實上看到的卻是「不管是什麼,我都反對到底」。因此「國家領導人困死於政治壓力」,「官民合力使台灣破產」。這就是明年一月總統大選前的淒慘實況。有人好奇地問:為什麼還會有人要去選總統?
第三項觀察:台灣只能是「短暫的富裕」?
剛去世的李光耀,在其去世前的著作中,眼下已無台灣。作者問:「台灣的大亂又要開始了?」我的看法:台灣長期經濟下滑,就像絕大多數歐美國家 (它們的經濟成長率大都在一~三%之間) ,從一九九○年李登輝推動民主化就開始。高度威權的中共可以維持較高的成長,低度威權的新加坡也可維持比其他三小龍較高的成長。民主的代價就是犧牲二至三個百分比的成長率。
第四項觀察:自由而無秩序,終將失去自由
環繞這項觀察,作者有二十七篇文章來反覆討論。流行的「媒體誤國」論誇大嗎?作者提出:〈新聞『製造工業』仍未夕陽〉,〈專業記者愈來愈難找了?〉;作者更問:〈什麼樣的『人』辦報才好〉,〈沒有人性才能做傳媒〉這兩篇與我這篇短文的標題正可相互呼應。
第五項觀察:獅,醒了;龍,怎樣了?
面對「統,不願;獨,不敢;維持現狀,不甘」,作者提出了「大陸現代化是統一條件」,「贊成以公投決定台灣統獨」。當前的狀況是:在世界舞台上,大陸已與美國分庭抗禮;台灣只能自求多福。如果還有一些人堅持仍要鎖國,不要與大陸多來往;那麼台灣真就會加速走上衰落之路。如果「兩岸一家親」,資源相互合作、整合,讓台灣跳在大陸的肩膀上,雙方互補互利,那麼台灣還有機會靠經濟實力,維持相當尊嚴。
三十年來睡獅醒了,也開始發威了;小龍在民主─民粹的困境與僵局中,已是欲振乏力了。
(三)才華折服,觀點傷感
在典範人物缺少的台灣社會,作錦兄是少數之一。
在政壇及新聞界,君子已是鳳毛麟角,作錦兄是少數之一。
當「星雲真善美傳播獎」於二○一○年第二屆選出他獲得「終身成就獎」時,大家都認為實至名歸。
在一九五○~六○台灣兩岸對峙動盪不安的年代;在六○~七○台灣經濟起飛意氣奮發的年代;在八○後台灣民主化夾雜民粹的「寧靜革命」中不寧靜的年代;在九○後大陸和平崛起,台灣內部分裂,兩岸關係不確定的年代;作錦兄或在現場報導,或在編輯台上取捨新聞,或埋首撰寫重要評論。
作錦n兄是台灣社會及新聞事件半世紀變化中,站在前線的見證人。他這些銳利生動的評論,使海內外讀者宛如身歷其境。沒有人不被他的才華折服,似乎又很難不引起迷惘。這就需要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台灣人、華人做深刻的反思。
(二○一五年四月於台北,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後記
「感時篇」的最後一篇:告別讀者
張作錦
苟有主張,悉出誠意;錯謬定多,欺罔幸免。──張季鸞
「感時篇」專欄結束,今天刊出最後一篇,敬向讀者告別。
這個專欄始於一九八七年。二十七年來,世界、台灣、兩岸,浪起波湧多少事,但躲在報紙一角小小的一片文字,誰知能否取一瓢飲?
一九八三年筆者被派到紐約《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工作,但身在域外,心懷故土,對台灣的風吹草動都很牽掛,忍不住寫些文章,提點意見,分刊於新聞版和副刊,後經當時聯副主編詩人瘂弦的安排,以「感時篇」之名統一於副刊版面。我一九九○年調回台灣後,繼續執筆。先是每週一篇,近幾年改為每兩週一篇。「感時」開篇時,聯副已另有兩專欄,彭歌的「三三草」和張繼高的「未名集」。兩位都是名家,崔顥題詩在上頭,真叫後來者忐忑難安。
台灣雖曾連年有兩位數的經濟成長,躋身「亞洲四小龍」,民主化進展快迅,但還是沒走出偏安王朝的歷史舊路──強敵壓境,而內鬥不歇。
清朝末季,外患此去彼來,主持「洋務運動」的李鴻章,提出他的救國方針:外需和戎,內需變法。和戎,與外國和平相處;變法,要努力革新自強。今天台灣的局面不也是這樣嗎?我們要和大陸和平交流,打仗就是玉石俱焚;我們自身則要戮力建設,以實力爭取國家的未來。這些年我的專欄小文,大致不離這兩條主線。
台灣實行政黨政治,但弊病不少,我寫《「政黨」政治與「我黨」政治》,「政黨」尚或可能心存國家社會,「我黨」必然只是一黨之私。我又寫《政黨收買選票,百姓零售國家》,警告選民貪圖政黨放送「社會福利」和亂開空頭支票的危險。我體認到台灣社會對政黨輪流執政還不太適應,呼籲人民《要把政黨輪替養成習慣》。
台灣最引以為傲的是我們的自由開放,但自由顯然已被揮霍濫用。我認定《自由而無秩序,終將失去自由》,也指出《沒有道德的自由社會從來就沒有過》,希望國人警覺。
不錯,台灣是民主了,但民主的品質如何恐怕還要接受檢驗,我寫《有民主之人,才有民主之國》,大家要反躬自省自己的民主素養。而且,有民主若無建設,國家不會前進,所以我說《民主並不能保障國家不走向衰亡》。我祝望《台灣不能是「短暫的富裕」》。
民主的精神面貌,國家的實體進步,都靠法律維護和推動,而法律出自立法院。我們立法院之醜陋不堪,以及對國家發展的阻礙與戕害,國人盡知。我問《怎樣搶救立法院?》答案有,但誰能做到呢?
兩岸關係複雜,端賴時間解決,有些專事挑撥、想火中取栗者的態度,叫人憂心。二○○三年十一月三日國防部副部長陳肇敏在立法院說,「台灣獨立,中共一定動武」。若開戰,「國防部戰耗動員為十二萬八千人」。所謂「戰耗動員」,就是我軍第一波傷亡人數。當時陳水扁總統正規劃二○○六年制定新憲,二○○八年建立新國家。那麼○六到○八年之間要不要打仗?我在專欄裡問:《誰家的孩子列在攻台第一波十二萬傷亡名單上?》這篇文字有不少讀者反應,足證很多人不願兩岸以戰爭解決問題。一位讀者更把文章自費影印一千份,分送各方,希望為阻止殺戮盡一點力。
台灣近年流行檢驗別人是否「愛台灣」,且常以出生地為判斷依據。自明朝以降,西方傳教士來華,有些人力行「華化」,忠貞不二的替中國人服務,我舉了些例子,問道《誰說人只愛自己出生的地方?》我並引申以談《愛國與憂國》,我的結論是:心中若無國家,憂國是妄言,愛國是謊言。
我是職業新聞記者,自然會談本行本業的事。我寫過《新聞「製造工業」仍未夕陽》,也寫過《媒體應擺脫政治附庸地位》。於役新聞界數十年,內心的無奈與倉皇,盡在這兩題中。
提起新聞界,像其他行業一樣,自亦有典範人物,譬如當年大公報的張季鸞。他為大公報所訂「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是報界永遠的碑石。他曾在文章中強調,他個人及同僚「雖技能有限,幸品行無虧」。又說,「苟有主張,悉出誠意;錯謬定多,欺罔幸免。」張氏的文采與事功,令人高山仰止,但他著文「悉出誠意」和「欺罔幸免」的篤實與嚴謹,後人還是可以學習與追求的。
寫這個專欄,結識很多讀者朋友,他們給我的指正,我敬謹接受;他們給我的鼓勵,我永銘在心。台灣處境艱難,國人望治心切,而筆者力薄能鮮,專欄雖云「感時」,但文章未能「濟世」,辜負了讀者的期許。
長亭外,古道邊。耕耘小小一方土地二十七年的老農,此刻放下鋤頭,走過田梗,然猶屢屢回頭張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