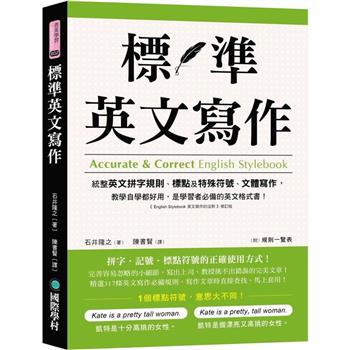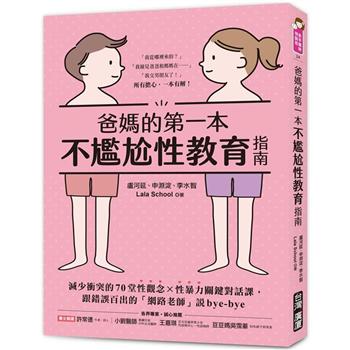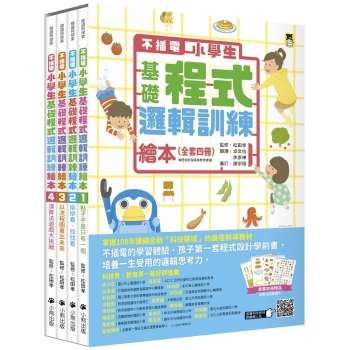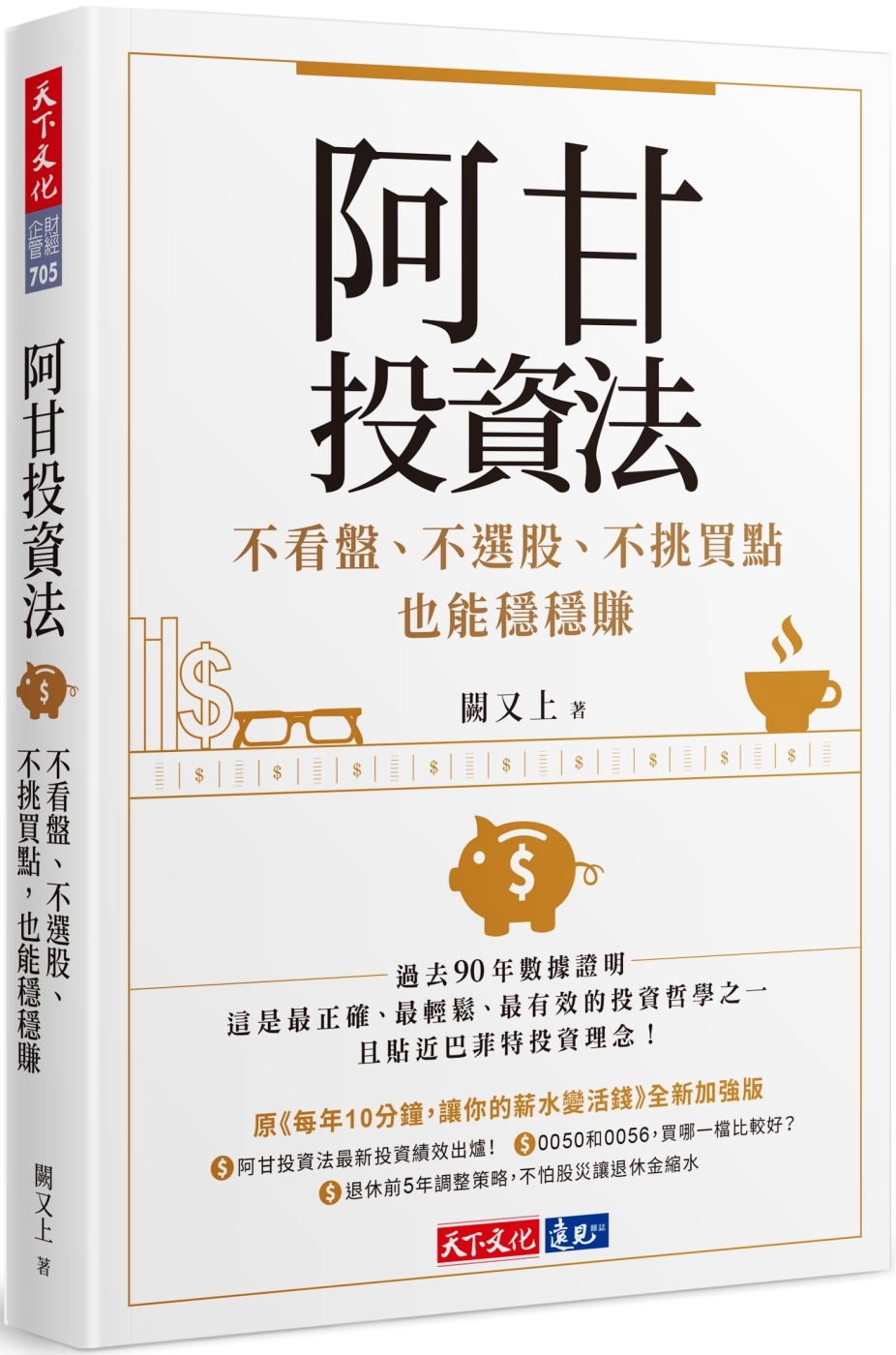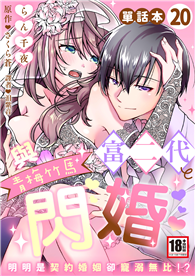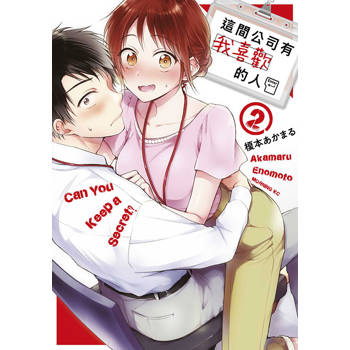自序—穿越時空的相學
世人對於相學,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相學是無稽之說,睇相先生只不過是見人見得多,用心留意不同人物的相貌特徵,把他們的性格、職業、六親緣分、人生際遇、健康狀況等等一一記下來,得了一個大概,再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把一切說得頭頭是道,就可以打正旗號做大師,為客人「指點迷津」。但說到底,這只是他們的經驗之談罷了。
亦有人甚至覺得,相學毫無科學根據,根本只是一套用作欺騙婦孺、愚弄客人、鼓吹迷信的說辭而已。例如,肥胖被說成是有福氣,是發達之相;瘦削被說成是辛苦命,難得富貴。可是,君不見不少容光煥發的瘦富人、精神萎靡的胖窮漢?
又有一些擁有很高的學歷的人,他們並不一定因遇煩惱而求相,而是純粹出於好奇,覺得好玩而已;又或者他們的確有疑難,不介意花些金錢去聽取一個有學問、有閱歷且有專業知識的第三者意見。這類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張,並不會全盤接受相學家之言,而是抱着姑且聽之的心態,作為解決問題的參考。
另一方面,有人將相學作為致富工具,一些自稱國師、居士的術士,利用學員五官和面部形態掌握對方心理,抬高自己身價,從而獲利;他們更會開辦學生會,讓學生參加義工活動,為組織添加慈悲為懷的色彩。甚至有人未足四十歲已自稱擁有三十多年玄學經驗,他們認為,只要令人相信自己具有高人一等的相學「大師」身份,一切都可以隨心所欲。
以上大概代表了大部分人對相學的看法:有人絕不認同,有人半信半疑,有人信到十足。由此可知,相學仍然是一門被不少人誤解及用作騙財的學問。
然而,真正的智慧可以穿越時空,這是不容置疑。事實上,識人術從古至今歷久不衰,可見它是真實存在,並擁有崇高價值。
相學智慧亙古不滅
歷史上有不少傳頌千古的識人術故事。李悝是戰國時期的政治家。《史記.魏世家》中記載了一段故事:魏文侯想從魏成子和翟璜中選出一人為相,但因二人才幹相若,不知應該如何取捨,便詢問重臣李悝的意見。李悝向魏文侯提出了「識人五法」:「一曰,居視其所親;二曰,富視其所與;三曰,達視其所舉;四曰,窘視其所不為;五曰,貧視其所不取。」魏文侯根據李悝提供的標準,最後錄用魏成子為相。李悝將「識人五法」運用於處理政事中,廣攬天下人才,為魏國主持變法,實行盡地力、平糴法,大大地促進了魏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使魏國因此而富強。司馬遷說:「魏用李克(悝)盡地力,為強君。」班固稱許李悝「富國強兵」。
三國時期的風雲人物諸葛亮選擇效力劉備而非劉表,乃因他觀察出劉表好謀少決、優柔寡斷、空有聲名而不會用人,為人重私情而捨大義,終不能守住荊州;至於當時依附在荊州、駐防新野的落魄皇叔劉備,年近半百,為人自謙,事業無成卻是聞名天下的英雄。諸葛亮認為劉備能以德足服人,才能足以擔當大任,故答允輔佐對方成就大業。諸葛孔明以神機妙算聞名於世,擅長運籌帷幄,無論是在尋找主公、行軍打仗,還是處理國事時,都能起用大量人才,全因他擁有一套識人術。他在《知人性》一文中提到「觀人七法」:「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曾國藩是晚清四大重臣之一,他興辦洋務運動,組建湘軍,幕僚裏人才濟濟,獨撐晚清危局。傳說曾國藩能廣結各路豪傑,成就一代偉業,全因他具有高明的識人術。關於他精於相人的故事甚多,俞樾在《春在堂筆記》評論曾國藩:「湘鄉出入將相,手定東南,勳勞之盛,一時無兩,而尤善相士,其所識拔者,名臣名將,指不勝屈。」曾國藩認為,辦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他與李鴻章有師徒關係,一次李率領三人求見曾聽候差遣,曾在庭外散步時瞥見三人後向李表示不用傳見,李問原因,曾答:「一人俯首不敢仰視,此謹厚之人也,可任保管之責;一人值余面則正視不苟,背余面則左右探視,乃陽奉陰違之人,不可任事;另一怒目注視,始終挺立
不懈,此人功名事業,將來不在你我之下,可寄以重任。」後來三人果真如曾國藩所言,而可寄以重任者,便是淮軍第一名將劉銘傳。此事一出,海內之士,盡皆信服曾氏之善於觀人。後世評價曾國藩之所以能成功,大部分原因就是因為他擅長觀察細節,尤其是在飯桌上觀察別人,因為往往最生活化的時刻,最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性。
縱觀歷史,善於識人者比比皆是,除以上幾位,還有周文王渭水河畔識得姜太公,呂叔平選得劉邦為婿等等。從各個歷史人物事跡,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相學是一門知人的學問,而且起源於實際用途。由於生活上、工作上有知人的需要,所以才產生了識人之術—相學。出生於二十世紀、已故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說過:「在我們身邊有很多的人,其中不乏好人、壞人、善人、惡人、君子、小人,可以說甚麼人都有。但是我們一時看不出哪一個人究竟是屬於哪一種人,必須要有一些因緣、境界,才能觀察得出其人的操守、精神、度量、心境。」
由此可見,兩千多年以來,相學都是從日常生活出發的,存在價值極高。已故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也曾高度評價相學:「不是生就的相貌,而是長期的心與行為的修煉在臉上的投影,這些相貌也在預示着其未來的命運。相術也就是一種經驗積累,相由心生,由臉觀心,由心知未來。」
外相與內相
然而,談到相學,大部分人尤其一些自稱國師、居士的玄學家,都只會聯想到五官面相,其實相學包括掌面相與體相,當中體相又包含了靜相和動相。掌紋、五官在外,體相在內,彼此相輔相成相配,才有完美的判斷。先賢寫下了傳頌千古的相人事跡,也歸納了多種識人之術。《呂氏春秋》中的「八觀」,就是依據人在不同環境的表現來識才:「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論語》中三句識人口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巧言令色,鮮矣仁。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莊子》也記載了「八驗」的觀人方法:「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以觀其敬,煩使之以觀其能,猝問之以觀其智,急與期以觀其信,醉以酒以觀其性,雜以處以觀其色,示以利以觀其廉。」司馬光《資治通鑑》:「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
不論是李悝的「識人五法」、諸葛亮的「觀人七法」、曾國藩的識人之術、「八觀」、孔子相人訣、「八驗」,都跳出了五官面相的框框,而是從行為舉止以論人善惡智愚,在這之前則要辯人之身體形態,如肩腰背胸臍腹臀四肢等等,這就是古人的智慧。可惜,現今術家論相,只注重五官表現,鮮少提到內相的重要,辜負了前人遺留下來的寶庫。筆者行走術數江湖四十多年,年事漸高,本想在往後歲月專心授學,但有鑑於習相者日眾,希望他們能學得完整而正確的相法,便決定執筆編寫一系列「相學識人術」,將半生相法心得傳承後世,一方面填補相學領域缺少的關鍵板塊——內相,另一方面向先賢致敬。
相學的真義
相由心生,「形神不相離,未有有諸內而不形諸外者」,心有善惡,亦有厚薄,面相、體相的吉凶好壞與此息息相關,如影隨形。相學就是相心。
相的義理,在理而不在術。相學從來都不是單純預測禍福吉凶或教人如何致富,也不是生財工具,更不是單方面論說人生既定歷程的術數,而是一門生命教育,不僅教育相學知識,更重要的是教育如何為人,上下求索生活上所遇問題的根源。「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行者心之表,觀行而禍福可知。」一個人的性格乃由心出發,一個人的行為反映命運順逆;性格或行為偏歪或有缺失者若能夠遇上人生導師,接受導師教育為人之道,必能轉凶為吉,為自己重寫命運。
有別於一般著書者,將古籍胡亂編輯分拆成書,然後自許為國師、居士,自抬身價,混騙謀生,愚弄世人,實非真聖;筆者半生從事生命教育,不管是為客人論相、課堂上授學或著書傳世,目的都是希望客人、學生和讀者能知人惜命,啟迪智慧、認識生命、了解自我、捨惡揚善,從而為自己作出最佳選擇,規劃美好的人生,實踐終極的趨吉避凶。
若本書能為後學者提供管道吸取精華,福澤後世,余願足矣!
| FindBook |
|
有 56406 項符合
《人的圖書,這是第 26 頁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肩腰背胸識人術
相學博大精深,附五官面相外,更有身相,兩者相輔相成相配,相法才有完美的判斷。
《西嶽先生相法》:「好頭不如好面,好面不如好身」。在相學歷史長河中流傳的多種識人之術如戰國李悝的「識人五法」、蜀漢諸葛亮的「觀人七法」及晚清曾國藩的「八觀」,也都跳出了五官面相的框框。由此可見,身相比面相更為重要。
身相包含肩、腰、背、胸、臍、腹、臀、四肢、肌肉、皮膚、毛髮等,不同部位形態各有指示,論善惡智愚,斷命運吉凶,嘆為觀止。李英才師傅縱橫相學界四十年有餘,耗數年心血編寫成《肩腰背胸識人術》,作為身相系列首部曲,為習相者提供完整而正確的身相知識,以期向先賢致敬,並能福澤後學。
作者簡介:
李英才,廣東電白縣人,沉醉術數,雅好琴箏,自稱「相琴兩癡」。一九八四年開始在社區設班公開教授掌相學及風水學,學生人數為全港之冠。所辦課程,相理、心理、哲理、情理共冶一爐,課堂上生動活潑,為全港唯一一位最專業而細緻、實例最多的術數老師,並為傳媒爭相報道。
作者序
自序—穿越時空的相學
世人對於相學,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相學是無稽之說,睇相先生只不過是見人見得多,用心留意不同人物的相貌特徵,把他們的性格、職業、六親緣分、人生際遇、健康狀況等等一一記下來,得了一個大概,再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把一切說得頭頭是道,就可以打正旗號做大師,為客人「指點迷津」。但說到底,這只是他們的經驗之談罷了。
亦有人甚至覺得,相學毫無科學根據,根本只是一套用作欺騙婦孺、愚弄客人、鼓吹迷信的說辭而已。例如,肥胖被說成是有福氣,是發達之相;瘦削被說成是辛苦命,難得富貴。可是,君不見...
世人對於相學,不同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相學是無稽之說,睇相先生只不過是見人見得多,用心留意不同人物的相貌特徵,把他們的性格、職業、六親緣分、人生際遇、健康狀況等等一一記下來,得了一個大概,再憑着三寸不爛之舌,把一切說得頭頭是道,就可以打正旗號做大師,為客人「指點迷津」。但說到底,這只是他們的經驗之談罷了。
亦有人甚至覺得,相學毫無科學根據,根本只是一套用作欺騙婦孺、愚弄客人、鼓吹迷信的說辭而已。例如,肥胖被說成是有福氣,是發達之相;瘦削被說成是辛苦命,難得富貴。可是,君不見...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一—當夢想照進現實9
序二—當內相遇上心理學12
序三—學相就是學做人15
序四—以相入心,以心輔相18
自序—穿越時空的相學21
身相三停圖30
第一章 肩相看命運
內相故事一—知福惜福造福32
肩譜
(1)平肩40
(2)瀉肩44
(3)聳肩47
(4)左肩高右肩低51
(5)右肩高左肩低55
(6)鳶肩59
(7)犀肩63
(8)寬肩66
(9)窄肩69
(10)薄肩73
(11)寒肩76
肩相詳解
肩之基本意義81
肩在相學上的定義84
肩之外觀相理89
肩膀相理總論99
女性肩相命理專論107
第二章 腰相看命運
內相故事二—往事只能回憶112
腰譜
(1)腰正而直122
(2)腰圓而厚126
(3)腰圓而細129...
序二—當內相遇上心理學12
序三—學相就是學做人15
序四—以相入心,以心輔相18
自序—穿越時空的相學21
身相三停圖30
第一章 肩相看命運
內相故事一—知福惜福造福32
肩譜
(1)平肩40
(2)瀉肩44
(3)聳肩47
(4)左肩高右肩低51
(5)右肩高左肩低55
(6)鳶肩59
(7)犀肩63
(8)寬肩66
(9)窄肩69
(10)薄肩73
(11)寒肩76
肩相詳解
肩之基本意義81
肩在相學上的定義84
肩之外觀相理89
肩膀相理總論99
女性肩相命理專論107
第二章 腰相看命運
內相故事二—往事只能回憶112
腰譜
(1)腰正而直122
(2)腰圓而厚126
(3)腰圓而細129...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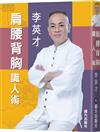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