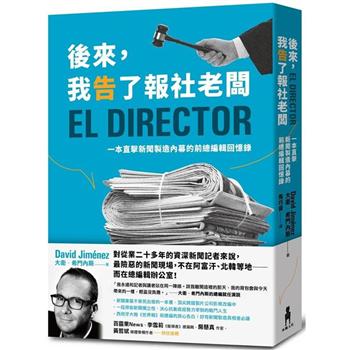推薦序
一部偉大的書可以怎樣讀
一
人生如寄,來去匆匆。這世界上,有些書可以走馬觀花,一掠而過,有些書則需要、也值得投注生命、情感和智慧,浸淫涵泳,反復研讀。毫無疑問,成書於西元五世紀的六朝志人小說名著《世說新語》,就應當屬於後者。
《世說新語》,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四○三—四四四)撰,梁代史學家劉孝標(四六三—五二二)注,是中華文化史上一部極重要的經典。自其成書以來,一直受到歷代文人士大夫的喜愛,它所傳遞的那種特立獨行的「魏晉風度」有如光風霽月,彪炳千古,令無數讀書人心向神往,諷詠步武,歷一千五百餘年而未曾稍歇。
大凡好書,往往見仁見智,從不同角度看《世說新語》,觀感常常迥異,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從文化思潮立論者,說它是一部「清談之書」;從名士風流著眼者,說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書」;自其大者而觀之,即便稱之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亦不為過;自其小者而觀之,覺得它不過就是一部瑣碎餖飣、以資談助的「叢殘小語」、「尺寸短書」。蔡元培先生所謂「多歧為貴,不取苟同」,正此意也。
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把《世說新語》稱作一部中國人的「智慧之書、性情之書、趣味之書」,以為生為中國人而不讀此書,殊為憾事!這部傳世經典我讀了十餘年,周而復始,欲罷不能。無形之中,《世說新語》成了我精神生活中一個「不可須臾離也」的大自在,大迷題,無從回避,也不願回避。不僅不回避,而且樂此不疲——樂讀、樂說、樂思、亦樂解。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就此而言,《世說新語》又是我精神生活中的大美味,大享受!我甚至覺得,我所讀過的所有書(那當然是極其有限的),都是為讀懂《世說新語》所做的準備!讀的遍數越多,想的越深入,我便越覺得這部書堪稱漢語言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經典,其主要編撰者劉義慶亦堪稱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兩者偉大的程度實不亞於我國古典小說的不朽名著《紅樓夢》和它的作者曹雪芹!
《中庸》有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人大多讀書,能讀出書中三昧的又有幾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人一生真能讀懂一本書,足矣!東晉「風流宰相」謝安年少時,曾請名士阮裕講解戰國公孫龍子的《白馬論》,阮裕遂寫了一篇論文以示謝安。謝安對文中要旨並不能馬上理解,於是多次諮詢請教,直到明白為止。阮裕不禁感嘆道:「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世說新語.文學》二四,下引不再注書名,僅注篇目及序號)這裡的「能言人」亦可謂「解人」,蓋指阮裕自己,而「索解人」——尋求解答的人——則指謝安。阮裕是說:不僅對此一問題能夠融會貫通的「解人」很難得,現在就連謝安你這樣孜孜不倦的求解之人也找不到了!
我於《世說新語》,當然不敢妄稱「解人」,但自信還算是個勉力而為的「索解人」。我「索解」的結果,就是發現《世說新語》和《紅樓夢》一樣,都是我們民族文化遺產中的「偉大之書」,它們的作者,也都是我們民族傑出人物中的「偉大之人」,他們的心靈,更是一顆放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多乎哉?不多也」的「美麗心靈」!
法國大雕塑家羅丹說:「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我要說,任何一雙發現美的眼睛,必然來自一顆大慈悲、大關愛、大寬容的「美麗心靈」!沒有一顆這樣的「美麗心靈」,你就是獲得再多獎項,賺取再多銀子,贏得再多粉絲,甚至被專家學者寫進了「文學史」,又能怎樣?孫悟空剛當上弼馬溫的時候,何等志得意滿,等他知道真相,便轉而埋怨玉帝老兒不僅「不會用人」,而且嚴重地「以貌取人」:「他見老孫這般模樣,封我做個什麼弼馬溫,原來是與
他養馬,未入流品之類」(《西遊記》第四回)。——這世界上,有多少文學上的「弼馬溫」終生不曾獲得孫悟空的「自知之明」,不知道紅得發紫的自己,事實上「未達一間」、「未入流品」呢?
二
歷史已經證明,未來也將繼續證明:在中華文明史上,《世說新語》足可躋身「偉大之書」而無愧!說它偉大,主要還不是從文化、文學或文獻價值上著眼,而是從民族的審美經驗史、心靈體驗史和人類的精神超越史角度立論而得出的印象。從這一角度出發,如果說曹雪芹的《紅樓夢》堪稱一部偉大的靈性之書、人性之書、詩性之書的話,那麼,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亦然。某雖不才,請試稍作解說,以就教於讀者諸君。
(一)說《世說新語》是一部「靈性之書」,理由至少有二:
其一,書名是靈性的。我曾在拙著《世說新語會評》(鳳凰出版社,二○○七年版)的〈自序〉中,指出《世說新語》有「五奇」,位列第一的就是「書名奇」。「世說新語」這書名,其實是對前代文化典籍繼承借鑒的產物:漢代學者劉向就有一部子書,題為《世說》;漢初的名臣陸賈也寫有一書,名為《新語》。儘管「世說新語」這個書名在宋以後才真正確定下來,此前它還有《世說》、《世說新書》等名目,但無論如何,「世說新語」這四個漢字,已經成為我們今天對這部書的唯一專用書名了。
這書名「奇」在哪裡?我以為首先在這個「世」字上。「世」字既可組成「世界」一詞,亦可組成「世代」一詞。「世界」是個空間概念,「世代」則是個時間概念,所謂「三十年為一世」。正是這個神奇的漢字,點明了這部書的「人間性」和「歷時性」。
再看「說」和「語」。這兩字其實指涉了這部書的文體性質,「說」和「語」都是與歷史有關、而帶有小說性質的文類概念,在經、史、子、集四部中應該放在「子部」,在「子部」中又應放在「小說家」這一類。有人把《世說新語》當作純粹的歷史記載,其實是不夠嚴謹的,因為歷史記載在於「求實」,而小說雜記則更多傾向於「好奇」;歷史著作重在宣示道德訓誡,所謂鑒往知來,而小說則常常逸出道德藩籬而直奔審美經驗,重在賞心悅目。所以,這一類著作可算是歷史的「邊角料」和「剩餘物」,大多由「好事者為之」,被稱為「史餘」之作,或曰「稗官野史」。在「九流十家」中,「小說家」的地位一向都是最低的,不像現在,「小說家」甚至可以成為大眾偶像。
再看「新」字。我以為這個「新」字最能標明整部書的精神氣質。「世說」如果可以理解為「關於這世界的某一時代的傳說」,那麼「新語」,則暗示了它與前代的傳說大不相同,它的記載,無不體現了這一時代特有的「新面貌」和「新價值」,以及「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唯其如此,《世說新語》這部書才能「歷久彌新」,長盛不衰。別的不說,這個書名到現在都很「時尚」,許多報刊媒體的專欄動輒以「世說新語」冠名,文人墨客寫篇小品雜文,也常以「新世說」標目,「一世之說」而成「百代新語」,說明「世說新語」這四個十分具有內在張力的漢字,本身即充滿了深廣的文化內涵和無窮韻味,且已滲入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成為「日日新,又日新」的文化遺產、人文符號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其二,形式是靈性的。這裡的所謂「形式」,也即「編撰體例」或「文體」之謂。眾所周知,《世說新語》是一部編撰之書,魯迅說它「纂輯舊文,非由自造」(《中國小說史略》),基本符合事實。但也要看到,《世說新語》的編者在編撰體例上的創造性貢獻,實不亞於任何一部「全由自造」的敘事文本,以至於最終形成了我國文言小說史上一種特殊的文體——「世說體」。大略而言,此書之體例約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分門別類,以類相從。《世說新語》根據不同的主題,分成三十六個門類,分別是:
上卷: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所謂「孔門四科」)
中卷:方正、雅量、識鑒、賞譽、品藻、規箴、捷悟、夙惠、豪爽
下卷:容止、自新、企羨、傷逝、棲逸、賢媛、術解、巧藝、寵禮、任誕、簡傲、排調、輕詆、假譎、黜免、儉嗇、汰侈、忿狷、讒險、尤悔、紕漏、惑溺、仇隙
和《論語》不同,《論語》的標題是後來所加,一般是該篇第一則的頭兩個字或三個字,而《世說新語》的門類標題則是對記述主題的概括,可以統攝全篇,不僅如此,各門標題還暗寓褒貶,自《德行》以至《仇隙》,越往後越貶,大致遵循一個「價值遞減」的原則。這是此書一目了然的一個形式特點。
二是敘事以人為本,所記俱為「人間言動」,所以魯迅稱之為「志人小說」。而言、行之間,又重在記言。
三是形制上多為叢殘小語,篇幅短小。長則一、二百字,短則數十字,甚至一句話。
四是各門條目的編排,大體以人物所處時代為序。往往先兩漢,次三國,再次西晉,複次東晉,秦末和劉宋時也有零星記載,但不在主流。每門內容,有一種潛在的「編年」意味。但同寫一個人物,相連的幾個條目,未必一定有事實上的先後關係。從整體上看,《世說新語》的結構正是一種既以時序為經、人物為緯,又以三十六門敘事單元為綱、具體事件(人物言行)為目的雙重的「網狀結構」,從而使文本形成了一個無論是在歷史維度還是在文學(文本)維度都遙相呼應、氣脈貫通的「張力場」。
五是每則所記,一般有一中心人物,此人處於主位,其他人物則處於賓位。作者的意圖,大概是想以一個具體人物為中心,組成一條相對獨立的「故事鏈」。條目與條目之間,藕斷絲連,既留下了大量「空白」,又可獨立欣賞,後來的小說如《水滸傳》、《儒林外史》「雖云長篇,頗同短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佈局結構,未嘗沒有受到《世說新語》的影響。
可以說,《世說新語》的這種體例,上承《論語》、《孟子》等文化經典的記言傳統,下開後世文言筆記小說之先河,在美學上最具「民族特色」,堪稱一種英國文論家克萊夫.貝爾(一八八一—一九六六)所謂的「有意味的形式」。因為它的體例具有某種「程式化」特徵,便於模仿,所以,後世續書和仿作層出不窮,這一系列的文言筆記小說體例,被稱為「世說體」。這一文體的閱讀效果極具形式美學和接受美學的闡釋價值。我曾借用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博爾赫斯(一八九九—一九八六)的小說題目,把《世說新語》稱作我的「沙之書」,因為它的確是一部「循環往復,無始無終」的「活頁式」文本,無論你何時打開它,都恍如走進一座「小徑分岔」的文字迷宮、故事迷宮和人物迷宮,留連忘返,不知所之。這樣一種文體形式,看似簡單便宜,其實非有大才華與大手筆者莫能辦,所以我說劉義慶是個偉大的藝術家。
上述兩點,早已逸出文本之外,甚至逸出時間之外,這是《世說新語》歷久彌新的文化密碼,也是其作為「靈性之書」的最佳證明。
(二)說《世說新語》是一部「人性之書」,理由至少有三:
其一,它的分類是高度人性的。《世說新語》的三十六門分類,不僅具有「分類學」的價值,以至於成為後世類書仿效的典範,而且還具有「人才學」甚至「人類學」的價值,它體現了魏晉時序期人物美學的新成果和新發現,也濃縮了那個時代對於「人」的全新的審美認知和價值判斷。我們知道,孔子論人,承認智力(或根性)上存在差異,曾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還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這裡的「學而知之」和「困而學之」者,所指其實就是「中人」。可見孔子是以「中人」為分水嶺,把「人」分成了三類。這也就是所謂的「三品論人」模式。
降及東漢,班固撰寫《漢書》,特別開列了一張〈古今人表〉,對孔子的「三品論人」進一步細化,將古今人物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個品級,開啟了「九品論人」的新模式,並直接催生了曹丕時代的「九品中正制」。三國時的思想家劉邵,又寫成《人物志》一書,對人的內在才性進行細緻入微的學理分析,成為中國古代人才學理論的扛鼎之作。
成書於劉宋初年的《世說新語》,正是受到漢末以來人物品藻和玄學清談風氣影響的產物,它不僅記載了眾多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同時也展現了那一時代對「人」的全新觀照和理解方式。班固的「九品論人」模式,還只是訴諸倫理道德的功利判斷,標準是單一的,眼光是靜止的,結果是固定的,所謂「蓋棺論定」,不可更改。而《世說新語》則「發明」了一種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的對「人」的認知評價模式,將「人之為人」的眾多品性分成自「德行」至「仇隙」的三十六門,加以全景式的、客觀的展現,和相容式的、動態的欣賞。這三十六個門類的標題,都是當時與人物評價和審美有關的文化關鍵字,分散來看,各有各的特色,合起來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個體的「人」的眾多品性及側面。從這個角度上說,《世說新語》既是一部展現眾多人物言行軼事的「品人」之書,也是一部把「人」所可能具有的眾多品性進行全面解析的「人品」之書——毋寧說,它是用一千一百三十條小故事塑造了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大寫的「人」!《世說新語》的這一體例創變,在我國人物美學發展史上的貢獻可說是「劃時代」的,充分體現了對人性理解的寬泛和深入。
其二,作者的視角是客觀的、多元的、寬容的,因而也是人性化的。儘管很多學者以為《世說新語》乃「成於眾手」,劉義慶只是掛名主編,但結合劉義慶的出身、履歷、性格及生平思想,我以為,「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詞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宋書.劉義慶傳》),且與名士、文人、僧侶多有交遊的劉義慶,在《世說新語》的編撰過程中,其作用是決定性的,主編身份實在不足以概括其貢獻,至少也應該是「第一作者」。我們雖然不能說劉義慶就是一個玄學家,但作為一個由晉入宋的文人政治家,無論在政治觀念、文化趣味、哲學思想等方面,他都表現出鮮明的玄學氣質,則是不爭的事實。所謂玄學氣質,毋寧說是一種追求精神超越、生命自由的氣質,所以在《世說新語》中,我們看到了儒、釋、道、玄等諸多思想的交匯、碰撞、合流。順便說一句,有玄學精神的人可能未必是安邦定國的棟梁之材,但一般也絕不是冷血嗜殺的殘忍之輩。只要看看《政事》門的數十條故事,便可明瞭劉義慶認可的乃是寬厚仁慈的無為之治,而非嚴刑峻法的苛酷之政。
唯其如此,劉義慶才能用超越自我和時代局限的「第三隻眼」來看待世界、歷史和芸芸眾生。這隻眼睛幾乎可以等同於所謂「上帝之眼」,它明亮在歷史之前,也照燭在歷史之後,由於它有著某種常人稀缺的「神性」,因而才更接近於「人性」的本真。儘管三十六門分類暗寓褒貶,但作者的立場卻是客觀的、多元的、寬容的,是淡化道德判斷而深化審美判斷的。你甚至可以說,作者是無立場、無是非的,只要是人的品性和特點,優劣、雅俗、美醜、善惡等,作者一律「等距離」地展示在讀者面前,不加主觀評判,而相信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關鍵是——作者相信讀者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第一章》)早已揭櫫語言作為「言道」「達意」工具的有限性。孔子也說:「予欲無言。」又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所以「信而好古」的他選擇了「述而不作」(《論語.述而》)。順此思路,莊子也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這樣一種純客觀的「不言」、「不議」、「不說」的立場和視角,其實更接近於我們通常所謂的「道」。而這個「道」,又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這也就是所謂「言不盡意」。所以莊子又說:「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外物》)在《世說新語》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來證明,劉義慶是個看重「不言之教」的藝術家:
謝太傅(謝安)絕重褚公(褚裒,字季野),常稱:「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德行》三十四)
王中郎(王坦之)令伏玄度(伏滔)、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言語》七十二)
桓茂倫(桓彝)云:「褚季野皮裡陽秋。」謂其裁中也。(《賞譽》六十六)
劉尹(劉惔)道江道群(江灌):「不能言而能不言。」(《賞譽》一三五)……
劉義慶大概深知「言不盡意」之道,或者,他自知是個「不能言」的人,所以才選擇了「皮裡陽秋」式的「能不言」。這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價值中立」視角,毋寧說是一種「大觀」視角。作者對他筆下的人物似乎不負任何道義的責任,喜怒哀樂、妍蚩美醜,全交給他們去「扮演」,自己則抱持「無可無不可」的心態,純作「壁上之觀」。古語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果說作者主觀之「言」就是「形下之器」,那麼,將這種「形下之器」降低到最小值甚至徹底「刪除」,無疑是明智之舉,因為只有這樣,一部充滿「人與事」的書,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性與天道」。所以,我們看到,對待一個人格上有嚴重污點的人,只要他在某一特定瞬間的言行,發出了人性的光芒,作者總能夠報以同情的甚至是欣賞的目光。
劉義慶似乎要告訴我們:人是有缺陷的,人性是複雜的,但人又是可愛的,值得欣賞和同情的,人性的閃光之處是可以照亮現實世界的黑暗的。在看似不動聲色的敘述中,作者不僅給那些歷史人物撣去了時間的灰塵,也給道德減了壓,給人性鬆了綁,這是一種「偉大的寬容」,也是一種大境界和大智慧!
其三,對女性才智的欣賞和發現。孔子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歷來對聖人的這句話,文過飾非、曲意解說者多有,但大家都忘了,聖人
首先也是個「人」。我熱愛孔子,但我不能不說,他老人家對女性似乎缺乏一種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別的不說,在他創辦的史上最早的「私立大學」裡,我們就找不到一個「女生」!西漢學者劉向撰有《列女傳》,對歷代符合儒家道德的女性予以表彰,引起後世史家紛紛效仿,這固然可算是一個創舉,但以「三從四德」表彰女性,還不如直接表彰男性來得乾脆。《世說新語》正是在這一點上顯得不同流俗。《賢媛》一門看似推重女性之「賢德」,實際上是標舉女性之「才智」,三十二條故事個個精彩,可說是一篇縮微版的《女世說》,如此集中地讚美女性的才能智慧,意義真是非同小可。此外,像《言語》篇裡的「謝女詠絮」,《文學》篇中的「鄭玄婢引詩」、謝安稱讚「家嫂」,《任誕》篇中的「阮籍別嫂」、「阮咸追婢」,《惑溺》篇中的「荀奉倩與婦至篤」以及王戎妻「卿卿我我」等故事,無不表現出一種嶄新的、不是「俯視」而是「平視」的女性觀。這固然是魏晉之際女性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現,又何嘗不是劉義慶個人的女性觀的投影?而對女性的尊重和欣賞,正是《世說新語》作為一部「人性之書」的最有力的證明。
可惜的是,這種對女性才智的欣賞和發現,在後來的古典小說中被忽略甚至拋棄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中的女性依舊處於被貶斥、被醜化、被仇視、被清算的地位,直到古典小說的偉大名著《紅樓夢》橫空出世,舊道德中「男尊女卑」的觀念才遭遇到最有力的挑戰甚至徹底被顛覆,取而代之的是「女清男濁」,甚至是「女尊男卑」。君不見大觀園裡的那些美麗女子,無不多才多藝,敢愛敢恨,個個是男人世界中難得一見的「性情中人」!從這個意義上說,《紅樓夢》所塑造的性情女子恰與《世說新語》所發現的才智女性一脈相承,遙相呼應。那個對女性的美有著深刻體察和感悟的賈寶玉,其實繼承了熱愛女性到「情癡」境界的荀粲、阮籍等魏晉名士的「文化基因」。杜甫詩云:「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從這個意義上說,劉義慶和曹雪芹,豈不是一對心心相印的「隔代知音」?
(三)說《世說新語》是一部「詩性之書」,至少也有兩條理由:
其一,它的文字是詩性的。《世說新語》是中古語言文字的「活化石」,是許多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的「集散地」,凡讀過此書的人,無不被其「簡約玄淡,爾雅有韻」(袁褧語)的文字所傾倒,所折服。在後世文人的詩詞中,《世說新語》中的人、事、物、語,都有著驚人的「引用率」。那些美妙的文字,如王子猷的「何可一日無此君」,謝道蘊的「未若柳絮因風起」,司馬紹的「舉目見日,不見長安」,桓溫的「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言語》篇的「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賞譽》篇的「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等等,稍加改動便是絕妙好辭,它們不僅是詩歌的「素材」,它們本身就是詩!魯迅稱道《世說新語》的語言,說它「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正是把握住了這種在敘事文學中並不多見的詩性特質。難怪,每當人們發現一則文字雋永、意蘊豐厚的掌故妙語,總是會說——「可入《世說新語》」!
其二,它的總體審美趣味是詩性的,能夠喚起讀者超越性的生命體悟和形而上的哲學思考。中國古代的小說書,除了《紅樓夢》,很少有像《世說新語》這樣涉及到人的存在問題並做出超越性和詩性解答的。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猶如一個超凡脫俗的理想國,從園中人經常賦詩聯句,可以讓我們聯想到西哲「人,詩意地棲居」這個著名的命題,而《世說新語》中的《雅量》、《容止》、《任誕》、《巧藝》諸篇,實則早已點醒人的自我超越和詩意棲居問題。可以說,《世說新語》早於《紅樓夢》一千多年,率先在「說部」中尋求著「人」在這個世界上的精神出路和靈魂皈依。更有甚者,此書通篇體現了某種和諧與包容,有一種海納百川的大氣度,大風流,作者的目光是別有賞會的那種:儒與道,禮與玄,莊與諧,雅與俗,智與愚,狂與狷,一言一動,一顰一笑,一象一境,一丘一壑,但凡體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主體創造性以及自我超越性,作者無不報以「瞭解之同情」,予以真心的欣賞和傳神的描繪,這使得無論何時何地的讀者,只要開始閱讀這本書,總會產生一種「近在咫尺」的親切感,進而走進一幅波瀾壯闊的史詩性畫卷。那些特立獨行的人物、膾炙人口的故事、傳神寫照的描畫、活色生香的文字,正是附著在這樣一艘擺脫了空間和重量羈絆的時光之船上,才獲得了抵達現在和撞擊心靈的巨大能量和撩人魅力!王子猷「雪夜訪戴」的故事之所以迷人,正在於人的「沉重的肉身」在王子猷「造門不前而返」的那一刻,飛升到了一種自由澄明之境,難怪凌濛初評點說:「讀此飄飄欲飛!」
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詩而勝似詩,並非哲學而富含哲學氣質——這就是《世說新語》帶給人的充滿哲思和詩性的審美愉悅。它不斷地啟發我們思考:人究竟應該怎樣超越自我的局限和世俗的藩籬,雖不遺世而自高蹈,雖不?赫而自高貴,實現真正的「神超形越」?
有人把《世說新語》當作「史料」來看待,甚至用於階級分析的鬥爭哲學,這正如把《紅樓夢》當作階級鬥爭的活教材一樣,實在是「見木不見林」、棄其「神」而就其「形」的一孔之見。暴殄天物至此,煮鶴焚琴若斯,可發一嘆!
三
近讀劉再復先生的《紅樓夢悟》,發現他在闡釋《紅樓夢》時,也提到了《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不寫帝王功業,只寫日常生活,它記錄了許多遺聞趣事,呈現了許多人物的音容笑貌,從而奠定了中國小說的喜劇基石。《儒林外史》可以說是《世說新語》的伸延與擴大。中國小說有輕重之分,「重」的源於《史記》,「輕」的源於《世說新語》。《三國演義》、《水滸傳》都太「重」,學得走樣。《紅樓夢》則輕重並舉,而且舉重若輕,有思想又有天趣,極深刻的思想就在日常的談笑歌哭中。(《紅樓夢悟》,三聯出版社,二○○六年版,頁一○八。)
劉先生以「輕」「重」論文學,可謂別具隻眼。更為難得的是,他從小說史的角度出發,把《世說新語》稱作「中國小說的喜劇基石」,是古典小說中「輕」的一脈的源頭,真是言人未言,道人未道。事實上,《世說新語》從頭至尾都洋溢著這麼一種超越倫理道德、是非功過的「喜劇精神」,可以說,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幽默文學正是從《世說新語》開始的。諸如《言語》、《任誕》、《排調》、《輕詆》、《假譎》等門類充滿幽默感自不必說,就連《傷逝》、《忿狷》、《汰侈》、《儉嗇》、《惑溺》等門類,也隨處可見讓人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的開心故事。特別是它那短小、輕靈、雋永的形式特點,不是和我們今天喜聞樂見的「段子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嗎?《世說新語》不是沒有涉及歷史道義、國家興亡和個人悲劇,但它絕不在任何一個悲情對象身上做過多的盤桓和流連,作者不斷變換的視線和被剪裁成吉光片羽似的人、事、物、語,使人世間序原本沉重乏味的一切,變得短暫、輕快、生動、美麗!作者似乎在說:一切都將過去,肉體終會消滅,永恆的,不過就是那一瞬,一個不可愛的人也會因為那一瞬,變得嫵媚可喜!這,就是我們民族文化中土生土長的喜劇精神。生活再艱難,世道再黑暗,都無法阻擋我們飽經滄桑和憂患的臉上隨時綻放出如花笑顏!
宗白華先生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乍一看這段議論充滿矛盾和荒誕,但它所描述的又恰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裡的「藝術精神」表現在《世說新語》中,就是一種充滿靈性、人性和詩性的「喜劇精神」!而且,越是動盪不安、禮崩樂壞的亂世,越是盛產這種偉大的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因為所有虛偽的道德偶像、清規戒律和「絕對真理」都被顛覆了,打碎了,世界——人的世界和語言的世界顯示出了赤裸裸的荒謬和猙獰,這時候,唯一具有欣賞價值的只有「人與自然」而且是「自在」、而非「自為」意義上的「人與自然」!
所以,我們看到,在魏晉那樣一個亂世,「存在」的廢墟上竟開出嬌豔的生命之花來,對人生悲劇性和荒誕性的發現,使名士群體轉而去追求它的喜劇性和藝術性:藥與酒、嘯與歌、仕與隱、美貌與才情、山水與巧藝、愛情與死亡……無不顯示出可觀、可賞、可笑與可愛的一面來。學理一點說,正是漢代以來建構起來的儒家「認識論」體系的瓦解,才迫使人們轉而去擁抱老莊、去探求那「無中生有」的「本體論」,進而從「禮」走向了「玄」。當我們回眸一望的時候,發現他們的成績是偉大的,用宗白華先生的話說就是——「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的美),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如果沒有這種「超越一切而上」的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亂世人生該是多麼無聊和無趣!
《世說新語》肇始的這種「藝術精神」和「喜劇精神」,不僅於我們民族有價值,於東方文明有價值,甚至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每一個熱愛生命、自由和藝術的人,都會為之傾倒,為之唏噓,為之流連!日本人大沼枕山就曾寫過兩句漢詩:「一種風流吾最愛,六朝人物晚唐詩。」誠哉斯言也!
四
作為一個《世說》愛好者和研究者,我很早就有一個想法,就是用一種相對比較平易的形式,和適合一般讀者接受的方式,將《世說新語》與「魏晉風度」的方方面面,展現在讀者面前,讓更多的人能夠打開這部豐富多彩的奇書,看看一、兩千年前,生活在我們這個國度上的非常之人,以及他們的非常之語、非常之事。於是,就有了這本《世說新語今讀》。
本書共分三個部分,分別是:人物篇、典故篇和風俗篇;共三十二講。需要說明的是,無論典故還是風俗,我的立足點和著眼點仍舊是一個「人」字。當然,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