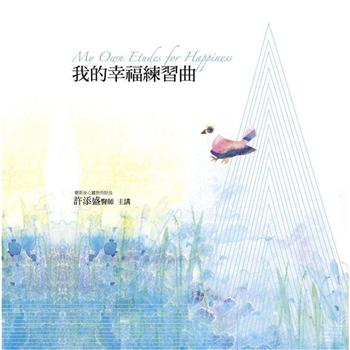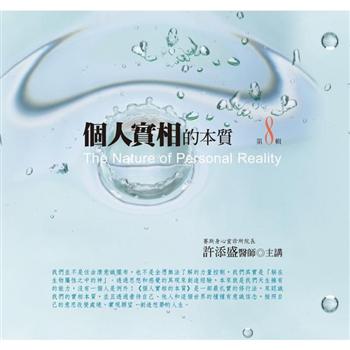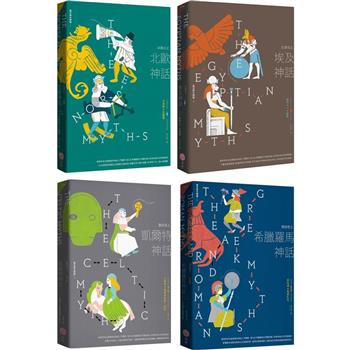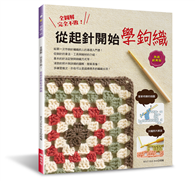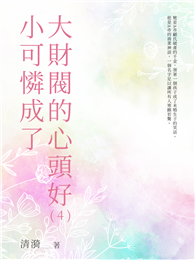周初的分陝而治,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東西分劃。山東山西(關東、關西)兩詞的出現是在戰國中期。西漢時期之山東山西,是全國的精華所在,前者是經濟、工商業、學術、文化的中心,後者是政治、軍事的中心。
長江中下游在東漢有快速的發展,主要是王莽末年因北方動亂,有大量的人民南移。三國時期,吳蜀互為犄角,結成與國抗魏,秦嶺、淮陽山脈、淮河成為南北之天然分界線,也成南北之政治界線。東漢末年「南」「北」的地域觀念開始出現,至此南北二個地域觀念遂取代了秦漢時代的山東、山西(關東、關西)。
因為南北二百七十多年長期的分裂與敵對,(311-589A.D.)於是南北的地域觀念日益強化。如北魏稱南人為「島夷」,宋人稱北魏為「索虜」,南北的經學、文學也互有不同,風俗的差異就更大了。
經濟重心的南移,使得政治重心的南移成為可能。漢魏是中國地域觀念轉變的時期,到三國時南北的地域觀念已取代從前的山東山西(或關東、關西)。宋時又一次的向南播遷,南方的經濟更繁榮。此後中國人南北的地域觀念就更強固了。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中國中古地域觀念之轉變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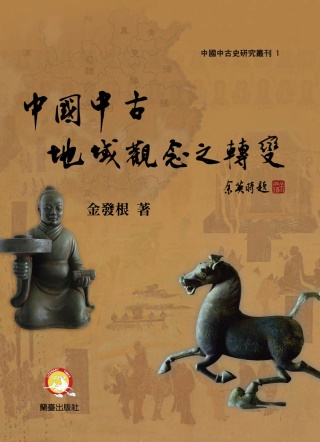 |
$ 720 | 中國中古地域觀念之轉變
作者:金發根 出版社:蘭臺網路 出版日期:2014-04-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16頁 / 19 x 2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中古地域觀念之轉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金發根教授
臺灣省立台北建國中學初中畢業(1950)、高中畢業(1953)、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文學士(1957)、歷史學硏究所文學碩士(1960)、香港大學歷史學系哲學博士(1988)、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1965--67)、英國劍橋大學Senior I.U.C. Fellow,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1979-1980)、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臨時助理硏究員(1961-62)、助理硏究員(1962-68)、副硏究員(1968-71)(1971-72留職留薪)(1972-74留職不留薪)、香港大學中文系歷史組講師(1971-95)、亞洲硏究中心硏究員(1981-95)、榮譽硏究員(1995)、香港新亞硏究所兼任教授(1994)
金發根教授
臺灣省立台北建國中學初中畢業(1950)、高中畢業(1953)、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文學士(1957)、歷史學硏究所文學碩士(1960)、香港大學歷史學系哲學博士(1988)、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1965--67)、英國劍橋大學Senior I.U.C. Fellow,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1979-1980)、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臨時助理硏究員(1961-62)、助理硏究員(1962-68)、副硏究員(1968-71)(1971-72留職留薪)(1972-74留職不留薪)、香港大學中文系歷史組講師(1971-95)、亞洲硏究中心硏究員(1981-95)、榮譽硏究員(1995)、香港新亞硏究所兼任教授(1994)
目錄
壹、前言 1
貳、緒論 4
一、中國東西地域觀念之由來 4
二、山東山西兩詞的產生與演進 11
(一)敘論 11
(二)各家山東山西說 13
(三)戰國中期後秦國國土的擴充 16
(四)函谷關的遷徙 24
(五)東漢定都洛陽、(末年)潼關之建置 28
(六)本書山東山西(關東、關西)之界說 31
三、中國古代北方與南方的交通 39
叄、西漢時期(206 B.C. ~ 8A.D.)之山東山西 45
一、兩區之發展及相關性之分析 45
(一)兩區農業、水利及工商業之發展 45
(二)山西對山東糧食之依賴、西漢對山東之倚重 56
(三)人口之分布 61
(四)政治、學術人才之分布 63
二、兩區對建都及邊疆政策之分歧─附論兩區人士在政治地位上之差別 65
(一)建都之論辯 66
(二)西漢初期功臣集團對政權之控制、官僚集團之崛起、山西人才之被抑制 68
(三)對邊疆政策之分歧 71
(四)西漢對山東山西之調和 84
肆、東漢時期(25A.D.-220A.D.)之山東山西 88
一、建都洛陽及其衍生之問題 88
二、山東大族對政權之控制 93
三、兩區農業、水利及工商業的發展 99
四、山東山西對西羌政策之分歧 109
五、東漢末年山東之戰爭、山東水利設施之破壞及其沒落 118
六、山西軍閥與東漢之亡 122
伍、兩漢時期(206B.C.-220A.D.)長江流域的發展 131
一、長江上游的發展 131
(一)敍論 131
(二)西漢時期之巴、蜀、漢中 138
(三)王莽末年及東漢時期 149
(四)兩漢時期本區人口及人才之遞增 153
二、長江中下游的發展 154
(一)敍論 154
(二)兩漢時期的發展 157
(三)兩漢時期本區政治、學術人才之遞增 167
陸、中國南北地域觀念之形成、強化及其取代東西 170
一、三國鼎立與南北觀念之取代東西 170
二、東晉的建國與南方地域觀念 176
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與南北地域觀念之強化 182
柒、結論 191
附錄 199
參考書目 294
圖表目錄
秦與列國盟會表 8
秦晉爭奪河西函殽表 21
西漢山東山西圖 37
先秦方言地理區圖 38
禹貢所載雍、冀、兗、青、徐、豫六州土壤、賦、田畝表 45
漢書地理志所載鐵官、銅官、金官分布表 52
漢書地理志所載鹽官分布表 53
漢書地理志所載工官、服官、木官分布表 55
史記漢書所載山東郡國災荒表 60
西漢山西人口分布表 61
西漢山東人口分布表 62
西漢丞相籍貫分布表 63
東漢雲臺功臣籍貫表 95
兩漢山東人口比較表 99
兩漢山西人口比較表 101
兩漢墾田畝數比較表 102
秦與巴蜀漢中交往史事表 134
兩漢巴蜀漢中人口分布表 153
兩漢荊揚人口分布表 165
西漢時期荊揚地區鹽、鐵、銅、金官分布表 166
兩漢交州人口分布表 169
三國時期南北圖 175
東漢九卿籍貫分布表 199
西漢山東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07
西漢山西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19
東漢山東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26
東漢山西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61
西漢巴蜀漢中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73
東漢巴蜀漢中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74
西漢荊揚二州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82
東漢荊揚二州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84
貳、緒論 4
一、中國東西地域觀念之由來 4
二、山東山西兩詞的產生與演進 11
(一)敘論 11
(二)各家山東山西說 13
(三)戰國中期後秦國國土的擴充 16
(四)函谷關的遷徙 24
(五)東漢定都洛陽、(末年)潼關之建置 28
(六)本書山東山西(關東、關西)之界說 31
三、中國古代北方與南方的交通 39
叄、西漢時期(206 B.C. ~ 8A.D.)之山東山西 45
一、兩區之發展及相關性之分析 45
(一)兩區農業、水利及工商業之發展 45
(二)山西對山東糧食之依賴、西漢對山東之倚重 56
(三)人口之分布 61
(四)政治、學術人才之分布 63
二、兩區對建都及邊疆政策之分歧─附論兩區人士在政治地位上之差別 65
(一)建都之論辯 66
(二)西漢初期功臣集團對政權之控制、官僚集團之崛起、山西人才之被抑制 68
(三)對邊疆政策之分歧 71
(四)西漢對山東山西之調和 84
肆、東漢時期(25A.D.-220A.D.)之山東山西 88
一、建都洛陽及其衍生之問題 88
二、山東大族對政權之控制 93
三、兩區農業、水利及工商業的發展 99
四、山東山西對西羌政策之分歧 109
五、東漢末年山東之戰爭、山東水利設施之破壞及其沒落 118
六、山西軍閥與東漢之亡 122
伍、兩漢時期(206B.C.-220A.D.)長江流域的發展 131
一、長江上游的發展 131
(一)敍論 131
(二)西漢時期之巴、蜀、漢中 138
(三)王莽末年及東漢時期 149
(四)兩漢時期本區人口及人才之遞增 153
二、長江中下游的發展 154
(一)敍論 154
(二)兩漢時期的發展 157
(三)兩漢時期本區政治、學術人才之遞增 167
陸、中國南北地域觀念之形成、強化及其取代東西 170
一、三國鼎立與南北觀念之取代東西 170
二、東晉的建國與南方地域觀念 176
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與南北地域觀念之強化 182
柒、結論 191
附錄 199
參考書目 294
圖表目錄
秦與列國盟會表 8
秦晉爭奪河西函殽表 21
西漢山東山西圖 37
先秦方言地理區圖 38
禹貢所載雍、冀、兗、青、徐、豫六州土壤、賦、田畝表 45
漢書地理志所載鐵官、銅官、金官分布表 52
漢書地理志所載鹽官分布表 53
漢書地理志所載工官、服官、木官分布表 55
史記漢書所載山東郡國災荒表 60
西漢山西人口分布表 61
西漢山東人口分布表 62
西漢丞相籍貫分布表 63
東漢雲臺功臣籍貫表 95
兩漢山東人口比較表 99
兩漢山西人口比較表 101
兩漢墾田畝數比較表 102
秦與巴蜀漢中交往史事表 134
兩漢巴蜀漢中人口分布表 153
兩漢荊揚人口分布表 165
西漢時期荊揚地區鹽、鐵、銅、金官分布表 166
兩漢交州人口分布表 169
三國時期南北圖 175
東漢九卿籍貫分布表 199
西漢山東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07
西漢山西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19
東漢山東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26
東漢山西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61
西漢巴蜀漢中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73
東漢巴蜀漢中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74
西漢荊揚二州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82
東漢荊揚二州人士任守相刺史表 284
序
壹、前言
拙著原名「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206B.C.─589A.D)中國地域觀念之轉變及其對政治之影響」,因其太長而改成今名,惟所論則完全不變。地域觀念之轉變對政治、社會、經濟之影響,尤為拙著措意所在。我作此研究完全是受傅斯年先生夷夏東西說一文的啟發。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治。
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纔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纔有獨立的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一大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
後來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讀書時,業師勞貞一先生為孫同勛、陳文石和我三人講授「漢魏六朝史研究」,論及「山東」、「山西」的問題,使我得到更多的啟迪。所以從1957年以來,不管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香港大學和劍橋大學做研究或教書時,我都一直留意這個問題。1973年夏天我在法國 巴黎第29屆國際東方學會議宣讀的論文,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一個小節。 1977年的秋天,我正式開始作此題的研究。
這真是一個非常深邃的題目,幾乎是可以終生事之的。而我對自已所懸的鵠的太高,要求太嚴,所以進度緩慢。又由於這三十多年來考古的發掘,諸如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西樵山文化、青蓮崗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金沙江遺址…一系列的發現,近年考古學界遂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不是僅僅發源於黃河流域一地,而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和遼河流域四區互相影響,互相融合、演進而成的。雖然這新穎的說法尚未得到中國歷史學界普遍的公認,但對我的研究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我開始作此研究時,是以傳統的說法,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作基礎的。所以這時期地域觀念的轉變,實質上是一個文化傳播的問題。 這使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非常躊躇。最後,我終於徹悟,不管長江、珠江、遼河三流域史前有多高的文化,但從中國進入信史時代,黃河流域的中原區域(河、濟、淮流域為中心)確實已演進為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並由此而向四周傳播。所以上述考古學界新穎的說法並不與我的假設衝突。
其次,自1971年我來香港大學後,始終以教學、指導和鼓勵學生讀書、研究為首要。所以雖然任課繁重,一度授課五門之多,我也甘之如飴。這自然影響到自己研究的進度。例如1986年我原擬利用港大休假回到中研院史語所做研究一年,以完成此書的撰述;然後再去哈佛短期研究。港大並已准許給我Study Leave一年和旅費的補助。後來卻因為有位同事為修橋鋪路,利用休假去台灣講學一年,他留下的一名M.Phil.學生,全系沒有一個同事願意接手指導她修改碩士論文──該文幾乎是要重新全部寫過的。
我犧牲自己的撰述計畫,用大量的時間來指導該生,最後她終於通過校內外碩士的論文審查和口試。另外,我在港大中文系中國歷史組任教期間所受種種不可思議的困擾,也無時不阻礙和中斷我研究的進程。
今天拙著終於能夠出版。我要衷心感謝Prof.L.K.Young不斷的鼓勵,勞貞一、王叔岷、和楊蓮生三位恩師對我的期許,不時的來信鼓勵和指導,全漢昇、嚴歸田兩教授的厚愛。許多摯友:孫同勛、謝文孫、王業鍵、陶晉生、張春樹、張存武、余英時、劉翠溶、周成竹、施敏、劉震慰、陳三井、P.D.Reynolds、M.G.Spooner、陳耀南、古紹璋、唐煥星、葉永恆……他們都鼓勵我、協助我,在我稍有鬆懈時,陳耀南教授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督責我。我謹在此向他們敬致衷心的謝忱。我更要特別感謝賢妻袁萬蒂女士節衣縮食克勤克儉,獨力挑起全部家務和撫育三個孩子的重任,(孩子們也個個努力,成器成材。),讓我可以全力講學和硏究,完成此書的撰述。感謝台北市蘭臺出版社盧瑞琴小姐慨允出版拙書;郭鎧銘先生、林育雯小姐辛勤的編排和校稿。感謝中學階段長期培植我的五叔金福民先生,感謝周紹德伯父母視我如親子女,對我一家的愛護和照顧幾乎無微不至。最後衷心感謝邢義田教授,得知拙書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網上可以找到時,立即全文下載閱讀,當印就初校稿後,又在百忙中惠允再次審閱,盛情永誌難忘。惟全書所有錯誤仍是筆者之責。敬祈海內外專家學者不吝指正,俾稍後修訂增益,冀對中國學術有些微的貢獻。
拙著原名「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206B.C.─589A.D)中國地域觀念之轉變及其對政治之影響」,因其太長而改成今名,惟所論則完全不變。地域觀念之轉變對政治、社會、經濟之影響,尤為拙著措意所在。我作此研究完全是受傅斯年先生夷夏東西說一文的啟發。傅先生說: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於北方為外族所統治。
但這個現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東漢,長江流域纔大發達,到孫吳時,長江流域纔有獨立的政治組織。在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一大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勢只有東西之分,並無南北之限。
後來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讀書時,業師勞貞一先生為孫同勛、陳文石和我三人講授「漢魏六朝史研究」,論及「山東」、「山西」的問題,使我得到更多的啟迪。所以從1957年以來,不管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香港大學和劍橋大學做研究或教書時,我都一直留意這個問題。1973年夏天我在法國 巴黎第29屆國際東方學會議宣讀的論文,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一個小節。 1977年的秋天,我正式開始作此題的研究。
這真是一個非常深邃的題目,幾乎是可以終生事之的。而我對自已所懸的鵠的太高,要求太嚴,所以進度緩慢。又由於這三十多年來考古的發掘,諸如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西樵山文化、青蓮崗文化、良渚文化、湖熟文化、金沙江遺址…一系列的發現,近年考古學界遂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不是僅僅發源於黃河流域一地,而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和遼河流域四區互相影響,互相融合、演進而成的。雖然這新穎的說法尚未得到中國歷史學界普遍的公認,但對我的研究卻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我開始作此研究時,是以傳統的說法,中國文化起源於黃河流域作基礎的。所以這時期地域觀念的轉變,實質上是一個文化傳播的問題。 這使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非常躊躇。最後,我終於徹悟,不管長江、珠江、遼河三流域史前有多高的文化,但從中國進入信史時代,黃河流域的中原區域(河、濟、淮流域為中心)確實已演進為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並由此而向四周傳播。所以上述考古學界新穎的說法並不與我的假設衝突。
其次,自1971年我來香港大學後,始終以教學、指導和鼓勵學生讀書、研究為首要。所以雖然任課繁重,一度授課五門之多,我也甘之如飴。這自然影響到自己研究的進度。例如1986年我原擬利用港大休假回到中研院史語所做研究一年,以完成此書的撰述;然後再去哈佛短期研究。港大並已准許給我Study Leave一年和旅費的補助。後來卻因為有位同事為修橋鋪路,利用休假去台灣講學一年,他留下的一名M.Phil.學生,全系沒有一個同事願意接手指導她修改碩士論文──該文幾乎是要重新全部寫過的。
我犧牲自己的撰述計畫,用大量的時間來指導該生,最後她終於通過校內外碩士的論文審查和口試。另外,我在港大中文系中國歷史組任教期間所受種種不可思議的困擾,也無時不阻礙和中斷我研究的進程。
今天拙著終於能夠出版。我要衷心感謝Prof.L.K.Young不斷的鼓勵,勞貞一、王叔岷、和楊蓮生三位恩師對我的期許,不時的來信鼓勵和指導,全漢昇、嚴歸田兩教授的厚愛。許多摯友:孫同勛、謝文孫、王業鍵、陶晉生、張春樹、張存武、余英時、劉翠溶、周成竹、施敏、劉震慰、陳三井、P.D.Reynolds、M.G.Spooner、陳耀南、古紹璋、唐煥星、葉永恆……他們都鼓勵我、協助我,在我稍有鬆懈時,陳耀南教授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督責我。我謹在此向他們敬致衷心的謝忱。我更要特別感謝賢妻袁萬蒂女士節衣縮食克勤克儉,獨力挑起全部家務和撫育三個孩子的重任,(孩子們也個個努力,成器成材。),讓我可以全力講學和硏究,完成此書的撰述。感謝台北市蘭臺出版社盧瑞琴小姐慨允出版拙書;郭鎧銘先生、林育雯小姐辛勤的編排和校稿。感謝中學階段長期培植我的五叔金福民先生,感謝周紹德伯父母視我如親子女,對我一家的愛護和照顧幾乎無微不至。最後衷心感謝邢義田教授,得知拙書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網上可以找到時,立即全文下載閱讀,當印就初校稿後,又在百忙中惠允再次審閱,盛情永誌難忘。惟全書所有錯誤仍是筆者之責。敬祈海內外專家學者不吝指正,俾稍後修訂增益,冀對中國學術有些微的貢獻。
承余英時教授題簽,允為此書增色,謹此特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