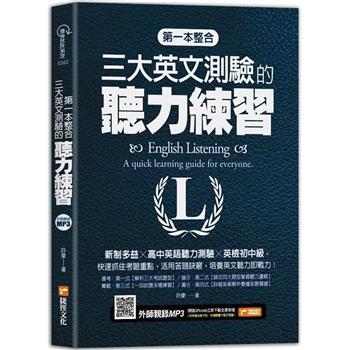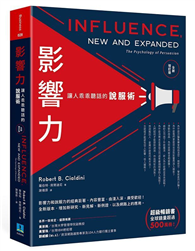鐵甲依然在!
「如果只讀一部中國奇幻作品,那就是江南的《九州縹緲錄》!」──星雲獎、雨果獎得主,《三體》、《流浪地球》作者劉慈欣
所有英雄,都曾是凡人,而身為凡人的,未必不能成為英雄。
熱血、澎湃、霸氣,2019最值得注目,非看不可的原創IP鉅作!
「因為有想要保護的人,所以我,必須更強大。」
▶ 東方版《魔戒》+《冰與火之歌》,2019全新修訂版,百萬人傳唱的經典,鐵甲依然在!
▶ 《豆瓣》書友大力推薦,TOP250,高分9.1!
▶ 中國作家榜榜首江南開創東方奇幻宇宙之作!特別收錄九州地圖!
▶ 2019強勢科幻片《流浪地球》、歐巴馬直接催更小說《三體》原著作者劉慈欣大讚:「如果只讀一部中國奇幻作品,那就是江南的《九州縹緲錄》!」
▶ 橫跨十年的不朽傳奇,鐵甲依然在!
▶不遠萬里取材,誠意實景拍攝!同名電視劇由當紅小生及演技女星劉昊然╳宋祖兒╳陳若軒英氣主演!九州炫風永不停息!
──▶ 九州介紹 ◀──
▶ 這片土地被叫做九州,傳說有個神帝統一過整個世界,將它劃分成九個州並取了名字,可是誰也不知道那個神帝是誰。
▶ 北陸有三個州,殤州、瀚州和青州。有人說北陸是古代一條巨龍,牠活了很多年,終於死了,沉積在海床上,泥沙堆在牠的骨頭上,就變成了北陸。殤州是牠的頭,從頭裡生出了夸父族,又高又大,凶猛得像是野獸;青州是牠的尾,生出了羽族,又輕又柔軟,可以飛上天空;而瀚州的草原是龍的胸膛,從心裡生出了蠻族,最勇敢。
▶ 草原上有七個大部落……如今沒有七個了,真顏部被滅族了……剩下青陽,還有陽河、朔北、瀾馬、沙池、九煵,一共六個。
▶ 九個州的疆域大小相差不多,貧富卻差得大。瀚州一年的出產,若是折成東陸金銖,大概是三千萬。可是東陸四州,光是中州一年的出產就不下八千萬金銖。而據說宛州一州的出產,就比東陸其他三州加起來還多。華族人占據最肥沃的四州,而蠻族六部只有一個貧瘠寒冷的瀚州。
▶ 東陸四州,中州、宛州、瀾州、越州。胤朝開國的大皇帝白胤建國時候,就把土地分封給了大將和親隨,當時是十二諸侯國的制度,六公國、六侯國,大皇帝只統治天啟城周圍的一片王域,面積還不及大的諸侯國。
▶ 後來的七百年裡,諸侯們爭鬥,有的兩國合併,也有的一國分裂。到了現在一共十六國,其中又有五家大諸侯,分別是中州北面的淳國、瀾州北面的晉北國,還有號稱「天南三國」的宛州下唐國、越州離國、宛州和越州之間的楚衛國。
──▶ 青陽三王子‧呂鷹揚 ◀──
他長得極像父親,永遠帶笑,總是最晚出手卻最能射到獵物。
他是朔北白狼王樓炎的外孫,以血統為傲,外公讚他年輕英明可成頭狼,但不同母的大哥比莫干啐他不過是雜種草蛇。
他沒告訴過任何人,他也擁有禁忌的青銅之血,是練武奇才,能使出絕頂武技,就這樣沉默了二十年。這是英雄的天命,為此他願忍受孤獨。
不世偉業方可安撫他寂寥的心,可盤韃天神或祖宗都未曾眷顧他,他只能向亡母祈禱成功,即使得陷害兄長、用萬人鮮血鋪平往上的道路。
直到最後一刻,他才能好好看向最小的弟弟阿蘇勒,平靜地面對兄弟相殘、青銅之血對決的命運。他們是家族最後的男兒,其中一人必須死去,今天之後輝煌便要凋零。
他是大閼氏所生的三王子呂鷹揚•旭達罕•帕蘇爾,背叛族人的篡權者,卻只有他是青陽與朔北和平的樞紐──
他的野心不死,而他的頭顱,可以平息戰爭。
作者簡介:
▍江南
作家。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留學於美國華盛頓大學。代表作有《九州縹緲錄》、《龍族》、《上海堡壘》等。其中《龍族》總銷量超過兩千一百萬冊,《九州縹緲錄》銷量超過百萬冊。曾兩度登頂「中國作家榜」榜首,並獲得最具幻想小說家獎、最具商業價值作品獎。
▍九州系列:
九州縹緲錄
九州飄零書:商博良
九州捭闔錄
章節試閱
九州縹緲錄(八)
喊殺聲已經逼到百步外,金帳的簾子被掀開,一個提著長刀的人緩步走了進來。
呂鷹揚看了那人一眼,露出一個驚詫的笑來。「阿蘇勒?你還活著?你怎麼來這裡的?」
「我告訴斡赤斤家的次子說,如果他們能掩護我來到金帳,我就能殺了你,我也有青銅之血,和你是一樣的,他答應了。」
「你殺了爺爺嗎?」
「沒有,我不會用刀對準自己的爺爺。」
「那你殺不了我,因為你太懦弱。」呂鷹揚搖頭。「阿蘇勒,你是錯生在我們帕蘇爾家了。」
「四哥死了,你很難過吧?如果早知道是這樣,你還會這麼做嗎?」
「天地不仁,容不得懦弱的人。我很難過,但我仍會這麼做,要成為英雄,就要狠絕,你不懂,所以你只會趴在比莫干的屍體上流眼淚。」
「旭達罕,你所說的我都不懂。算我是個傻子吧。」阿蘇勒說:「我都傻了那麼多年了,改不了的。」
「你們這些愚夫,只有我才是能夠救北都城的人,可你們沒一個相信,你們一個個都只想著殺了我!殺了我之後,狼主就會攻入這裡,殺了城裡所有人,這樣就稱了你們的心意嗎?」
「我在東陸,見過一種走鋼絲的藝人,他們在離地幾十尺的鋼絲上走來走去,翻跟頭。如果掉下來,他們就會摔傷,甚至摔死。可他們覺得自己不會掉下來,因為他們總在鋼絲上走,鋼絲對於他們就像平地一樣。但我見過那些走鋼絲的老藝人,他們很多人的腿都瘸了。」阿蘇勒說:「旭達罕,你一輩子都在鋼絲上走,一定會掉下來的。」
「阿蘇勒,這麼說話可真不像你啊,我能感覺得出你是真的恨我了。」呂鷹揚輕輕地嘆了口氣。「你這樣一個人,要讓你真的恨誰,也很不容易。」
「我知道我很懦弱,可流血已經流得太多了啊,我走到這裡來,一路上死了幾百人,我已經退不出去了。旭達罕,我們兩個的背後都是懸崖,是不是?」阿蘇勒仰起頭,長長地呼吸。
影月旋轉,阿蘇勒換為反手握刀,刀尖沒有指向呂鷹揚,而是指向了他自己的腰間。長刀回到刀鞘,他默默地踏上一步,沉腰側身,五指落在血跡斑駁的刀柄上。他的動作終止在拔刀前一瞬間的姿勢上,歸於絕對的寂靜。額前的長髮垂下,遮住了他的眼睛。
「瞬殺?」呂鷹揚的眼睛微微地亮了。
他聽說過這種刀術,來自東陸的雪國晉北,號稱世間刀法中最肅殺也最淒厲的一種。晉北的武士們在漫長的雪季裡用冰水沐浴,磨練精神和肉體,把強烈的殺戮之氣隱藏在心底深處,這是危險的魔鬼,只能在戰場上釋放。他們使用這種刀術時,被刀的殺氣駕馭,不見血而回鞘的刀被視為不祥和妨主的。
呂鷹揚把呂賀的屍體輕輕地放在地上,走下寶座,看著那柄藏於鞘中的五尺長刀,濃重的血腥氣透過刀鞘滲出,撲面而來。
他雙腿分立,輕輕地活動手腕,把獅子牙鬆鬆地提在手中,刀尖落在地面上。
阿蘇勒知道面前的哥哥有多麼危險,他在沒有食物和水的「鎖龍廷」中關了近三日之後,終於有機會和同樣有青銅之血的哥哥正面對敵。他使用瞬殺刀,因為這是可以逆轉局面的一刀。在殤陽關決戰前,他從古月衣那裡學到了這種刀術,也曾目睹古月衣用這種刀術斬殺雷騎,凌厲如妖鬼,曼妙如蝴蝶。
瞬殺刀的精髓,是凝聚全部的力量於拔刀的瞬間,這一刻力量的爆發,就像滔天狂浪衝破了閘門,沛然不可抵禦。運刀的人往往無法控制這一刀的力量,而必須藉助刀鞘,刀鞘的位置和角度將控制出刀的方位。刀沿著鞘掙脫束縛的瞬間,會獲得鬼神般的速度。
但是通常只有一次揮斬的機會,如果沒能命中,後背將留下巨大的破綻。
呂鷹揚無聲地笑了,他喜歡強而有力的對手,他已經不用再隱藏自己的力量扮成一個劍術平庸的三王子,他是帕蘇爾家頂尖的武士,需要頂尖的對手。他看得出來,阿蘇勒的力量和精神就像被鎖在紙盒中的火焰,那層薄薄的壁壘隨時可以被突破。
呂鷹揚聽見自己心臟劇烈跳動的聲音,血流速度已經快到了極致。
「阿蘇勒,我說過的,你是那種男人,永遠為了別人而活著,你是終要用一個哥哥的血去祭奠另一個哥哥的靈魂。」呂鷹揚輕聲說:「可你的星命在那顆永寂的玄一上,和你有關的人都會一一死去,等到那一天,他們都死了,你又要用誰的血去祭奠誰呢?」
「那就等到那一天,再說吧。」阿蘇勒腳步微挫,腳跟震地的聲音彷彿一記巨錘擊打,身形如離弦之箭射出。疾風掀起了他的長髮和他的長衣,向著兩側獵獵招展。
「阿蘇勒,你果然在東陸學到了不得了的東西啊。」呂鷹揚深深吸氣,瞳子裡彷彿吞吐著火焰。
「依馬德、古拉爾、納戈爾轟加,這是我祖宗的血。
「他們的靈魂在黑暗中看我,他們傳給我尊貴的血和肉,他們傳給我天神的祝福。
「我們註定是草原之主,我們註定是世界的皇帝,我們註定是神唯一的使者。」
他對著阿蘇勒發出咆哮,那古老的、咒文般的語言像一粒火種,落到他幾近乾枯的血脈深處,要把他千瘡百孔的身體再次點燃,熔煉為金剛。
歷史中還沒有任何人曾連續兩次喚醒青銅之血,但是他必須做到。他是呂鷹揚.旭達罕.帕蘇爾,他不能允許自己作為一個戰敗者倒下。在他對面的人流著和他一模一樣的鮮血,他更加不會退縮。他可以為了這次勝利付出任何代價,每一次的成功,他也從未計較過代價。
「帕蘇爾家祖先的靈魂,在我這裡!」他墜入了黑暗深處,眼中閃動著野獸般的光,傾盡全力探身一斬。
那一刀斬出的軌跡,是天地間最圓滿肅殺的弧線,那是天神以戰斧劈開世界的一斬,永恆的存在,帕蘇爾家歷代祖先們斬出的都是同樣的圓弧。
呂鷹揚完美地重現了大辟之刀!
阿蘇勒的刀貼著刀鞘發出刺耳的長嘶聲,影月離鞘,光如滿月。他全力吐出肺裡的空氣,封鎖在刀鞘中的凶煞之氣夾著那些因親人死而生的仇恨,潮湧而出。刀光細若一線。
兄弟兩人擦肩而過。阿蘇勒衝出十幾步才艱難地剎住,兩個人背向而立。呂鷹揚幽幽地嘆了口氣,丟下獅子牙,阿蘇勒的手中已經沒有了刀,淋漓的鮮血順著手臂而下。
「你是從我斬狼的那一刀裡學會大辟之刀的吧?開天闢地的一刀……天地間最圓滿的弧線……那是帕蘇爾家刀術的精髓……你是對的,你是帕蘇爾家最強的武士,只憑一眼就能學會沒人教過你的刀術。」阿蘇勒輕聲說:「其實你才是比我更適合這刀術的人,你總想著要權力、要武力、要為自己開闢一片天地……而我只想保護自己身邊那幾個人。」
「這時候還要嘲諷我嗎?你在瞬殺刀後的第二擊,用的是什麼刀?」
「這不是刀術,是槍術。」阿蘇勒說:「極烈之槍,破一切圓!」
他轉過身。影月留在呂鷹揚的胸膛裡,五尺長的利刃徹底貫穿了他的胸膛,他的胸口一直抵到了刀柄上。
能夠斬斷最圓滿弧線的,只有最凌厲的直線,姬氏極烈之槍的「焚河」,被阿蘇勒用在了刀術中,姬野曾教過他如何在最凶猛的突刺中調整呼吸、肌肉和精神,「焚河」擊出的時候,握槍的位置在尾部,和刀術沒有區別。
「你在東陸,真的學會了了不起的東西。」呂鷹揚說。
呂鷹揚也轉過身,微微瞇起眼睛看著阿蘇勒,青銅之血的效果從他身上迅速地退卻,他的面容漸漸恢復了英挺,脣邊帶著冷冷的笑意。他伸手握住影月的刀身,緩緩往外拔,每拔出一寸都有汩汩的鮮血湧出,但他像是絲毫不受影響。他終於把五尺長的影月從身體裡拔了出來,血淋淋地扔在腳下。
阿蘇勒覺得有隻陰冷的手握住了自己的心臟,他不知道在呂鷹揚身上發生了什麼,但他忽然想起了殤陽關裡的喪屍。
「一般的人,心臟毀了,早該死了吧?」呂鷹揚按住心口的巨創。「不過你和我不同,狂戰士有兩顆心,你身體裡那顆血嬰其實是顆很小的心臟,當它和另外一顆心臟同時跳動,比常人更多的血就會被輸送到全身,全身脈絡都會舒展開來,這就是青銅之血的祕密。但那顆小的心臟是個魔鬼,它裡面滿是毒素。你的青銅血脈不完整,因為你那顆小的心臟沒有長成,是個殘疾的魔鬼。」
阿蘇勒一步步後退,死死地盯著呂鷹揚空著的左手,以眼角的餘光在地上尋找合適的武器。他感覺到呂鷹揚所說的那顆心臟了,那個小小的魔鬼,在鮮血的召喚下已經開始搏動了,正把帶著毒素的血輸往他的全身,當那兩顆心臟的跳動被調整到一致的時候,他就會控制不住狂血,變成完完全全的狂戰士。他的體力已經差不多耗盡了,除了任狂血控制自己,他不知道還有什麼機會能戰勝呂鷹揚。
呂鷹揚忽然笑了笑。
「別怕,一顆小心臟,我支撐不了多久。你贏了。」他仰頭,望著金帳頂上的豹子圖騰,輕輕吁出一口氣。「阿蘇勒,你很好,不是我說的懦夫……」
呂鷹揚鬆開了手,創口處一股血泉沖出,在半空中灑開,彷彿濃墨潑灑的一朵紅花。他仰面倒在地上,身下一攤血漸漸變大。
阿蘇勒默默地看著他,呂鷹揚勉強地抬起手,衝阿蘇勒招了招。
「來。」呂鷹揚說:「放心,不是圈套。」
阿蘇勒一步步走近,直到呂鷹揚身邊。他站在那裡,盯著呂鷹揚的眼睛看了許久,呂鷹揚也一直在看他。阿蘇勒想他們這對兄弟從不曾這樣認真地凝視彼此,現在他們應該抓緊最後的時間了。
他忽然想起件小事,大概是他四歲的時候,跑去金帳找父親,看見那時候十四歲的呂鷹揚抱著一顆東陸產的藤球站在金帳外的陽光裡,穿著白色的半袖,陽光把金色燙在他的身邊。那時候阿蘇勒還不明白呂鷹揚這個哥哥到底和他是什麼關係,卻看見那顆藤球上纏著五彩的絲線,墜著流蘇,他就吵嚷著要那顆藤球。伺候他的女官急忙上來抱起阿蘇勒,說那顆藤球是父親賜給三王子的,不能強要,她們也明白在大君家裡,兒子們之間的關係是不會很好的。
阿蘇勒在女官懷裡大哭大鬧,而呂鷹揚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一直抱著那顆藤球站在陽光裡,神情淡淡地看著這個煩人的孩子。那時候他們也對視,一個十四歲、一個四歲,他們的眼睛都還清澈,不染塵埃。
那件事的結束是燙著陽光金邊的呂鷹揚把藤球遞給了女官。「給他吧,這是小孩子的玩具,我不玩了。」
阿蘇勒則抱著好不容易要來的藤球,看著那個少年的背影消失在遠處的陽光裡。
他對呂鷹揚的戒備消散了,慢慢地跪下來,把呂鷹揚抱起來,用手按住他的創口,讓失血變慢一些,可他知道這不能阻止呂鷹揚的死。
「爺爺死了嗎?」呂鷹揚低聲問。
阿蘇勒猶豫了一刻。「他死了,很安詳。」這是實話,那個老人對於這個世界已經不再留戀了。
「我感覺到了……同時有三個狂戰士的時代,帕蘇爾家本該橫掃整個草原吧?」呂鷹揚說:「可很快就只剩下一個了,還是不完整的那個。」
「事到如今還有野心嗎?橫掃草原,又有什麼用?」阿蘇勒說。
他們兩個的語氣都淡淡的,外面那些喊殺聲、咆哮聲、哀號聲好像暫時遠離了他們,這對兄弟好像是在下午的陽光裡喝著茶,一起說說閒話。
「有啊,我這樣的男人,野心總是不會死的。」呂鷹揚說:「只是力量不夠。」
阿蘇勒心裡一動。「如果回到從前,讓你重來一次,你還會這麼做嗎?」
「會啊,在知道自己有青銅之血時,我想我應該成為英雄,這是天命賜予我的機會。我要成為遜王那樣的男人,我可以忍受孤獨,但要成就事業。」呂鷹揚低聲咳嗽,嘴裡湧出血來。「因為我這樣的男人已經很孤獨了……如果不能成就英雄的事業,還有什麼能安撫自己的心呢?」
「你原本可以不孤獨,可你總是把自己和其他人隔開,哥哥,你永遠不相信其他人,你害怕他們傷害你。」阿蘇勒說:「或許有很多人傷害過你,對你不好……可是也有人只是把你看作哥哥,看作親人。」
「貴木嗎?是啊,如果我告訴他完整的計畫,他原本不會死。」呂鷹揚說:「他是我在這世上最愛的人。」
「還有我啊,你給我那顆藤球的時候,我可羨慕你了,覺得你又高大、又漂亮,那麼有禮貌,我長大要能像你一樣就好了……」阿蘇勒說著,有種泫然欲泣的感覺。
「什麼藤球?」呂鷹揚笑笑。「我忘了。」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兒,呂鷹揚說:「其實我也很羨慕你,你有母親在身邊,又是最小的孩子,很多人都覺得你沒用,但也有很多人會可憐你。但沒有人會可憐我,我只能變得強大,我要忍著,要給貴木信心。你知道嗎?我第一次發覺自己有這血統,是因為我控制不住,殺了一個伺候我的女奴,當時害怕得整夜整夜睡不著,我想我會不會變成殺人的魔鬼。我不敢告訴別人我有這血統,因為我覺得我說出來就會被殺死,我不是純血的帕蘇爾家子孫,卻有帕蘇爾家最高貴的血統……那時候我還太小,像隻小小的螞蟻。」
「跟我從真顏部回來時差不多大?」
「是吧。」
「最終你還是暴露了青銅之血,因為覺得機會到了,再不用畏懼了吧?」
「不,還是畏懼。」呂鷹揚說:「我永遠記得被我殺死的那個女奴的眼睛,大得可怕,月光照在她的眼睛裡。」
「我也是啊……」阿蘇勒也說:「這些天我總是做惡夢,想起那些被我殺了的人,在夢裡,我還在殺他們,不知道停止。」
「我在想……十年之前,我們都那麼孤獨……可彼此都不知道。」呂鷹揚說:「或許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個孤獨的孩子啊……」
「嗯。」阿蘇勒想起十年前北都城的陽光下他和呂鷹揚的對視,彼此看不穿對方的眼睛,眼底都藏著刻骨的孤獨。
「明天早晨,如果沒有人出城投降,狼主就會攻城……你要代替我出城,但你不是我,你沒法跟狼主議和,你要帶兵埋伏在城門口……在他們進城的瞬間給他們重創,把他們的人推出城外,然後再議和。這很冒險,但也是最後的機會……狼主相信我會向他投降,我已經寫信給他,他在等我,他會放鬆警惕。」呂鷹揚說:「進城時他們不會全軍出動,你要竭盡全力地斬殺他們的精銳,重創他們。你至少要帶一萬上過戰場的男人,但是越多越好。」
「明天?」阿蘇勒一驚,而後搖搖頭。「晚了,你聽聽外面的聲音,現在整個北都城裡,你殺我、我殺你,所有人都要復仇,所有人都瘋了。哪裡還有一支一萬人的軍隊?」
「把我的頭插在旗杆上,帶去各個寨子裡展示,告訴他們……我才是那個內奸,我才是一切禍亂的原因,他們會相信你的……其實他們也不想打下去了,只是停不下來。如果還需要證據什麼的,去我的寨子裡搜搜,總有的。」
「你真的出賣了軍情?」
「沒有,可總要有人承擔一切。你將是這城裡的大君,但或許只到天明之前,你還有三個對時而已。」
「這時候還要把別人玩弄在掌中嗎?你這個自信的男人。」阿蘇勒的眼淚無聲地流了下來。
「青陽,交給你了,抓著它,別放手……就像那顆藤球一樣。」呂鷹揚盯著阿蘇勒,握住他的手,而後慢慢闔上了眼睛。
他的三哥呂鷹揚.旭達罕.帕蘇爾死了,轉瞬間帕蘇爾家的男人們凋零了,他們曾經彼此敵視,如今一樣的冰冷。
「你本該是拯救青陽的人啊!」阿蘇勒再也控制不住,號啕大哭起來。「是什麼把你變成這個樣子的啊?」
不知道過了多久,呂鷹揚的身體完全沒有了溫度,阿蘇勒仍舊抱著他坐在金帳中央,仰頭看著天穹般的金帳頂幕。
他記得幾天之前自己也是這麼抱著呂守愚的身體,心裡的憤怒和悲傷像是要衝破牢籠的野獸,可現在他不再憤怒悲傷了,只是覺得累。他不想再哭了,可是眼淚還是無聲地往下流,像是永不乾涸的小溪。
他解開呂鷹揚的束髮帶,以手梳理他一頭沾著血汙的長髮,而後拾起影月,用衣角拭去刀上的血跡,在青冷的刀身裡,照見了自己的眼睛。
九州縹緲錄(八)
喊殺聲已經逼到百步外,金帳的簾子被掀開,一個提著長刀的人緩步走了進來。
呂鷹揚看了那人一眼,露出一個驚詫的笑來。「阿蘇勒?你還活著?你怎麼來這裡的?」
「我告訴斡赤斤家的次子說,如果他們能掩護我來到金帳,我就能殺了你,我也有青銅之血,和你是一樣的,他答應了。」
「你殺了爺爺嗎?」
「沒有,我不會用刀對準自己的爺爺。」
「那你殺不了我,因為你太懦弱。」呂鷹揚搖頭。「阿蘇勒,你是錯生在我們帕蘇爾家了。」
「四哥死了,你很難過吧?如果早知道是這樣,你還會這麼做嗎?」
「天地不仁,容不得懦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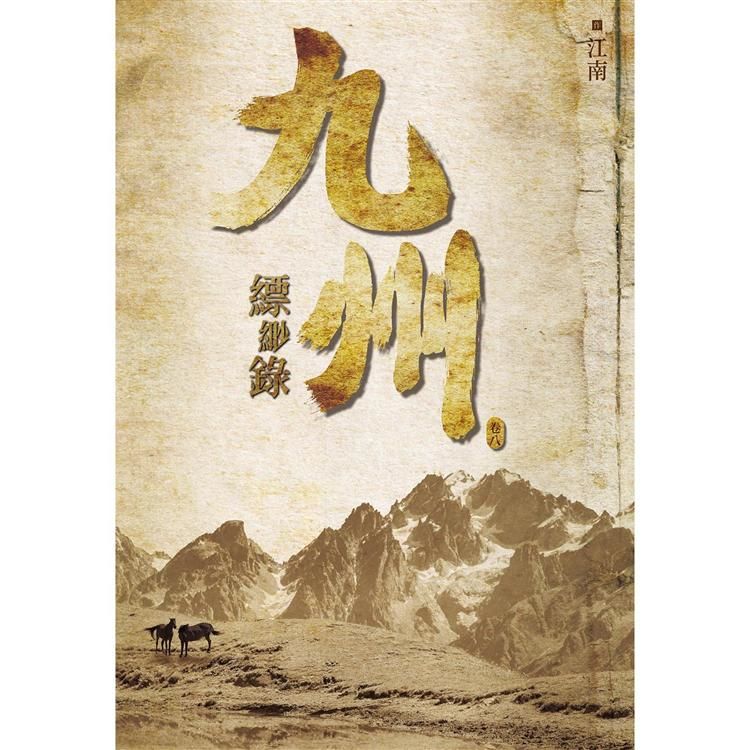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