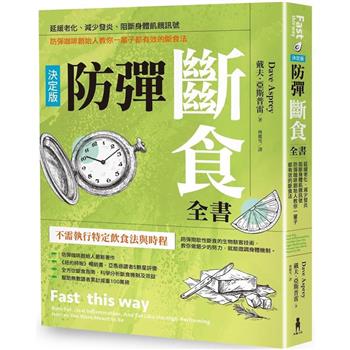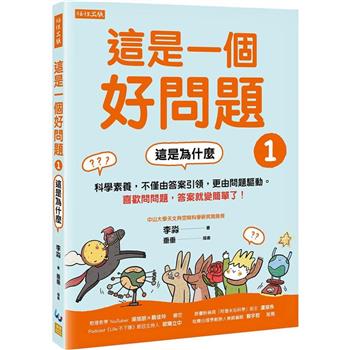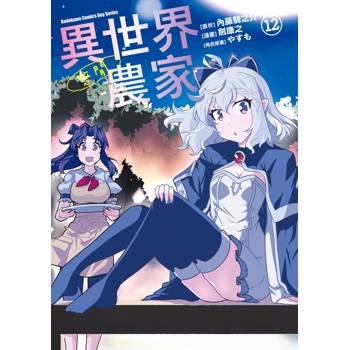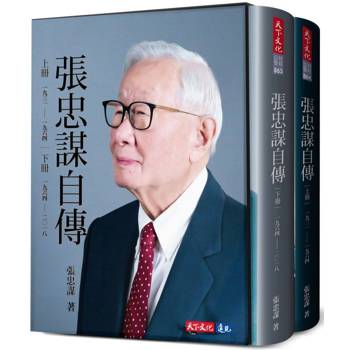第138屆芥川獎得獎作品
收錄得獎後最新作品〈你們的戀愛瀕臨死亡〉
日本亞馬遜讀者5顆星感動推薦
出版首月熱銷超10萬冊!
青春、成長、衰老——這具不知從何而來的軀體,今後,又將往何處去?
姐姐帶著女兒自大阪來訪。
三十九歲的姐姐打算隆乳。
外甥女跟媽媽生悶氣,不肯開口說話。
於是三人共度這奇妙夏日的三天時光。
這是發生在三個不同年齡女性之間的故事。卷子是大阪一家陪酒吧的陪酒女,與丈夫離婚後和小六的女兒綠子一起住在大阪。為了要隆乳,卷子帶著女兒到在東京的妹妹家做客。綠子正處於青春發育期,對自己身體的變化十分敏感、困惑,而媽媽卻一心只想要做隆乳手術,使她很不諒解,於是拒絕講話,用「寫」的方式與他人溝通,並抒發她的生氣與擔憂。
在這三天兩夜的相處中,三位女性對於自身的存在,各自有不同的質問與解讀。作者藉由這不同年紀的三位女性對身體的看法,也探討了女性自我生存的價值。
本書並收錄作者得獎後最新作品,故事場景設定在日本最繁華的新宿街頭,描述在這樣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裡,一位單身熟女的尷尬存在,意識流加上寫實的細膩手法,更充分展現出川上未映子的寫作風格。
作者簡介:
川上未映子
1976年生於大阪府。原為唱片公司歌手,曾發行過「夢見機械」、「腦中與世界的結婚」等音樂專輯。2003年開始在部落格上創作,每日瀏覽人數高達二十萬人次,2006年,將部落格文章結集,出版《放空的腦袋很大,世界猛然進入》,同時開始在雜誌上發表短篇作品,隨後《早稻田文學》亦即邀請她發表小說。
2007年,首度嘗試的中篇小說《我的牙齒,比率,或世界》入圍第137屆芥川獎決選名單。同年與村上春樹分獲第一屆坪內逍遙獎大獎和鼓勵獎。2008年,《乳與卵》獲得第138屆芥川獎,也被VOGUE評選為年度女性。2009年詩集《用先端,戳刺,被戳刺,那很好哇》獲第四屆中原中也獎。
譯者簡介:
劉子倩,政大社會系畢,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
章節試閱
卵子真正的名稱應該是卵細胞,至於為何會加上一個子,說來,只是為了配合精子這個名詞,才加上去的。學校的圖書室我去過幾次,可是借書手續很麻煩,基本上書又少空間又小光線又暗,有的人還會偷窺你在看什麼書這種感覺很討厭,所以最近我都是趁放學回家時去附近的圖書館。反正在裡面可以盡情使用電腦,而且學校很累人。很蠢。包括各方面。要說愚蠢這樣寫出來的確很蠢,不過學校的事放著也就過去了無所謂,問題是,家裡的事放著可不會過去,所以兩者不能一概而論。書寫這碼事,只要有紙和筆在哪都能寫,而且什麼都能寫,所以這是個很好的方法。我稱之為記錄。ない,漢字可以寫成厭或嫌,我覺得厭更有真正討厭的感覺,所以我要練習寫厭。厭。厭。
綠子
卷子他們將從大阪來,只要知道抵達的時間,不可能碰不上面,況且月台只有一個,我也已把事先問過的抵達時間輸入手機,按下通話鍵確定存入,所以這點可以安心。走在路上越過一又一個緊緊纏裹在圓柱上的光滑廣告,可是廣告中那個老牌女星穿的和服上,圖案到底是鏡餅(譯注:將二個大小不同平坦如鏡的圓形麻糬疊放,新年或喜慶節日時的供品)還是兔子,實在看不清楚呢。檢視電子告示板後上樓,赫然回神才發現自己正一邊數數一邊踩樓梯,雖被新幹線吐出的種種巨響震得腳步踉蹌,還是一眼就找到卷子他們。
即便遠眺也能清楚看出累壞的二人,夾雜在無數乘客之中倚靠長椅癱坐,不是用腰也不是用屁股,而是靠背而坐的二人,乍看之下和周遭的氛圍格格不入,彷彿只有那塊地方的色調不同。不知為何,看起來毫無血色,二人頹然垂首,我連忙一邊出聲招呼一邊小跑步過去,但二人之間,果然如同事先聽說的有種凝結的沉重氣氛,二人發現我後抬起眼,站起來各自伸展全身。
綠子才一陣子不見就長高了,不過整體來說,身材還是很纖細,大腿連像樣的肉也沒有,找不出半點圓潤,雖未親眼看過,但她的身體直線令我聯想到火鶴。不過就整體比例來說,她的腿果然特別長,簡直像省略胃部到大腸的部分直接冒出兩條腿。啊?妳連那種地方都是腿?我忍不住一邊故作感嘆順便打招呼,一邊拍拍她的屁股、大腿腿根確認,她沉默地縮腰閃躲。不過讓我驚訝、或者說令我在瞬間啞然的,倒不是睽違多日的綠子種種變化,而是卷子就整體而言的縮水程度。
卷子,本來就不是那種肉感或健康型美女,但我印象中的卷子,無論體格或臉蛋,感覺上,應該更大,更渾圓,有那種豐滿的味道才對,怎麼會縮水成這樣。她垂及肩下的頭髮,可能也因為燙過或染過看起來呈現紅褐色很沒精神,彷彿精氣神都從髮尾跑掉了。她穿著用立體英文字寫了什麼鬼玩意的灰色連帽外套,看起來硬邦邦的牛仔褲,還有不知該說是高跟涼鞋還是木屐的鞋子,而且以這副打扮來說,未免塗得太厚的濃豔口紅,口紅上出現幾道縱向皺紋。使用的粉底,不知是便宜沒好貨還是塗抹的手法不到家,或者純粹只是與膚色不合,總之厚薄不均,粉都浮起來了,臉和脖子的顏色明顯不同。在月台無數面孔中黯然失色卻又格格不入的卷子,好像不太自在,若是以前,我本來會當下取笑她,阿卷妳的妝有點太濃喔,這時卻像被什麼東西阻擋住說不出口,我笑著說聲我來拿,從卷子手中接過她的旅行袋。
卷子是我的姐姐,而綠子是卷子的女兒,所以綠子是我的外甥女。我這個小阿姨還沒結婚,而綠子的父親和卷子早在十年前就分手了,綠子打從有記憶起就沒跟親生父親同住過,也沒聽說卷子讓他們父女見過面,所以她對父親毫無所知,那當然也沒什麼大不了。因此我們到現在還是頂著同一個姓氏,平時住在大阪的這對母女,在這個夏天,基於卷子的心願決定來我位於東京的公寓住上三天。
接到卷子關於這次東京之行的電話約莫是一個月前的事。
她打電話的主旨是「我想去隆乳」。
「對這件事妳有什麼看法」本該是卷子在深夜下班後還特地打長途電話給我的目的,但她對於我的感想或意見從頭到尾都不像有餘裕或準備接受,卷子好像只是介於「把胸部變大」,或「自己真的能辦到嗎」的界線上極度亢奮,她那邊的時間消逝速度,和我這邊的好像差異頗大。
卷子雖談不上本就性格陰沈,卻也不算活潑健談。我還記得很小的時候,該說是一般所謂的內向自閉嗎,她一直交不到朋友,所以母親還曾為此被級任老師請去學校。說到朋友少,這點我也一樣,所以我倆總是同進同出。卷子騎腳踏車載著我,我們走遍了可以到的所有地方,只要不經意回想起當時,在我腦海中自動想起的總是卷子的指尖,卷子每每總是死命地啃指甲,啃得指甲都光禿禿了還不肯停嘴,所以指尖老是滲出一點血絲。我暗自想著,她那個毛病現在不知治好了沒有。
電話彼端,一直不斷地傳來隆乳手術、隆乳手術……聽到的只有隆乳這個字眼,我的耳朵與腦袋試著集中在卷子的話語,但,結果到底是在說誰的事、說了些什麼,我即使再怎麼努力試著集中心神,隨著時間流逝,還是越來越聽不懂。唯有名詞和聲音不斷盤旋打轉,漸漸地,好像連我正與卷子說話的實感都失去了,真是傷腦筋。
況且先不說別的,卷子以前從未像這樣在深夜打電話過來,而且是天天打。光是這樣,就已打亂了我的生活步調,而且電話每次一講就是一個小時,連著四天通通都是在講隆乳手術,說來說去,內容不外乎是隆乳的方法,以及「我想做做看」的決心或者說心境。在那些反反覆覆的過程,以及隆乳的小小話語夾縫之間,她會忽然冒出一句,「我跟綠子也不對勁好一陣子了」。這事我之前也聽過,而且我個人其實還挺擔心的,嚴格說來,我覺得這件事比起隆乳,在我們之間應該更重要。但卷子在電話中實在太努力發表讓胸部變大的話題,我根本逮不到機會打斷卷子像機關槍一樣的敘述,只能對她那沒完沒了毫無營養的胸部話題適時地出聲附和。可是,一旦話題在不意間忽然帶到綠子,本來如龍捲風撲天蓋地滔滔不絕的卷子,就會像要含糊其詞或假裝沒什麼事,忽然聲調一變,不知為何似乎有點尷尬,說什麼「哎呀綠的事情,沒問題的啦」,然後用莫名開朗的聲音說:「不過我跟妳說喔,我們最近,唉,都是用筆談,就是用寫的啦、用寫的。」「用寫的?什麼意思?」「沒有啦,我還是用說的,我是會跟她講話啦,可是綠都是用筆寫。她都不說話。一直這樣。好像已經快半年了吧。」卷子說,「半年?不會太久嗎?」「算滿久的,對吧。」「的確很久。」「我一開始當然也試著問她各種問題,可是她一直是那副德性。會變成這樣的原因,一開始也許是出在我身上或我做錯了什麼,可是不管我怎麼問她就是不肯告訴我,也不跟我說話,也沒有生氣,真是傷腦筋,雖然傷腦筋,可是我心想,哎,小孩都有這種時期,所以姑且就當作是這樣嘍。」
☆班上的同學,好像大部分都已來了初潮,今天如果就字面來思考,初潮的初就是起初的初,這個我懂,那麼後面這個潮是怎麼回事呢,我納悶地查資料,書上只有解釋初潮就是第一次的月經,害我覺得好像被唬弄了,應該沒這麼簡單吧。所以我又查潮這個字,結果有很多種意思,上面寫著月亮與太陽的引力使得海水時漲時退,也就是會波動,是海浪,所以,也有好時機之意,我最不解的是不知為何還寫著「愛嬌」,我再查愛嬌的意思,這也有各種解釋,不過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商店努力討好客人,或令人產生好感之類的,這個,為什麼會跟從雙股之間頭一次出血的初潮有關,實在令我一頭霧水莫名地感到氣憤。
綠子
卷子現在三十九歲,年底就要滿四十了,目前的職業是陪酒小姐。陪酒小姐,其實包含著各種形態,只要看工作的酒店位於何處,便可大致了解薪資及客層。大阪雖有多得數不清的酒店街,但卷子工作的地方在大阪的京橋,這裡算是所謂的貧民區吧,和一般人口中的高級品完全扯不上關係。放眼而去,只見整體變成褐色的老舊電玩場,以及簡陋的立飲屋(譯注:只能站著喝沒有座位的小酒屋)林立,已呈歪斜狀的個體戶書店旁,是店面細長的燒肉店。毫無縫隙緊貼在一起的,是有著俗豔的店面,裝潢得超級閃亮刺眼的色情電話及口交特種行業。隔壁還有可以吃到河豚的店,不過這裡的河豚,到底哪一點算是河豚,即便嚼在嘴裡還是令人很納悶,不知這玩意到底哪個部位算是河豚。再加上排山倒海而來的小鋼珠的音流,霓虹燈飾的閃爍電光,桌面內藏電玩機的黑漆漆咖啡店,沒見過店主也沒客人出現過的印章店,等等等等。人們在此發洩內心鬱憤,大笑,路旁啤酒瓶堆積如山碎了一地,總之一切亂七八糟,說得好聽,算是一個人情味濃厚,隨性又自在的地區,但其實聚集的店全都又窄又小。每間酒家一定都有卡拉OK,大樓裡面,到處都有麥克風嗡嗡的餘音,聽久了幾乎令人頭暈。早已年過六十的熟女忙著拉客,或者遊說著「可以跳舞喔,二千圓無限暢飲,要不要進來坐,」,總之大致類似這樣形形色色的店都有,不過卷子上班的地方算是所謂的酒廊。
吧台前有幾張椅子,還有幾張用沙發圍起的卡座,只要來十五個人就會客滿。因此即使開再貴的酒,了不起也不過一個人一晚花個一萬圓,為了提升業績,陪酒小姐也得點各式飲料,必須喝個不停,直到灌滿一肚子酒。光喝酒還不夠,所以又叫了烤香腸、煎蛋捲、油漬沙丁魚這類分不清是便當菜還是下酒菜的東西,回音嗡嗡響。雖然唱一首歌,只要一個百圓銅板,但積少成多也可以換成鈔票,所以非讓客人多唱幾首不可,即使如此,大家多半也花不到五千圓就走了。也有很多只來一次的過路客,純粹是為了無限暢飲,從頭到尾賴著不走。撇開那個不論,生意是靠常客捧場才能勉強維持,幾乎都是熟面孔,自然也不便傷和氣,所以客人如果不走,基本上就無法打烊,徹底以客人為第一優先,這就是卷子上班的地方。
卷子的家計,雖也有領單親家庭的補助金,但那點錢不過是杯水車薪,卷子離婚後陸續做過超市事務員、工廠兼職工、站收銀台、捆包工種種工作,但那種薪水無法糊口,所以只好也開始兼差做起陪酒小姐。嚴格說來,個性很怕生,又低調平庸的卷子,起初在酒家陪客,自然不可能勝任愉快。但她一再跳槽後,在現在這家酒廊好歹也待了三年。這裡的老闆是個五十幾歲的媽媽桑,員工就只有卷子及兩個二十歲左右的兼職女孩。兩個小女生自然不可能有什麼出眾美貌,也不懂得機靈拉客,再加上動不動就不假曠職,就算勉強陪客也一直看手錶心不在焉,只顧著聊自己的事。可是話說回來,如果罵得太狠把人趕跑了,店裡又會缺人手,所以也沒辦法,只好忍耐嘍,這些話已成了媽媽桑的口頭禪。而卷子長得既不是特別漂亮,說話技巧更不出色,所以與其說深受倚重,倒不如說是被抓住弱點,所以就連正規工作以外的差事也漸漸推給她。比方說,店裡每逢啤酒進貨的那天,她就得提早上班負責收貨。在大樓一樓的電燈招牌插上電,也是卷子的工作,還要烹調下酒的小菜、清掃廚房和洗手間,等客人走後,還要洗餐具、丟垃圾、採買用品。就這樣包辦店中一切雜務。
可是,在週六週日還要上班的卷子,完全採時薪制,雖然我沒詳細問過她每月賺多少,但單純計算下來,就算不眠不休工作順利,最多也只能賺到二十五萬圓左右。幸好現在她的健康還沒出問題,母女倆的生活不至於驟然陷入困境,可我也不相信她有足以安心的存款。況且,卷子今年就要四十歲了,難保將來會發生什麼事,基本上把綠子一個人晚上留在家裡就值得商榷。不過,這也不是現在才開始的事,況且,聽說這年頭的單親家庭還有更悲慘的情況,就這點而言,附近就住著與卷子有多年交情的好友一家人,如果卷子不在家時,萬一出了什麼事可以就近立刻給予協助,至少會比較安心。不過,基本上今後也繼續讓綠子晚上單獨在家的安排,肯定不妥。雖然不妥,但那種事卷子自己想必也很清楚,況且我也沒什麼資格替人操心、自以為是地批評,更無法具體幫上忙,所以也不好意思插嘴干涉。
總之,當我想起今後卷子母女要如何克服每個當下的局面,不免也會心情黯然。雖知那是無可奈何的事,當然若說在正常公司上班就能安心,也不能這樣一概而論,畢竟這是當今社會的事實。很多事,雖然自認很清楚、很了解,但是越想只會越累,一想到當頭壓下的是大阪、母女,從那字面從那聲音從那方位從那心像,總是宛如悄然無聲平板均一的夜晚,朝我背後襲來、抹也抹不去的疲憊感,彷彿漸漸濡濕我的肺與眼。
卵子真正的名稱應該是卵細胞,至於為何會加上一個子,說來,只是為了配合精子這個名詞,才加上去的。學校的圖書室我去過幾次,可是借書手續很麻煩,基本上書又少空間又小光線又暗,有的人還會偷窺你在看什麼書這種感覺很討厭,所以最近我都是趁放學回家時去附近的圖書館。反正在裡面可以盡情使用電腦,而且學校很累人。很蠢。包括各方面。要說愚蠢這樣寫出來的確很蠢,不過學校的事放著也就過去了無所謂,問題是,家裡的事放著可不會過去,所以兩者不能一概而論。書寫這碼事,只要有紙和筆在哪都能寫,而且什麼都能寫,所以這是個很好的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