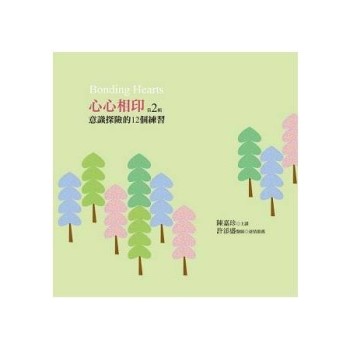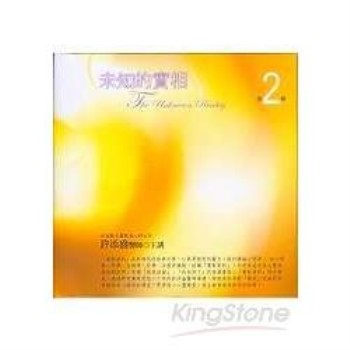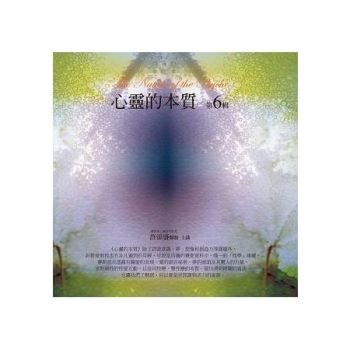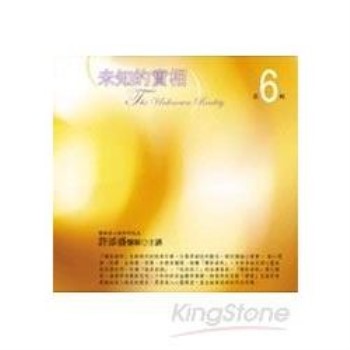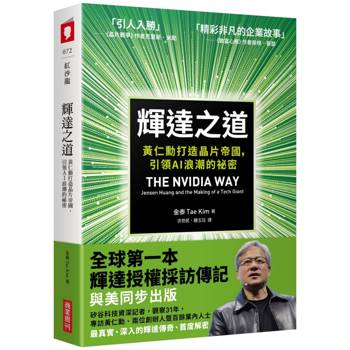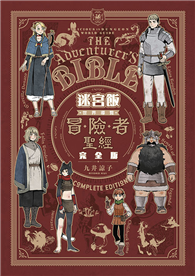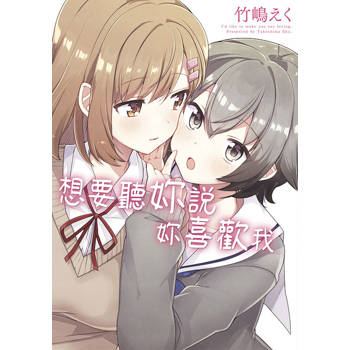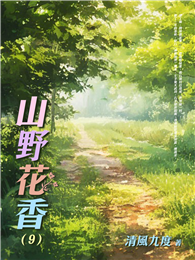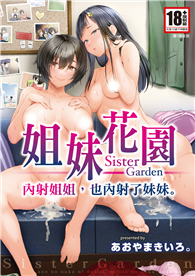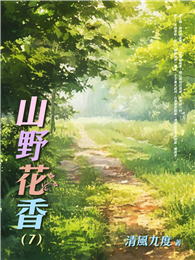引 言 徐 文 助
在中國小說史上,平話小說的出現,是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年間;那時候民間有一行業叫「說話」,相等於現在的「說書」,專門以歷史和民間故事為題材,鋪演成曲折的情節,以吸引聽眾,從事這一行業的人稱為「說話人」。說話人說書時各有他們的底本,稱之為「話本」,話本的作者多為無名的「書會先生」。這些作者寫作話本的目的很單純,只是提供說話人說書的稿本而已,沒有類似一般文人創作的動機,所以他們的文筆非常粗率,情節很曲折,題材不脫離市民生活的領域,小說人物的行為、思想,也都是平民化的;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用淺顯的白話文寫成,有些還夾雜相當多的方言俚語,這點和傳統的筆記體、傳記體等文言小說不同,平話小說是更通俗化、群眾化了。
話本是一種講唱會合的文學,說話人靠講唱話本作為謀生的行業,為了吸引聽眾,它自然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體例,和一定的語言。就體制來說,一般話本可分:篇首、入話、頭回、正話、篇尾等五大部分,篇首是以詩詞做為開頭。入話是把篇首的詩詞加以解釋,或加以議論。頭回是一個完整的故事,故事內容和正話可能相類,也可能相反;頭回又可稱為「得勝頭回」,或者「笑耍頭回」(如清平山堂話本的刎頸鴛鴦會)。以上篇首、入話、頭回三種,都是說話人在開講前吸引、穩定聽眾,使他們不至離開,以等待更多聽眾到達的權宜作法;由於時間長短不一,所以這三者的內容也可作彈性的伸縮,或解釋、或議論、或感慨、或評估,說話人需要有豐富的歷史、社會等知識或文學素養,才能勝任。
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印刷業發達,書本已較以往容易流通,市場的需要,促使文人也參與話本的著作,話本小說也因此由聽講方式漸進為「只能看不能聽」的文學作品了,直到馮夢龍的擬話本小說「三言」出現,文人擬作話本的風氣開始興盛起來。馮夢龍以其深邃富哲理的思想、豐富的人生體驗,奠定擬話本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但馮氏「三言」裏的一百二十篇小說,有些並不是完全自作,而是錄自前人的話本,或者就原來話本稍加修訂的;真正完全自作話本小說,得到社會廣大群眾歡迎的,應該是凌濛初,凌濛初所編撰的話本定名為拍案驚奇,原有初刻、二刻各四十篇共八十篇,初刻現只剩三十六篇,二刻雖有四十篇,但最後一篇為雜劇,實際只有三十九篇。凌濛初的話本小說雖然都是自作,但無論體例或語言,卻完全模倣民間的話本小說;就體例、結構說,民間話本的五種結構:篇首、入話、頭回、正話、篇尾等都具備完整;以二刻拍案驚奇為例,除了少數篇卷如第十二卷「硬勘案大儒爭閒氣,甘受刑俠女著芳名」,篇首以一首詩「世事莫有成心,成心專會認錯,任是大聖大賢,也要當著不著。」為起,入話裏就這首詩稍加議論,認為人不可有成心,一有成心連聖賢也要偏執起來,數句帶過,就緊接正話,敘述大賢朱熹因一點成心在心,而錯斷了事的情節,「頭回」的存在較不清楚,其餘大都體例完具,甚至還有不少兩個頭回的例子,如第三十五卷「錯調情賈母詈女,誤告狀孫郎得妻」,第一個頭回描述陳氏女子守貞,不和婆婆同流合污,終被虐待自縊身死的故事;第二個頭回描述姑嫂二人勾搭男人不成,反而身遭奇禍,自縊而死的故事;兩個頭回故事情節各自獨立,和正話雖說性質相同,但情節毫無關聯。
另外就話本獨特的語言來說,擬話本也一概模倣採用,如「卻說、話說、且說、只說、看官聽說、看官且聽小子說、閒話且不說」等,在拍案驚奇裏,可說俯拾皆是。如果情節複雜,說話人為了劃分層次,最常用的語句是:「……不題,話分兩頭」、「自不必說」、「只因此一去,有分交」,這些全部是民間話本遺留下來的詞語,而擬話本全部加以保留採用。
凌濛初擬話本唯一在形式上和話本不同的,就是篇名。從洪楩清平山堂話本和京本通俗小說所收錄的話本裏,可看出民間話本的篇名都是簡單具體的散文句,尤其是清平山堂話本所收錄的,大都以「記」、「傳」為名,到了馮夢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裏,才加以改變,改以兩卷為一的對偶句,做為該兩卷的篇名,例如警世通言第一卷篇名是「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第二卷篇名是「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兩個篇名很明顯的是對仗工整的對偶,第三、四卷情形也一樣。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驚奇沿承馮夢龍的作法,也以工整的對偶句做為篇名,但他不採用兩卷合一的作法,而是在一卷之內,就用兩句工整的對句做一篇的篇名,這是凌濛初和馮夢龍體例上唯一不同的地方,不過他們兩人同樣以對偶句做為篇名,和民間的話本是不同的。可見擬話本不管在形式上怎樣模倣民間話本,畢竟作者的思想、生活背景不同,總有不同的痕迹存在,在形式上如此,在內容上更是如此,我們可以把話本和擬話本內容上的差異,稍微比較如下:在取材上,民間話本的取材都是通俗性的人物,情節也大都是小市民身邊的,日常生活所可能發生的事情;在清平山堂話本所收錄的十五種話本,除了第一的「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第十的「張子良慕道記」是以歷史人物為背景外,其餘都是一般社會上的奇事奇聞,例如京本通俗小說所收錄的七卷話本小說,除第十四卷的「拗相公」外,也都是如此;但是擬話本出現後,取材更加擴大了,例如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第二卷「莊子休鼓盆成大道」,第三卷「王安石三難蘇學士」,這三卷都刻意在表現文士的才情,顯然也較脫離市民的生活領域;迨至凌濛初的初、二刻拍案驚奇,以地方官吏和大戶貴室為題材的就更多了。從主題意識上看,民間話本裏人物對社會的不平,和政治的黑暗,有切身的感受,他們所表現出來的喜怒哀樂的感情,也是直接而坦率的,對鬼神的態度也是一味的傾倒迷信;而文人擬作的話本裏,雖然仍舊在暴露社會、政治的黑暗面,但對這些黑暗已能做仔細的觀察、細膩的刻劃,對鬼神的態度也較能以理智的態度處理,例如二刻拍案驚奇第十八卷「甄監生浪吞秘藥,春花婢誤洩風情」描繪善惡報應純由巧合,和鬼神無關;古今小說(喻世明言)第二十四卷「楊思溫燕山逢故人」裏,鄭義娘說:「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這種較有思想的話,顯然是出自文人的手筆。此外,擬話本的作者由於出自有學養的文人,一般都較能注意藝術、情境的塑造,對於小說應具備的條件:人物、結構、背景等也較能注意到,所以常常有技巧不錯,情節感人的作品出現,例如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杜十娘怒沈百寶箱」描繪男主角李甲理智和情感的衝突,女主角杜十娘為情而死的決心等,都很深刻;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背景描繪的細膩,都是一般民間話本不易達到的境界。
初、二刻拍案驚奇是凌氏最暢銷,也是最令他成名的兩部著作,這二部書共收錄八十篇白話短篇小說,內容和技巧優劣互見,從其中可以看出凌氏對白話短篇小說的見解和觀念,他在初刻拍案驚奇序文說: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輕薄,初學拈筆,便思污衊世界,得罪名教,莫此為甚。有識者為世道憂,列諸厲禁,宜其然也。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書,頗存雅道,時著良規。復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詼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凡耳目前之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總以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云爾。
由文中「復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睹,佐詼諧者,演而暢之」,可看出初刻拍案驚奇都是他自作,和馮夢龍「三言」大都取自古今小說者不同。序文又提到初刻內容「怪怪奇奇,無所不有」,這當是「拍案驚奇」所以命名的原因;底下雖有「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為戒」的話,但到底還是著重在「奇」字,這種堂皇的說法不過是炫人耳目而已。就實際內容看,像卷一「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卷八「張溜兒熟布迷魂局,陸蕙娘立決到頭緣」、卷十六「喬兌換胡子宣淫,顯報施臥師入定」、卷十七「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畫錦黃沙衖」等,都有十分露骨的色情描寫,足以說明凌氏的寫作態度並不十分嚴謹,雖然他寫作的時間和馮夢龍非常接近,如馮氏「三言」中最後一言醒世恆言編撰的時間在天啟七年,和初刻拍案驚奇出版的時間相同,但顯然地馮夢龍的三言是純淨多了;馮氏在醒世恆言序說:「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通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也。」不像凌氏著重在「奇」字,為了「奇」,當然就不得不在主題和技巧上做一些犧牲。初刻之後,崇禎壬申五年(西元一六三二年)二刻拍案驚奇又刻成,凌氏在序文中說:
丁卯之秋,事附膚落毛,失諸正鵠,遲迴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非曰:「行之可遠」,姑以游戲為快意耳。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為書賈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為鈔撮成編,得四十種。支言俚說,不足供醬瓿,而翼飛踁走,較撚髭嘔血,筆塚研穿者,售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詎有定價乎?賈人一試之而效,謀再試之。余笑謂:「一之巳甚。」顧逸事新語可佐談資者,乃先是所羅而未及付之於墨,其為柏梁餘材,武昌剩竹,頗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復綴為四十則。其間說鬼說夢,亦真亦誕。然意存勸戒,不為風雅罪人,後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為綺語障。作如是觀,雖現稗官身為說法,恐維摩居士知貢舉又不免駁放耳。
這段序文,說明凌氏二刻拍案驚奇的出版,是因為初刻銷路大好,應商人之請,再事搜集「逸事新語、可佐譚資」者付墨出版的,如此一來,著述的動機已純為利的打算,取材也大受限制,以至於寫作目的所標榜的「意存勸戒,不為風雅罪人」,就變成不易達到的理想而已,理想和實際不能配合,是凌氏初、二刻拍案驚奇的最大致命傷。
誠如書名「拍案驚奇」的提示,小說內容既要「怪奇」到令讀者「拍案」叫絕,又要符合賈人所要求的「通俗」條件,內容範疇已經大受限制,加上初刻已選出四十卷,再刻所能選的已所剩無幾,二刻拍案驚奇的內容主題因而更顯狹隘;綜觀全書四十卷,沒有一篇真正在刻劃忠孝節義的,馮夢龍「三言」裏極力刻劃的義氣知己之交,在本書裏也看不見;大概忠君和義氣知己向為知識分子所嚮往,凌氏既以銷路為第一考慮,為了通俗的要求,這一方面的內容只好割愛。反看以神鬼為題材的有第六卷、第十一卷、第十三卷、第十六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第三十七卷共九卷,幾佔全書的四分之一,而且凌氏所描繪的鬼神世界較前人更為複雜;人鬼之間的關係也更為親近,而至於人鬼不分。凌氏筆下的鬼魂行步有影,衣衫有縫,婚姻生活和生人無異,例如第三十卷「瘞遺骸王玉英配夫,償聘金韓秀才贖子」裏的女鬼王玉英不只可以寫詩,還和韓生結婚生子;鬼如此,神也不例外,例如第三十七卷「疊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顯靈」敘述商人程宰旅途落魄,受海神垂青,不只夜夜美人(海神)在抱,並得海神之助,生意大發,財源廣進;第二十九卷描繪靈狐魅惑蔣生,後來蔣生得靈狐之助,不只身強體健,又娶得如意佳人,文中的狐仙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從小說藝術的觀點看,由於作者屈於賈人的要求,創作了這些迎合世俗趣味的東西,無形中貶低了二刻拍案驚奇在小說中的地位。但從另一個觀點看,凌氏對當時政治風氣、社會環境等客觀的描繪,也提供我們對明代亡國前一段政治、社會背景的瞭解,可見它仍然具有相當的意義的;以第十三卷「鹿胎菴客人作寺主,剡溪里舊鬼借新屍」為例,敘述劉念嗣死後,妻子改嫁,棄孤兒於不顧,乃借張家老丈剛死之屍體還魂,以託好友直生上告官府,得發還田產,孤兒才能免於凍餒;又如第十六卷敘述陳祈田契暫質毛烈家,毛烈欺心不還,陳祈告到官府,以無執照為憑官府不受理,陳祈乃夜告社公祠,毛烈受神懲罰而死。這類小說在當時必然相當盛行,凌氏乃因應習俗而加以創作;按理說有狀應告到官裏,但那時官場一片黑暗,到處貪官污吏,尤以獄訟特別嚴重,民間有冤無處訴,有債無處討,只好訴諸鬼神了;在百姓的觀念裏,鬼神已變成正義的象徵,所以民間之傾向於鬼神,不是用單純的「迷信」一詞就可解釋的;又如在卷三十八的頭回裏,李三被縣官屈打成招,點名起解時,突然霹靂一聲,將掌案孔目震死,屍背上寫著「李三獄冤」四個篆字;如果不是這一聲霹靂,李三的冤情就永遠不白,因為「有勢力的人才可能在上司反告下來。」(語出卷三十八正話)而李三沒有勢力,唯一可依賴、期待的就是鬼神,總算鬼神沒有遺棄他,救了他一命,但別人能有相同的運氣嗎?鬼神之事確實是可疑的,但百姓卻寧可信其有,這說明百姓內心有多少無奈。
災難的消除固然需要鬼神的幫忙,富貴的尋求也非鬼神莫辨;在那是非不明、善惡不辨的時代裏,靠正當途徑而得富貴已不可能;一般守法的百姓對富貴既已沒有能力追求,只有把這種慾望寄託在烏托邦式的幻想裏,所以在明代話本、擬話本小說裏,變泰發迹的故事特別多;二刻拍案驚奇第十九卷敘述言寄兒生來愚蠢,為人看牛,以出力作工度活,這種人富貴簡直和他絕緣,但他卻得道士之助,夜夜做夢享盡榮華富貴,最後還掘得一窖金銀;第三十六卷裏的王甲,也虧得神鬼幫忙,而得到聚寶鏡,才能夠享盡人間的富貴;沒有神鬼做後盾,百姓又如何能滿足他們的富貴之夢呢?
除鬼神外,貪官污吏、屈打成招的事例,在二刻拍案驚奇裏觸目都是,其中尤以第三十一卷「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對「簡屍」的毒害百姓,說得最為痛切。「簡屍」就是「驗屍」,古代驗屍的人叫做「仵作」;在政治清明的時代裏,簡屍原是追查兇案真相的必要手續,想不到風氣敗壞的明代末年,簡屍變成害人的東西;作者在第三十一卷入話裏說得好:
話說戮屍棄骨,古之極刑。今法被人毆死者,必要簡屍。簡得致命傷痕,方准抵償。問入死罪,可無冤枉,本為良法。自古道法立弊生,只因有此一簡,便有許多奸巧做出來,那把人命圖賴人的,不到得就要這個人償命。只此一簡,已彀奈何著他了。你道為何?官府一准簡屍,地方上搭廠的,就要搭廠錢;跟官、門皁、轎夫、吹手多要酒飯錢;仵作人要開手錢、洗手錢;至於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硃墨錢、筆硯錢。氈條坐褥俱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肖佐貳,要擺案酒,要折盤盞,各項名色甚多,不可盡述。就簡得雪白無傷,這人家已去了七八了。就問得原告招誣,何益於事?
簡屍既如此害人,苦主不簡就可以了吧?事情卻沒這麼簡單,作者又說:
豈知世上慘刻的官,要見自己風力,或是私心嗔恨被告,不肯聽屍親免簡,定要劣撅做去,以致開久殮之棺,掘久埋之骨,隨你傷人子之心,墮傍觀之淚,他只是硬著肚腸不管。原告不執命,就坐他受賄;親友勸息,就誣他私和。一味蠻刑,打成獄案。自道是與死者伸冤,不知死者慘酷已極了。
在這種情況下,有良心、有孝心的兒女,只要事情一發生,只有死路一條,再沒有他路可走了,這就是這一卷故事裏王世名寧可夫婦同死,也不願官府簡亡父之屍的原因。又如第四卷的楊巡道,第十六卷的州官,第二十卷的武進縣知縣,第三十六卷的提點刑獄使者渾耀,都是較為顯著的貪官污吏,尤以第四卷楊巡道的嘴臉刻劃得最為精彩:
這巡道又貪又酷,又不讓體面;惱著他性子,眼裏不認得人;不拘甚麼事由,匾打側卓,一味倒邊。還虧一件好處,是要銀子,除了銀子再無藥醫的。有名叫做楊瘋子,是惹不得的意思。
至於屈打成招的例子也相當多,如第二十一卷吳帥之刑盛彥,第三十八卷大庾縣官之刑李三,第三十八卷兵馬司之刑楊二郎等等,對於這些黑暗面,凌氏都不時地加以描繪,說明凌氏還有讀書人的良心,不是只知一味討好世俗,以求名利的人可比的。
就社會風氣來說,凌濛初的文筆更像一副鏡子,把地方上的一群牛鬼蛇神照耀得原形畢露,讓後人清楚瞭解明末亡國前的社會真象,真個是百害俱生,無毒不有。綜觀二刻拍案驚奇所描繪的傷風敗俗,至少有下列幾條:
1.紮火囤:紮火囤就是一般人所說的「仙人跳」,第十四卷就敘述吳宣教中了人家的圈套,弄得財物盡失,還生了一場大病,送掉了老命。這是明末的惡俗之一。
2.好男風:這種惡習,凌氏雖沒有專文加以鋪陳,但第十七卷裏記載人物魏撰之的話說:「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想來這種惡習在當時必然相當盛行。
3.煉內丹:煉內丹另有一種名稱,叫做「採戰工夫」,如第十八卷描繪甄監生家中廣蓄三妾四婢,以為採戰煉丹之用;其他篇目也時有形容人物深懂採戰工夫的(馮夢龍「三言」中的警世通言第三卷「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裏面的劉璽也「善於採戰之術」);再參考當時一般色情小說如金瓶梅之類的流行,可以看出當時社會必然呈現一片淫穢之風。
4.蓄妾婢:古代社會,女子地位卑下,有錢人家的男人,除妻妾之外,又蓄養很多女婢;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十四卷描繪宋時楊太尉姬妾之多,已令人驚奇,如加上養娘侍婢,更是不勝枚舉,這種風氣,在社會嚴重貧富不均的明末尤其厲害;所謂侍婢,也不過是主人洩慾的工具而已,凌氏在二刻拍案驚奇第十卷裏說:「況且曉得人家出來的丫頭,那有真正的女身?」明顯地說出了這種情況。
5.女偷男:男女偷情或畸戀,古今中外都有,不足大驚小怪,但一般情況都是男方主動,女方接受,有時女方還是在男方刻意的欺騙下,而成為犧牲品的,像二刻拍案驚奇裏的女偷男這樣大膽的描繪,不要說歷史上少見,其大膽的程度,以現代人的尺度,也不能不令人驚訝;例如第三十四卷「任君用恣樂深閨,楊太尉戲宮館客」裏的楊太尉姬妾成群輪流偷任生,放肆囂張的程度,已到肆無忌憚的地步,而凌氏描繪這些情節所用的文字,也淫穢到不忍卒睹;又如卷三十五「錯調情賈母詈女,誤告狀孫郎得妻」頭回一裏的陳氏,自己和姦夫私通,還要逼媳婦和姦夫同床,終於逼死了媳婦;頭回二裏敘述姑嫂二人不過是二八之齡,就已妄想偷漢子,弄得身敗名裂,自殞而死;其他篇目的偷情情節,所見的女子已不是楚楚可憐的接受者了。這些都可看出當時社會風氣的一般情況。
綜合以上所說,二刻拍案驚奇所保持的民風土俗、社會各階層的生活、官場內幕等,都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它所刻劃的民間思想觀念,又可做為牧民者治政的借鏡;論二刻拍案驚奇的價值,應當從這個觀點去尋求。
就寫作技巧看,二刻拍案驚奇雖然具有如前面所說的,話本小說先天體例上的缺陷,但有幾卷純粹描繪人事,和鬼神無關的篇目,卻也寫得相當不錯。就人物性格的刻劃來說,第二十六卷「懵教官愛女不受報,窮庠生助師得令終」裏高愚溪做了幾任官宦,只因沒有兒子,只有三個女兒,因此退休後把宦囊所有盡數分給三個女兒,指望能獲得女兒們的孝養,安渡晚年。開始時,女兒們看在父親的金錢上,也爭著巴結,但想不到三個女兒在分得家財後,態度漸漸冷淡,幾年之間,高愚溪已變成女兒們心目中的老厭物,他氣忿之餘,正想尋個自盡,正巧姪兒高文明遇見,收容了他,並盡心孝順他,高愚溪感慨萬千,愧無半點財物留給姪兒;正當此時,他以前一位學生李御史來找他,李御史幼年時家貧,讀書時繳不起拜見錢,多虧高愚溪幫忙,今日學成業就,身任御史,為感恩圖報,前來拜見。高愚溪後得李御史看覷,贈受很多程儀,府縣官仰承御史意旨,贈送尤豐,他把所得盡數送與姪兒,女兒們雖再度前來逢迎巴結,他已不再理睬了,後來善終於姪兒家。這篇小說把高愚溪的女兒們由熱衷變成冷淡的過程,寫得相當精彩、細膩;高愚溪老年的心境由期待變成失望,終至絕望意圖自盡的內心刻劃,都很傑出;末了李御史拜見高愚溪時,高愚溪受寵若驚的尷尬舉止,描繪得非常生動有趣。整篇小說不只主題發人深省,人物個性的描繪尤其突出,是相當成功的小說。就結構技巧講,第二十八卷「程朝奉單遇無頭婦,王通判雙雪不明冤」算是較好的一篇,該篇小說不只內容曲折,情節構造也很具匠心;內容敘述富人程朝奉飽暖生淫慾,看上賣酒的李方哥的妻子;李方哥由於窮苦,和妻子協議,答應借妻子給程朝奉一用,價錢為三十兩,想不到在完成約定的那晚,李方哥的妻子卻被人砍了頭,兇手為一敲梆子的游僧,因見李妻倚門盛妝而坐等人,乃起淫慾之心,李妻不從而砍下她的頭,掛在趙大門前樹上,趙大發現人頭,因為自己也做過虧心事,所以雖不知人頭來歷,也不敢聲張,暗中埋在後花園裏;後來東窗事發,官府尋線到趙大家起出人頭,人頭卻是男的。原來這個男頭是趙大所殺的仇家,和李妻一同埋在後花園裏,趙大帶領官府掘土的地點,是埋藏李妻頭的地方,想不到卻陰錯陽差的掘出了仇人的頭,趙大也因此成了殺人犯,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個案件破得太湊巧了,如果情節安排不好,很容易就令人有「無巧不成書」的感覺,但全文的情節發展相當自然,結局令讀者痛快淋漓,絲毫沒有牽強附會的感覺,尤其本文的善惡報應和其他各篇不同,其他各篇的善惡報應脫離不了鬼神關係,而此篇的報應則純由人事的偶然巧合,比較具有服人的力量。另外第十九卷「田舍翁時時經理,牧童兒夜夜尊榮」把言寄兒日間的放牛,和夜間的榮華富貴,雙管齊下一起寫出,牧牛的艱苦,和富貴的享受,成為鮮明的對比,這種交叉的寫作方式相當創新,現代小說和電影技術也有採用這種技巧的,這是很值得提出的一點。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二刻拍案驚奇(三版)的圖書 |
 |
$ 0 ~ 367 | 二刻拍案驚奇(三版)
作者:凌濛初##徐文助##繆天華 出版社:三民 出版日期:2020-05-22 規格:平裝 / 796 / 25K / 單色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二刻拍案驚奇(三版)
承襲《拍案驚奇》的風格,本書為凌濛初另一力作,收錄四十篇白話短篇小說,對於明代民風土俗、社會各階層生活、官場內幕等,都具有相當的研究價值,寫作技巧也有值得重視之處。本書正文綜合各種《二刻拍案驚奇》版本之優劣,取長補短,同時將艱僻的俗字、古字改為正體字,文後所附注釋簡明扼要,讀者可免去查考之煩,方便閱讀。
作者簡介:
作者:凌濛初字玄房,號初成,別號即空觀主人,明朝官員,文學家、小說家。著述甚豐,最大的貢獻是在通俗文學創作方面,其中以《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兩書影響最大。又與馮夢龍所著《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合稱「三言二拍」,是中國古典短篇小說的代表。
作者序
引 言 徐 文 助
在中國小說史上,平話小說的出現,是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年間;那時候民間有一行業叫「說話」,相等於現在的「說書」,專門以歷史和民間故事為題材,鋪演成曲折的情節,以吸引聽眾,從事這一行業的人稱為「說話人」。說話人說書時各有他們的底本,稱之為「話本」,話本的作者多為無名的「書會先生」。這些作者寫作話本的目的很單純,只是提供說話人說書的稿本而已,沒有類似一般文人創作的動機,所以他們的文筆非常粗率,情節很曲折,題材不脫離市民生活的領域,小說人物的行為、思想,也都是平民化的;最重要的一點,是...
在中國小說史上,平話小說的出現,是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年間;那時候民間有一行業叫「說話」,相等於現在的「說書」,專門以歷史和民間故事為題材,鋪演成曲折的情節,以吸引聽眾,從事這一行業的人稱為「說話人」。說話人說書時各有他們的底本,稱之為「話本」,話本的作者多為無名的「書會先生」。這些作者寫作話本的目的很單純,只是提供說話人說書的稿本而已,沒有類似一般文人創作的動機,所以他們的文筆非常粗率,情節很曲折,題材不脫離市民生活的領域,小說人物的行為、思想,也都是平民化的;最重要的一點,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 次
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一
卷之二 小道人一著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一九
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四七
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蹤 紅花場假鬼鬧 六九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九七
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一一九
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一三九
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一五七
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㑳梅香認合玉蟾蜍 一七三
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一九七
卷十一 滿少卿饑...
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一
卷之二 小道人一著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一九
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四七
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蹤 紅花場假鬼鬧 六九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九七
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一一九
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一三九
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一五七
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㑳梅香認合玉蟾蜍 一七三
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一九七
卷十一 滿少卿饑...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