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啟示錄》是一部六集紀錄片,由伊莎貝爾‧ 克拉克執導,她曾獲得遺產類電影大獎,國際歷史電影節銀鷹獎和最優秀紀錄片電影桂冠。幾乎可以說,她的精力,她的嚴格以及她對剪輯的理念幾乎都呈現在該片的品質和成功中。為何在2009 年上映該影片?因為2009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七十周年,值此周年之際,法國電視集團決定以高標準重新處理全部的畫面和色彩,使畫質更清晰。於是,伊莎貝爾‧克拉克獲得了集團的信任,著手拍攝該片。我為該片寫過影評,並且在影片中激動的發現了我的兩位導師—讓‧路易‧吉魯和亨利‧德‧圖熱納,他們是系列紀錄片《偉大的戰爭》(1967∼1974)的編劇,這部由13 部影片組成的系列劇充分見證了他們的才華和表達的力量,該片曾經在世界各地電視臺播出,甚至包括美國電視臺。因此,兩位原劇作家也創造了電視的歷史。
《偉大的戰爭》是對歷史影響資料搜尋和研究的結果,在同時期還沒有類似研究望其
項背,由此也構成了《啟示錄》的拍攝基礎。目前,我們想做到的是,超越衝突本身,杜絕原始戰爭故事。戰爭不是一個陣營對另一個陣營的勝利,而是全人類的失敗,是造就人類基本原則的失敗。我們所有人都討厭戰爭,但是我們卻表現了好鬥性。正因為有了來自不同陣營的黑白影像資料,我們將之製作成彩色畫面,這一技術今天絕對稱得上科幻。
我還想解釋一下長期以來被稱作「彩色化」的一個術語,它曾經和長膠捲的色彩斑斕聯繫在一起,這一術語起初給那些後來我認為是技術奇蹟的東西帶來壞影響。
我從導演助理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我目睹他們滿懷希望將電影拍成彩色,我也目睹當時如雷貫耳的大名,他們被不清晰的黑白畫面折磨得痛苦不堪。於是,技術人員重新發明了那著名的「黑與白的魔力」,因為他們別無他法。至於戰爭的拍攝,當時的黑白畫面簡直就意味著最根本資訊的失真:當時的戰鬥中,天是藍色的,地是褐色的,血是紅色的……我對此有所了解,沒錯,他們一邊為我展示電影,一邊跟我講述這些事情,是他們的畫面缺少色彩,而不是回憶。後來,我們發展出一種製作技術,稱為「著色」,我更喜歡這個新的命名。
我們發現,在著色過程中,最關鍵的不是技術人員,而是歷史學家,因為技術人員可以輕而易舉幫一套軍服著上任何綠色:這些綠色之間有數以百計的細微差別,其中只有一種顏色是對的。每一分鐘的著色,都需要幾天的研究,因為需要每一個畫面細節的色彩。由此,《啟示錄》的著色過程肯定是狂躁不安的,但技術確實是近年來最熠熠生輝的。其結果也令人震驚,畫面的光點和白點消失了,因為其他的技術將畫面還原到半個多世紀前剛剛拍攝時的狀態。
對於生活在影像檔案時代的我們來說,這樣的資訊技術和電視技術奇蹟—我找不到別的詞彙來形容—深深的震撼我們,對這種震撼,我毫不掩飾。
另一個奇蹟,就是有如此多的資料待我們去發現,我簡直不敢想像,多年以後,《啟示錄》還可以看到這麼多「陌生」的資料,這一點讓我深受震憾。我堅持自己喜歡「陌生」的這個詞語,而不是「原始」,並不是因為我看到以前從未示人的畫面,而是構成《啟示錄》的許多畫面對我們都是陌生的(本片沒有採訪,全部由真實紀錄影片構成)。
這些資料來自世界各地,需要好幾年時間才將它們分門別類,甚至還有許多畫面和情景重新展現,這些都是那麼的令人難以置信。
對我來說,從最初開始,這些影像資料的研究工作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充滿了神祕和寶藏,讓我為之著迷。
最後,我把發現意外驚喜當成了家常便飯,這樣的感覺可以傳染,克拉克也和我一樣,我們一起在看片過程中不斷發現愈來愈多「陌生」的畫面。
該書是紀錄片的全面反映,每一個章節都沿用紀錄片的標題,只是添加了少量評論。書中照片全部來自影片剪輯,這是為了保留書本的原汁原味,因為沒有任何攝影師拍過這些照片。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二次世界大戰啟示錄:還原歷史真相的圖書 |
 |
$ 308 | 二次世界大戰啟示錄:還原歷史真相
作者:Daniel Costelle、Isabelle Clarke / 譯者:王天星 出版社:漢宇國際文化出版 出版日期:2013-05-01 語言:繁體/中文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世界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二次世界大戰啟示錄:還原歷史真相
「這是一部真實的二次大戰史,目的是希望後代不要忘記戰爭的啟示。」
馬修‧卡索維茨(法國著名導演)
第二次世界大戰遠遠超出了恐怖的極限。《啟示錄》透過當時的戰鬥英雄、被迫加入戰爭地獄的普通士兵、不顧一切倖存下來的普通平民,以及不計其數的受害者和沒有名字的戰士……,即時向我們講述了戰爭的過程。這部關於勇氣和恐懼的歷史畫卷擴大了人們關於本次戰爭的視野。在歐洲戰場激烈對抗的同時,太平洋地區也正在上演戰爭的瘋狂。
本書飽含感情,以高度概括又不失歷史的細節,準確還原了戰爭衝突的全貌。
本書特色
本書照片是紀錄片《二次世界大戰啟示錄》的縮影,它們記錄了戰爭全程,其中不乏令人震驚的歷史時刻。所有照片均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博物館,它們的真實性不言而喻,許多圖片甚至是首次面世。
這是一本震撼的書籍,一段珍貴的資料,它的歷史和情感價值舉世無雙。
作者簡介:
Daniel Costelle、Isabelle Clarke
伊莎貝爾‧克拉克和達尼埃爾‧克斯泰爾共同完成了許多優秀的電視紀錄片作品,如《圍捕納粹》、《林白傳》、《越南戰爭》等。克斯泰爾還出版專著十幾部,其中《航空的歷史》獲法蘭西學院大獎。
作者序
《二次大戰啟示錄》是一部六集紀錄片,由伊莎貝爾‧ 克拉克執導,她曾獲得遺產類電影大獎,國際歷史電影節銀鷹獎和最優秀紀錄片電影桂冠。幾乎可以說,她的精力,她的嚴格以及她對剪輯的理念幾乎都呈現在該片的品質和成功中。為何在2009 年上映該影片?因為2009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七十周年,值此周年之際,法國電視集團決定以高標準重新處理全部的畫面和色彩,使畫質更清晰。於是,伊莎貝爾‧克拉克獲得了集團的信任,著手拍攝該片。我為該片寫過影評,並且在影片中激動的發現了我的兩位導師—讓‧路易‧吉魯和亨利‧德‧圖熱納,他們是系列...
»看全部
目錄
第一章 侵略
第二章 潰敗
第三章 震撼
第四章 激戰
第五章 反擊
第六章 煉獄
第二章 潰敗
第三章 震撼
第四章 激戰
第五章 反擊
第六章 煉獄
商品資料
- 作者: Daniel Costelle 、Isabelle Clarke 譯者: 王天星
- 出版社: 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5-01 ISBN/ISSN:978986228343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16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軍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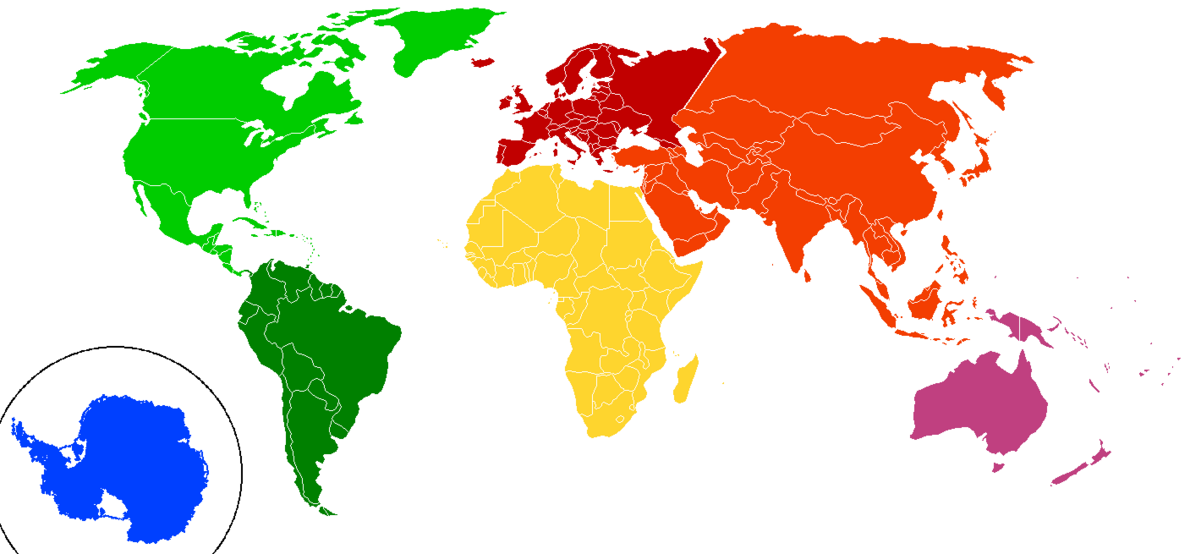 世界一詞在現代社會意為對所有事物的代稱。原本是佛教概念,由「世」和「界」組合而成的世界,即所謂由所有時間空間組成的萬事萬物。
世界一詞在現代社會意為對所有事物的代稱。原本是佛教概念,由「世」和「界」組合而成的世界,即所謂由所有時間空間組成的萬事萬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