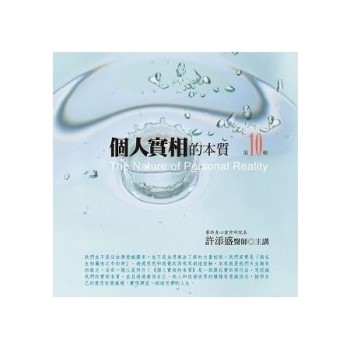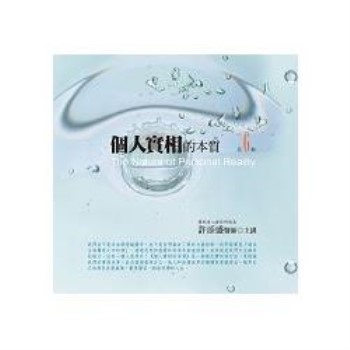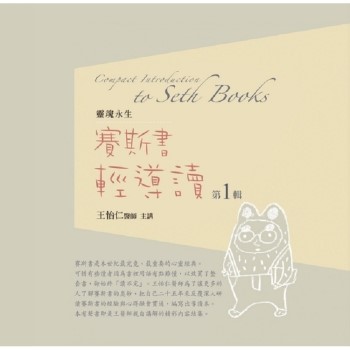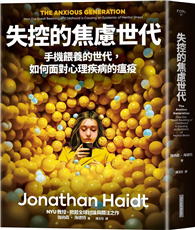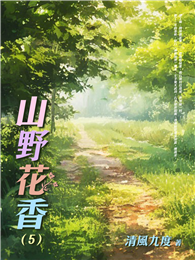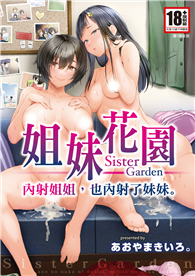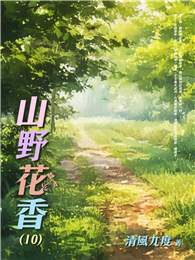他曾擁抱的理想與使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美國最大、最具影響力的雜誌王國共同創辦人亨利魯斯,同意接受他生平第一次的電視獨家採訪。當時魯斯六十八歲,兩年前甫自時代公司編集長一職退休。他在許多美國人心目中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許多人深受其雜誌的內容影響,崇拜他或偶遭其激惱,由於難得見到他拋頭露面,更對他充滿好奇。
採訪員艾瑞克.高德曼(Eric Goldman)是普林斯頓歷史學家,前幾年曾在詹森總統的白宮任職,此時主持NBC電視台的節目──「開放心胸」。高德曼是個有禮貌的訪談人,但絕不溫馴。他窮追不捨,追問環繞魯斯一生若干具爭議性的議題。魯斯所創辦的《時代》、《財星》、《生活》和《運動畫刊》等雜誌是「共和黨的雜誌」嗎?它們是否隱含著「保守派的觀點」?他「本身的態度和信念構成(雜誌的)內容」嗎?他有沒有「跨越界線」,推銷他特別敬佩、公開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和艾森豪?最重要的是,魯斯多次介入美國國際政策的辯論,是否代表「一種現代的美國帝國主義」?
訪談過程中,魯斯大部分時間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衣服略皺,領帶略歪,褲管因兩腳交疊而拉高。他神情憔悴,舉止顯得有點侷促。他講話散漫,經常話說一半就打住,隨後又從頭來過;回答問題前往往先兜圈子,有時講得極快,似乎想戰勝他童年時有過、壓力大時又會重現的口吃。儘管如此,他面對高德曼的尖銳提問卻毫無惱怒之意。高德曼說:「一般人覺得你有一種美國肩負著世界使命的觀點……(美國)要跨出去,把這些國家帶進和我們近似的文明當中。」魯斯在其一九四一年的著名文章──〈美國世紀〉當中確實是這麼說的。他說,當時的觀點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環境的影響,不過他並未駁斥高德曼的說法。他說,歐洲「不再能以過去一、兩百年的方式領導世界。領導的重擔將愈來愈落到美國肩上……這個領導的擔子,必然希望走向我們所知道的理想方向。」
當話題轉到亞洲,魯斯一生懸念、長久以來的委曲,變得更加明顯。高德曼認為,其他國家應該「走自己不同道路」,美國不應為共產中國而困惱,魯斯對此加以駁斥。儘管他承認美國在一九六六年已經拿共產中國莫可奈何,也無法推翻它,對於美國在之前力猶能及時不能「拯救」中國,他仍深感惋惜。他在一九四○年代曾說:「我認為我們有責任恢復蔣介石在戰前的地位。中國絕不是一定要走向共產主義。」此時,他依然無法「原諒美國政府」。
我們可以想像,或許能用另一種迥異的方式來訪問魯斯,聚焦在他的雜誌輝煌成就、他因而擁有的極大力量、他奮鬥捍衛的理念、他積累的巨大財富、他結交的全球人脈,甚至也可以談他和美國非常著名的某位女性之婚姻。數十年來,他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歷任總統刻意交好、敵人心懷畏懼的對象;他能把一介之士捧上天,也能把名流打倒在地。他想必感到挫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電視專訪,竟然環繞著糾纏他半輩子的種種批評。在他暮年,他最重視的是應是他的歷史功過──他曾經擁抱的理想與使命。
◆既反動,又進步
我和同世代的許多美國人一樣,跟著魯斯的雜誌一起成長,但又對它們所知不多。我的父母多年來持續閱讀《時代》,興趣固然不變,卻經常被觸怒。《生活》是我生平訂閱的第一份雜誌。不久之後,我和同一代許多青年一樣,成為《運動畫刊》的忠實讀者。當我開始進入歷史學家的專業領域時,我接觸到魯斯的〈美國世紀〉。在陰鬱反戰的一九七○年代,這篇文章對我而言,宛如之前更為陽剛、如今卻已過氣的美國年代。我不知道這樣的情緒何時才會恢復流行。
許多年之後,我動念寫一本亨利.魯斯的傳記,於是開始閱讀一系列魯斯年輕時期與傳教士父親之間的來往信函。魯斯從十歲開始,先後在中國和美國就讀寄宿學校,此後,他與家人聚少離多,鮮少碰面。他的家人關係親密,他透過持續多年、非比尋常的通信來維持和家人的親情,我也因而從中認識了這位了不起的青年。魯斯是個志向遠大的孩子,成年後依然雄心勃勃。他從幼年起就奮鬥不懈,一直很清楚自己有過人的才智,但從不自滿──無論在學校或在後半生皆是如此。這個男孩經常感覺孤單——幼年時在中國上英國寄宿學校,覺得遭受遺棄;在哈奇基斯(Hotchkiss)靠獎學金唸書時,覺得被邊緣化,不善於發展深刻的友誼和維持親密關係。縱然如此,至少在他年輕時期的家書裡,他展現了另一面的他——一位不怕承認自己的脆弱和失敗、努力向上並冀求成功的年輕人,同時也渴望自己能和父親一樣,成為受人尊敬、有美德的人。他一生奮勉精進,毫不懈怠。我沉浸於他早年生平的研究,開始了解他何以發展出日後的思想和事業。
魯斯並不是唯一一位日後成為重要公共人物的傳教士子弟。許多人和年輕的亨利一樣,也受到父母的志向或身教的影響,希望效法他們基於信仰、為改善他人福祉而做出重大犧牲的行為。許多傳教士子弟也和魯斯一樣,日後在外交、政治、學術、文學和其他領域有著出人頭地的傑出表現。關於魯斯的第一本傳記是史旺柏格(N.A. Swanberg)撰寫的《魯斯和他的帝國》(Luce and His Empire),出版於一九七二年,距魯斯謝世僅有五年。它反映了與魯斯同時代的許多人對他的強烈意見;它將魯斯描繪成一位雄辯家,至於他的雜誌,宣傳工具的色彩大過純做報導的新聞傳媒。多年前我在紐約的史傳德書店(Strand)找到一本史旺柏格的舊書,當中有位過去的讀者用鉛筆在蝴蝶頁上批注:「偉大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九真實。」
對史旺柏格、這位不知名的批註者,以及許多多年來不信任甚或蔑視魯斯的人而言,魯斯一生事業重要的是他的傲慢自大、他的教條主義,以及他反動、武斷的政治──這一切都反映在他雜誌的內容上。魯斯的確傲慢自大。他經常高唱教條,尤其是對他深切關注、又自認了解的議題,特別武斷。他的堅持己見早已聲名遠播,並且毫不猶豫地堅持將其意見反映在他的雜誌內容裡。關於中國、冷戰、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和共和黨等議題,他有自己一套深刻、不可動搖的意見,有時甚至使他因盲目而看不見周遭的事實。
然而,魯斯也有另外的一面。為他工作的人經常痛恨他的干預和命令,有些人甚至憤而求去,但他們幾乎都承認他是個聰明、有創意,甚至有吸引力的人。在他個人不那麼迷戀的許多議題上,魯斯寬容又好問,渴望汲取新資訊、新點子,甚至有雅量容忍挑戰和反駁。魯斯的雜誌如同其人,也有許多面向。它們既好爭辯,又寬大公平;既反動,又進步;既死守教條,又兼容並蓄;既僵固呆板,又具高度創意。它們是美國當代的偉大雜誌:缺陷固然極大,寬度、原創性和創意也極大。
◆多元的出版帝國
魯斯締造的出版帝國,是二十世紀中期美國欣欣向榮宏偉景象的一部分:全國大眾文化興起,主要為快速成長的新興中產階級服務。這個新文化有許多載具:連鎖報系、電影、無線電台,乃至電視。那些年也是全國性雜誌最旺盛的時期,而魯斯的雜誌是其中最成功、最暢銷、最具影響力的翹楚。魯斯遠遠超越美國出版業的任何人物;他賦予他的雜誌一種鮮明、合理、一貫的聲音──某種程度而言,他貫入了自己的聲音。這些雜誌各不相同,但全都反映魯斯所相信的一套普世皆然的價值和假設。他的一部分重大成就,就是能提供美國生活的印象,協助一個世代的讀者相信全國文化的迷人風華。
魯斯一九六七年逝世時,他本人或許並不知道他的雜誌已走上過時之路,未來將出現截然不同的風貌。《生活》於一九七二年壽終正寢;《時代》、《財星》甚至《運動畫刊》,慢慢不再是平民文化的代言人。它們必須成為對一個更多元、衝突更明顯的世界加以紀實的刊物——這個角色使它們的影響力與一致性大不如前(而且一度獲利今非昔比)。然而,魯斯聲名鼎赫的四十年期間,他從不認為他無法了解這個持續變動的世界;他堅信自己可以運用其雜誌來打造更美好的未來。

 共
共  雜誌是一種定期發行的連續出版物,介於書籍和報紙之間,其中包含各種文章內容。大多數的雜誌的收入來源都是廣告和讀者的購買。
雜誌是一種定期發行的連續出版物,介於書籍和報紙之間,其中包含各種文章內容。大多數的雜誌的收入來源都是廣告和讀者的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