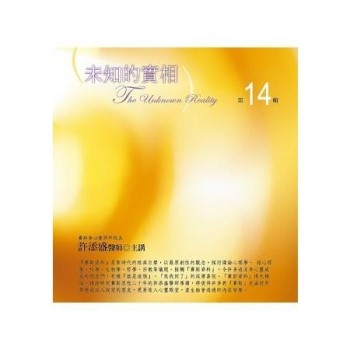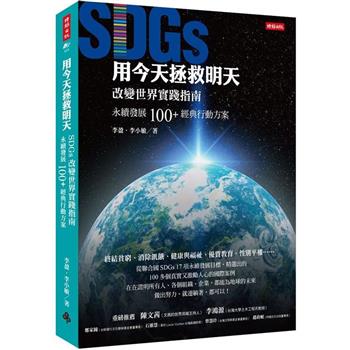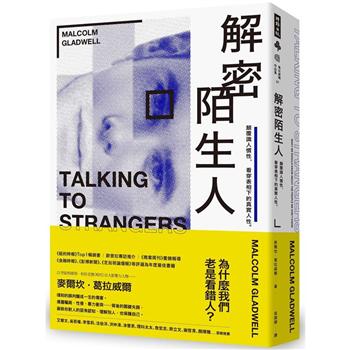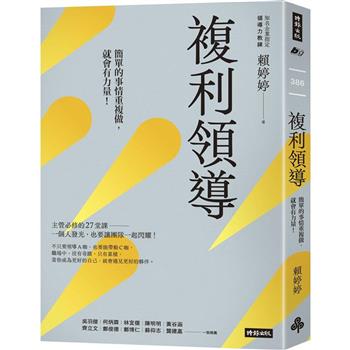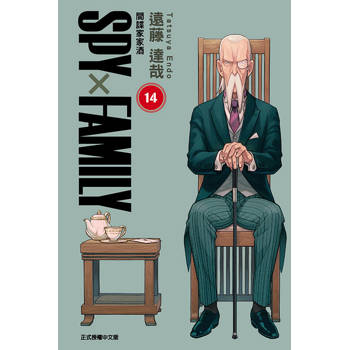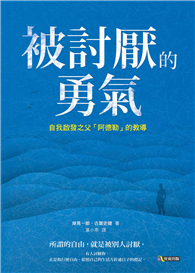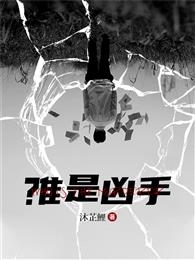※節錄自本書〈第九十二章〉、〈第九十三章〉、〈第九十四章〉:
二月一日,在篷窗之夢未醒之前,船隻早已解纜開航,來到Kusangai。此一帶地勢稍有變化,河流兩岸丘陵相逼,此後船隻行駛不久,丘陵延伸至河邊,形成一處處懸崖峭壁,有如堤壩綿長延續。地質為赤砂岩,高度在三十公尺左右,略有凹凸。
從船上望去,面臨河流之丘陵懸崖上,有兩個向岩中挖進之山洞引人注目。於是讓船夫停船靠岸,欲登岸調查山洞。詎料此洞比岸邊高出三十公尺左右,且在懸崖峭壁上,故只能仰望而無法靠近。余認為此山洞並非天然形成,而是人工開鑿而成,故無論如何亦須進洞調查,無奈缺乏繩索,未能達至目的。然從下望上看,一個洞穴入口為正方形,高寬為一兩公尺左右,洞中大小如何不得而知,據想像應比入口寬大;另一個洞穴入口為雜草遮蔽,無法看清。據不完全觀察,其形狀與日式短布襪使用之指甲形別扣相似,尺寸比前一個洞穴稍小,高約五尺,寬約四尺。兩洞穴位於丘陵最高處,二者相距約二十公尺。似乎過去人們可以攀爬到洞穴附近,然如今崖崩坡陡,根本無法接近。不過或許正因為坡陡,反倒有利於洞穴之保存。
(…中略…)
於前日首次發現蠻子洞之Kusangai一帶,河流兩岸皆赤砂岩丘陵,然今日所經之處,右岸為赤砂岩丘陵,而左岸則成為沖積平原。船隻漸漸駛向眉州城一帶時,右岸丘陵則變為小山丘,然地質仍為赤砂岩。在如此砂岩上挖墳掘墓,乃極為便利之事。於漢陽壩上游二十五里多之處,右岸曾出現丘陵,彼處有許多洞穴群,而於此一帶,則四處皆發現與日本相同之「橫穴」。只因水流湍急,船速極快,故於思索如何登岸調查時,船隻已如脫韁之馬,飛速通過,故余只能徒呼奈何,然根據記憶,在船上畫了草圖。此洞穴與昨日所見洞穴種類相同,根據此一事實可以判斷,在從成都一帶到此地之間,有許多蠻子洞分布。又據聞,明日將到達之嘉定一帶亦有此類洞穴。如此看來,此蠻子洞不僅分布於錦江沿岸,而且廣泛分布於岷江流域。總之,此一帶丘陵高度為五、六十公尺,錦江右岸丘陵上有許多蠻子洞。
今日從舟中望去,見到自湖南出發以來最為美麗優雅之山水景致。此景致與沅水上游深山幽谷、雲貴兩省童山曠野,以及彞族山區幾無人跡之熊徑鳥路大異其趣:河流穿行平原之中,河面斷無威脅船隻之奇礁怪石;有凝翠結黛之山巒,無逼仄壓迫之峻嶺;江山平遠開闊,風景優雅,若不在四川此地附近一帶,絕然看不到如此景致。
(…中略…)
嘉定府城附近赤砂岩小山有許多蠻子洞。此山稱Baxianton,並列三個蠻子洞。之後余棄舟上岸,登上距岸邊二、三百公尺遠之小山,見此處有眾多洞穴存在,或三個一組,或數個集合,其中亦包括方才在船上望見之洞穴。結束此處調查後,於下游二、三百公尺處又發現有洞穴存在。此處亦數洞集聚,然余一一精確調查。入口僅一處,然洞中分為部分,而且自成體系,結構相當複雜。凌雲古寺所在凌雲山,亦有許多此類洞穴。余於嘉定對岸親自調查之洞穴不下四、五十處。
就此類洞穴詳細調查之情況介紹從略,然於此應大致闡明,此類蠻子洞用於何事?何民族與此有關?其年代如何?若盡信中國人之說,則此洞穴乃「蠻族」所居窯洞遺跡無疑,而霍斯、巴伯之流亦似有模仿中國人鸚鵡學舌之嫌。余親赴現場,對洞穴做了觀察,不得不遺憾地認為,礙難接受以上結論。余就此有以下看法:第一,此洞穴形狀並非窯洞結構,而帶有墳塋性質;第二,其中有骨殖存在,亦有陶器等隨葬品;第三,有石棺痕跡;第四,內壁刻有文字,至遲可追溯至後漢時代前後;第五,與日本「橫穴」形制相同;第六,形制、雕刻皆中國樣式,其中刻有漢字;第七,模仿宮殿房舍式樣雕刻,刻有瓦形或人、鳥、魚等。基於以上理由,余認為該洞穴並非窯洞,而是墳塋,而且與日本「橫穴」非常相似。即使當地人偏聽偏信為「蠻人」窯洞遺跡,亦絕不可輕信。從洞穴形狀與其他方面來看,此洞穴並無半點「蠻人」留下之痕跡,而散發出純粹之漢人氣息,時間可溯及漢代,精確說來應屬後漢。故可認為,此類洞穴乃當時居於蜀地之漢人,經選擇此類地形挖掘洞穴,待自身過世後葬於此處之墳塋。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人類學上所見之西南中國(下)的圖書 |
 |
$ 387 | 人類學上所見之西南中國(下)
作者:鳥居龍藏 / 譯者:胡稹、賴菲菲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25-02-21 語言:繁體書  看圖書介紹 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人類學上所見之西南中國(下)
《人類學上所見之西南中國》是烏居龍藏於1902年至1903年間走訪中國西南邊區進行田野調查的見聞錄,與其於1907年出版的民族誌專書《苗族調查報告》不同,本書採用日記體紀行,並附十餘幅風俗人物照片或素描圖像。兩書在「鳥居人類學」的形成上具有重要意義,也是近代中國西南民族研究的開拓性文獻。
鳥居龍藏踏查的地區包括當時清帝國統治下的湖南、貴州、雲南、四川一帶,主要調查當地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傳統中國文獻中被稱為「三苗」、「蠻」、「玀猓」等的苗族、彝族,以及藏族等。書中舉凡當地的地理、物產、民族、語言、風俗到建築、考古、藝術等,都有詳細的記錄,這些記述,在百年後的今天看來,尤為珍費。
作者簡介:
作者/〔日〕鳥居龍藏(1870-1953)
日本近代文化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曾任東京大學副教授、國學院大學教授、上智大學文學部部長等職,為日本近代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先驅。曾深入走訪臺灣、滿蒙、華北、西南及朝鮮等地進行田野調查,蒐羅大量第一手資料,並留下重要記錄。著作有《鳥居龍藏全集》傳世。
中譯/胡稹
福建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退休教授,現任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學。
中譯/賴菲菲
福建師範大學協和學院外語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學。
※此書為【日本人中國邊疆紀行】系列之一
主編:張明杰(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特聘教授、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主編:袁向東(廣東技術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館館長,日本成城大學訪問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章節試閱
※節錄自本書〈第九十二章〉、〈第九十三章〉、〈第九十四章〉:
二月一日,在篷窗之夢未醒之前,船隻早已解纜開航,來到Kusangai。此一帶地勢稍有變化,河流兩岸丘陵相逼,此後船隻行駛不久,丘陵延伸至河邊,形成一處處懸崖峭壁,有如堤壩綿長延續。地質為赤砂岩,高度在三十公尺左右,略有凹凸。
從船上望去,面臨河流之丘陵懸崖上,有兩個向岩中挖進之山洞引人注目。於是讓船夫停船靠岸,欲登岸調查山洞。詎料此洞比岸邊高出三十公尺左右,且在懸崖峭壁上,故只能仰望而無法靠近。余認為此山洞並非天然形成,而是人工開鑿...
二月一日,在篷窗之夢未醒之前,船隻早已解纜開航,來到Kusangai。此一帶地勢稍有變化,河流兩岸丘陵相逼,此後船隻行駛不久,丘陵延伸至河邊,形成一處處懸崖峭壁,有如堤壩綿長延續。地質為赤砂岩,高度在三十公尺左右,略有凹凸。
從船上望去,面臨河流之丘陵懸崖上,有兩個向岩中挖進之山洞引人注目。於是讓船夫停船靠岸,欲登岸調查山洞。詎料此洞比岸邊高出三十公尺左右,且在懸崖峭壁上,故只能仰望而無法靠近。余認為此山洞並非天然形成,而是人工開鑿...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導讀〉 陳偉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人類學上所見之西南中國》是鳥居龍藏一九○二至一九○三年的中國西南調查紀行,以日記體撰寫,本書一方面是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紀行文本,同時也是一種探險旅行文學的文本。
●作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文本
此次田野調查,是鳥居龍藏受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派遣,前往當時清帝國統治下的湖南、貴州、雲南、四川一帶,調查當地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在傳統中國文獻中被稱為「三苗」、「蠻」、「夷」等的苗、玀猓(本譯本皆改為中國在一九○五年代實施民族識別之後的「彞族」)...
《人類學上所見之西南中國》是鳥居龍藏一九○二至一九○三年的中國西南調查紀行,以日記體撰寫,本書一方面是人類學田野研究的紀行文本,同時也是一種探險旅行文學的文本。
●作為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文本
此次田野調查,是鳥居龍藏受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派遣,前往當時清帝國統治下的湖南、貴州、雲南、四川一帶,調查當地的少數民族,特別是在傳統中國文獻中被稱為「三苗」、「蠻」、「夷」等的苗、玀猓(本譯本皆改為中國在一九○五年代實施民族識別之後的「彞族」)...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六十一章
半漢半彝居民
今日所經過地區之地勢與民眾
第六十二章
地形變,風俗變
金沙江司
第六十三章
橫渡金沙江途中風景
姜驛
第六十四章
白彝習俗與我國出土銅鐸圖紋之關係
途中景致
「阿拉衣」彝人與我國出土銅鐸圖紋風俗之
相似性
途中狀況
第六十五章
自綠水河至川心店
與「里斯人」相遇──到鳳山營
途中景致
第六十六章
自鳳山營至會理州城
會理州城
羅州山上黑彝
第六十七章
調查彝人
送別會與「忘年會」
第六十八章
...
半漢半彝居民
今日所經過地區之地勢與民眾
第六十二章
地形變,風俗變
金沙江司
第六十三章
橫渡金沙江途中風景
姜驛
第六十四章
白彝習俗與我國出土銅鐸圖紋之關係
途中景致
「阿拉衣」彝人與我國出土銅鐸圖紋風俗之
相似性
途中狀況
第六十五章
自綠水河至川心店
與「里斯人」相遇──到鳳山營
途中景致
第六十六章
自鳳山營至會理州城
會理州城
羅州山上黑彝
第六十七章
調查彝人
送別會與「忘年會」
第六十八章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