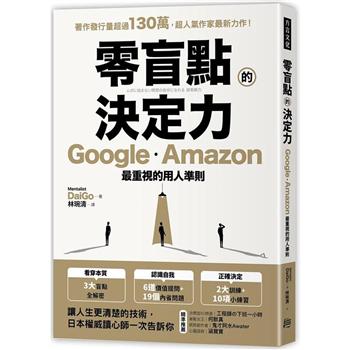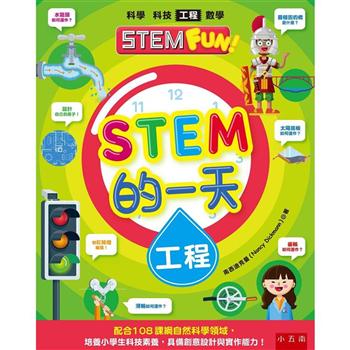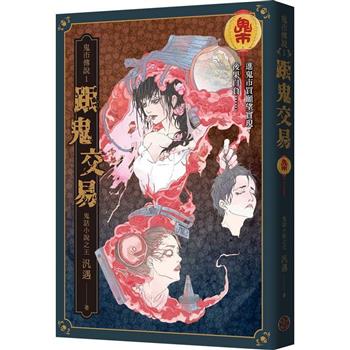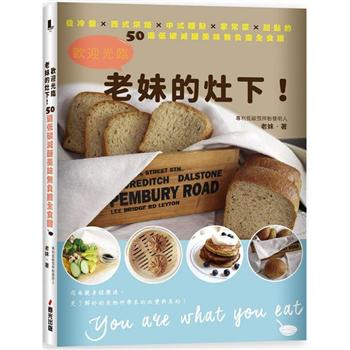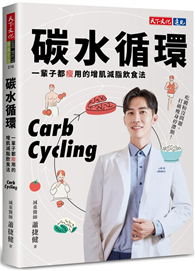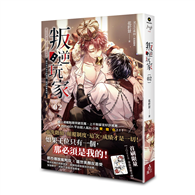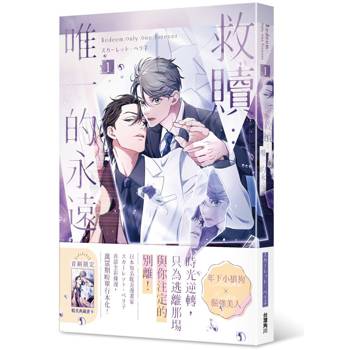《因信說話》是由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和救世傳播協會、遠東福音會、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聯合出品的大型書信朗讀視頻節目。透過眾多華語“好聲音”聲臨其境的演繹,眾多學者牧者的精彩分享,生動呈現宣教士等基督徒在生死疾病、患難傷痛等各種人生際遇中的生命態度以及公共關懷。
本書是節目編導張強歷時兩年有餘,在新冠疫情期間,重新梳理和記述了八位宣教士、基督徒文化人士,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其中有殉道者安麗莎的痛與愛,有蘇慧廉的宣教事業對當下社會與福音的啟發,有戴德生與「揚州教案」的故事,也有路易斯、梵谷、張曉風等的文化關切……作者以真實細膩的文筆,穿越歷史與當下,使我們看見掌管歷史的那一位,在今天這個充滿不確定性且撕裂的世界中,仍舊向我們說話。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今天他仍舊說話:不能遺忘的〝信〞與記〝疫〞的圖書 |
 |
$ 221 ~ 252 | 今天他仍舊說話:不能遺忘的〝信〞與記〝疫〞
作者:張強 出版社: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出版日期:2023-10-02 語言:繁體書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今天他仍舊說話:不能遺忘的〝信〞與記〝疫〞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強
科技媒體人,社會創新顧問,傳播影響力分析平台DataWeco 創始人。曾創辦《新知客》月刊、任職7GTV,關注社交媒體上的社群共識,參與網絡宣教與新媒體福音。觀察評論文章收錄於《用愛心說誠實話》(2021);圖書編輯《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2022);圖書譯著《人類起源與演化》( 即將出版);書信朗讀節目編導《因信說話》(24 集,2020-2021);研究報告「2017/2018微信基督徒影響力數據評價與研究系列」。
張強
科技媒體人,社會創新顧問,傳播影響力分析平台DataWeco 創始人。曾創辦《新知客》月刊、任職7GTV,關注社交媒體上的社群共識,參與網絡宣教與新媒體福音。觀察評論文章收錄於《用愛心說誠實話》(2021);圖書編輯《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2022);圖書譯著《人類起源與演化》( 即將出版);書信朗讀節目編導《因信說話》(24 集,2020-2021);研究報告「2017/2018微信基督徒影響力數據評價與研究系列」。
目錄
序 生死契闊,誰是你我的安慰?/安平
推薦序 從一封信開始……/林治平
推薦序 撥開幽暗,注目日光之上的永恆/施瑋
前言 超越生死的靈魂拷問/張強
第一章 安麗莎:殉道母子
第二章 蘇慧廉:從宣教到文化
第三章 戴德生:心繫中國,心繫基督
第四章 台約爾:活字為永道
第五章 路易斯:來自納尼亞的書信
第六章 梵谷:挖煤人的牧師
第七章 潘霍華:捲入刺殺密謀的神學家
第八章 張曉風:山水中國仍需宗教精神
附錄
創始故事/張強
【故事篇】祁家豁子的深夜咖啡
【心得篇】節目製作緣起與幕後花絮
黃綺珊專訪:因信而歌,今天你仍舊說話/安平、黃綺珊
因著信,內心的「狂熱」再次被點燃/突兀的捍衛者、大海
因著信,她留給我們一份特殊的抗疫日記/Jessie
從播音到錄影,經歷祂的預備和供應/方華
特別鳴謝
推薦序 從一封信開始……/林治平
推薦序 撥開幽暗,注目日光之上的永恆/施瑋
前言 超越生死的靈魂拷問/張強
第一章 安麗莎:殉道母子
第二章 蘇慧廉:從宣教到文化
第三章 戴德生:心繫中國,心繫基督
第四章 台約爾:活字為永道
第五章 路易斯:來自納尼亞的書信
第六章 梵谷:挖煤人的牧師
第七章 潘霍華:捲入刺殺密謀的神學家
第八章 張曉風:山水中國仍需宗教精神
附錄
創始故事/張強
【故事篇】祁家豁子的深夜咖啡
【心得篇】節目製作緣起與幕後花絮
黃綺珊專訪:因信而歌,今天你仍舊說話/安平、黃綺珊
因著信,內心的「狂熱」再次被點燃/突兀的捍衛者、大海
因著信,她留給我們一份特殊的抗疫日記/Jessie
從播音到錄影,經歷祂的預備和供應/方華
特別鳴謝
序
序
生死契闊,誰是你我的安慰?
安平(普世佳音中文事工主任)
憂傷的苦杯
2019年聖誕期間,《因信說話》節目開播時,並沒有想到它會和肆虐的新冠疫情進入同一個節奏。和大家一樣,那時我們對這個即將給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帶來恐慌和傷痛的大流行病一無所知。
我們選擇梵谷開篇,主要因為這是一封聖誕家書,我們關注的是藝術,是一個殘破的生命如何用自己的真實來回應上帝的美善。同樣,選擇潘霍華獄中情書在新年前播出,主要是因為他的信本來就是一封新年寄語。未曾想「囚禁中」,居然成了接下來幾年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
在我們吟唱他那首《所有美善力量》的時候,我們常常想到的是前半段中神的庇護與安慰,現在回頭看,方能感受後半段歌詞的深沉含義:
主啊!賜給我們那救恩
就是你為我們不安心靈所預備的
若你遞給我們憂傷的苦杯
裏面裝滿我們要承受的愁苦
讓我們毫不顫抖地感恩接過那杯
從你公義、慈愛的手中
愛裏沒有懼怕
然後是蘇慧廉。當他在溫州勤勉耕耘20年,走上人生事奉高峰的時候,選擇就任山西大學校長,從事似乎更為間接的宣教之路。要讓福音傳開,需要先「除草」,扔掉「亂石」,預備「好土」。「山西就是庚子教難中犧牲傳教士最多的一個省份。不過這種局面,現在已被李提摩太博士改變。他認為恐怖事件源於人們的無知,尤其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士大夫階層的無知。」
接下來當然就是戴德生。1870年,戴德生經歷了人生巨大的悲痛。他的兩個小兒子相繼去世以後,愛妻瑪莉亞也因感染霍亂而離世。他在巨大的傷痛中寫信給自己的母親:「神知道要結的果子,有悲傷也有歡樂。神藉著他慈父一般的手安排萬事。我在這樣的信息中得到安息:祂確實看顧,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大家對戴德生耳熟能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岳父台約爾。其實他也是一名宣教士。其信仰的虔敬、對中國的熱愛讓人敬佩,他對宣教乃至中國現代文明的貢獻都非常巨大。差不多10年前,我讀到《雖至於死——台約爾傳》,非常感動,特別是讀到台約爾病危中寫給妻兒的信,更讓我期待未來有一天可以用最適合的藝術形式將其再現。
2019年6月,我受邀在馬六甲舉辦的一個宣教營會分享專題。剛好戴德生的第五代孫——戴繼宗牧師擔任大會主題講員,我便與他分享《因信說話》節目的構思,並邀請他來讀戴德生和台約爾的信,他欣然應允。2020年1月23日,也正是《台約爾:身染熱病,在愛裡沒有懼怕》一集播出的第二天,因新冠疫情,武漢封城。
馬其頓的呼聲
4月8日,武漢解封。從聖誕節到復活節,第一季也剛好播完。隨著疫情的緩解,北京也放鬆了管控,趁這段時間,我們拍攝錄製了主題曲《今天他仍舊說話》。錄製過程也算是不得已的創舉。演唱者黃綺珊和導演張強在北京的錄音棚,作曲周德威在台北的工作室,我作為詞作者則在密西根的家中,中美台三地Zoom 在線溝通,及時修改。之後黃綺珊姐妹朗讀了山西庚子教難中被殺的安麗莎師母寫給親人們的遺言,開啟了第二季的製作。到2020 年感恩節,我們用盡了疫情前可以自由旅行時所拍攝的素材,製作並播出了兩季24集正片,並加2集特別節目。
最後一集是張曉風老師於20世紀80年代寫給青年讀者的信,講到中國人是何等需要奉獻和投入的精神,也剛好呼應了第一集梵谷的聖誕家書。因為梵谷這封信的核心其實是「馬其頓的呼聲」:「那個呼求的馬其頓人,也和他們一樣是有著悲傷、痛苦和疲勞的工人,沒有榮耀的樣子,卻有一個不朽的靈魂。這個靈魂需要神的靈糧,即神的話語,來承受永遠的生命!」這豈不也正是疫情籠罩下的民眾的呼聲?!
今天他仍舊說話
轉眼一年過去,疫情在全世界範圍內起起伏伏,隨著疫苗的廣泛接種,終於露出結束的曙光。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2022年3月28日,上海竟突然宣布封城。張強剛好出差在滬,也被困在其中。開始以為只需幾日便可離開,未曾想越來越遙遙無期,他的心情難免消沉低落。有一天通話,我鼓勵他不防趁此時間,整理一下《因信說話》節目的文字檔案,也是難得的資料和記錄。相信書寫也是一種抒發和醫治。於是,就有了這本《今天他仍舊說話》。
這是一本導演手札,回顧了他拍攝《因信說話》期間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和幕後花絮;這是一個電影劇本,蒙太奇地將魔幻的現實和真實的歷史無縫對接,交織疊印;這也是他的抗疫日記,讓我們看到那如雲彩般的見證如何幫助他勝過封城帶來的絕望和恐懼,用意識流的筆法展現了一種超越時間和地域,不屬於這個世界卻存在於其中的信心、盼望和愛。
死生契闊,你是我唯一的安慰!
非常感恩,張強作為導演可以將縈繞我心頭多年的一個想法落地並美好地呈現,也很感恩他可以將這些繁雜的文檔整理成書,既是珍貴的記錄,更是有價值的獨立存在。更為他驕傲的是,他能夠以靜水深流的動人筆觸,勇敢而坦誠地書寫,從而成為記錄這個時代的為數不多甚至屈指可數的疫情文學代表作。
感謝上帝的帶領,祂才是《因信說話》節目的製片人和導演,而「我們則成了一台戲,演給天使和世人觀看。」(參《哥林多前書》4:9)這台戲就是關於生、關於死、關於生死之間你我的每一個抉擇。
我個人很喜歡《海德堡要理問答》。它不僅強調真理和教義,也強調在心靈和生活上對真理和教義的體證和實踐,被稱為「安慰之書」。選擇「安慰」作為整本要理問答的核心主題,是為了應對當時教會普遍的屬靈焦慮。在戰事、饑荒、災難、瘟疫綿綿不斷的時代,《海德堡要理問答》宣告,安慰是因為我們屬於那位「保守我……叫萬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的基督,是因為我們屬於那位「藉聖靈使我有永生確信」的基督。
與其說《因信說話》節目和張強這本《今天他仍舊說話》的主題是「生死」,倒不如說更是「安慰」。我一直想把《海德堡要理問答》以詩歌體重譯,但發現自不量力,到今天只完成了四五首。現藉此文把第一問的譯稿和大家分享,也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身我靈,或死或生,不再屬我,皆歸基督。
他以寶血,償我罪債,賜我自由,脫離凶惡。
身體髮膚,他必看顧,萬事效力,成全救贖。
因我屬他,更得永生,盡心盡意,為主而活。
死生契闊,你是我唯一的安慰!
寫於2020年4月,修改定稿於2023年5月
推薦序
從一封信開始……
林治平(財團法人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董事長)
「信」的意義:搭建溝通橋樑
各位朋友,你能否告訴我,人世間什麼時候有「信」這玩意的存在呢?人與人之間彼此接觸溝通、認識瞭解,「信」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這個字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媒介溝通角色。人與人相交,人言為信。既然是「人言」為「信」,那麼什麼是「人言」?先有「人」言、只有「人」言,而後才有「信」。
由此可見,「信」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動靜之間,「信」所牽動指涉的,自然關係重大,影響人際的溝通瞭解,建構可見或不可見的歷史網絡。「信」讓寫的人一訴衷腸、盡吐心底隱密;也讓看「信」的人深入執筆者的心靈秘境,了悟真實。「信」在人與人之間搭建起的溝通瞭解的橋樑,功莫大焉。
「信」的消亡:現代文化的奢侈品
這本書的雛形就是從一封封或長或短的信件中摘錄編輯而來。這些年來,幾位從事文字廣播宣教工作的好友同工們,面對網絡資訊的快速發展、AI 人工智能科技的突飛猛進,尤其是後現代主義學者憂心忡忡,哀歎「人不見了」(dehumanization)的「去人化」雜沓混亂的腳步,聲勢洶湧地攪亂了傳統以人為本的文化社會。「人」既不存,人言何在?人活得越來越不像人,我們到哪裡去找「信」呢?
幾年前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跟老友安平幽幽地談到當前現代人所面臨的文化社會中「人不見了」的危機。我們每天伏在不同的電子化資訊工具前,穿梭往返在不同的資訊網絡中,忙得沒有時間跟一機之隔的同事朋友們打一聲招呼,喊一聲哈囉!在這一片嘈雜忙亂的混亂中,我們看不到「人」、自然也聽不到「人言」。至於「人言為信」的「信」,更成為現代人的奢侈品。想要看到、聽到現代忠臣烈士慷慨陳詞、視死如歸的豪情壯志,幾乎不可能;推窗望月、面迎清風,牽扯出來的似乎也只剩多年來一直埋在心靈深處的一絲悸動;使人不由自己地任憑內心種種思念懷想,意圖飛越窗欞、跨山履海與萬里外的至親密友,把酒言歡,互道心聲。但只在一瞬間,我們會慨然發現,心手所觸及的仍然是冷冰冰的電子媒體。
不知怎麼搞的,面對取代本我的資訊材料,只那麼一瞬間,便把找不到本我的自我,捆鎖在「我是誰?」的失落捆鎖中,哀哀呼叫。人不見了!「人言」銷聲匿跡了。「信」何在?「信」早已成為所謂現代文明中的奢侈品。
新冠三年,不可能的工作
緊接著,在人類群體逐漸失去「信」的惆悵震驚中,新冠病毒(Covid-19)更在世人毫無瞭解準備的情況下,蔓延世界各地。面對來勢洶洶、不可捉摸的新冠疫情,驕傲的現代人只好乖乖地被隔離起來。即使有千萬個不甘心、不情願,也只好被關鎖在隔離空間中。在這個普世性的災難中,人際關係越來越疏遠淡薄,但透過互聯網的連結,也許可以彌補搶救當前教會拓展宣教工作的瓶頸,為教會宣教工作另闢一條蹊徑。
首先我們決定,這件工作應由幾家對文字視聽、影音佈道、網絡宣教工作有心整合嘗試的機構共同合作、群策群力,以抵於成。於是在安平牧師奔走聯繫之下,徵得遠東廣播公司、救世傳播協會、宇宙光等機構和安平牧師所帶領的普世佳音同工們共同合作,分別從文字資料收集、聲音錄製剪輯、影像錄影後製,正式展開試作及籌備工作。
經過多方討論尋覓,先從已有的信函文獻中,挑出寫信者生命歷程中最想與收信者分享的內心故事。這些發自內心深處的呼喊或傾訴,或如長江大海,澎湃洶湧;或如掬面春風,沈穩溫柔,細數生命情懷,都是書寫者在面臨不的生命歷程時,心靈深處隱藏的真實對話。幾經討論,我們選定了多位不同生命背景的人,將他們在不同的生命歷程情景中所寫的信作為這本書的主軸,開始了編輯與整合的工作。
選定了書信內容之後,誰來朗讀這些信件也花了大家不少心思。我們希望朗誦者最好跟寫信者有某種親密關係,如血緣關係、事工聯結、研究工作等。確定了朗誦者之後,又花了許多心思和時間尋找寫信人的解說者,並由安平親自出馬,主持一個談話性節目,邀請學者專家、牧長同工共同參與。最後由後製單位透過不同的網絡渠道推廣行銷至各相關機構、教會及社群。
如今,這項整合各相關機構,各取所長、互補短缺的工作,總算跨出了第一步。回想如飛而逝的三年,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我們這群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渺小有限的神的僕人,竟然在同一個異象的驅使下,初步完成了這項似乎不可能的工作。回頭數算,新冠病毒的肆虐仍然存在,媒體功能的日新月異、迅速變遷,更是時刻干擾攪亂了我們宣教的前進步伐。但神的工作從來不會因為這些因素而受到攔阻,祂必親自堅立和帶領合祂心意的事工。
信:傳播媒介的起點
請為我們禱告!為普天下從事文字影音宣教工作的人禱告!讓我們無論在任何困難變幻之中,仍然能從心靈深處,平靜坦然地寫下一封又一封叩擊人心的生命信函。
寫一封信,似乎是小事一樁,但無論媒體資訊如何發達,「信」永遠是傳播媒介的起點。作為一個投身福音傳播工作已達50 年的宇宙光同工,請容許我問一聲:「親愛的同工朋友們!在這個資訊時代密鑼緊鼓敲響警鐘的時候,為著福音的緣故,你什麼時候會寄出你的第一封生命信函?」
推薦序
撥開幽暗,注目日光之上的永恒
施瑋(國際靈性文學藝術中心主席,靈性文藝出版社社長)
收到張強《今天他仍舊說話》的書稿,正是我連續八年寫作,終於完成中國教會歷史文學三部曲《叛教者》《獻祭者》《殉道者》,共計150 萬字的書寫。完成重負之時,卻也深感身心靈疲乏、倦怠。十年前,因著上帝的呼召,我開始研究並寫作中國教會歷史中的人和事,並呼喚同路人一起來書寫「銘賢書系」。我曾經立志「用筆揭開遮蔽的歷史,用靈喚醒蒙塵的忠魂」,今天卻深深地感到,十年來,正是這些蒙塵的忠魂,這些生命的種子,這些被遮蔽的見證,在不斷喚醒我常常會在世俗世界中昏昏欲睡、倦怠無力的心靈。
歷史,從上帝的角度看充滿信心和真理的榮耀;從人的角度看卻瀰漫著無盡的悲哀、無奈,甚至是絕望的憤怒。書寫歷史、閱讀歷史,我們是被榮耀照亮?還是陷入幽暗、絕望?如果我們不迴避真實,不停止思索,那麼這兩種狀態也許是並存的、交替的、掙扎的,甚至也是相映襯的。當我閱讀《今天他仍舊說話》時,這幾年我參與及聆聽大型書信朗讀節目《因信說話》的過程及情緒,都穿越目前灰朦朦的濃霧,光一般射入內心。那些遙遠時代的書信再一次走進我的書房;那些溫暖的聲音再一次對我的心娓娓訴說;那些在渾濁歷史中星晨般閃亮的生命,也再一次出現在漆黑的夜空……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這三年中,新冠疫情、美國大選、俄烏戰爭、台海局勢……索鏈囚女、偶像「塌房」、上海封城、物價飛漲……從網絡到實體、從居住國到祖國,從平民生活到全球格局,世界彷彿進入了一個最為荒誕、燥動、無序、無望的時代。當我突然從書寫世界回到現實後,發現很多人都和我此刻一樣,陷入困惑,感覺無力。
張強的這部書將他自己在這三年中從四處奔波到與封控隔離的現實生活,與他所拍攝和講述的人物交替穿插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一部風格獨特的散文隨筆集,也是一部《因信說話》節目製作編輯手記。他讓我們這些讀者不斷地進出一道「門」,門這邊是眼見的現實,門那邊是另一個時空裡的現實,但更是那眼未見的「確據」、所信之事的「實底」。
這些真實的歷史書信,將寫信者生命中的信仰之光呈現出來,指向日光之上的永恆。並且,藉著讀信、解信,製作者同被聖靈所感,靈與靈的唱合與傳遞,讓日光之上的永恆臨到囚禁在日光之下的人們。當我們看1900 年庚子教難中殉道的安麗莎;當我們瞭解在中國拓展福音和社會關懷的蘇慧廉;當我們感佩全然奉獻,在中國宣教一生的戴德生和台約爾;當我們走入大文豪路易斯的真實生活;當我們闖進天才畫家梵谷追求信仰與純粹的精神世界;當我們閱讀潘霍華從神學家到卷入參與刺殺計劃……
我們看到他們所處的時代同樣充滿戰爭、瘟疫;他們的生活同樣有缺乏與病痛;他們的精神同樣遭遇逼迫、陷於幽暗。然而,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困境中的信仰者們,以樸實無華、平平淡淡的家信,為今天的我們撥開「眼所見」的幽暗與迷霧,讓我們看見「眼未見」的日光之上的永恆,看見信仰者在日光之下可以走的十架之路。這條十字架的路,有逼迫、有血淚、有嘲笑、有軟弱、有犧牲、也有跌倒,但它是我們主耶穌走過的路。因著與祂同行,先行者們已經成為了如雲的見證人,今天的我們,也可以成為他們中的一位。當代著名基督徒作家張曉風寫給青年的書信,彷彿正是中國基督徒在當下對日光之上永恆的信心回應與傳承,是傳道者的生命種子結出的子粒。
基督教救贖的真理是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穌,不僅僅是一套道理,更是一群人,一群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的人,一群基督耶穌跟隨者的生命見證。因著信,他們依舊說話,你聽見了嗎?
2022 年10 月11 日寫於洛杉磯東谷書屋
生死契闊,誰是你我的安慰?
安平(普世佳音中文事工主任)
憂傷的苦杯
2019年聖誕期間,《因信說話》節目開播時,並沒有想到它會和肆虐的新冠疫情進入同一個節奏。和大家一樣,那時我們對這個即將給全中國乃至全世界人民帶來恐慌和傷痛的大流行病一無所知。
我們選擇梵谷開篇,主要因為這是一封聖誕家書,我們關注的是藝術,是一個殘破的生命如何用自己的真實來回應上帝的美善。同樣,選擇潘霍華獄中情書在新年前播出,主要是因為他的信本來就是一封新年寄語。未曾想「囚禁中」,居然成了接下來幾年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態。
在我們吟唱他那首《所有美善力量》的時候,我們常常想到的是前半段中神的庇護與安慰,現在回頭看,方能感受後半段歌詞的深沉含義:
主啊!賜給我們那救恩
就是你為我們不安心靈所預備的
若你遞給我們憂傷的苦杯
裏面裝滿我們要承受的愁苦
讓我們毫不顫抖地感恩接過那杯
從你公義、慈愛的手中
愛裏沒有懼怕
然後是蘇慧廉。當他在溫州勤勉耕耘20年,走上人生事奉高峰的時候,選擇就任山西大學校長,從事似乎更為間接的宣教之路。要讓福音傳開,需要先「除草」,扔掉「亂石」,預備「好土」。「山西就是庚子教難中犧牲傳教士最多的一個省份。不過這種局面,現在已被李提摩太博士改變。他認為恐怖事件源於人們的無知,尤其是那些受過教育的士大夫階層的無知。」
接下來當然就是戴德生。1870年,戴德生經歷了人生巨大的悲痛。他的兩個小兒子相繼去世以後,愛妻瑪莉亞也因感染霍亂而離世。他在巨大的傷痛中寫信給自己的母親:「神知道要結的果子,有悲傷也有歡樂。神藉著他慈父一般的手安排萬事。我在這樣的信息中得到安息:祂確實看顧,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大家對戴德生耳熟能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岳父台約爾。其實他也是一名宣教士。其信仰的虔敬、對中國的熱愛讓人敬佩,他對宣教乃至中國現代文明的貢獻都非常巨大。差不多10年前,我讀到《雖至於死——台約爾傳》,非常感動,特別是讀到台約爾病危中寫給妻兒的信,更讓我期待未來有一天可以用最適合的藝術形式將其再現。
2019年6月,我受邀在馬六甲舉辦的一個宣教營會分享專題。剛好戴德生的第五代孫——戴繼宗牧師擔任大會主題講員,我便與他分享《因信說話》節目的構思,並邀請他來讀戴德生和台約爾的信,他欣然應允。2020年1月23日,也正是《台約爾:身染熱病,在愛裡沒有懼怕》一集播出的第二天,因新冠疫情,武漢封城。
馬其頓的呼聲
4月8日,武漢解封。從聖誕節到復活節,第一季也剛好播完。隨著疫情的緩解,北京也放鬆了管控,趁這段時間,我們拍攝錄製了主題曲《今天他仍舊說話》。錄製過程也算是不得已的創舉。演唱者黃綺珊和導演張強在北京的錄音棚,作曲周德威在台北的工作室,我作為詞作者則在密西根的家中,中美台三地Zoom 在線溝通,及時修改。之後黃綺珊姐妹朗讀了山西庚子教難中被殺的安麗莎師母寫給親人們的遺言,開啟了第二季的製作。到2020 年感恩節,我們用盡了疫情前可以自由旅行時所拍攝的素材,製作並播出了兩季24集正片,並加2集特別節目。
最後一集是張曉風老師於20世紀80年代寫給青年讀者的信,講到中國人是何等需要奉獻和投入的精神,也剛好呼應了第一集梵谷的聖誕家書。因為梵谷這封信的核心其實是「馬其頓的呼聲」:「那個呼求的馬其頓人,也和他們一樣是有著悲傷、痛苦和疲勞的工人,沒有榮耀的樣子,卻有一個不朽的靈魂。這個靈魂需要神的靈糧,即神的話語,來承受永遠的生命!」這豈不也正是疫情籠罩下的民眾的呼聲?!
今天他仍舊說話
轉眼一年過去,疫情在全世界範圍內起起伏伏,隨著疫苗的廣泛接種,終於露出結束的曙光。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是,2022年3月28日,上海竟突然宣布封城。張強剛好出差在滬,也被困在其中。開始以為只需幾日便可離開,未曾想越來越遙遙無期,他的心情難免消沉低落。有一天通話,我鼓勵他不防趁此時間,整理一下《因信說話》節目的文字檔案,也是難得的資料和記錄。相信書寫也是一種抒發和醫治。於是,就有了這本《今天他仍舊說話》。
這是一本導演手札,回顧了他拍攝《因信說話》期間不為人知的心路歷程和幕後花絮;這是一個電影劇本,蒙太奇地將魔幻的現實和真實的歷史無縫對接,交織疊印;這也是他的抗疫日記,讓我們看到那如雲彩般的見證如何幫助他勝過封城帶來的絕望和恐懼,用意識流的筆法展現了一種超越時間和地域,不屬於這個世界卻存在於其中的信心、盼望和愛。
死生契闊,你是我唯一的安慰!
非常感恩,張強作為導演可以將縈繞我心頭多年的一個想法落地並美好地呈現,也很感恩他可以將這些繁雜的文檔整理成書,既是珍貴的記錄,更是有價值的獨立存在。更為他驕傲的是,他能夠以靜水深流的動人筆觸,勇敢而坦誠地書寫,從而成為記錄這個時代的為數不多甚至屈指可數的疫情文學代表作。
感謝上帝的帶領,祂才是《因信說話》節目的製片人和導演,而「我們則成了一台戲,演給天使和世人觀看。」(參《哥林多前書》4:9)這台戲就是關於生、關於死、關於生死之間你我的每一個抉擇。
我個人很喜歡《海德堡要理問答》。它不僅強調真理和教義,也強調在心靈和生活上對真理和教義的體證和實踐,被稱為「安慰之書」。選擇「安慰」作為整本要理問答的核心主題,是為了應對當時教會普遍的屬靈焦慮。在戰事、饑荒、災難、瘟疫綿綿不斷的時代,《海德堡要理問答》宣告,安慰是因為我們屬於那位「保守我……叫萬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的基督,是因為我們屬於那位「藉聖靈使我有永生確信」的基督。
與其說《因信說話》節目和張強這本《今天他仍舊說話》的主題是「生死」,倒不如說更是「安慰」。我一直想把《海德堡要理問答》以詩歌體重譯,但發現自不量力,到今天只完成了四五首。現藉此文把第一問的譯稿和大家分享,也作為本文的結束。
我身我靈,或死或生,不再屬我,皆歸基督。
他以寶血,償我罪債,賜我自由,脫離凶惡。
身體髮膚,他必看顧,萬事效力,成全救贖。
因我屬他,更得永生,盡心盡意,為主而活。
死生契闊,你是我唯一的安慰!
寫於2020年4月,修改定稿於2023年5月
推薦序
從一封信開始……
林治平(財團法人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董事長)
「信」的意義:搭建溝通橋樑
各位朋友,你能否告訴我,人世間什麼時候有「信」這玩意的存在呢?人與人之間彼此接觸溝通、認識瞭解,「信」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這個字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媒介溝通角色。人與人相交,人言為信。既然是「人言」為「信」,那麼什麼是「人言」?先有「人」言、只有「人」言,而後才有「信」。
由此可見,「信」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動靜之間,「信」所牽動指涉的,自然關係重大,影響人際的溝通瞭解,建構可見或不可見的歷史網絡。「信」讓寫的人一訴衷腸、盡吐心底隱密;也讓看「信」的人深入執筆者的心靈秘境,了悟真實。「信」在人與人之間搭建起的溝通瞭解的橋樑,功莫大焉。
「信」的消亡:現代文化的奢侈品
這本書的雛形就是從一封封或長或短的信件中摘錄編輯而來。這些年來,幾位從事文字廣播宣教工作的好友同工們,面對網絡資訊的快速發展、AI 人工智能科技的突飛猛進,尤其是後現代主義學者憂心忡忡,哀歎「人不見了」(dehumanization)的「去人化」雜沓混亂的腳步,聲勢洶湧地攪亂了傳統以人為本的文化社會。「人」既不存,人言何在?人活得越來越不像人,我們到哪裡去找「信」呢?
幾年前在一次偶然的談話中,跟老友安平幽幽地談到當前現代人所面臨的文化社會中「人不見了」的危機。我們每天伏在不同的電子化資訊工具前,穿梭往返在不同的資訊網絡中,忙得沒有時間跟一機之隔的同事朋友們打一聲招呼,喊一聲哈囉!在這一片嘈雜忙亂的混亂中,我們看不到「人」、自然也聽不到「人言」。至於「人言為信」的「信」,更成為現代人的奢侈品。想要看到、聽到現代忠臣烈士慷慨陳詞、視死如歸的豪情壯志,幾乎不可能;推窗望月、面迎清風,牽扯出來的似乎也只剩多年來一直埋在心靈深處的一絲悸動;使人不由自己地任憑內心種種思念懷想,意圖飛越窗欞、跨山履海與萬里外的至親密友,把酒言歡,互道心聲。但只在一瞬間,我們會慨然發現,心手所觸及的仍然是冷冰冰的電子媒體。
不知怎麼搞的,面對取代本我的資訊材料,只那麼一瞬間,便把找不到本我的自我,捆鎖在「我是誰?」的失落捆鎖中,哀哀呼叫。人不見了!「人言」銷聲匿跡了。「信」何在?「信」早已成為所謂現代文明中的奢侈品。
新冠三年,不可能的工作
緊接著,在人類群體逐漸失去「信」的惆悵震驚中,新冠病毒(Covid-19)更在世人毫無瞭解準備的情況下,蔓延世界各地。面對來勢洶洶、不可捉摸的新冠疫情,驕傲的現代人只好乖乖地被隔離起來。即使有千萬個不甘心、不情願,也只好被關鎖在隔離空間中。在這個普世性的災難中,人際關係越來越疏遠淡薄,但透過互聯網的連結,也許可以彌補搶救當前教會拓展宣教工作的瓶頸,為教會宣教工作另闢一條蹊徑。
首先我們決定,這件工作應由幾家對文字視聽、影音佈道、網絡宣教工作有心整合嘗試的機構共同合作、群策群力,以抵於成。於是在安平牧師奔走聯繫之下,徵得遠東廣播公司、救世傳播協會、宇宙光等機構和安平牧師所帶領的普世佳音同工們共同合作,分別從文字資料收集、聲音錄製剪輯、影像錄影後製,正式展開試作及籌備工作。
經過多方討論尋覓,先從已有的信函文獻中,挑出寫信者生命歷程中最想與收信者分享的內心故事。這些發自內心深處的呼喊或傾訴,或如長江大海,澎湃洶湧;或如掬面春風,沈穩溫柔,細數生命情懷,都是書寫者在面臨不的生命歷程時,心靈深處隱藏的真實對話。幾經討論,我們選定了多位不同生命背景的人,將他們在不同的生命歷程情景中所寫的信作為這本書的主軸,開始了編輯與整合的工作。
選定了書信內容之後,誰來朗讀這些信件也花了大家不少心思。我們希望朗誦者最好跟寫信者有某種親密關係,如血緣關係、事工聯結、研究工作等。確定了朗誦者之後,又花了許多心思和時間尋找寫信人的解說者,並由安平親自出馬,主持一個談話性節目,邀請學者專家、牧長同工共同參與。最後由後製單位透過不同的網絡渠道推廣行銷至各相關機構、教會及社群。
如今,這項整合各相關機構,各取所長、互補短缺的工作,總算跨出了第一步。回想如飛而逝的三年,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之際,我們這群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渺小有限的神的僕人,竟然在同一個異象的驅使下,初步完成了這項似乎不可能的工作。回頭數算,新冠病毒的肆虐仍然存在,媒體功能的日新月異、迅速變遷,更是時刻干擾攪亂了我們宣教的前進步伐。但神的工作從來不會因為這些因素而受到攔阻,祂必親自堅立和帶領合祂心意的事工。
信:傳播媒介的起點
請為我們禱告!為普天下從事文字影音宣教工作的人禱告!讓我們無論在任何困難變幻之中,仍然能從心靈深處,平靜坦然地寫下一封又一封叩擊人心的生命信函。
寫一封信,似乎是小事一樁,但無論媒體資訊如何發達,「信」永遠是傳播媒介的起點。作為一個投身福音傳播工作已達50 年的宇宙光同工,請容許我問一聲:「親愛的同工朋友們!在這個資訊時代密鑼緊鼓敲響警鐘的時候,為著福音的緣故,你什麼時候會寄出你的第一封生命信函?」
推薦序
撥開幽暗,注目日光之上的永恒
施瑋(國際靈性文學藝術中心主席,靈性文藝出版社社長)
收到張強《今天他仍舊說話》的書稿,正是我連續八年寫作,終於完成中國教會歷史文學三部曲《叛教者》《獻祭者》《殉道者》,共計150 萬字的書寫。完成重負之時,卻也深感身心靈疲乏、倦怠。十年前,因著上帝的呼召,我開始研究並寫作中國教會歷史中的人和事,並呼喚同路人一起來書寫「銘賢書系」。我曾經立志「用筆揭開遮蔽的歷史,用靈喚醒蒙塵的忠魂」,今天卻深深地感到,十年來,正是這些蒙塵的忠魂,這些生命的種子,這些被遮蔽的見證,在不斷喚醒我常常會在世俗世界中昏昏欲睡、倦怠無力的心靈。
歷史,從上帝的角度看充滿信心和真理的榮耀;從人的角度看卻瀰漫著無盡的悲哀、無奈,甚至是絕望的憤怒。書寫歷史、閱讀歷史,我們是被榮耀照亮?還是陷入幽暗、絕望?如果我們不迴避真實,不停止思索,那麼這兩種狀態也許是並存的、交替的、掙扎的,甚至也是相映襯的。當我閱讀《今天他仍舊說話》時,這幾年我參與及聆聽大型書信朗讀節目《因信說話》的過程及情緒,都穿越目前灰朦朦的濃霧,光一般射入內心。那些遙遠時代的書信再一次走進我的書房;那些溫暖的聲音再一次對我的心娓娓訴說;那些在渾濁歷史中星晨般閃亮的生命,也再一次出現在漆黑的夜空……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這三年中,新冠疫情、美國大選、俄烏戰爭、台海局勢……索鏈囚女、偶像「塌房」、上海封城、物價飛漲……從網絡到實體、從居住國到祖國,從平民生活到全球格局,世界彷彿進入了一個最為荒誕、燥動、無序、無望的時代。當我突然從書寫世界回到現實後,發現很多人都和我此刻一樣,陷入困惑,感覺無力。
張強的這部書將他自己在這三年中從四處奔波到與封控隔離的現實生活,與他所拍攝和講述的人物交替穿插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一部風格獨特的散文隨筆集,也是一部《因信說話》節目製作編輯手記。他讓我們這些讀者不斷地進出一道「門」,門這邊是眼見的現實,門那邊是另一個時空裡的現實,但更是那眼未見的「確據」、所信之事的「實底」。
這些真實的歷史書信,將寫信者生命中的信仰之光呈現出來,指向日光之上的永恆。並且,藉著讀信、解信,製作者同被聖靈所感,靈與靈的唱合與傳遞,讓日光之上的永恆臨到囚禁在日光之下的人們。當我們看1900 年庚子教難中殉道的安麗莎;當我們瞭解在中國拓展福音和社會關懷的蘇慧廉;當我們感佩全然奉獻,在中國宣教一生的戴德生和台約爾;當我們走入大文豪路易斯的真實生活;當我們闖進天才畫家梵谷追求信仰與純粹的精神世界;當我們閱讀潘霍華從神學家到卷入參與刺殺計劃……
我們看到他們所處的時代同樣充滿戰爭、瘟疫;他們的生活同樣有缺乏與病痛;他們的精神同樣遭遇逼迫、陷於幽暗。然而,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困境中的信仰者們,以樸實無華、平平淡淡的家信,為今天的我們撥開「眼所見」的幽暗與迷霧,讓我們看見「眼未見」的日光之上的永恆,看見信仰者在日光之下可以走的十架之路。這條十字架的路,有逼迫、有血淚、有嘲笑、有軟弱、有犧牲、也有跌倒,但它是我們主耶穌走過的路。因著與祂同行,先行者們已經成為了如雲的見證人,今天的我們,也可以成為他們中的一位。當代著名基督徒作家張曉風寫給青年的書信,彷彿正是中國基督徒在當下對日光之上永恆的信心回應與傳承,是傳道者的生命種子結出的子粒。
基督教救贖的真理是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穌,不僅僅是一套道理,更是一群人,一群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的人,一群基督耶穌跟隨者的生命見證。因著信,他們依舊說話,你聽見了嗎?
2022 年10 月11 日寫於洛杉磯東谷書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