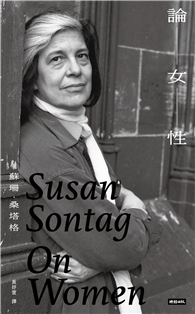妖異綻放的「惡之華」◎駱以軍
這是一本「創痛之書」,一本「過去之書」,一本「等待之書」。整個故事從主角的哥哥艾瑞克自精神病院逃脫,打電話宣告他「正在趕回家的途中」(這樣如同瘋人狂躁囈語的電話突擊,不斷在書中出現)開始,我們被敘述者那面無表情,看似平穩卻不斷翻牌展示的殘暴瘋狂景象所感染,被裹脅進那個「等待的時光」:既期待又畏悚,一種拖延的、憂鬱的空轉。那個哥哥從邊界(時間上是難以啟齒,核爆般的大傷害初啟時刻)尖叫著、瘋笑著,像復仇使者朝著主角「我」所在的這個等待之點靠近。
主角的身旁有一個鐘樓怪人般的父親,一個施暴者衰老的形象,主角和哥哥私密通著電話的那個伊底帕斯的對象。此處這對兄弟(在故事的結尾,「我」的性別認同像魔術方塊被扭曲旋轉)的連結讓人想到《惡童日記》的雙生子:他們殘虐,冰冷,以孩童或少年的形體執行著讓人慘不忍睹的殺戮──《捕蜂器》中,哥哥放火燒狗,虐待小孩;弟弟殘殺兔子、鳥類、昆蟲,甚至謀殺親戚間的小孩,其屠殺設計之智商與美感更遠超過其兄──惡童之惡有其小說心靈史的合理性:他們是邪惡父親鏡廊裡的投影,二十世紀戰爭人類大規模屠殺同類的集體噩夢的濃縮版,他們是啟示錄畫面難以重現的罪之負軛者(譬如葛拉斯《錫鼓》中的侏儒男孩奧斯卡)。他們像一只小鐵罐,把大人們填裝進去的巨幅惡之全景,以一種孩童劇場的純潔形式翻印出來。
作為讀者,很難不為書中主角娓娓陳述的那些殺戮場面(殺動物以及殺人)之駭麗魔幻、詭魅創意所顛倒著迷。那種精準、對詩意的偏執、波赫士式自閉少年的迷宮花園、將所有的死亡拉高至一種宇宙祭壇的哲學頓悟:
獻祭給「捕蜂器」的黃蜂多數會自己死亡......如果牠來到「火焰湖」,那麼按下活塞桿,讓它點燃打火機,從而引爆汽油的,也是我。(見一六一 ~ 一六二頁)
我們的生命都是符號。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有「捕蜂器」,它和現在、未來有關,而不是過去。(見一五六 ~ 一五七頁)
這種種瑰麗夢幻,卻又將手術刀解剖之理性精準,或鐘錶工匠技藝之精微感官,進占一齣接一齣少年獨自布置的「死亡遊戲」(像少年用模型小兵或傀偶布置的遊戲密室),在本書中不勝枚舉,讓閱讀成為一種喘不過氣來,「殺戮成為純粹美感運動」的視覺饗宴。讀者在被那一朵接一朵妖異綻放的「惡之華」炫技所催眠進入的激爽、歎服、沉醉,甚至逗笑之後,難免不幽微浮出某種道德迷惘:「如果殺戮、處死,成為一種純粹美感的客物化行為,一種將感覺獨立於其它倫理脈絡之外的創造能力......?」
關於「惡」──惡之華,惡的妖艷靡麗,惡的大教堂巍峨高矗,惡的夢遊化、嘉年華化、去人化──我們這個世代的小說讀者或許讀過不少。一種純機械理性的標本剝皮師傅式的細節慢速運鏡,純感官地將血淋淋的肝膽心肺或人皮人腦、生殖器官割裂、施暴。將傷害詩意化,成為薔薇花瓣,成為收藏的香味,成為一種性愛快悅如神祕河流分支漫漶的冒險,成為一種偽啟蒙、偽悲劇(同樣有一種巨大的哀憫與恐怖造成情感之洗滌,卻與命運無關,純粹是喪失與剝奪後的動物性地獄變)......
經典當然是徐四金的《香水》,無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卻深諳「將人的古典定義摧毀,成為破碎的客體,成為淬取極品香膏的材料」之專業技藝;譬如莫言的《檀香刑》,人如神壇上傀儡,懷抱著班雅明式對古典靈光之手工技藝的崇敬與傷逝,以虐殺人體之慢速延緩其「抵達死亡」之快速,打開一個痛苦之繁花簇放、一個週期表展列、「一百萬個天使站在針尖上」的感官之顯微、放大、爆炸;或如丹尼洛.契斯的《死亡百科全書》,僵直心靈的無意義虐殺;或如符傲思的《蝴蝶春夢》,誤解的詞,以剝奪、監禁、將對象標本化的機械操作而進占「愛」這個字;或如威廉.高汀的《蒼蠅王》,自然主義的表親,作為文明人雛形的孩童,在一個封閉劇場(奇怪,「島」通常是這一類型「惡童故事」的空間設定)內如何失去文明之殘餘,變成獵殺同類,被自我的殘虐與獸性驚嚇而無從救贖的「被遺棄者」......
譜系龐雜,掌紋紊駁。這些「惡之華」們,大抵已離杜斯妥也夫斯基之《罪與罰》遠矣。甚至可能早已脫焦「惡」的哲學性思辨,成為一種讓人胃囊發冷、眼腫灼疼、腎上腺素飆升的創造力極限運動,一種純潔的虐殺,一種對撲天蓋地全球化、系統化、人之零件化、感性鈍化的即興掙跳(或反刺)。血液在析光鏡裡瑰麗地噴灑,或系統化、屠宰場意象地切截人體(電影《恐怖旅店》)。背後總有一個二十世紀的幽靈:法西斯,一個關鍵系列詞組:「現代性與大屠殺」。
「人為何要無意義的殺人?」電影《八厘米》裡尼古拉斯.凱吉演的憂鬱偵探這樣悲傷地問。「不為什麼,只因為他有能力。」這幾乎隱蔽進推理小說、城市犯罪小說,被專案處理的提問,譬如小說《八百萬種死法》裡馬修.史卡德這樣問,影集CSI掌握了高科技與兇殺現場還原能力的鑑證科組長這樣問,甚至電影《人魔》裡那個古典貴族教養的變態殺人魔感傷而不以為然地問那些新世代「無品味」的殺人狂......掌握了更高的權力者,更有錢,更具高智慧(自由脫逃於警網),更新品種病毒般可扭曲古典人性的意識型態,更進化的國家機器、軍隊、傳媒、運輸與現代化屠殺工具......
「祭祀柱」對書中這位少年主角來說,是島中之島,所有傷害暴風中心那唯一寧靜安全之地,因為島上其他居民不會闖入,對敏感、乖誕(故事接近尾聲我們才意識到,他∕她是個性別認同錯亂的「閹人∕偽造閹人」)、殘虐版《艾蜜莉的異想世界》的少年而言,是避風港。但同時亦是無成人秩序的《颱風俱樂部》──我們一開始以為是個受創少年在他的祕密基地虐殺小昆蟲的感傷成長小說,待伊恩.班克斯的敘事魔術劇場一全幅展開,才驚嚇地意識到那是「變形金剛版」的恐怖大屠殺。
奇怪,即使少年的「殺戮史鐘面」由殺昆蟲、殺動物,而至殺活生生的人類小孩,他對它者的痛苦喪失感性的冷酷讓我們不寒而慄,但我們同時會對他那惡魔般才華洋溢的殺人創意,奇異地湧起一種近乎幽默的智性歡樂。(「天啊,那些殺人的點子和場面實在太屌了!」)你很難不產生這種同時欣羨同時不安的道德焦慮。從「祭祀柱」到「捕蜂器」,一個大場景的祕密祭壇到微宇宙的精密屠宰場,那穿透少年外在與內在的詩意象徵連結,本就是一個扭曲、尖叫、傷害的歪斜風景。它本來就透過少年的「像蜜蜂被無意義的拔翅掐頭火燒」的受難畫(「反基督?」)反證了一個邪惡的、成年人類打造的文明:這個文明的史詩說穿了,就是對屠殺的技藝的飛躍進步與理性啟蒙。
但《捕蜂器》當然遠不止於此,一如傅柯曾在詳閱中世紀法廷死刑犯罪行(殺害全家、殺父殺母、肢解分屍自己妻子......)與精神病監獄中瘋人病例──往往只是寥寥幾句──後說,他們乖奇的一生:「像一句詩那麼短。」而那其實是那些人名們在那些瘋魔駭異時,眼中所見的洶湧地獄之景。
寫稿的此刻,我其實仍難以釐清這本小說帶給我的狂暴、華麗、激情,甚至幽默的笑......那濃郁豐饒的詩意到底是什麼(絕對和《南方四賤客》裡血漿亂噴、屍塊亂飛的遠離真實的尖嘩謔笑完全不同)?那憂鬱且拖著鈍重陰影的童話感是什麼?那種同時對「殺人」形上本質的不安但又催眠進入一種純粹的、小說美學的高度飛升的分裂感是什麼?對我而言,小說結尾的骨牌逆翻(此處亦不宜轉述)如果意圖作為印第安沙畫般,將全書之「童謠謀殺案」作一道德翻盤,是不具說服力的(究竟它不是如《中性》,或吳繼文的《天河撩亂》,全書的抒情資產與「匱缺之傷慟」之機關全設定在「他∕她」的性別指稱代名詞之顛倒),套句老梗:「表層即核心」、「過程即終點」,這是一本將「殺戮」演劇,魔法綻放到一如「漫天紛飛的銀杏葉片」,讓人眼花繚亂,為之癡迷,但卡爾維諾是這麼說的:
漫天紛飛的銀杏葉片的祕密在於,在每一刻,每一片正在飄落的葉子,出現在不同的高度,視覺座落的空洞無感覺空間便可以區分為一系列連續的平面,在每一平面,我們發現有一片葉子在旋轉,且只有單獨的一片。

 共
共  班克斯,又譯為班克西,是一位匿名的英國塗鴉藝術家、社會運動活躍份子、電影導演及畫家。他的街頭作品經常帶有諷刺意味,在旁則附有一些顛覆性、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和精警句子;其塗鴉大多運用獨特的模板技術拓印而成。他的作品富有濃厚政治風格,儼如一種以藝術方式表達的社會評論,並已經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街道、牆壁與橋樑出現,甚至成為當地引人入勝的城市面貌。
班克斯,又譯為班克西,是一位匿名的英國塗鴉藝術家、社會運動活躍份子、電影導演及畫家。他的街頭作品經常帶有諷刺意味,在旁則附有一些顛覆性、玩世不恭的黑色幽默和精警句子;其塗鴉大多運用獨特的模板技術拓印而成。他的作品富有濃厚政治風格,儼如一種以藝術方式表達的社會評論,並已經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街道、牆壁與橋樑出現,甚至成為當地引人入勝的城市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