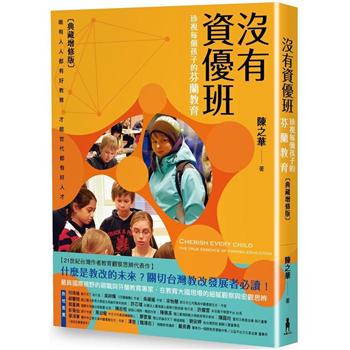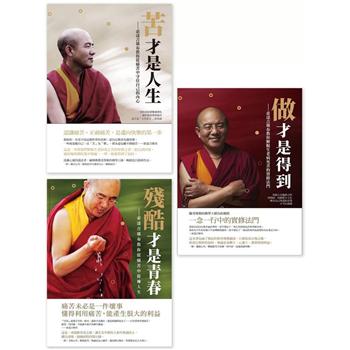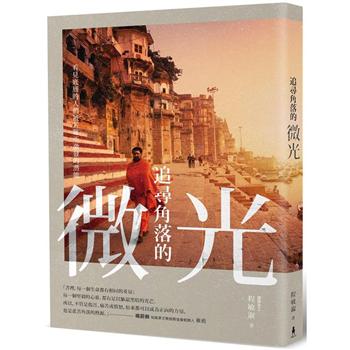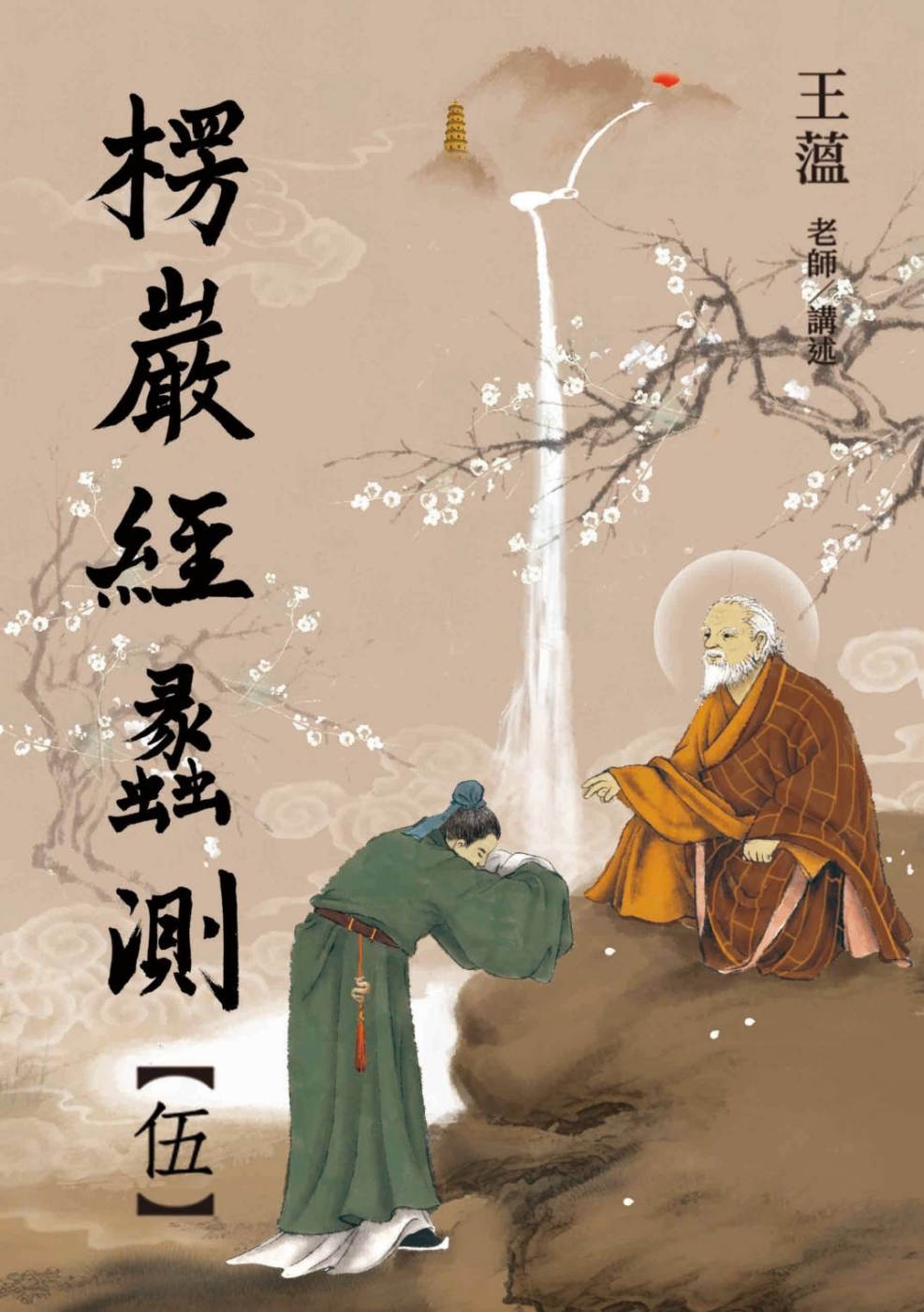一場意外,讓她的心跳無端改變了四個人的命運,
他們都沒有想過,失去與獲得的那瞬間並不是結束,
而是另一個開始……「不要感謝我。如果我可以決定,我會要妳死,而讓我太太活著。」
「我只是想讓他知道我有多感謝他。如果不是他太太的心臟,我早就完了。」
「我以我的女兒為榮,因為她的先見之明,我們只失去了一個人。」
「光有捐贈者是不夠的,還要有毀滅行動的執行者;沒錯,我撞死了一個女人,但我也救活了另一個。」一年前,艾力克斯在一場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伊莎貝爾……但不包括她的心臟。
一年後,那個叫珍娜的女人試圖跟他聯絡。感謝伊莎貝爾的慷慨?感謝艾力克斯的成全?不,不用了,他沒有打算抱著什麼「遺愛人間」的偉大情操,把妻子的心臟還來就是了。岳母伯妮絲希望他和珍娜聯絡的要求雖然讓他有點吃不消,但令他最瞠目結舌的是,當時的肇事者賈斯柏竟也出現在他門前乞求原諒,甚至想與他為友?
原來,伊莎貝爾的死不是結束,而是一切的開端。
艾力克斯以為只要他繼續保持疏離、態度冷淡,總有一天可以回復平靜,就像伊莎貝爾還活著的時候。接到電話的那個下午,艾力克斯意外發現,即使是已經死去的人,仍然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個縫隙中,而且,仍然會受傷害。因此,他做了一個決定,雖然他知道這個決定只會讓他早已失序的生活更加波濤洶湧……
作者簡介:
史蒂芬.拉弗里(Stephen Lovely)
出生於德州的達拉斯,童年時期則在俄亥俄州度過。在肯揚學院(Kenyon College)求學時寫下他第一部小說作品,是他涉足寫作的開端。1990~1992年他加入愛荷華州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跟著黛博拉.艾森博格(Deborah Eisenberg)、瑪歌.李席(Margot Livesey)、伊森.坎寧(Ethan Canin)以及法蘭克.康洛伊(Frank Conroy)等知名作家學習小說寫作技巧。
史蒂芬曾在愛荷華州立大學附設醫院的小兒加護中心擔任夜間櫃檯服務員長達七年之久,該書即為他在這段期間寫作而成的。
目前定居愛荷華市,同居人包括女友、三條狗與三隻貓。
譯者簡介:
謝瑤玲
美國伊利諾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東吳大學英文系級政治大學英語系副教授。從事翻譯工作多年,譯作超過兩百本,代表作有《玫瑰的名字》、《英美兒童文學簡介》、《女教皇》、《花園宴會》、《標點符號全面通》、《最動人的英文》、《布萊森之英文超正典》、《死也要上報》等。目前從事教學、研究、論述,並持續翻譯,從不間斷。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本書充滿對失落之物的懷想,書中對於人物的個性、對事物細節的描寫讓我為它傾倒,如果任何人想要讀一本有關信念、浪漫、希望、愛與歡欣的書,我絕對會推薦這一本,而它也絕對是我贈送給朋友的禮物首選。
──J. Uppengahl
本書非常動人、非常善於分析,當然題材也很新穎。作者發掘了每個人物在不同面向的感情,而對我這樣一個接受過肺臟移植(所以我有兩個肺)的人來說,我也會常常想到捐贈者的家人,以及我在接受移植前的生活。這本書真的非常引人入勝,你也應該在家裡放一本。
──Risa G.
本書是關於傷痛、默想、失去與生存的書,實在令人愛不釋手,忠實地表達出人們在這種狀況下所面臨的掙扎與困惑。作者對他筆下的角色投入了極深的情感,它談論的並不是「要不要成為器官捐贈者」的問題,而是每個傷痛靈魂所背負的重擔與記號。
──Daniel Gerwin
我發現這本書真的有讓人停不下來的魔力!剛開始讀前兩章時,我以為我已經猜到了接下來的發展和結局,沒想到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真等不及看到作者的下一部新作品了!
──Cynthia Bunten
史蒂芬.拉弗里的小說裡充滿智慧、令人心碎的糾葛、趣味以及不同的人性。他將心臟移植這樣一個枯燥的話題以極富人性的方式表現出來。藉著一個偶然,讓未曾露面的犧牲者與接受器官移植的幸運兒,還有他們的家庭產生了永不斷裂的連結。《Irreplaceable》是如此令人難忘,而我是如此純粹地喜愛著這本書。
──安.胡德(Ann Hood),知名作家
《Irreplaceable》是一部溫柔又令人愛不釋手的小說。它發掘了人生的神祕與變幻莫測之處,並以溫柔而充滿理解的筆調讓人心之間的隔閡得以填補。史蒂芬.拉弗里是位深深明白人性的作家,他的作品的確擁有讓人一見鍾情的魅力。
──盧安.萊斯(Luanne Rice),知名作家
你可以想像得到這是多麼戲劇化的場景:面對著心臟移植,一端是失去的痛苦,一端是重生的喜悅。史蒂芬.拉弗里以他的生花妙筆將每個人的不同心境與經驗一一展現在讀者眼前,寫出一個關於悲傷、失去與重生的故事,它的內涵如此豐富、如此深刻,也如此有力。
──約翰.道爾頓(John Dalton),知名作家
《Irreplaceable》提醒我們,人的心──當然,在這裡指的是字面上的──讓我們以連我們自己也無法預期的方式對待他人……這真是一本完美的處女作。
──約夏.亨金(Joshua Henkin),知名作家
本書中說明了許多難以言喻的情感,並以明白流暢的筆調闡述了在人性與人際關係之下流動的複雜情緒。
──《芝加哥太陽報》
初試啼聲的拉弗里毫不畏縮地選擇了心臟移植作為小說的主題,同時細膩地刻劃了捐贈者家屬以及受贈者的複雜心境,即使是故事周圍的第三者,也仔細地描寫了這些人想法及思路的轉變,拉弗里敏銳而充滿感性地掌握了故事所須的所有細節,熟練地彷彿寫作老手般,絲毫不覺生澀。
──《圖書館期刊》
本書的目的並不在傳達器官捐贈的重要性與捐贈後可能發生的問題,而是客觀地提供所有的讀者各種觀看事物的角度,關於失去與給予同時發生,而且難以抉擇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的問題。
──《Examiner.com》網站
拉弗里以敏銳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敘事筆法道出了悲傷、失去、獲得與罪惡感的種種面向,故事中人物們的想法誠實得近乎刺眼,卻又讓人心折不已。
──《The Sacramento Book Review》網站
拉弗里就是有辦法讓你一直讀下去;即使你已經猜到故事的結局會是怎樣。
──《美聯社》
本書告訴讀者,一份「真心」的禮物究竟能讓讀者心碎到什麼地步。渴望、理解、包容成為本書最大的魅力所在,故事的節奏感也掌握得恰到好處,它絕對是你書單裡的上上之選。
──《圖書報告網》(Bookreporter.com)
媒體推薦:本書充滿對失落之物的懷想,書中對於人物的個性、對事物細節的描寫讓我為它傾倒,如果任何人想要讀一本有關信念、浪漫、希望、愛與歡欣的書,我絕對會推薦這一本,而它也絕對是我贈送給朋友的禮物首選。
──J. Uppengahl
本書非常動人、非常善於分析,當然題材也很新穎。作者發掘了每個人物在不同面向的感情,而對我這樣一個接受過肺臟移植(所以我有兩個肺)的人來說,我也會常常想到捐贈者的家人,以及我在接受移植前的生活。這本書真的非常引人入勝,你也應該在家裡放一本。
──Risa G.
本書是關於傷痛、默想、失去與生...
章節試閱
伊莎貝爾.霍華
伊莎貝爾低伏在單車上,雙手壓低,兩腿用力踩踏。她的單車衣背部已被汗溼透,緊貼著皮膚。汗水自她的額頭和太陽穴淌下,不斷滴進她的眼睛。她以戴著手套的手背抹掉額頭上的汗,然後以三根指頭輕按頸動脈,感覺血管的跳動。
一小時前她離開鎮上時,天色已經有點陰暗,現在還起了風,雲層快速地流動著。天空一片墨黑,空氣裡飄浮著溼氣和堆肥的氣味,電話線上的紅翅黑鸝鳥噪動不安,她猜在大雨傾盆落下之前,還有五到十分鐘的時間可以騎到鎮上。
風又猛又急。她減少了握住把手的力道,好減輕單車的受力;接著放低身子,以抵禦強風的衝擊。在狡猾的風往後退去之前,她只能勉強維持平衡,而在風遠離之後,則必須迅速再度轉移重心,以免失控飛向路肩。
她覺得自己毫無遮蔽,既渺小又無助。這裡是愛荷華州,即使她沒聽到龍捲風的警報聲,仍在地平線附近搜尋著漏斗狀的烏雲。她必須回家去。她想看見丈夫艾力克斯、想摸她的狗、想喝一杯柳橙汁,然後躲進地下室去──如果真有龍捲風警報的話。如果沒有,那麼就沖個熱水澡。
但在此同時,她也覺得很刺激,甚至有點亢奮。和狂風、和即將來臨的暴風雨對抗;和危險擦身而過。
現在她直線衝下一處陡坡,任憑風呼嘯而過,身體與單車融為一體,宛如一枚飛射而出的子彈;在逐漸增加的速度、既像是自由落體又像是和周遭脫離的感覺中獲得某種快感。
她在一條向前延伸的平直道路上快速滑行,經過一片在還留有玉米殘株的農田、一幢農舍、遠方的牧地、漫步在牧地上的牛群,和一小片橡樹林。
她一路用力踩著踏板,朝另一座山丘而去,換低速檔,衝向山坡。她伏低身子,緊握著把手,鼻尖幾乎碰到下臂。她將重心往後移,使勁踩著踏板,並保持節奏,勉力向上爬。前二十碼,她覺得自己像一部運作平穩、馬力強勁、符合完美標準的引擎,安裝在單車上以驅動踏板。接著,她力氣用盡了。這段上坡路又長又陡,而她的體能還不算太好;這不過是她這一季第三次騎車出門。她覺得肺部灼熱,兩腿如鉛塊般沉重。在她的身下,單車搖晃不穩。
她抬起頭,看見山頂已近在眼前,剩下不到十碼。前面是一片大豆田,盡頭是一座農場,穀倉門前擠了一群山羊。
她奮力騎到山頂,此時強風夾著如尖銳口哨般的呼嘯聲席捲而來。
一輛車子引擎的吼叫自她後方的路面傳來,她一陣驚慌:在撞擊前的那一瞬間,她才意識到她騎在馬路中央。
珍娜.寇可蘭
珍娜.寇可蘭個兒很高、肩膀很寬,今晚穿著一件淺藍色的絲質襯衫,垂在黑色七分褲上。以前這件七分褲很寬鬆,但現在卻緊貼著她寬闊的臀部。如果她沒有打算減肥,她就得去買大號的衣服穿。她特別想去除臉頰和下巴的贅肉,雖說那些多餘的肉此刻都藏在她為了預防感染而戴的淺藍色外科口罩下。她並不喜歡戴口罩,人們看到時都會刻意迴避她,雖說他們才是經由咳嗽和噴嚏而帶給她威脅的人。她告訴自己,戴口罩使她看起來很神祕,而她的綠色眼眸、白皮膚,和特意將馬尾紮在頭頂的蓬亂紅髮則十分引人注目,多少可以轉移別人的注意力,讓她稍稍好過些。
發生在這個女人和那個女人之間的劇變,再加上珍娜的成功存活,這比任何事物都更能說明她究竟是誰。當別人問起時,她可能會高估對方的好奇程度,對電鋸如何從中切斷她的胸骨、她的胸腔如何打開、她的壞心臟如何切除後再換上一個好的……之類的事侃侃而談。她並不刻意隱藏她的疤痕,今晚,在超市裡,那道長達十吋的疤痕便自她敞開的領口露出一吋左右,粉紅色、線形、微微凸起、摸起來硬硬的。
透過窗戶看著街道上車子熙來攘往。珍娜取下口罩,享受吹拂在臉上的涼爽空氣。她津津有味地吃著沙拉,暫時忘卻一切,什麼也不想。如此理所當然地活著,不就是生命的特權之一嗎?自由自在,任憑時間流逝?要不然,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呢?一個女人的猝死、她的家人所面臨的哀傷和悲痛、醫生和護士幾個小時的努力,更不要說珍娜自己的掙扎和痛苦……這一切不都是為了讓她可以多活這珍貴的幾年,好承擔每一時刻都要過得充實的不可能任務嗎?
她希望伊莎貝爾.霍華會了解。「伊莎貝爾.霍華」,沒有這個名字的話,珍娜該如何是好?她當然明白為何器官取得機構不想讓捐贈者和受贈者發現彼此的身分。有一些例子是捐贈者的家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無論是金錢或其他方面;也有一些是騷擾、威脅、突然造訪等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珍娜打從一開始就相信,雙方接觸所帶來的好處會大於危險,因此,運氣使然(一位醫師不小心說出「愛荷華州」以及「一輛單車和一輛車子互撞」),再加上芝加哥圖書館的報紙館藏、網路搜尋,以及數不清打了多少通電話後,珍娜終於突破了這不知名的障礙。要不是她突破了障礙,她可能就得為這個女人杜撰一個名字,而且珍娜想像這個女人會從墳墓裡用近似英格麗.褒曼在《美人計》裡的奇怪聲音時而鼓勵她、時而指責她。此刻這個聲音很慷慨地對她說:放輕鬆。這是我們努力得到的。不用管我。
只是珍娜還是會想。她真希望伊莎貝爾也可以在這裡,呼吸空氣、看著窗外的世界、吃著多明尼克做的羊肉捲餅。
「到星期六就滿一年了。」她說,並不特別對著誰說。「我希望她丈夫過得還好。」
「那是一定的。」
「你怎麼知道?」
大衛將羊肉捲餅放在盤子上,用餐巾紙擦擦嘴,然後揉成一團。「都已經一年了。他應該要往前看了,至少要試試。」
「如果我已經死了,你現在會往前看嗎?」
「我不會……也許不會是現在。」大衛有點不知所措。「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妳。我不會想要接到器官受贈者寫來的卡片和信,那感覺多怪啊!」
珍娜氣沖沖地說:「心臟是一份禮物。」
「又不是他送的。」
「他支持他太太的決定,他同意捐贈。不然整件事可能不會發生;不然我可能就沒辦法坐在這兒。」
「所以妳謝謝他。但兩張卡片就夠了吧?兩張卡片和一封四頁的信?」
「三頁。」沒錯,第一封信很長,而且寫這封信是珍娜目前為止所做過的最困難的事。要如何以不過分感激又不至於忘恩負義、不過分誇張又不至於對這不公平交易麻木不仁的口氣,向一個人解釋他妻子離世的悲劇雖造成他的錐心之痛,卻也使她這個陌生人可以活下來?她花了一整個星期塗塗改改,最後她覺得自己至少努力過了,雖說那封信只有薄薄三頁,但內容可以說是她所有感激、困惑、和歉疚的濃縮。
「我相信他會認同信上的內容。」珍娜說:「我不覺得那封信會騷擾他,那張週年紀念卡也只是一個象徵,如果我不聞不問,也未免太沒良心了。要是他不想看,可以把它撕掉;又不是法院的傳票。」
大衛嚼著羊肉捲餅,短暫地沉默了一下。接著他開口:「假如妳有機會可以和這個人說話,妳想說什麼?」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
「要是妳跟他見面呢?妳要怎麼面對他?」
珍娜待在醫院裡的時候,不論是接近死亡,還是等待心臟,她會常常想像,或根本就是希望有車禍發生,造成某位捐贈者的死亡。「如果你想讓我覺得愧疚,我告訴你,我已經很愧疚了。或許我會這麼告訴他,說我覺得很愧疚。」
「如果那是禮物,像妳說的;妳不需要感到愧疚。」
「你說的倒輕鬆。」
「我只是不覺得那男的是個大英雄。」大衛有點痛苦地辯道:「他太太才是英雄。或者曾經是。」
「她的苦難已經過去了。」珍娜說:「但他還活著,他還在繼續付出代價。」
大衛對她的一針見血感到惱怒,翻了個白眼說:「我們不都是嗎?」
伯妮絲.霍華
當晚稍後,伯妮絲讀了一本科幻小說的幾個章節後,在沙發椅上睡著了。醒來的時候她覺得頭很痛。吃了碗穀片後,她打開電腦,檢查電子郵件。蘿妲寫了一封信。
伯妮絲,妳好!愛荷華州春天騷動的微風和色彩結束了嗎?我們的植物多半都過了花期,現在很不情願地加入草地和矮樹叢的翠綠,準備夏天的到來。
珍娜情況良好。她這一年的課已經結束了,所以她會有比較多屬於她的時間,她準備多陪陪大衛和孩子。前幾天晚上她帶卡莉去上空手道課,上星期六她和大衛帶兩個小孩去看芝加哥小熊隊的棒球賽。她和大衛仍在討論是否要搬離市區,到郊區去住──珍娜對這想法並不感興趣;這是最保守的說法。
這個週末,大衛要帶山姆去密西根加入一個生態夏令營,在那裡山姆可以深入了解自然界的各種變遷,我想珍娜會享受與卡莉獨處的時光。下個週末她和大衛要把孩子送到我這個外婆旅館來,再到威斯康辛的多爾郡(Door County)去度幾天假。那對他們來說應該會是個很好的小假期。
艾力克斯好嗎?我希望他安好。如果妳認為可以的話,請帶我向他問好。
對了,最近珍娜提到想要打電話給艾力克斯。妳認為這是個壞主意嗎?我告訴珍娜,她可能還要等一等。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聽進去了。有時候她還真固執。
嗯,這些就是來自北方所有的消息了。對了,妳去買了奧杜邦學會出版的《北美鳥類指南》了嗎?只是好奇而已。
希望妳平安順利。保重。
蘿妲
伯妮絲按下「回信」,寫道:
嗨,北方的人!我們這裡天氣很熱,而且還會更熱。妳提到山姆去參加生態夏令營,還真巧,昨天有個某環保團體來的男孩來敲門,要我簽名在七月六日「地球暖化行動日」那天關掉電器設施,包括冷氣機;而且我也不應該開車。我簽了名,也許我應該去清一下舊單車的灰塵才行。喔,我的天!我剛想到七月六日是艾力克斯三十一歲生日!我的環保信念真不堪一擊。我可能必須打破不開車的規則了。
很高興聽到珍娜健康安好,我希望她和大衛的假期過得開心。聽到珍娜的消息總讓我覺得開心,那會提醒我,原本可能會有兩個女人死去的,但因為伊莎貝爾,我們只失去了一個人。雖然伊莎貝爾的生命已經消失,生命的總數卻是增加的,而且是因為我女兒的作為,我真以她為傲。
但願我可以讓艾力克斯明白我的看法,但我不確定。我偶爾會對他提到珍娜,但不像以前那麼頻繁,因為這話題太容易引起爭論。因此,我會勸告珍娜暫時先不要打電話他。我不希望她得到不好的回應。也許以後有機會再說吧?
希望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見見面,蘿妲。我很想與妳面對面用真正的聲音對話。請代我珍娜一家人致上溫暖的問候。
伯妮絲
艾力克斯.佛曼
「歡迎!」蘿妲伸開雙臂,十指打開。伯妮絲上前與她相擁。當兩個女人緊握雙手時,艾力克斯站在一旁,發出一聲緊張、謙卑的笑聲。她們的擁抱堅定但快速:不明就裡的人會以為她們是多年不見的好友。伯妮絲介紹艾力克斯。蘿妲伸出手。艾力克斯與她握了手。蘿妲告訴他:「我們真高興你們來了。聽到你們要來我們都很興奮。你們……這裡沒有很難找吧?」
「喔,很容易。」伯妮絲向她保證。
蘿妲期待地望著他們,睜大眼睛,面帶笑容:他們其中一人應該有更多話要說才對。伯妮絲不知道該如何填補沉默的空檔,艾力克斯瞪著半空。大老遠開車到這裡和自我介紹,他們已經費盡所有的力氣,現在他們虛脫地無法思考了。當蘿妲說:「呃,你們要不要進來見見大家呢?」伯妮絲很高興有人給予提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病房門上的標示牌用紅色油墨筆寫著「珍娜.寇可蘭」幾個字。這是個多角型的房間,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提供了照明,牆上漆成粉藍色。病床上的厚床墊上堆著被單,病床朝後靠著牆上的一個控制板,上面設有氣壓計各種有刻度的瓶罐、按鈕、開關、指針。珍娜躺在病床上,一件白色被單鬆鬆地蓋著她的腰部和雙腿,單膝撐高,如安地斯山的山峰。伯妮絲第一個想法是:這個女人不是伊莎貝爾,不是她的女兒。這令她有些垂頭喪氣,她絕不會承認她期望看到伊莎貝爾在這裡,活生生的,躺在病床上;但她的失望卻說明了就某個層面上她的確有此期望。
珍娜掙扎著坐起身,用腳蹬著床墊,雙手用力撐在臀部兩側,朝床頭向上挪動。「哇。哇!你們來我真高興。」她的聲音透著緊張,但清澈,且意外地有力。「我真不敢相信你們真的在這裡。真是太神奇了。」
對於珍娜的熱烈,艾力克斯不知該如何回應,因為他無法配合她,反而有一股衝動想澆熄她的熱情。他以不置可否的聳肩和皺眉,讓所有人打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受到傷害且感到困惑,而她所說的神奇對他而言卻是尷尬又怪異的。
「我希望你們沒有為我擔心。」珍娜注意到他的關注,說道:「我很好,真的。我很可能比現在要糟得多,我曾經比現在還要糟糕得多。」
「我並沒有擔心妳。」艾力克斯說著,想像伊莎貝爾的身體──衣服被脫光了、臉部瘀血、嘴脣腫脹、雙眼潮溼、呼吸管從她的牙齒之間穿過──重疊在珍娜的身體上,躺在病床上。「妳的氣色很棒。我喜歡妳那些時髦的小包裝。」他對著掛在鉤子上的兩只點滴袋點點頭說:「至少妳沒有幾公噸的狗屎塞在每個妳想得到的縫隙中。」
「這裡有小孩。」蘿妲說。
「珍娜不會死。」伯妮絲聽出了他言下之意的比較,提醒艾力克斯說:「她明天就要回家了。」
「我看得出她不會死。」艾力克斯說。
蘿妲說:「她比我們想像的更接近。」
是艾力克斯的想像嗎?還是蘿妲很得意?她剛剛說這裡有小孩,令他很不高興。他很想告訴蘿妲,「狗屎」這兩個字如果有任何不好或褻瀆,比起某些不好或褻瀆的可怕事件,例如他太太被一輛貨車撞死,她必須承認小孩聽到的算是很輕微的,至少他們不必聽到保住他們母親一命的是多可怕的事。
伯妮絲嘗試與珍娜重新開始較輕鬆、愉快的談話。她只有手臂上那根點滴管嗎?他們為她施打什麼?她喜歡她的醫生和護士嗎?他們是她在等待心臟時的同一批醫生和護士嗎?艾力克斯感到厭煩,努力迴避蘿妲的目光,冷淡地盯著珍娜頭部上方的監視器,上面以金色、紅色和藍色的數字顯示她的生命指數。因為曾在伊莎貝爾的病床旁看過這些數字,所以艾力克斯對它們的排列感到熟悉,而且看得懂,讓他感覺很怪。珍娜的血壓是122/85。她的血氧飽和度是百分之九十八。她的心搏在九十上下,但是吸引他注意的是珍娜的心電圖──充滿活力、跳躍的綠色波形圖,看起來像要跳出螢幕,好像只要它想,就可以跳過整個芝加哥似的。
艾力克斯覺得有些頭重腳輕,他還沒準備好要面對這個。那是伊莎貝爾的心電圖,那是伊莎貝爾的心跳,伊莎貝爾的心臟在這間病房裡。他要如何相信,在珍娜的衣袍下,連到她胸部的導線所接收到的是伊莎貝爾心臟的電波?那是曾經在數百哩之外活過並死去的一個女人的心臟?他曾經和它一起生活、睡覺,也曾在做愛後將手放到伊莎貝爾的乳房之間感覺它的跳動。這是同一顆心臟嗎?
艾力克斯注視珍娜波動不止的心電圖。他為什麼沒有任何感覺呢?某種連結?某種存在?跳躍的小綠線沒有任何啟示,跳躍的小綠現線拒絕顯露跡象或給予證據,艾力克斯覺得他的胸口有一種張力,介於平凡與神祕之間的拉扯。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一直想要扯掉她的氣管內管。」蘿妲說:「這條內管通過喉嚨,幫助呼吸。她就像一隻野生動物一樣。他們必須用魔鬼氈將她的手腕綁在圍欄上。」
珍娜模擬當時的情景:她以紅猩猩一般的調皮,用力抓著從她嘴裡伸出的一根假想的管子,用力拉扯,翻著白眼。伯妮絲笑出聲來,蘿妲和珍娜也笑了,那奔放的笑聲使得三個女人猶如同盟。艾力克斯覺得有種衝突感,同時也有某種正義感油然而生。他不喜歡看到伯妮絲坐在凳子邊緣,前傾著身體,兩手掛在珍娜病床的圍欄,像個見習修女一樣;他不喜歡珍娜和蘿妲回應給她的那種輕快、讚許的笑容,像是奇異的獎勵。他擔心他和伯妮絲都被騙了,受到寇可蘭一家的要脅。
「我們知道氣管內管是什麼。」他對蘿妲說:「伊莎貝爾也有一根;她裝了呼吸器。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腦死的人,但他們無法自己呼吸。」
「我看過腦死的人。」蘿妲說:「我念大學時兼差當護士助理。」
「不要說那個,媽。」珍娜說。
但艾力克斯想要繼續。「當妳看到妳的家人腦死時卻不一樣。例如妳的丈夫,或者,妳的女兒。」
蘿妲不以為然地看了他一眼。「我看著我的女兒只差一點點就是了。」
「然後,變!她現在在這裡。」艾力克斯假裝用手掀開布幔。「安然無恙。」
「艾力克斯,拜託。」伯妮絲說。
「謝謝你們。」珍娜堅決地說:「我要正式向你們兩位致謝,現在,面對面,雖然說絕對不是最後一次,但也絕對不是因為這可以彌補任何損失,或是我對你們的感激永遠都不夠。但是我一定要這樣做,謝謝你們,為你們所做的一切。」
伯妮絲喃喃接受,接著發表簡短且有禮貌的演說,表明她很高興這一切有了某種好的結果,而這就是伊莎貝爾要的。
珍娜將目光轉向艾力克斯。在她的眼睛裡,他看到伊莎貝爾突出、充血的瞳孔。他聽到電鋸的颼颼聲,看到鮮血從她的乳頭流過,流到她的胃部,在她的肚臍匯聚,同時,收割者圍了上來。
「不要謝我。」他麻木地說:「我什麼也沒做。我應該說什麼?不客氣嗎?我說不出口。」
珍娜怒瞪著他,受傷又氣憤。
「艾力克斯,拜託。」伯妮絲說:「她並沒有要你說『不客氣』呀。」
「那她要我怎樣呢?」他問伯妮絲,然後又對珍娜說:「妳要我說什麼?妳不能期望我假裝我對這一切的結果感到開心。如果我可以決定,我會要妳死,而讓伊莎貝爾活著。很抱歉我這麼說,這與妳個人無關,但卻是真心話。或者也許真的與妳個人有關吧。也許我只能這樣看妳。」
看到珍娜眼睛變得迷濛,下顎和下脣開始顫抖,艾力克斯感到驚訝。蘿妲的瞪視指控著艾力克斯毫不必要的殘酷。伯妮絲抬頭注視珍娜的監視器,神情關注,臉色也變得緊張起來。她轉向艾力克斯:「沒有人這樣計算生命的。你不可能回到過去,用珍娜交換伊莎貝爾。無論其他人有沒有做什麼,伊莎貝爾都還是會死的。」
「妳要不要再多說一點?」艾力克斯臉頰發燙。他覺得痛苦、生氣、怨恨。他覺得他有權利感到痛苦、生氣、怨恨。這樣的痛苦、這樣的怨懟就是證據嗎?伊莎貝爾在這裡的證據?這可以證明嗎?
他深深想念伊莎貝爾,這是一種深切的渴望。伯妮絲伸出安慰的手,但他將那隻手推開。此刻他只想罵她是叛徒,想要引誘他陷入與這些無動於衷、太過幸運,又自以為重要的掠奪者的複雜關係中。
賈斯柏.柯拉斯
珍娜本來已經快要睡著了,偏偏這個開門進來的人毫不謹慎、不曉得要放輕動作,反而笨拙地衝進來。起初珍娜以為是她對大衛的想念把他召來了,以為他到醫院來看她的情況,也許來問他可不可以搬回家;但是這個人比較矮、比較粗壯。珍娜努力想藉著門口透進的光線看清那張臉,但當他關上房門後光線就消失了。也許是個新來的清掃人員,還沒學會躡手躡腳地進病房為病人倒垃圾。但是病房裡有足夠的亮度可以看出他並未穿著清潔人員的鐵灰色制服。他穿著一件寬鬆的長T恤、牛仔褲和慢跑鞋。他呼吸急促,似乎剛剛爬樓梯上來。他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門邊,頭對著病床,等待眼睛適應光線。
她的訪客靠近床邊,伸出手。「我叫賈斯柏。賈斯柏.柯拉斯。」
「告訴我你是誰。」
賈斯柏呆了片刻,想決定事情該如何進行。「我是開貨車撞上妳的捐贈者的人。」他說:「一年又三個月前。二OO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妳沒想過是誰做的嗎?呃,是我。我就是妳要的人。」
珍娜覺得自己因無法置信和恐懼而冒著冷汗。她全身都緊張起來。他說對了日期,這令她驚奇。賈斯柏.柯拉斯,她對這個名字有點印象,她心想,從報上一則有關伊莎貝爾車禍的報導,報導中必定提起過他。小貨車的駕駛人,她不會故意忘掉那個名字。她鬆開放在叫人鈴上的手,難以相信這就是他,撞死她的捐贈者的人。她呆若木雞,想到要不是這個人的粗心大意,或不管是什麼,她可能已經死了,令她既驚奇又惱怒。
「你說那是意外。」她說:「所以你不是故意那麼做的。撞死一個人。」
賈斯柏用手指敲著床板。「她騎在馬路中間,在我這線車道的中間,我根本沒時間煞車,沒時間減速。她被坡頂擋住了,我一駛上山坡,她就──」他猛地拍了一下手。
珍娜忍不住想,賈斯柏說的是否是全部的真相?他是否省略了一些對他不利的細節,例如他的車速和他沒注意到單車,可以讓艾力克斯和伯妮絲要他負責的?她自己也必須更勇敢,才有可能去探問這些問題。她很害怕,這個人,據她所知是唯一的目擊者,要聽他談論那場車禍和他可能告訴她的話令人感到害怕:鮮血、殘破的肢體、傷口。
賈斯柏走到床邊。「她被一輛貨車撞了,這妳知道吧?結果妳得到了她的心臟。」他以眼睛打量她的身高。「她的個子跟你差不多高。她的心臟一定很適合妳。」
珍娜將被子拉到胸口。「我不想像在討論鞋子一樣討論心臟。它的大小正好適合我的身體,那很棒,但並不只是這樣而已;我們的血型相同、我們有四種抗原一樣,那很罕見。」
「妳喜歡那樣,哼?血型?抗原?這件事還真讓人覺得溫馨啊。」
珍娜武裝自己,準備辯論。「你是不是想說,我不明白要不是你撞死了一個器官捐贈者,我現在不可能活著嗎?我明白。你不用一直提醒我。」
「我並沒有要提醒妳任何事情。」賈斯柏將兩手平伸,強調他極力避免發怒。「我只是想確定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幻想。」
他說「幻想」那兩個字時,她想起大衛的聲音。在最近的一次談話中,大衛指控她固執、冥頑不靈。
「我敢說那天晚上這裡應該很歡樂吧。」賈斯柏說。
「是的。」珍娜決定說實話。「大家都很高興。」回想其當時的感覺,她感到驚駭。「很多人到病房來向我道賀,還有親吻和擁抱。」
「沒有人來向我道賀,沒有人親吻和擁抱賈斯柏;倒也不是我期望得到就是了。」賈斯柏走到珍娜的點滴架前,細看滴入珍娜體內的抗排斥藥劑。他伸出手,手指張開,像是要碰觸一個按鈕。「另一方面,如果妳意外撞死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器官被送去救活其他人的命,妳會覺得至少應該得到點什麼;一通電話,或一封信。」
「不要碰那個。」珍娜說。
賈斯柏縮回手。「妳不認為嗎?」
珍娜深吸一口氣,讓自己鎮定下來。「聽著,賈斯柏,我不想低估你……所給我的。」她想到艾力克斯和伯妮絲若聽到她這麼說會有什麼反應,忍不住在心裡呻吟。「可是一個人不能走險路去酬謝害死別人的人,無論那是不是意外。每當有人建議器官捐贈者應該得到補償時所引發的爭論就已經夠多了。」
賈斯柏拉來一張凳子,在床邊坐下,一邊試驗性地轉著凳子,一邊上下打量她蓋著被子的身體。「器官捐贈者。器官捐贈者是很了不起,很慷慨。不過,說真的,器官捐贈者只是一些口袋裡裝著捐贈卡的人。光只有器官捐贈者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毀滅的代理人。器官取得體系、醫療體系,不管你說的是哪個體系,這些體系中沒有人喜歡談到真正使一切可行的體系,那就是美國機動車死亡體系。」
賈斯柏站起身,把凳子推開,朝房門走了幾步。「妳不覺得這裡太亮了嗎?」他說著,把燈關掉。「別誤會我的意思,妳活著是很神奇的;妳是我的一線希望,妳是我從灰燼中長出的一朵花。」
「我不是你的花朵。請把燈打開。」
賈斯柏看起來很受傷。他朝她走了幾步。「好吧,伊莎貝爾的花朵;但妳是我種出來的。」
「你沒有。」珍娜說:「你不能自稱你也有像她那樣的先見之明和慷慨。如果你堅持說那場車禍只是意外──不是你預謀的──那麼一切就都不是預謀的。總之,我怎麼可以感謝你呢?那是不得體的,那很卑劣。」
「我並不要妳感謝我。」賈斯柏的聲音透著怒意。「我只是要妳……」他似乎不知道。他看起來困惑且不知所措。他的目光在房間內巡視,好似他第一次看到這間病房。他的注意力又轉回到她身上。他走到床邊,站在很靠近她的位置,兩手垂下在身體兩側。他的手指粗短,左手腕上有一條細細的粉紅色新月形疤痕──是貓的抓痕嗎?他的目光在她的胸口上徘徊。珍娜覺得他的眼睛流露出複雜又混亂的需求。
賈斯柏問:「我可以摸嗎?」
珍娜準備要尖叫和撲打了。「我想你最好離開。」
「嘿,別這樣。」賈斯柏平靜地說,抱著一絲期待:「我才剛到啊。」
伊莎貝爾.霍華
伊莎貝爾低伏在單車上,雙手壓低,兩腿用力踩踏。她的單車衣背部已被汗溼透,緊貼著皮膚。汗水自她的額頭和太陽穴淌下,不斷滴進她的眼睛。她以戴著手套的手背抹掉額頭上的汗,然後以三根指頭輕按頸動脈,感覺血管的跳動。
一小時前她離開鎮上時,天色已經有點陰暗,現在還起了風,雲層快速地流動著。天空一片墨黑,空氣裡飄浮著溼氣和堆肥的氣味,電話線上的紅翅黑鸝鳥噪動不安,她猜在大雨傾盆落下之前,還有五到十分鐘的時間可以騎到鎮上。
風又猛又急。她減少了握住把手的力道,好減輕單車的受力;接著放低身子,以...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