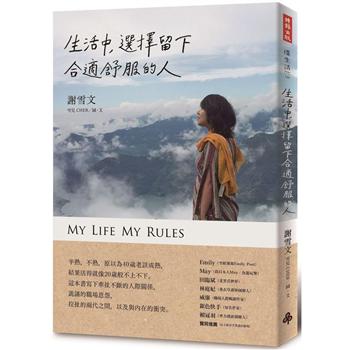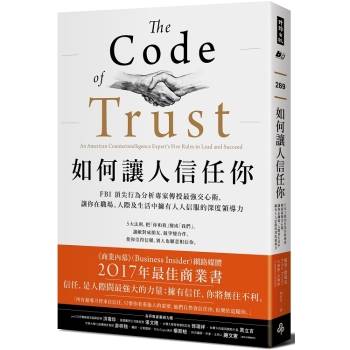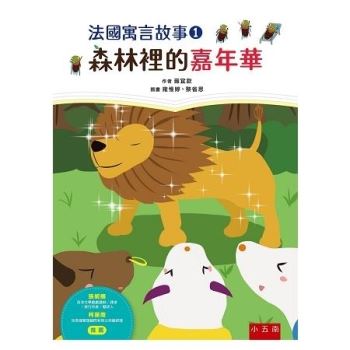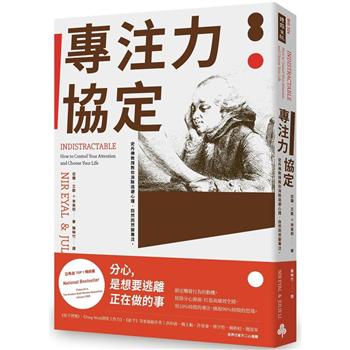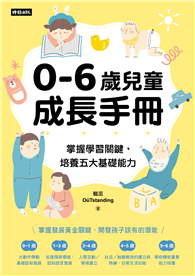作者序
海是我們共同的前世
在這東海岸的大學已進入第十一個年頭。台北花蓮奔波來回,歲月匆匆,儘管總有心神耗弱、勉強上路時候,但,回到那片海,這個畫面映入眼中,我便又可以打起了精神。
有時是從氣流搖晃的高空,有時是在昏沉搖晃中的隧洞,突然,那片海就張開了他的懷抱。
凌空鳥瞰地圖上的海岸線,竟成了一筆藍絹上的揮毫。飛白。渲洗。皴刷。潑染。這座島是美麗的,因而造物者在此題款。
鐵軌穿山,頃刻豁然眼開,不論陰晴,海面總是耀目。人生一站過一站,能在無盡的跋涉中有海相伴一段,便得到心情的沉澱。
從小都是身在繁忙擁擠的城市,十一年前從紐約回到台灣,竟在看似空寥寥的濱海之鄉紮下另一個據點,作家朋友們都不相信我能在此久留。尤其在歸國第二年母親過世,突然而毫無心理準備,遊子返鄉卻更覺孤伶。
請假一個月,從母親病危到辦完後事,再一次拎起行囊回校上課,當時只有滿心的茫然與不孝的自責。出了機場,電話預約好的計程車等在那兒,載了我一學期的司機先生問我:直接回學校嗎?我失神地看著他,那個山東與阿美混血的年輕人,不知道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結果他幫我做了決定,把我載到了海邊。那是個風浪很大的午後,僅兩三個海釣客的身影。司機放我在石堆間坐下,他走開到另一頭看漁船拖網。我並不想跟任何人說話,他似乎知道,於是把我交給了海。
那個下午,海就這樣一點點含納了我的悲傷,用一種沉穩的節奏,帶我找回了自己的路,讓我終能平靜的呼吸而不哽咽。天蒼雲低中的那片海,有個名字叫太平洋,我唸著這三個音節,想起了多年前第一次來此,住在面海的旅館,天還濛濛亮便聽見母親邊叫喚著,邊嘩地一聲拉開了窗簾:「快看!太平洋上的日出喔!」海洋的聲音與母親的聲音合而為一,超越了時間,沒有生死界線,看不見開始或盡頭。但,我突然感覺有了一片自己的海。加州明媚的藍天碧海勝地我見過,法國浪漫優雅的度假海灘也去過,但眼前的海是那麼樸實而平易近人,原來這是故鄉的海。
司機先生遠遠從拍浪處回望,一個下午的生意泡湯了他並不在意。愛海的人有種溫暖的慷慨。
生長在四面環海的國家,之前的我對海竟如此冷漠,自己都有點吃驚而慚愧起來。更汗顏的是,我到現在仍然沒寫出一篇有關海的像樣文章。彷彿是相處越久,他越像家人般親近而有了一種私密。家人總是最難下筆的,一想到總是千頭萬緒。雖然十年光景中,有一大部份時間都跟這片海有關,但是總自覺比起更親近海洋的一些作家來,我跟海洋的交情未免淺薄了些。
如果一個人寫不出一整片海,那麼可不可以很多人一起來寫呢?這個念頭在我心中盤旋了數年。起初構想一趟邀集作家參加的海洋之旅,經費的現實面便難以克服。最後終於下定決心,那就來編一本海洋文學之書吧!
我與我的兩位學生,廖律清與何亭慧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蒐羅,同時發現,除了一九八七年由已故的林燿德曾編過的一套三冊的海洋選集外,將近三十年,我們的文壇或出版業界對這個題材竟興趣缺缺,這更堅定了我一定要把這本海洋選集完成的決心。
這回,我不循先前選集以小說、散文、詩三種文類的分冊法,而以「抒情的海」、「人文的海」、與「詩歌的海」分卷。這樣一來,重點便從文學史的思考轉移到了地域情感與生活歷史的紀錄。海洋不應只是設定成一種文學主題,對此地的創作者與讀者來說,它就是生命的記憶與文化的底蘊。三十年後的今天,不論島上的社經局勢如何轉變,不變的永遠是環繞著我們的海洋。他依舊質樸無華,依舊溫柔包容。想想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內陸國家,他們的人民畢生渴望見一次海,相對地,海就在我們身邊,是多麼幸福的事!
若只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海洋這個主題,或許有人要問,我們為甚麼就寫不出《白鯨記》、《老人與海》那樣的作品?但我希望,看過這本選集後的人就會明瞭,自然共存就是我們的海洋文化,我們的海洋語言裡沒有征服、搏鬥或廝殺。我們的血液中沒有海洋霸權的因子。海洋不是刻意浪漫的場景,也不是人性波濤洶湧的隱喻。在這裡,海是故事,海是生活,海是歌。
海是我們共同的前世,因而相聚於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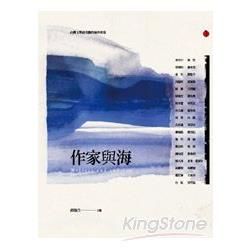
 共
共  作家特指文學創作上有盛名或成就的人,近代已泛指以寫作為職業的人。相對於「作者」一詞而言,「作家」一詞比較廣義,包括網上寫手、自由撰稿人、任何種類出書的作者都可以被稱為或自稱為作家。
作家特指文學創作上有盛名或成就的人,近代已泛指以寫作為職業的人。相對於「作者」一詞而言,「作家」一詞比較廣義,包括網上寫手、自由撰稿人、任何種類出書的作者都可以被稱為或自稱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