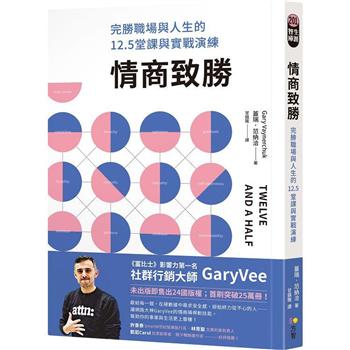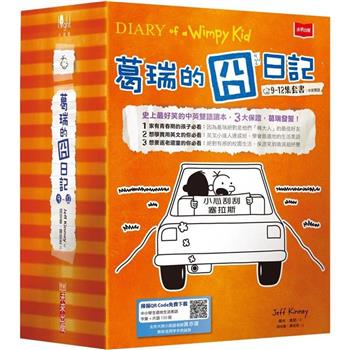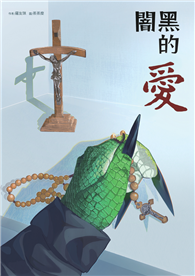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實際的天才──理察‧史特勞斯
理察‧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 1864—1949),被喻為李斯特(Franz Liszt, 1811—1886)的交響詩、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的歌劇的傳人,卻有著和二者完全不同的行事風格。一生身兼當代名指揮家、名作曲家的身分,讓人對他又羨又忌。
史特勞斯雖然長壽,但是身體並不健壯。由於懂得保養,卻也平安無事地活到八十五高壽。在生活裡,他篤行華格納的「天才至上論」,明白地為自己、進而為其他的音樂家爭取應有的權利。由於經常事涉金錢,而被譏為貪利者。然則一生處事講求實際的史特勞斯卻並不在乎,事實上,他若沒有這份「實際」,不可能早早購置嘉美別墅,亦不可能為我們留下那麼多的音樂財產。
行事似乎斤斤計較的史特勞斯在音樂中流露的卻是多層次的高級幽默。在經過狂飆的年輕期後,1890年代裡,史特勞斯開始發覺自已的人生觀其實是旁觀樂天的。這個情形在交響詩作品《狄爾的惡作劇》(Ti11 Eulenspiegels lustige Streiche, 1894/95)、《唐吉訶德》(Don Quixote, 1896/97)中已可見端倪,在歌劇《火荒》(Feuersnot, 1901)中更是明顯。雖然緊接著的兩部歌劇《莎樂美》(Salome, 1905)和《依雷克特拉》(Elektra, 1909)讓他奠定了歌劇史上的地位,史特勞斯卻以《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 1911)的作者自許──1945年,他如此告訴前來接收的美軍。
作品中洋溢著愛的作曲家,私底下卻是個感情極其內斂的人。經常登台指揮的音樂家,在私人場合像是個謎。史特勞斯不在乎外界對他個人的批評,卻很在意妻子予人的潑辣形象,數度以作品將他對妻子的愛意訴諸大眾。失掉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1, 1874—1929)這個工作上的夥伴,史特勞斯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卻在他人為他慶八十五歲大壽時,要求演出《那克蘇斯島上的阿麗德奈》(Ariadne auf Naxos)1912年的第一版,因為那是老夥伴主導的大構想,結合話劇和歌劇演出於一劇,可惜首演效果不佳。八十五歲的老人在等待大限之際,強烈地思及去世多年的老友,指定這部作品,自有其不為人知的心境和等待。霍夫曼斯塔去世的廿年裡,史特勞斯再也找不到能和他合作的劇作家,口雖不言,心中對老友、老夥伴的思念是可以想見的。
一生順遂的史特勞斯卻在老年栽在納粹的手中。他一生篤信藝術至上,願為藝術的存續做任何事情,包括表面上的妥協。他的不離開德國,不僅是因為年事已高、不僅是因為猶太兒媳,更是因為不願看到德國的音樂藝術傳承中斷。他對自己當時在這方面的重要性的認知,以及他認為無論在何種狀況下,藝術都不應該停頓、被犧牲的信仰,讓他雖不情願,卻能在表面上妥協。因之,最後的妥協不成,是讓老人迷惑、更讓他傷心的。
但是,史特勞斯旁觀的睿智和樂觀的人生觀,終能讓他活著親見大戰的結束,亦讓他度過審查納粹舊案的難堪日子,更讓他在1948年的垂暮完成《最後四首歌》,呈現一位智慧老人回顧走過的人生歲月,泰然地面對人生最後時刻到來的心境。史特勞斯的配器不復年輕時的意興風發和戲劇性,取而代之的是晶瑩、透明,清楚地流露出他的這一生沒有什麼大遺憾,該走的路都走了,該做的事故做了。最後一首《黃昏》(Im Abendrot)老人與愛妻心手相攜走完人生的景象躍然於音符間,作品辭世之味雖濃,然而展現的平靜、澄澈,和馬勒同樣使用管弦樂伴奏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的最後樂章〈告別〉(Der Abschied)的意境又是大不相同。一生以音樂為其語言的史特勞斯在此依然,在聲樂部分唱出最後一句「莫非這就是死亡?」時,法國號吹起《死與變容》(Tod und Verklarung)中和「死亡」相對的「變容」主題做為回答,將史特勞斯一生不變的人生觀再度呈現。
在這一史特勞斯本的傳記中,作者大衛‧尼斯引用了許多當代的人和史特勞斯往來的信件、對史特勞斯行誼的敘述,生動地勾畫出一位自視極高、卻能入世的天才。他對白己存在價值的認知和自信,對藝術高於一切的推崇,他如何活好每一分一秒,在面對人生必有的終站,那份安詳、那份坦然,作者沒有用很多炫麗的字眼,卻活生生地都勾畫出來了。
德國海德堡大學音樂學博士
現任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羅基敏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