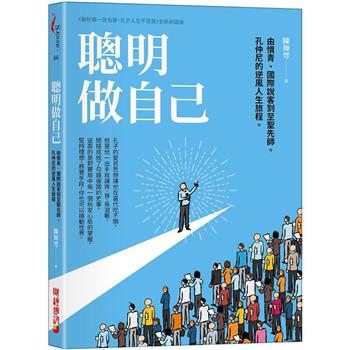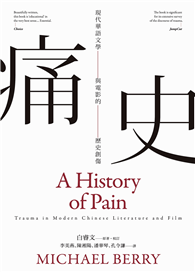(如果)我的姊姊是石原聰美
「啊,幹。」
我的視線從電腦螢幕前抽離,打直胸膛,看向坐在一旁的姊姊。
「怎麼了?」
「你看。」
她舉起手中一瓶易開罐的寶礦力水得,拉環移位微微翹起,看來是打算打開可是失敗了。
「指甲斷了喔?」我問她。
她搖搖頭。我覺得也是,我姊是絕對不可能把她的指甲伸進易開罐拉環中間然後被掰斷的。
「你看。」她彎下腰,從地上撿起兩塊不知名的物體。
是從中間斷成兩半的信用卡。
「妳真的很誇張。」
一
我媽對我姊,特別是離開家裡之後的我姊,一直覺得她「有病」。潔癖到有病,吹毛求疵到有病,連流眼淚頭都要跟地面平行讓它直接滴下去不能碰到肌膚會傷到,整個人都有病。但對我姊來說,這些是理所當然,更甚至,她覺得她從以前所在意的小細節,例如下雨天撐傘搭捷運一定要長傘,然後一定要套透明袋子,這些都是身為一個人維持基本的步驟。
「不然雨水會濺到別人身上。」姊姊小時候曾經解釋給我聽過。
我會覺得,我媽說我姊有病這件事對她來說是一個赤裸裸的攻擊。說她有病,不是正常的,是代表,我媽才是正常的,而正常是應該的。只是姊她也希望自己是「正常」的,所以面對我媽那種妳不正常妳有病活不下去啦的態度,會特別惱火。
「那如果旁邊的人傘上面的水濺到小腿上一點點點點點點妳OK嗎?」我問姊姊。
「我當然可以啊!」姊姊說:「可是就會對接下來要見的客戶或朋友很不好意思,褲子上有水漬的話對對方超不尊重的,所以其實是不OK。」
「沒家教。」姊姊這麼補充。
我覺得這個地方可以完全展現出我姊對自己的態度,就是「有病」其實沒差,我姊大約心底也覺得自己有病,可是是真的那種病,關於人的缺陷,她不會逃避與否認。但敢說她不「正常」,並且同時還宣稱只有自己是「正常」,例如我媽,她就會整把火燒起來。
「那妳會覺得媽有病嗎?」
「不會啊,就覺得她很髒而已。」
或許是同樣都抱持著類似的想法,我和我姊,兩個人都已經許多年沒有回高雄了。太久沒回去,過年不回去、中秋不回去、阿媽的生日,兩個人都有默契地缺席。每次春節左右,我媽都會打來探聽一下今年的風聲。幾年前還是:「你姊已經說不會回家過年了,啊你有要回來嗎?」也慢慢變成:「今年過年回來一下吧?」總之我們可能都已經忘記自己上次回家是幾歲的事情了。
但其實年這件事,或者說,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兩人和這個世界標準不太一樣的地方。我姊的記法是:十八歲之後,就沒有年了。所以一般人認為的十九歲生日,對她來說是十八歲又三百六十五天。二十歲,是十八歲七百三十一天,她剛好那年是閏年。大約是這樣的算法,據她自己說,一個人大約是十八歲三萬天左右。
我的話比較簡單。我十七歲,大約從十多年前就是十七歲了。一直到今天,明天,都會是十七歲。
堅持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我和我姊都造成許多困擾。例如上一個冬天,我曖昧對象是個還得每天穿著制服去搭公車上學的小女生。她明明晚了我滿多年出生,但在我們認識時她卻已經大我一歲。她十八,我十七。她跟我姊同年,我姊比她大幾天而己。幾千天吧。但其實還好,十七歲的少年對這個世界本來就很不友善。我十七歲很多年了,一直在嘗試跟這個社會找到共識,但也一直失敗。人習慣自己不成功的樣子久了,也會覺得改變沒什麼必要。
我姊再三跟我確認,在台灣和高中女生交往沒有法律問題。她那天很誇張。就是,平常她就很誇張,但那天當我跟她說我正在跟一個大我一歲的姊姊來往,瞬間眼睛瞪大,死死地盯著我看。在日本,和還在學校的未成年少女有戀人關係是一種犯罪。但我覺得我姊只是擔心,怕十七歲的弟弟還不懂事,會被十八歲的女學生給套路走。
「喜歡年紀大的女生你很有經驗。」她這麼說:「但不是這種。你要有幾次十七歲我不管你,只是上次跟我說你喜歡的女生是十八歲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記得嗎?」
她那天忘了帶現金出來,我們約在一家小巨蛋附近一間韓國餐廳。從UNITED
TOKYO 的紅色褲子裡撈了半天,那件寬寬的,口袋也特別大,但最後只有一個十元銅板。她打開皮夾,是有鈔票沒錯,但,是日幣,一萬的三張五千的一張。我懶得嗆她,
她走進店裡時,穿著紅色西裝外套一身紅還配一頭後梳All back。我已經整個大傻眼了那時,這樣大根的辣椒在台北街頭行走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幸好最後那家餐廳可以刷卡,我那天是沒打算付錢的,完全沒有。
二
我姊口中那位,上次我喜歡的十八歲女生,是我們的鄰居。我們什麼時候認識,可能都得從各自出生開始算。因為嚴格來說,是我們兩家人的爸媽認識,朋友關係只是我們三個人降生於世時的贈品。
林卉慈作為一個水象星座,我認識最久的一位天蠍,我們在國中時一起偷了人生中第一台腳踏車。我姊沒有參與,身為一個以後要當女演員的人,小時候當然不能偷腳踏車。她只是站在旁邊看而己。
從小我們兩家出去玩,我永遠可以獨占一張床。因為從我姊和卉慈進房門開始,世界上就不會有比抱著棉被躺著聊天更重要的事了。吃飯也是三催四請的才上桌,吃沒幾口就說吃飽,回房間繼續講。有時候晚上還會把我趕去爸媽房間睡,她們兩個在遊覽車上睡飽了所以會一路聊到天亮。小學的時候,到了禮拜五或是週末的晚上,姊她就會問爸爸要不要去卉慈家。爸總是會很無奈地說:「還去啊?」「每個禮拜都要去啊?」他跟林伯伯是同事,早上要看到林伯伯一整天,放假了又要再見面。我姊每次一進去卉慈家,迅速地打了聲招呼就會直接衝上卉慈房間。我一般都還會繞去廚房看一下,摸一下,反正上去她們兩個女生也不會理我。
小一升小二那年暑假,我們三個報名了暑假游泳密集班。教練是個國字臉、肌肉很大的哥哥。在國小門口拿到的那張傳單上說,保證三個禮拜讓孩子一次學會蛙式、自由式和仰式。我姊在第三次上完課跟我媽說,那個教練哥哥上課的時候一直拉卉慈的手,還會抱她。隔天上課,哥哥就不見了,換成了一個有點年紀的阿婆。阿婆其實算大肌肉哥哥的師父輩,也就是我們的祖師爺,嗎?臨時要找沒有爭議的女教練來填這個空好像很困難,最後沒辦法只好去請以前聽說是專門在訓練國手,但早就退休的婆婆。婆婆第一天上課看了我們的游泳姿勢瘋狂搖頭,就刁了我們的蛙式一整個夏天。自由式什麼的,依阿婆的說法:「毛長齊再說。」
我們兩家住在旗津,是一個高雄港外邊的沙洲,南邊和前鎮有一個海底過港隧道連接,是我們通勤來往台灣本島的主要方式。北邊則是跟鼓山渡輪站有對開的遊輪,每每放假觀光客便會癱瘓那附近交通。從我們家的窗戶看出去就是高雄港,在對岸站著六台很巨大,好像一塌下來就是世界末日的貨櫃起重機。爬到頂樓水塔會發現四周望出去都是海,也因此,學會游泳小時候對我們的意義可能跟後來開始騎機車差不多,好像自己可以到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
對高雄來講,不適合下海的日子只有兩種,一種是颱風天,另一個是冬天。這兩個加起來大約一年有一個月吧,所以剩下十一個月都是我們衝進海浪裡玩耍的天氣。我們最喜歡中洲汙水處理廠後那一塊水域,那邊最刺激。別的區域浪的頻率可能是三小一大,或者四小一大。但那塊海域,暗流多,特別混亂。勉強要講,旁邊廟口的阿伯都說這裡的浪是九淺一深。意思就是以十次為一個周期的波浪,也可以說要別的地方三個海浪周期的能量積累才會爆發一次。但那一「深」來得十分隱祕,往往等人有意識的時候,已經來不及掙脫了。
要判斷那道「深」是有訣竅的,它會躲在幾個浪中間,就像正常的而已。但在靠近岸邊第三次下墜之前,因為地形的關係,會不規則地突然吸收前後兩波浪的能量長大起來,從視線抬高壓過遠方的海平面。對海不熟的人很難想像那道「深」撞上岸的規模,只是感覺有一點不一樣。我小時候作了許多次惡夢,就是泡在海裡的我旁邊突然出現一道「深」。被浪往海裡扯過幾次的自己,當然深知海的可怕。不斷地往前撲,想要回到岸邊,海卻一直拉著你,往你自己身後去。廟口的老伯說,那邊又叫九死一生。
我沒有被「深」捲進去過,我們三個人裡面唯一遇到過的是卉慈。她說,那很像一隻鯨魚出現在身旁,然後把人吃進去後,迅速地下沉回深海。幸運的是,小時候那隻鯨魚並沒有帶走她,我和我姊拚命把救生圈壓進水裡給卉慈後勉強讓它失敗了。三個人回家時都沒和大人提到這件事,這是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的祕密。
三
其實和一般想像的不一樣,我很少看姊姊的作品。不管是電影還是電視劇,倒不是因為太熟所以看到她出現在螢幕上會尷尬,而是單純身為一個社會人士,並沒有那麼多時間而已。不過作為弟弟,我還是常常能感受到當她弟弟的壓力。特別是長大後,有些場合總會碰到介紹我時我姊被提起。應該說,每一次。如果只是我單獨出現,可能在吃飯,在工作或研討會上有人說欸他姊是石原聰美耶!大家可能反應不會太大。因為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石原聰美,更不是所有人都對我姊感興趣。大部分的反應不會太大,但我可以從那個人介紹時感覺得出來他對我跟我姊的看法。如果是:「欸他姊是石原聰美耶!」這個人很大可能是她的粉絲,至少是對我姊是有好感而且會注意的。這句話裡,往往有驚訝有羡慕。
不過有一次,在我剛去日本就學時,研究室的教授邀請大家去家裡吃五平餅賞月 。「他是石原的弟弟喔!」教授這樣和師母介紹:「石原聰美的弟弟,就是這個人喔!」那是一對很善良嚴謹的老夫婦,聽到教授這樣的介紹時我趕緊回:「家姊一直以來受您照顧了。」師母笑著回:「姊姊有這麼一個漂亮的弟弟也真是辛苦了,我們家老的一直給你們年輕人添亂吧!」我其實分不清楚這是不是禮數周全的夫婦一貫的溫柔或是客套,但卻讓我第一次見面就好喜歡她們。
從很小的時候,十七歲吧,我就決定我這輩子最討厭的星座是魔羯座了。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媽是魔羯座。但這邊有一個有點尷尬的問題。我姊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十四日。雖然我上次祝她生日快樂己經是十七歲的事了,不過我有一直記得。我姊是魔羯座,最討厭的魔羯座。但我不敢討厭她,雖然她也很討厭我媽,但她絕對不能接受自己因為那個老女人而被牽連進自己弟弟最討厭的星座。所以我一直沒讓她知道這件事。
但我從來沒有討厭我姊,她完全沒有那種我媽魔羯座讓我討厭的尿性。也有可能是因為,從以前我們兩個就基本上是同一陣營的。我媽是大魔王,最討厭的人,魔羯座。而我姊是走在我前面的人,勇者,比我早十秒想到怎麼回嘴的聰明人,房門甩下去之前還會記得把弟弟一起拖進來的姊姊。姊姊很有想法,而且想法跟我很像,我們都跟媽媽不一樣。她比我勇敢,她比我善良,她也比我厲害。我很喜歡她,雖然她是個魔羯座,但我媽那些討厭的點,在她身上都不存在似的。全世界唯一一個好的魔羯座,我媽那些用來摧毀我信心的言詞,被她吸收後都變成她回打我媽的方法。所以我真的很討厭魔羯,但跟我姊無關。
我十七歲她十八歲又幾天那年。那陣子她和我媽的意見衝突已經多到沒有我上場的份,每次都是一挑一的個人戰。我媽大約也沒預料到最後會是這種結果,隔天早上還是準備了我姊那一份麵包和優格加桑葚果醬。但姊姊一直沒有出現在餐桌旁。我媽要出門上班時,她右手拿著鞋拔把腳塞進平底鞋,跟我說:「去叫你姊出來吃早餐。」
我說:「她昨天凌晨出門了。」
我媽本來看著地板,安靜了幾秒,抬起頭有點責怪地問我:「你怎麼都沒跟我說?」
姊姊的房間是我們家的風口,她在我們整間屋子的正南面,是風灌進來最多的地方。我的是在正西邊,所以我跟她的窗戶看出去景象是完全不同的,雖然大部分都是海。我姊離家後,家裡的人像是在躲避什麼一樣,沒怎麼在那裡進出。爸媽可能是,還不能接受吧,我不確定。但我的話是因為那時是我第一次十七歲,走進她房間時,有一股特殊的香氣。那時心裡總會產生一些奇怪、害羞的想法,讓我不敢待在那裡。所以反而大約半年後,最常進出她房間的人是林卉慈。
卉慈常一個人跑去她房間待著。偶爾會傳出音樂旋律,或冷氣開關的嗶嗶聲。每次她回家前都會順道過來旁邊我的房間跟我打招呼,彼此問一下這禮拜發生了什麼事,電視上陳漢典又模仿了什麼。她會曲起雙腳坐在我的床上,看著在旁邊書桌讀書的我。我的檯燈剛好只能照到她塗了粉色系指甲油的腳趾甲和腳趾頭,小腿以上都隱身在黑暗裡。短頭髮長度大約到耳垂,靠過來看我的教科書時會晃到我臉頰上。文科還好,但理科的話,她大約認真在旁邊盯著頁面二十秒後,就會靠回床上,說,不懂。然後傻笑一下。考學測前一天晚上,她陪我念書到很晚。臨走前跟我說明天加油,並告訴我,她交了一個男朋友。這句話搞得我直接成為指考戰士。
上大學那個夏天,我自己一個人北上。姊姊那時才剛在電視上出現了幾個月,我在搬宿舍那天,她突然跟我說她要去美國。多久不知道,是經紀公司出錢的。我問她:「什麼意思?培訓嗎?」
「不是啦,去美國一陣子就對了。」
「我是不是不能問多久?」
「對。」
我其實沒有自己的行李箱,就拿了姊姊留著的Samsonite BLACK LABEL 金色行李箱出門。挺質感的那東西。從台北車站搭捷運,在大安從紅線轉車時,午後兩點的陽光照進大片在月台之間移動天橋旁的落地窗。頭夾著手機的我突然發現,文湖線的顏色,在光影之間和她的金色行李箱是好類似的存在。
「那我也可以去嗎?」
「你去跟我製作人講。」
「這怎麼聽都很亂。」亂是我們姊弟那時喜歡的一個形容詞,並不是指淫亂或者混亂之類的,而是對一些兩人感到荒唐、不理解的事情的密語。
「是啊!」
「那要跟媽講嗎?」
猶豫幾秒,姊姊說:「講一下好了。」
「好亂喔!」我說。
「是啊!」我可以感覺到姊姊在電話那頭扶住了額頭,那是她覺得麻煩時的下意識動作。
不用擔心我啦—我以為她會這樣講,但她沒有。倒是傳了一張照片,背景是機場特有的大型格子窗。她的瀏海很爆炸,沒有化妝比她在家裡的模樣還土。手撐在桌子上,桌面還有一個白色的杯子,看起來像喝完的咖啡杯。奇怪的是杯口那邊完全沒有縐褶或水漬,好像全新沒有用過的。她笑得很開心,身上穿著一件長版T恤,我直覺是UNIQLO。她一直宣稱那是FRAY I.D 的,但我相信憑當時的她根本下不了手。
至於她去美國這件事應該是真的,畢竟週刊都有拍到,而且回來後那英文口說真是溜到一個不行。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像螺旋一樣的圖書 |
 |
$ 203 ~ 315 | 像螺旋一樣【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吳佳駿 出版社: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12-08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像螺旋一樣
你如果總是想著要有所看透,終究會陪著自己失敗。
光眩迷盲,這才是這個世界的真實。
──楊富閔 專文推薦──
一覺醒來,竟被從事醫美的高中死黨換了張臉!山林中傳來槍響,可是明明我才是槍的主人?如果姊姊是石原聰美的話,人生會是什麼樣子?……這些都太誇張了嗎?但是你又如何有把握自己真切了解身邊的人?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如一道長河,一趟只能自己完成的旅程,在偶然的節點上彼此交織,或者錯失。每一次的互動,都是一次交流、轉譯,甚或錯解誤讀;總有些美好印象會被篩留,然而或許最終其實我們都只是困守在自己的沙渚上,想像著那自以為是美好的一切……
吳佳駿以《新兵生活教練》初試啼聲之後,再次透過小說之筆叩問世間的真實與偽裝。作者以八個短篇,書寫八位各自關聯的男女;藉由不同視角的切換讓人物立體鮮活起來,同時帶引讀者看見每個角色,在「真」與「偽」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灰階」。而所有意圖將真偽界線判然二分的努力,終究是徒勞。
小說收尾的過港隧道是一個高度迷人的文學意象,那樣一條隧道,從幽暗出發,由佳駿帶路,鯨魚作陪。散落八篇小說的男一女一,不同人際關係的排列組合,不同的組織、單位,正在通過,通過這一條交錯閃著黃日光與白日光的暗路,這分分合合的世界──突然就像螺旋一樣。
——楊富閔
作者簡介:
吳佳駿
1995年生,高雄人。曾獲台積電青年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積電文學賞、葉石濤短篇小說獎等。著有《新兵生活教練》。
章節試閱
(如果)我的姊姊是石原聰美
「啊,幹。」
我的視線從電腦螢幕前抽離,打直胸膛,看向坐在一旁的姊姊。
「怎麼了?」
「你看。」
她舉起手中一瓶易開罐的寶礦力水得,拉環移位微微翹起,看來是打算打開可是失敗了。
「指甲斷了喔?」我問她。
她搖搖頭。我覺得也是,我姊是絕對不可能把她的指甲伸進易開罐拉環中間然後被掰斷的。
「你看。」她彎下腰,從地上撿起兩塊不知名的物體。
是從中間斷成兩半的信用卡。
「妳真的很誇張。」
一
我媽對我姊,特別是離開家裡之後的我姊...
「啊,幹。」
我的視線從電腦螢幕前抽離,打直胸膛,看向坐在一旁的姊姊。
「怎麼了?」
「你看。」
她舉起手中一瓶易開罐的寶礦力水得,拉環移位微微翹起,看來是打算打開可是失敗了。
「指甲斷了喔?」我問她。
她搖搖頭。我覺得也是,我姊是絕對不可能把她的指甲伸進易開罐拉環中間然後被掰斷的。
「你看。」她彎下腰,從地上撿起兩塊不知名的物體。
是從中間斷成兩半的信用卡。
「妳真的很誇張。」
一
我媽對我姊,特別是離開家裡之後的我姊...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過港隧道
楊富閔
最初接觸佳駿的小說是《新兵生活教練》,首先被他瞄準的軍事題材吸引,這條始終潛伏在台灣文學的一條文脈,重新浮現在佳駿的筆下,讓人驚喜;那是百年大疫,處處都在封閉。佳駿描述的那座新訓中心,好巧從我家門口出發,直直騎機車五分鐘就到了。那年剛好我人在大內,而且也在服役,只是我服的是家庭因素替代役,一整年都關在圖書館,本就低調安靜的圖書館,遇到三級警戒,入館人數更加低迷,而我就在退伍前夕讀著佳駿的新作。
再讀到佳駿的小說,則是在許多文學獎的初審會議,其中一篇〈川上的舞孃〉記得我...
楊富閔
最初接觸佳駿的小說是《新兵生活教練》,首先被他瞄準的軍事題材吸引,這條始終潛伏在台灣文學的一條文脈,重新浮現在佳駿的筆下,讓人驚喜;那是百年大疫,處處都在封閉。佳駿描述的那座新訓中心,好巧從我家門口出發,直直騎機車五分鐘就到了。那年剛好我人在大內,而且也在服役,只是我服的是家庭因素替代役,一整年都關在圖書館,本就低調安靜的圖書館,遇到三級警戒,入館人數更加低迷,而我就在退伍前夕讀著佳駿的新作。
再讀到佳駿的小說,則是在許多文學獎的初審會議,其中一篇〈川上的舞孃〉記得我...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
推薦序 過港隧道/楊富閔
夜永唄
無本生意
京都的星巴克們
最後的神木
川上的舞孃
木在層林中
在演習的早上開始寫的小說
(如果)我的姊姊是石原聰美
後記
推薦序 過港隧道/楊富閔
夜永唄
無本生意
京都的星巴克們
最後的神木
川上的舞孃
木在層林中
在演習的早上開始寫的小說
(如果)我的姊姊是石原聰美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