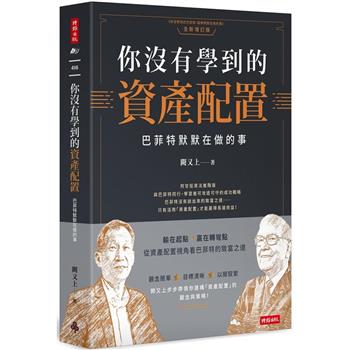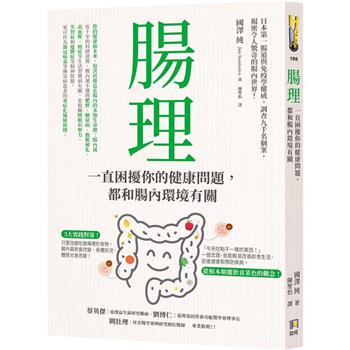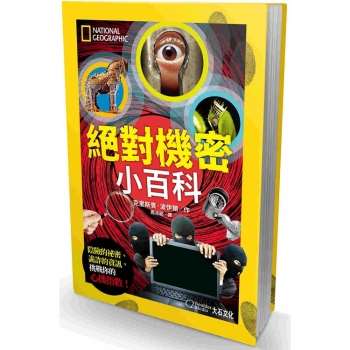代序
詩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主要形式;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近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對於近古各代的詩,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置之不理。中國的古典詩固然有其約定俗成的形式與基調,相沿既久,不容改變,卻不能因此就率爾斷定,以為無非陳詞濫調,毫無新意。事實上,在這注定的命運之下,古典詩還是在繼續不斷地推移和發展;問題在其推移發展的真相極為微妙,難於掌握,不易闡明而已。不過我確信如果敢於面對這個困難,必能對中國文學史,甚至於中國文化史,獲得更完整更周到的認識。我這個粗淺的研究,就是想充當陳勝吳廣的角色,希望有人引為同志,繼續並推展這個困難的研究工作。
以上是拙作〈關於漁洋山人的秋柳詩〉一文的結語。該文作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當時正逢中國國勢不振,世界上盛行著「東方文明停滯不前」的時髦論調。
爾後,歲月如流,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但我所企待的「同志」並沒有接踵而來。既然如此,只好勉為其難,再扮一下陳勝吳廣的角色,稍微擴大範圍,於去年先完成了《宋詩概說》,今年又接著完成了《元明詩概說》
我很希望這兩本拙著,能夠充分地受到日本學界的批評。是非優劣姑且不論,總之是我盡力而為的結果。過去我所寫的幾本著作,在國內往往如石沉大海,鮮有反響,反而總是先得到國外學者的評介。但願這次不會如此。
我想把自己與元詩明詩的因緣介紹一下,或許可供有意評論此書的人作個參考。
我與元詩或金元詩的接觸,開始於二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元雜劇研究〉的時候。為了論文上篇〈元雜劇的背景〉,必須蒐集元代有關戲曲的資料,所以曾經立下了「宏願」,要把現存的金元人詩文集全部閱讀一遍,或至少瀏覽一番。不知幸或不幸,這些集子全部加起來,其實也只能找到兩百種左右而已。不過,有關演劇的資料原則上不會出現在詩文集中,真是少之又少。這種調查的工作,就像在日本街上訪求愛斯基摩人一樣,不但要有耐性,也得靠運氣。幸而運氣還算不錯,終於在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裡,發現了一篇送給女伶的〈贈宋氏序〉,據其內容,得以確立了雜劇盛行的時代(詳《元雜劇研究》上篇第一章〈元雜劇的聽眾〉)。然而一旦有了收穫,「宏願」也就鬆懈下來。對著那些索然乏味的詩文集,興趣大減,越益感到海底撈針的徒勞,只好把剩下的稍加涉獵後,便草草收場了。
儘管如此,今天在日本與金元詩文集最有緣分的,說不定還是非我莫屬。還有一個人,為了搜尋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也曾細心地閱讀了所有金元人的集子。這個人就是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教授。但不幸的是,他在指出我的《元雜劇研究》有些資料的遺漏之後,不到幾個月,便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與世長辭了。
要之,當時我之所以涉獵金元人的集子,如上所說,另有目的,並非專為讀詩而讀詩。只是每看到自己喜歡的詩篇,便用朱筆做了記號。這原是無意為之,沒想到後來對這本書的寫作卻大有幫助。如果能像嚴謹的安部教授那樣一一作成卡片,那就更好了。
在金元作家裡,元好問最獲我心,所以把他的集子重複看了好幾遍。記得日本戰敗後一年,有機會與中國友人通信時,我曾寫了這樣的話:「平生所嗜,杜陵詩、遺山文,皆不祥物也。躬自閱歷,殆成言妖。」
至於我與明詩的結緣,則在元詩之後。
我的兩位恩師之中,鈴木虎雄先生酷好明詩。我在京都大學肄業時,就聽過他講李夢陽的課。狩野直喜先生卻正相反,以繼承清代學術自命;對於明朝文學成見頗深,認為是毒害江戶以來日本漢文學的罪魁禍首,故斥之不遺餘力。這位博聞強識,無人能及的先生,常說「不知明人的事」而引以自豪。有時也說過:「在明朝,曲也不行。好的只有小說。」
我聽從了狩野先生的教導,對明代的一切相當冷淡。偶爾翻翻明人的集子,也總覺得不大合乎我的性情。後來突發奇想,何不叛離師說,探討一下狩野先生不屑一顧的明代文學;那已是停戰的時候了。當時明野史叢書《紀錄彙編》的景印本剛剛出版,便找來隨意看了一遍;有感於明人的直情徑行,興趣大增,而引起了繼續加以探討的願望。
大概是停戰後的第一年,我還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時候,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請我去做了一次演講,題為「明代的精神」。那篇講稿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恐怕已經散失,不過演講的大意與本書第四章第一節所寫的大致相同。那時還在東北大學的小川環樹教授,因事來京都,談到「古文辭」運動。我說這個運動便是明人直情徑行的一種表現。他也贊成我的看法。
自從轉職到京都大學文學部以後,就一直想講授明清詩,但怕準備不足,遲遲不敢貿然嘗試,只好重複講授漢至六朝的文學。這樣年復一年,久而久之,忽然發現在這方面,已有年輕的學者開始發表起出色的論著來。於是,我才終於斷然改變了講授的時代。不過,我卻跳過明朝,而從清初的錢謙益講起。直到三年前,也就是大學學年的昭和三十五年度(一九六零─一九六一),才由錢謙益其人之詩再往上溯,利用並深入錢氏所編的明人詩選《列朝詩集》,正式開始講授明詩。在這期間,曾在《朝日雜誌》連載了〈沈石田〉一文,又為前輩橋本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寫了〈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
總之,我在二十年前就與元詩結緣,但對明詩有計劃的探討,卻是最近幾年的事。宋詩亦然。去歲,即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暑期,在完成了《宋詩概說》之後,就接著著手本書的撰述工作。那時已與哥倫比亞大學約好,定於年底赴該校訪問講學,所以不得不加緊努力,在出國前總算草草趕出了初稿,便隨身帶到了太平洋的彼岸。客居紐約期間,本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多看點英文的書,而事實上也盡其所能而為之,但是由於書店有交稿的期限,不得延誤,只好利用空隙進行修改,寫在航郵用的皮紙上,作成了第二稿。又經島田久美子小姐謄清後,我再加以補充,便是印成本書的第三稿。
本書的預告原為《元明清詩概說》,但由於頁數有限,而且我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只好暫時把清詩部分付之闕如了。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一次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住在該校招待所的二樓,早上在樓下的餐廳裡,偶然與一對英國人老夫婦同桌。他就是布里士妥爾大學希臘文學教授吉多先生。回到紐約後,買了一本他所著的《希臘》(The Greeks),一讀之下,才發現這本書也是半途而廢。不過,他在書裡說,如蒙上帝惠顧,假我數年,也許還有可能把剩餘的部分寫成一書。吉多先生看來比我年長。我在本書最後也說,盼能續寫一本《清詩概說》,說不定還有如願以償的機會。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