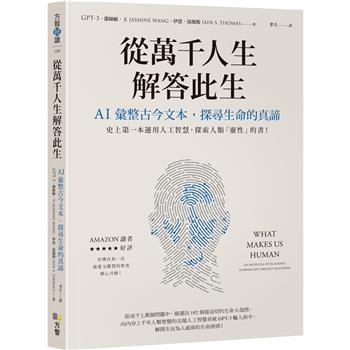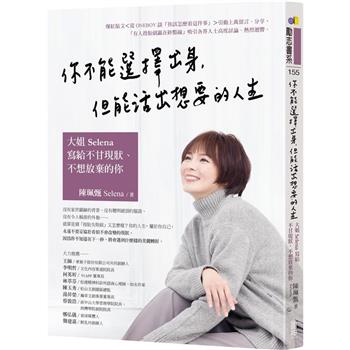1 被蠢蛋包圍
我以心理師身分私人開業那天,我沾沾自喜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我在我以知識搭建的 堡壘中,安於我習得的規則,很期待能擁有我可以「治癒」的病患。
我上當了。
幸好我當時不知道臨床心理學這一行有多麻煩,否則我可能就會選擇能夠控制受試者與變數的領域,純粹做研究。相反的,我必須在每週都有新訊息涓滴流入的時候,學習如何臨機應變。 在開業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心理治療根本不是心理師在解決問題,反而是兩個人面對面,一週又一週,致力於達成某種彼此可以一致同意的心理真相。
沒有人比我的第一位病患蘿拉.威爾克斯讓我更清楚地理解這一點。她是由一位全科醫師轉介給我的,那位醫師在他的語音留言裡說:「她會告訴妳細節。」聽到這個,我不知道是蘿拉還是我比較害怕。我剛從穿著牛仔褲與T恤的學生轉型成一位專業人士,身上是八○年代早期時尚必備的絲質上衣與厚墊肩的設計師西裝。我坐在我巨大的桃花心木書桌後面,看起來就像安 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跟瓊.克勞馥(Joan Crawford)的混合。幸運的是我二十來歲就早生華髮,這讓我的外表增添了某種非常必要的穩重莊嚴。 蘿拉幾乎不到五呎高,有著漏斗型的身材,臉上是大大的杏眼,還有一抹豐唇。要是晚個三十年看到她,我會懷疑她有打肉毒桿菌。她有著濃密的及肩明亮金髮,而她瓷器般的肌膚與她深 色的眼睛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完美的妝容、亮紅色的唇膏襯托出她的五官,身上是量身訂做的絲 質上衣、一件黑色的鉛筆裙搭配一雙細高跟鞋。
她說她二十六歲,單身,在一家大證券公司上班。她剛開始擔任的是祕書,但後來升遷到人資部門。在我問她我能幫什麼忙的時候,蘿拉坐著望向窗外許久。我等著她告訴我問題在哪。在 所謂的治療性沉默(therapeutic silence)之中——一種讓人不自在的安靜,理論上是要能從病人 身上導出真相——我繼續等待。終於她說了句:「我有皰疹。」
我問道:「帶狀皰疹或者單純皰疹?」
「如果妳整個人髒透了會得的那種。」
「性交傳染的。」我翻譯成大白話。
然後我問她的性伴侶是否知道他有皰疹,蘿拉回答說與她交往兩年的男友艾德,說過他沒有。然而她在他的藥櫃裡發現一個藥瓶,那跟醫師開給她的是同一種藥物。在我問她這件事的時 候,她表現得好像這樣很正常,而她對此無能為力。她說:「艾德就是那樣。我已經把他罵得狗 血淋頭了。我還能怎麼辦?」
這種司空見慣的反應,暗示了蘿拉很習慣這種自私欺瞞的行為。她說,她被轉介給我,是因為最強效的藥都無法遏制疾病反覆發作,醫生認為她需要精神醫學上的幫助。可是蘿拉很明顯沒 有進行心理治療的欲望。她要的只是解決皰疹。
我向她解釋在某些人身上,壓力是觸發潛伏的病毒發作的主因。她說:「我知道壓力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但我不怎麼清楚那是什麼感覺。我不認為我有壓力。我只是繼續過日子,被蠢蛋包 圍。」蘿拉告訴我,她生活裡沒有多少困擾她的事情,但也確實承認沒有別的事情比皰疹更讓她 傷透腦筋。
首先,我設法讓她安心,讓她知道從十四歲到四十九歲這個區間的人之中,六個人中就有一個長了皰疹。她的反應是:「那又怎樣?我們全都泡在同一池髒水裡。」我嘗試了另一個說法, 告訴她我理解為什麼她很心煩:一個宣稱愛她的男人背叛了她,再加上她身懷實際上讓她幾乎坐 不住的病痛,最糟糕的部分是羞恥。此後她必須永遠告訴她上床的每一個對象她長過皰疹,是帶 原者。
蘿拉同意這個看法,但對她來說最糟的面向是,雖然她盡全力擺脫她的家庭環境對她的影響,她現在還是在污穢中打滾,就像她家人一直以來那樣。「這就像流沙,」她說:「無論我多努力設法爬出軟爛的泥漿,我就是一直被吸回去。我知道的,我努力嘗試到要沒命了。」
我要求她告訴我她的家庭狀況,她說她不打算去講「一堆廢話」。蘿拉解釋說,她是個實際的人,而且她想要減輕她的壓力,不管那指的是什麼,好讓她可以控制住痛苦的皰疹。她本來計 畫就只來這麼一次,而我會在這裡給她一顆藥丸或「治好」她的「壓力」。我向她說明,偶有壓力或焦慮很容易解除的情況,但時常都會持續下去。我解釋了我們需要約診幾次,好讓她可以學 習壓力是什麼,還有她如何經驗壓力,以發現壓力來源,然後找到方法加以減輕。她的免疫系統 有可能盡全力在對抗壓力,以至於沒剩下任何力氣去對抗皰疹病毒了。
「不敢相信我真的必須這麼做。好像只是要來拔個牙,卻錯把整個大腦都拔下來了。」蘿拉看起來很厭惡這個結論,但她最後屈服了。「好吧,就讓我再預約一次。」
要治療一位沒打算取徑心理學的病人是很困難的。蘿拉只想治癒她的皰疹,而且在她心裡,心理治療只是達成那個目的的手段。她不想說明家族史,因為她想不通這跟治療皰疹怎麼會有關 聯。
在我開始做治療的第一天,有兩件事情是我沒預料到的。首先,這個女人怎麼可能不知道壓力是什麼?其次,我讀過數百篇案例研究,看過一大堆治療錄影帶,出席了幾十次教學訓練會 議,裡面沒有一次碰到病人拒絕提供家族史。就算我在精神病院裡值晚班的時候——在那個地方,心理學上的失落靈魂有如貨物,被他們儲存在後面的病房裡——我也從沒聽過任何人反對提供。有個自稱來自拿撒勒(Zazareth),父母是聖母瑪麗亞與約瑟夫的病患,就算是這種人也提出了家族史。而現在,我遇到的頭一個病人就拒絕提供!我領悟到我必須照著蘿拉怪異的方式與她自己的步調進行治療,否則她就會跑掉。我記得我在自己的筆記夾板上寫道,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讓蘿拉投入治療。
我們的下一次治療,蘿拉帶著四本談壓力的書走進來,書上貼著一張又一張黃色的 便利貼。她也抽出一大張圖,在上面畫出不同顏色標示的精細圖表。在頂端她寫下「壓力??????」,下面則是好幾個欄位,第一欄塗上紅色,標題是「應付混蛋」。次欄位裡寫出了幾個「混蛋」的名字:第一個是她的老闆克雷頓,第二個是她男友艾德,第三個是她父親。
蘿拉告訴我,既然她現在已經讀過了關於壓力的書,她會嘗試找出是什麼導致了她生活中的壓力。她花了一整個禮拜製作這張圖表。在我說裡頭沒有包括任何一名女性時,她仔細看著這張 圖,然後說道:「有意思。真的是這樣。我不認識任何混蛋女人。我猜想如果我有遇到過,我會直接避開,或者不讓她們煩到我。」我指出我們離壓力之於她的意義又更近了,然後要求她舉個例說明這些男人為何夠格登上她的名單。她跟我說:「他們任何規則都不遵守,而且真的徹底不在乎要讓事情行得通。」。
我告訴她,我很想建立她人生至今的歷史,尤其因為她父親就在這張名單上。蘿拉聽到這番話時,翻了個大白眼。我堅持不懈,繼續問蘿拉她對父親最鮮明的記憶是什麼。她立刻說,她四 歲的時候從一個溜滑梯上摔下來,被一片尖銳的金屬割傷了腳。她父親溫柔地把她抱起來,然後 帶她到醫院去縫傷口。他們在等候室的時候,一位護士講到蘿拉身上嚇人的傷口,還有她沒有哭 哭啼啼實在是太勇敢了。她父親伸出手臂環抱住蘿拉,然後說:「這就是我引以為傲的女兒。她 從不抱怨,而且強壯得像匹馬。」
她不曾忘記那天她從父親那接收到的是一個強勁的訊息,一個愛與柔情的宣言,仰賴的是她的強悍不抱怨。在我指出這種雙重含意的時候,蘿拉說:「每個人被愛都有某種原因。」很清楚 的是,無條件的愛這個概念,也就是無論妳做什麼,妳父母都會愛妳的觀念,對她來說很陌生。
在我問起她母親的時候,蘿拉只說母親在她八歲時去世了。然後,我問她母親是什麼樣的人,她只說了兩個我覺得有點不尋常的詞彙:「很疏離」跟「義大利人」。她想不起任何一個跟她有關的回憶。我再稍微施壓逼問她以後,她只說在她四歲的時候,她母親給她一個玩具爐子當 聖誕節禮物,而且在蘿拉打開禮物時露出微笑。
她也不確定她母親是怎麼過世的。實際上,我必須建議她多說一點。「她早上還好好的。然後我跟我弟弟妹妹放學回家時,家裡沒有準備午餐,這點很奇怪。我打開我父母臥房房門,看見她在睡覺。我搖搖她,然後把她翻過來。我現在還能在腦海中看到印在她臉上的床單絨線睡痕。 我沒有打電話給我爸,因為我不知道他在哪工作。我叫我弟弟妹妹回學校去。然後我打電話給九一一。」
警方找到她父親,然後用警車載他回家。「他們用一張毯子蓋住我母親的臉,毯子上印著多倫多東部總醫院財產。我完全不知道我為何記得這個,」她這麼 說。「然後那些男人用輪床搬運她下樓,我母親的屍體就消失了。」
「沒有守靈夜或者葬禮嗎?」
「我想沒有。我父親出去了,然後直到天黑過了晚餐時間都沒有人做飯。」蘿拉當時明白了做晚餐並且讓弟弟妹妹知道母親已經去世,是她的工作。她跟她六歲的妹妹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妹妹哭了,但她五歲的弟弟除了問蘿拉是不是會變成他們的媽媽之外,沒有其他反應。
我們在接下來的療程裡,回到蘿拉的父親身上。她告訴我,他曾是汽車推銷員,但在她小時候失去了這份工作。他總是有些由酒精、賭博及某種「誤解」造成的問題。儘管他是個金髮碧眼 的英俊男子,相當聰明又有個人魅力,他的社會階層還是往下流動了。
在她母親死去那年,她父親讓全家移居到巴伯坎基恩(Bobcaygeon),那是多倫多東北的一個區域。蘿拉認為有人在多倫多糾纏著他,而他搬走是為了躲避他們,不過她不確定。為了賺錢,他開餐車服務來避暑別墅度假的客人。弟弟妹妹在停車場玩的時候,蘿拉則做爆米花、薯條 供應這些遊客。他說她是他的「左右手」。他們住在城外的一間小木屋裡。屋主一家擁有幾間樸 素的小木屋,散布在他們地產上的樹林裡,地點偏僻又孤立。
他們手足三人從九月開始在那裡上學,當時蘿拉九歲。在避暑的遊客離開以後,餐車生意變得日漸蕭條。他們買了個小暖爐放在這棟只有一個房間的小屋裡,一家人依偎在一起。蘿拉回想 一次有兩個男人出現在他們家門口,要求他們為那輛餐車付錢,可是她父親躲在浴室裡。擺脫他 們是蘿拉的工作。
然後在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她父親說要開車進城去買香菸,一去就再也沒回來了。孩子們沒有食物,只有兩套衣服可供替換。在講到這件事的時候,蘿拉沒有展露出恐懼、憤怒,或者任何 感受。
她不想告訴任何人他們被拋棄了,就怕被送去寄養,所以她就只是繼續維持他們的日常生活。那間小木屋位在一個湖泊之鄉的森林深處,屋主是擁有三個小孩的五口之家。蘿拉跟屋主的女兒凱西玩的時候,那一家的媽媽葛蘭達對蘿拉很好。父親朗恩是個安靜的男人,常常好心地帶 著蘿拉六歲的弟弟克瑞格跟他自己的兒子一起去釣魚。
蘿拉很惱怒地說,她妹妹崔西「老是在哼哼唧唧」。崔西想去葛蘭達跟朗恩家,說有人帶走了他們的父親,而且想問是否可以跟他們同住。
蘿拉不像她的弟弟妹妹,她知道父親拋棄了他們。「他走投無路,欠別人錢,天知道還有什麼別的狀況。」她說。在母親死後,孩子們要是不守規矩,爸爸就會威脅要把他們丟在孤兒院,而蘿拉明白這不是隨口說說的。她只知道她的任務就是讓事情好好運作。在我問她對於被拋棄有 什麼感覺的時候,蘿拉看著我,就好像我在小題大作似的。她說:「我們不盡然是被拋棄。我爸 知道有我會處理事情。」
「妳九歲大,身無分文,獨自住在森林裡。妳會怎麼稱呼這種狀況?」我說道。
「我猜技術上來說這是拋棄,但我爸必須離開巴伯坎基恩。他並不想留下我們。他別無選 擇。」
在那一刻,我領悟到蘿拉跟她爸爸之間的情感連結有多強,還有她如何小心翼翼地自我防衛,避免感受到任何一絲失落。情感連結(bonding)是一種動物跟人類都有的普遍傾向,會向一位家長尋求親近感以形成依附,並且在那個人在場時感覺安全。蘿拉不記得當時有任何「感 受」,她有的就只是「計畫」。換句話說,她讓她的求生本能接管一切。畢竟要在荒野中度過加 拿大的冬天,還要照料兩個需要吃穿的幼童。蘿拉之後還會繼續嘲弄我不斷詢問她的感受,不止 一次指出感覺是那些過著逍遙日子、犯不著「絞盡腦汁」(這是她的說法)的人才擁有的奢侈品。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沒有通往蘿拉感受的入口,讓治療變得很困難。我很快就領悟到我的工作不是詮釋她的感受,而是去觸及她的感受。晚些時候我才會去詮釋它們。
當我在第一個月寫我的筆記時,我這樣總結:我有個不想投入治療的客戶,她記不清楚她擁有八年的母親,這種事在文獻裡聞所未聞;她根本不知道壓力是什麼,卻想要擺脫它,而且想不 起來她被拋棄時有什麼感覺。我眼前有很多工作要做。
蘿拉繼續描述她的磨難,很顯然當時她一直思慮清晰。她領悟到大多數的小木屋都已經為了過冬而打掃乾淨了,所以她跟弟妹們搬進最偏遠的那一間,那間在春天來臨以前都不太可能被打 開。他們帶著暖爐一起離開,知道他們必須維持例行公事,否則就會被發現,所以每天走將近一 哩路去搭學校的巴士。蘿拉會對外界提到她爸爸,就好像他還在小屋裡,並且指示她弟弟妹妹也 這樣做。
「所以你們在九歲、七歲跟六歲的年紀被單獨留下,住在一間小木屋裡,」我說:「如果妳在 找引起壓力的事件,這一件可以列入清單。」
「首先,這事情已經結束了,其次,我還好好的,」蘿拉反駁。「九歲其實沒那麼小。」 「這延續了多久?」
「六、七個月。」
在這節療程的尾聲,我總結了我怎麼看待這個情況。「妳一直很勇敢。妳的人生聽起來很艱 難,而且有時候還很嚇人。妳被拋棄,自己住在樹林裡,而且要為兩個更小的孩子擔責任,妳 自己要當他們的父母都太年輕了。」我說:「這是沒有麵包屑,卻面臨所有風險的漢賽爾與葛麗 特。」
她坐在那裡整整一分鐘以後才回話。在幾乎長達五年的治療裡,這是極少數她眼眶含淚的時 刻,然而卻是憤怒的眼淚。「妳講這種話幹嘛?」她質問。
我說我是在同理她,她駁斥我說:「這是有人死掉時才會講的話。醫生妳給我聽著,如果我還來到這,絕對不希望妳再做出這種事,否則我就走人。把妳的同理心還是別的什麼留給妳自己 吧。」
「為什麼?」我問道,真心感到困惑。 她強調:「在妳講到關於感受的事情時,我看到一道門打開了,裡面滿滿都是妖魔鬼怪,我絕對不會進去那個房間,我必須繼續過日子。如果我開始哭哭啼啼,就算只有一次,我都會溺斃。而且,這樣不會讓事情有任何好轉。」
在我點頭的時候,她補充說明:「今天在我離開以前,妳必須答應我,妳永遠不會再那樣做 了。否則我就不能再回來了。」
「所以妳在說的是,我對待妳的方式,絕對不要有一絲仁慈、同理或同情?」 「對。如果我想得到同情,我會從合瑪克(Hallmark)賀卡裡吸收我應付得了的分量。」
請記得,蘿拉是我的第一個病人。我不想跟客戶的病態需求做這種交易。然而我看得出來,她說要停止治療是認真的。來自我的一丁點同理心,對她來說就太過火了——這是她的底線,而且嚇壞她了。
如果我不是個新手治療師,我就會如實描述我的難題。就像完形療法的弗利茲.波爾斯 (Fritz Perls)建議的那樣,我們本來會在他所謂的「此時此地」處理這個問題。波爾斯相信,治療師與病人在療程中建立的動力,就是病患在她自己與其他世界之間建立的同一種動力。我本來 可以說:「蘿拉,妳在要求我表現出妳家長的行為,那個男人對妳的痛苦不感興趣。妳習慣沒有人回應妳的悲傷,但我不想要扮演那個角色。現在我覺得進退兩難。」但我反而說:「我同意尊重妳的期望,顯然妳非常堅決,而我想讓妳覺得自在,好讓我們可以一起工作。然而,我不會同意在整個療程裡都這樣做。」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凱瑟琳.吉爾迪娜的圖書 |
 |
$ 315 ~ 450 | 早安,我心中的怪物:一個心理師與五顆破碎心靈的相互啟蒙,看他們從情感失能到學會感受、走出童年創傷的重生之路 (電子書)
作者:凱瑟琳‧吉爾迪娜(Catherine Gildiner) / 譯者:吳妍儀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1-11-0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共 1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6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早安,我心中的怪物:一個心理師與五顆破碎心靈的相互啟蒙,看他們從情感失能到學會感受、走出童年創傷的重生之路
小紅帽該如何順利長大?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作者蘿蕊‧葛利布力薦——
吉爾迪娜堪稱是一名極為出色的治療師與作家。本書精采地捕捉到心理師被允許進入人們生活內在層面,同時看著人們逐漸成為自己該有的樣子時所帶來的意義。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Maybe You Should Talk to Someone)作者蘿蕊‧葛利布(Lori Gottlieb)
國內感動推薦——
這五個背景不同的治療故事提醒著我們,在走過創傷的路上,如何從灰心、傷心的狀態中,練習擁抱信心與希望;同時,在療癒的漫長路途上,許多時候,個案其實才是治療者最好的老師。
——蘇益賢|臨床心理師
周慕姿|諮商心理師
周志健|資深心理師、故事療癒作家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海苔熊|心理作家
馬躍比吼Mayaw Biho|紀錄片導演
瑪達拉‧達努巴克│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督導
蘇絢慧|諮商心理師、作家
蘇益賢|臨床心理師
凱瑟琳‧吉爾迪娜遙想她開業的第一天,便滿懷抱負期待以一身的心理學知識來「治癒」病患。沒料到踏進診療室的第一位個案就跌破她眼鏡,不僅拒絕分享家族史,還對何謂壓力沒有任何概念。從這名個案開始,凱瑟琳逐漸明白做為一名臨床心理師,與其期望自己能讓病患痊癒,不如與個案一起解決問題,引領他們來到理解自己的大門前——重要的是,陪伴病患直到他們願意走向自己的那一刻。
本書為一名心理師從新手到年屆退休的二十五年間,不斷在心理學理論與臨床實作間犯錯及調整的過程。作者也記錄下五名來自不同種族、性向及階級的個案,他們在童年曾被遺棄、忽視、虐待,甚至遭受慘絕人道的種族滅絕政策。雖然看似成功克服逆境順利長大,童年的創傷卻在某刻甦醒,使他們的人生再度迷航——
|一位以為心理諮商能迅速緩解生活壓力,以便治療皰疹問題的美麗女性,
意外揭開的是兒時慘遭父親遺棄,
獨自帶著弟妹在加拿大北方生存的悲慘經歷。
頑強求生的她視情緒為「有錢人的奢侈品」,
不允許他人,甚至是她的治療師,表露一點同理與同情。
|飽受性功能障礙困擾的華裔樂手,
五歲以前皆被視錢如命的母親獨自關在閣樓。
他以音樂撫慰自己,更成為樂手感動無數聽眾,
母親卻不斷將他對音樂的喜愛,貶低為西方墮落的象徵。
直到在診療室裡,
偶然觸及母親兒時在越南鴉片館受虐的不堪經歷,
解開兒時未能建立的情感依附如何影響他的生理。
|加拿大寄宿學校種族滅絕政策的受害者,
離開了家也背離了原住民傳統獵人文化,
成為一名戴著白色面具卻連妻兒意外身亡都了無情緒的盡責職員。
面對一位白人心理師,他能夠不講任何一句話長達三個月。
而他們之間的隔閡,
也代表了心理諮商背後的白人文化傳統,
處處都與原住民的世界觀有所不同……
|擁有一位長年將殺人魔泰德・邦迪視為楷模的父親,
在脫離父親性虐待的魔掌後,
面對的是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創傷觸發點,
與接連不斷的閃回症狀。
在診療中看似迅速好轉的她,
一天卻以完全不同的人格出現在會診室。
作者才驚覺為了維持身心的平衡,
她以多重人格來應付生活中出現的挫折,
是一名集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超群智商於一身的罕見病例。
|生於WASP白人菁英世家、曾旅行全世界的年輕古董商,
一天卻突然害怕搭機飛行,甚至到了危害公司營運的地步。
在童年老家那座豪華的宅邸裡,
等著她的是如同《白雪公主》後母一般的母親,
以及在外是成功的企業家,在家卻總躲在地下室瑟縮發抖的父親……
已執業二十五年、經驗老道的作者,
未曾料到那段治療她父親失敗的「婚姻諮商」經驗,
會回過頭來成為她在這段治療裡最嚴重的失誤。
看一名專精精神分析理論與談話治療的心理師,如何在五段如同犯罪小說一般詭譎的人生經歷中,成功引領他們直視成長過程中無意識間留下的傷痕,打破既有認知框架與情感模式,從麻木到學會感受情緒。這些個案也讓作者看見心理學與自身創傷的盲點,突破智識的限制與文化的藩籬,走上療癒心智與性靈的旅程。
本書榮耀——
★《早安美國》2020年最受讀者喜愛的讀物
★獲選紐約《新聞週刊》最富有啟發的三十本讀物
作者簡介:
凱瑟琳.吉爾迪娜(Catherine Gildiner)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1948年生於紐約劉易斯頓(Lewiston),1970年移居至加拿大。於多倫多維多利亞大學完成心理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後,成為一名私人開業的臨床心理師,從業超過二十五年。曾為多家報章媒體撰寫文章,也曾在加拿大女性媒體社群《Chatelaine》開立專欄。著有自傳《太靠近瀑布 》(Too Close to the Falls)曾於加拿大、美國與英國出版,亦著有小說《誘惑》(Seduction)。
譯者簡介:
吳妍儀
中正大學哲研所碩士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近年的譯作有《再思考》、《哲學大爆炸》、《冷思考》、《男人的四個原型》、《死亡禁地》、《復活》等書。
章節試閱
1 被蠢蛋包圍
我以心理師身分私人開業那天,我沾沾自喜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我在我以知識搭建的 堡壘中,安於我習得的規則,很期待能擁有我可以「治癒」的病患。
我上當了。
幸好我當時不知道臨床心理學這一行有多麻煩,否則我可能就會選擇能夠控制受試者與變數的領域,純粹做研究。相反的,我必須在每週都有新訊息涓滴流入的時候,學習如何臨機應變。 在開業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心理治療根本不是心理師在解決問題,反而是兩個人面對面,一週又一週,致力於達成某種彼此可以一致同意的心理真相。
沒有人比我的第一位病患蘿拉.威爾...
我以心理師身分私人開業那天,我沾沾自喜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我在我以知識搭建的 堡壘中,安於我習得的規則,很期待能擁有我可以「治癒」的病患。
我上當了。
幸好我當時不知道臨床心理學這一行有多麻煩,否則我可能就會選擇能夠控制受試者與變數的領域,純粹做研究。相反的,我必須在每週都有新訊息涓滴流入的時候,學習如何臨機應變。 在開業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心理治療根本不是心理師在解決問題,反而是兩個人面對面,一週又一週,致力於達成某種彼此可以一致同意的心理真相。
沒有人比我的第一位病患蘿拉.威爾...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作者註
蘿拉
1被蠢蛋包圍
2進入森林
3貓拖進來的東西
4天啓
5失去工作
彼得
1上鎖
2愛的表現
3燃眉之急
4遇襲
丹尼
1坦尼西
2皮鞋
3觸發點
4母牛獎牌
5哀慟悄然而至
6解凍
7在凍線之上
8獵人復歸
9重聚
艾倫娜
1泰德・邦迪粉絲俱樂部
2外出到祖母家去
3錄音帶
4暖爐後方
5克羅艾
6一村之力
瑪德琳
1父親
2女兒
3害怕飛行
4妳給什麼,就得到什麼
5潛水夫病
6啟示
後記
致謝
蘿拉
1被蠢蛋包圍
2進入森林
3貓拖進來的東西
4天啓
5失去工作
彼得
1上鎖
2愛的表現
3燃眉之急
4遇襲
丹尼
1坦尼西
2皮鞋
3觸發點
4母牛獎牌
5哀慟悄然而至
6解凍
7在凍線之上
8獵人復歸
9重聚
艾倫娜
1泰德・邦迪粉絲俱樂部
2外出到祖母家去
3錄音帶
4暖爐後方
5克羅艾
6一村之力
瑪德琳
1父親
2女兒
3害怕飛行
4妳給什麼,就得到什麼
5潛水夫病
6啟示
後記
致謝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