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名稱:史家的技藝
「在地景景觀的背後,在工具器械的背後,在看來最形式化的文件與制度背後,就是人本身。歷史研究想掌握的,也就是這些人。」1929年,由於不滿當時法國史學界劃地為限、自足於史料與制度史煩瑣考證的風氣,布洛克奮然與費夫爾豎起《年鑑》的大旗,力倡回到以人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時至今日,「年鑑史學」已蔚為當今史學巨流,透過本書,可以清楚看出這位奠基者當年為他們所揭櫫的綱領。
歷史有什麼用?歷史要如何研究,或者說,要如何來讀歷史?在本書中,布洛克再三強調,愈是能了解生活於歷史上與現在社會的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壁壘就愈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分明。從現實生活體驗歷史,由歷史研究返照現實與生命,這是布洛克一生的理想,他自己的確也已實踐。
「簡言之,在歷史研究裡,一如在其他地方,原因是不能事先設定的。我們得去尋找……。」《史家的技藝》一書擱筆於此,這句話也如實點出作者一生的追求。
作者簡介
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
法國近代最著名史學家之一,「年鑑史學」奠基者。
布洛克曾先後應法國政府徵召,參與兩次世界大戰。1943年,德軍南下控制全法,他加入地下反抗組織。1944年春為納粹所捕,同年6月16日遭納粹槍決,享年58歲。
曾任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中古史教授與巴黎大學經濟史講座。在史特拉斯堡大學擔任教授任內與費夫爾(L. Febvre)等人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鑑》,影響後世史學甚大。
重要著作有《法國農村史》、《封建社會》、《為歷史學辯護》、《奇怪的戰敗》、《史家的技藝》等書。
譯者簡介
周婉窈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台灣歷史與十六、七世紀東亞海洋史,著作包括學術論著、歷史普及書、人物傳記、散文集,以及部落格文章,並參與書刊的編輯工作。作者關心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文化等議題,最新撰有《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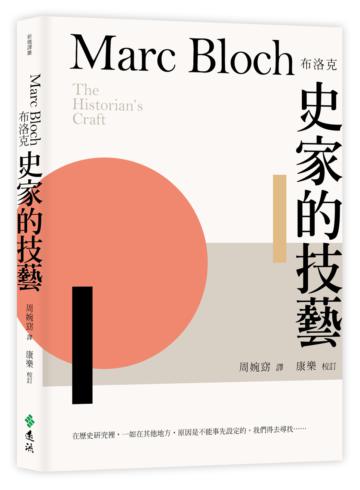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