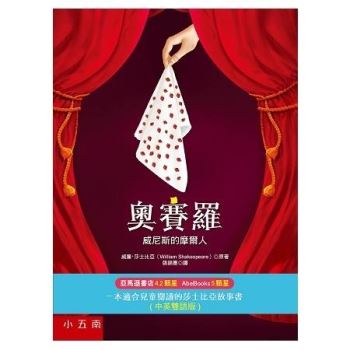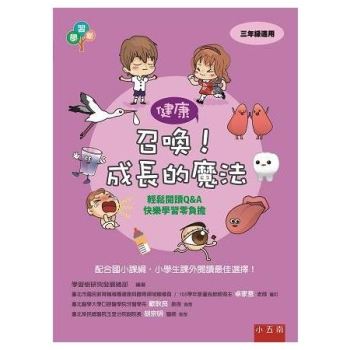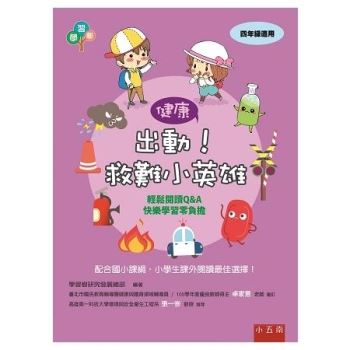【引言】 創造與毀滅
二○一二年七月四日,兩個國際科學團隊宣布,靠著大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這種地球上數一數二複雜的研究儀器,他們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這種基本粒子。自從一九六四年以來,認定希格斯場是宇宙一切物質質量的來源,而希格斯玻色子正是由於這套假設,於是成為物理學界近半世紀以來孜孜不倦搜尋的目標。然而,要有LHC才能找到希格斯玻色子。
大強子對撞機的建造者暨擁有者是歐洲核子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研究發現的宣布儀式也在此舉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觀眾和最高階層的物理學家。時年高齡八十三歲的彼得.希格斯(Peter Higgs)也親自到場,這位預測了希格斯玻色子的英國物理學家(此粒子也正是以他命名),就像其他所有賓客一樣,在CERN的演講廳裡緊盯著螢幕。螢幕上放著PowerPoint簡報,秀出LHC將兩束高能量質子束強力對撞、產生猛烈衝擊後的情形,希望在這場能量大混沌當中,能夠捕捉到希格斯玻色子現身那短到不能再短的瞬間景象。資料數據告訴他們,在可信的概率範圍內,實驗已經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簡報結束,眾人起立鼓掌,既是對研究小組致敬,也是對這套帶來勝利而令人難以置信的設備表達讚嘆。
大強子對撞機的一切,都值得用「大」字來形容。整套設備從構思到射出第一束質子束,就花了二十五年、一百億美元。這套機器位於法國和瑞士的邊界,深埋於一片田園風光地下約一百公尺,位於總長約二十七公里的圓型混凝土隧道之中。隧道裡共有九千六百個磁鐵,低溫冷卻到大約攝氏負三百度,引導質子束以接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光速的速度迎面對撞。
LHC與二○一二年夏日宣布的那項發現,正可說是「大科學」(Big Science)的最佳代表,也就是各種達到產業規模等級的研究,推動了我們這個時代種種重大科學計劃:原子彈、登月競賽、用機器人探測太陽系外的宇宙,以及在次原子粒子的微觀尺度研究自然的運作。直到今日,「大科學」仍然引導著產官學界的研究方向。大科學處理的是巨大的問題,也就因而需要巨大的資源,包括設備可能要由幾百、甚至幾千名專業的科學家和技術專家操作。大科學的計劃經費常常都不是單一大學、甚至單一國家所能承擔;CERN對撞機的經費及科技來源除了來自該組織的二十一個會員國,還有其他超過六十個國家和國際機構。這就是今日大科學的規模。正如物理學家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R. Wilson)所寫,這種規模的研究已經不是任何人能夠獨力完成:「要憑一己之力接觸到原子核,幾乎就像要自己到月球一樣難。」
然而,大科學本身的創造,卻是某個人獨力的成就。這種探索自然奧祕的方式,其誕生可追溯至將近九十年前的加州柏克萊,當時有一位年輕、機智、深具魅力的科學家,不但有物理天份,可能更有推銷的才能,他構思了一項新發明,接著大聲宣告:「我要出名了!」
這個人,就是厄尼斯特.奧蘭多.勞倫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他的發明將會徹底改變核子物理學,而且這還只是開始;他的發明也讓物理研究的操作方式全然改變,直至今日仍然影響深遠;他的發明讓我們對自然的基本建構元素有了全然不同的理解;他的發明,最後成了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助力。這項發明,勞倫斯稱之為迴旋加速器(cyclotron)。
迴旋加速器正是大強子對撞機的先祖,但現在已經很少人能看出其相似之處。畢竟,第一個迴旋加速器能直接放在勞倫斯的手掌上,而且成本還不到一百美元。至於LHC,則是由多個先進的迴旋加速器、同步迴旋加速器及其他先進的加速器組成,要將次原子粒子推動到異常迅猛的速度,而這一切追本溯源都會回到最原始的迴旋加速器。位於柏克萊的勞倫斯放射實驗室在鼎盛時期有大約六十名科學家、幾十名技術人員。在過去,例如厄尼斯特.拉塞福爵士也曾主持劍橋大學聲名遠播的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tory),只靠著兩名助手、各種手工工具(有些可以輕鬆放在他的工作台上),就在二十世紀初期找出一些驚天動地的發現;相較之下,勞倫斯放射實驗室簡直像是擁有一整支軍隊。然而,宣布發現希格斯的兩個研究團隊都各有三千名成員,相較之下,勞倫斯放射實驗室就又是小巫見大巫。
身為大科學的創造者,勞倫斯在當時的同儕之間廣受認可,但今日已幾乎遭到遺忘。然而出於幾項原因,我們值得重新認識勞倫斯。其一,正是他的直覺、抱負、以及個人管理風格,讓大科學像現在這樣可長可久。但還不只如此:他的人生也是一個動人的科學追尋故事,跨越物理學史上前所未見的大發現時代,讓他就這樣站在一個科學、政治和國際事務的十字路口。
從一九三○年代末開始,只要是關於國家科學政策的問題,幾乎都會去詢問勞倫斯的觀點意見。他發明了全世界最強大的原子粉碎機、領導著美國排名第一的研究實驗室,影響力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擴張。在那個歷史的關鍵時刻,因為有他個人支持同盟國建造原子彈,才拯救了這項幾乎被取消的計劃。而在戰後,也是因為他的聲望和影響力,才推動了氫彈的製造。我們現在的世界,頭上懸著核武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無疑是勞倫斯留給現代文明的遺產,只是其中的利弊難以逆料。
在一九二九年腦力激盪的那天,勞倫斯就知道自己發現了一種能夠極有效加速次原子粒子的新方法。他當時希望能將粒子加速做為探測器,研究原子核的結構(原子核由質子和中子構成,構成原子大部分的質量),就像是用螺絲起子來探索收音機的內部電子構造一樣。這裡的問題在於如何提升次原子粒子(特別是質子,也就是氫原子核)的能量,讓這些粒子得以穿透保護原子核的電場。當時,這是世界各地科學家和工程師都在研究的問題,而勞倫斯找出了解方。
在這之後,物理學研究開始了艱困的轉型期。過去像是拉塞福,或是艾蓮娜及菲特列.約里歐-居禮(Irène and Frederic Joliot-Curie,也就是瑪麗.居禮〔Marie Curie,即居禮夫人〕的女兒及女婿),都算是「小科學」的天才人物,但靠著大自然中能夠取得的研究工具,他們已經來到研究的極限。拉塞福靠著自己手工製作的研究設備,發現了原子核、也猜想到中子的存在,後來再由他的副手詹姆斯.查兌克(James Chadwick)在另一項小型實驗裡確認發現了中子。約里歐-居禮夫妻也是在自己平凡無奇的實驗室裡,繼續瑪麗.居禮對放射性的研究,學會如何透過將某種元素曝露在放射線下,讓元素蛻變為另一種元素。在這兩個實驗室,都是靠著像鐳及釙這樣的天然放射性物質,產生人眼不可見的次原子探針。
這些人的成果豐碩,卻很難再進一步研究原子核的結構,原因就在於他們需要能夠更快、更強、更精準的子彈,不能只靠從某些具放射性的礦物塊偶然發出的放射線。換言之,物理學家需要人造的放射線子彈。而要製造出這樣高能量、還要能夠集中在某個靶上的放射線,整套設備的大小絕不可能是放在實驗室的工作台上,而是可能要好幾棟建築物才勉強放得下。拉塞福和約里歐-居禮夫婦都知道,自己會是這種人工手動做科學研究的最後一代偉大領袖;很快地,就會有新一代科學作法興起。
勞倫斯給科學帶來的改變,必然會讓這些舊學派的物理學家大為嘆服。傑出物理學者莫里斯.高德哈伯(Maurice Goldhaber)的職涯,就是從小科學的鼎盛時期一路橫跨到大科學的時代,他回憶起期間的過渡:「第一個分離出原子核的人是厄尼斯特.拉塞福,還有一張照片,是他把整個實驗裝置放在腿上。但接著,我也總是記得後來的一張照片,是在柏克萊建造了那座著名的迴旋加速器,換成所有人坐在迴旋加速器上。簡單說來,這樣你就大概知道有什麼改變了。」
高德哈伯說的一點也不誇張。他所說的迴旋加速器是座龐然大物,位於一棟在一九三八年特地為它蓋的建築物裡。這台迴旋加速器巨大的電磁鐵重達二百二十噸,高度超過三點三公尺。至於高德哈伯所描述的那張照片,也就照下了勞倫斯實驗室的全體成員:共有二十七名成年男子,在迴旋加速器拱形的鋼鐵構造上或站或坐。
厄尼斯特.勞倫斯的角色,與他所創造的新時代可說是絕配。在學術研究的這個沉悶世界裡,很少見到像他這樣的科學經理人,善於鼓吹百萬富翁、慈善基金會和政府機構投入贊助。他除了在科學上有天份,不管對裝置設計或物理都有著近乎直覺的天賦,也有著美國中西部那種討人喜歡的個性,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關鍵。他心性善良,很少發脾氣,連髒話都不講。(他最髒的髒話就是「Oh, sugar!」)如果研究計劃想要得到大筆資金,常常需要有正面的宣傳,而只要報導對象有著迷人的性格、科學任務有著引人的內容,記者也總是很樂意提供這類宣傳。勞倫斯就能同時滿足這兩項條件。他才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成了美國本土出生最著名的科學家,登上《時代》雜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封面,標題寫著「他創造,他毀滅」。不久之後,就在一九三九年得到科學家在人世的最高榮譽:諾貝爾獎。
勞倫斯和我們對科學家的刻板印象完全是兩回事;在我們的刻板印象裡,科學家就是狂熱的神祕主義者,一頭埋在自己孤獨的工作裡,獨自待在某個偏遠的實驗室(通常是歌德式建築),而且他們的研究似乎總是差一點就會把他們都炸成碎片。在流行文化裡,總是把科學家描繪得與一般人格格不入:《時代》上的愛因斯坦形象是個古怪的天才,總是躲在閣樓裡,把自己鎖在鏗鏘作響的鐵門後,「憔悴、緊張、煩躁......數學家愛因斯坦連自己的銀行帳戶都算不清楚。」
相較之下,勞倫斯智識過人,同時精力充沛。他的成功為他帶來了一間實驗室,而且可不是什麼黑暗的歌德式城堡,而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小山上的現代科學神殿,俯瞰著舊金山海灣的壯麗景色。他也絕不是自己孤身一人做研究,而是領導著一支充滿活力的年輕科學研究團隊,有物理學家、化學家、醫生、工程師、研究生等等,跨學科共同合作、思考議題;而且他也有著如同企業高層一般的堅定信心,手中掌管著數百萬美元的經費。他所體現的是新世界的堅強無畏,深具抱負、氣魄、創意及財富。偏好進步主義的記者布魯斯.布萊文(Bruce Bliven),往來的對象通常是自私的政客與厭世的領域權威人士,而他也深為這位著名的勞倫斯教授所傾倒,認為這位教授「很好聊,完全就是可以想像的那種美國人的樣子」。
• • •
「大科學」一詞是由物理學家阿爾文.溫伯格(Alvin Weinberg)於一九六一年所創,當時厄尼斯特.勞倫斯已經去世三年。溫伯格時任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該所依勞倫斯的設計所建,製造原子彈所需的濃縮鈾)主任,他回顧了先前幾十年的科學研究,認為正如過去會用有著尖塔的石建築大教堂和巍峨的金字塔來崇敬天神,到了當時這幾十年,則是用各種由鋼鐵及電纜所構成的壯觀設備(例如高聳的火箭、高能量加速器、核子反應爐),崇敬著科學。
但這些崇敬科學的偉大作品,背後必須要有官僚結構的管理,才能維持其運作。在勞倫斯放射實驗室裡,主要的設備就是迴旋加速器,但這項設備技術複雜、操作困難,需要有人全職照料管理。溫伯格就回憶道:「要讓這個地方維持運作(不管說的是那套科學機器、又或是為了照顧那套科學機器所需的整個精心設計的組織),後勤管理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那些維護迴旋加速器的人心中,開始出現一種信念,認為正因為科學所面臨的問題如此複雜,才需要有這些巨大的設備;正如曾在勞倫斯實驗室工作的物理學家沃爾夫岡.「皮耶夫」.潘諾夫斯基(Wolfgang K.H.“Pief” Panofsky)所言:「要是沒有大規模的努力及大型的工具……不論是對於最微小的物質架構,或是最大規模的整個宇宙,我們就是不知道怎麼去取得相關資訊。」
這種要追求更大、更好的動力,成了自己的一套邏輯。運用迴旋加速器所帶來的每一個發現,都為物理學家打開新的探索展望;每要解開一個新的謎團,就又需要更強大的機器。每次得到新發現,都會讓這個研究機構的名聲更上一層樓,於是有更多動機與機會,可以有更多建築、更多科學家、更多的知名度,自然也就能募到更多經費。
最終確立大科學作為科學探索模型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兩大科技成就:雷達、原子彈。要不是當時大科學已經成為新典範,有著跨學科的合作、幾乎無限的資源,雷達和原子彈很有可能都尚未研發出來,當然也就不可能及時影響戰局結果。後來之所以能研發出投至長崎的原子彈,是靠著在原子反應堆裡首次觀察到了核能連鎖反應;而一般來說,認為這背後的最大功臣是構思與監督反應堆建造的恩里科.費米(Enrico Fermi)。然而,一如溫伯格的觀察,想實現費米的概念,需要由「物理學家、數學家、化學家、儀器專家、冶金學家、生物學家,以及能將這些科學家研究成果付諸實踐的各種工程師」,組成一支大軍。「連鎖反應堆絕不只是單一位核子物理學家的實驗。」
勞倫斯的這種研究方式,科學界一方面感到敬畏,但一方面也覺得不安,至今仍然如此。
就算是在勞倫斯的職涯早期、大科學仍在形成階段,已經有些科學家、大學校長和其他專家擔心這對知識追求及傳播的影響。一九四一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卡爾.康普頓(Karl Compton,這位物理學家本人手中也有一座迴旋加速器可用),就認為大科學讓學界開始追逐金錢與名聲,而對這種「不正常的競爭成份」深表遺憾。他不安地向朋友透露,「想維持計劃運作、有完整的人員編制,就需要積極的推銷手段,程度超乎科學專業所情願。」在某些科學家眼中,這種超級競爭、如工廠一般的研究風格實在是不友善到令他們感到絕望,於是逃離像柏克萊這種採用大科學作風的機構,轉而投向那些仍然遵行舊世界方法程序的大學。但也有某些像潘諾夫斯基這樣的科學家,認為要解決物理學的重大問題就必須要有大科學,於是他們在像是柏克萊這種新研究體系裡自我訓練,再將大科學的福音傳播至遠方。(潘諾夫斯基就把大科學帶到了史丹佛大學。)
在大戰期間,科學及科技社群還是以獲勝為主要考量,於是暫時不再擔心大科學將如何永久改變科學家的工作方式。但隨著和平到來,科學家又再次開始思考大科學將帶來怎樣的變化。有些人擔心,像過去那種由個人靈感得到突破的方式,以後是否還有存活的空間?例如匈牙利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Eugene Wigner)便問道:「像是相對論或薛丁格方程式這樣的理論,能由跨學科團隊想出來嗎?」他和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擔心出現愈來愈多管理方面的需求之後,會讓那些才華最出眾的科學家無法再在實驗室待下去。在小科學時代,研究者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研究自己的主題、再教給自己的學生,但現在卻得兼顧許多其他職責。研究者得要管理大筆捐助款、撰寫經費申請、擔任委員,還得到國會和位於華盛頓的各個機關運作,才能得到撥款。研究主持人不只得當科學家,還得負責背黑鍋、給團隊成員打氣,以及兼任業務。
這時候,雖然研究經費豐沛,但卻也帶著許多附帶條件。而隨著經費規模愈來愈大,附帶條件也愈來愈嚴格。在戰時,美國政府的經費自然是以軍事研究及發展為目標。然而,即使在一九四五年德國和日本投降之後,在美國,政府仍然是科學機構經費最大的單一來源,各個學科(特別是物理學)也仍然受到軍事目的的影響。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韓戰隨之而來,接著就是無止盡的緊張時期,也就是冷戰。此外,軍事現在也結合了另一個強大的合作夥伴:工業界。時至戰後,大科學開始與令艾森豪總統惴惴不安的「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共同成長。工業漸漸入侵學術實驗室,讓科學家開始感到壓力,需要注意其研究的可能商業發展。科學歷史學家彼得.蓋里森(Peter Galison)指出,物理學家開始放下基礎研究,轉而「為了經濟而非科學上的理由,花時間尋求能夠申請專利的概念。」厄尼斯特.勞倫斯身為大科學的先驅,自然比多數的同行更快面對這些壓力,但很快地,競爭就成了整個學術界普遍的現象,而且不只是爭專利概念,也要爭大科學團隊裡如何分配成果。另外,學術界也開始引進了政府和工業念茲在茲的概念(例如保密、管理控制),因為大筆的投資能夠帶來更大的報酬。
正是勞倫斯,讓出錢的各家贊助者看到迴旋加速器可能怎樣完成他們青睞的目標,於是讓贊助者的雄心壯志也愈來愈大,種下了工業參與研究的種子。對生物研究機構,他再三強調迴旋加速器生產大量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能力,而如果想瞭解複雜的光合作用,或是攻擊癌細胞,就需要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對工業家,他讓他們心中浮現一種願景:用原子核來發電,成本便宜得不得了,而且幾乎是永遠不虞匱乏。至於對那些仍然致力於基礎研究的慈善基金會,他提供的則是聲望:能夠參與解開世界謎團的研究專案,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獎勵。對於大科學的這個面向,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長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一語中的,他在一九四○年就表示:「新的迴旋加速器不單單是一種研究工具,更是一個強大的符號,象徵著人類對知識的渴望,代表著不屈不撓追求真理的努力,是人類精神最高尚的一種表現。」而在那年,這個非營利基金會的董事會便投票通過,撥款一百萬美元給勞倫斯,打造地球上最強大的迴旋加速器。
像勞倫斯這樣針對各家金主的利益、量身打造說帖,其實並不是什麼欺瞞的手段。他總是能說到做到,提出一系列真金實銀的研究成果,否則再怎樣努力募款到頭來也只會是一場空。後來,柏克萊的放射實驗室就開創了核子醫學這套新科學,用來對抗疾病。實驗室的迴旋加速器常常需要超時運作,為全世界的研究人員生產放射性同位素。另外,勞倫斯堅信來自原子的能量有一天能為幾百萬的家庭與工廠提供熱源及照明,並且讓船舶在遠洋乘風破浪,這在當時只是個願景、但絕對是出於真誠;而且當然,事實證明這也已經成真。
大科學的成功,讓科學家在社會上廣受敬重,認為是他們協助贏得了戰爭,也認為要靠著這些人,才能滿足人類對於解開自然祕密的渴望。然而,由於科學本來就不是絕對完美,大眾也總是想看到名人跌落神壇,大科學的發展並不可能永遠如此順遂。隨著大科學的各項計劃規模愈來愈大,可能佔據太多的公共資源,而拖累其他更急迫的社會問題,科學家的形象也開始動搖。
到了二十世紀末,社會對大科學的信心開始消退。回頭看,會覺得大科學的許多成就利弊難計:沒錯,原子彈讓同盟國贏了戰爭,但代價是人類的頭頂上似乎永遠掛著一朵蘑菇雲的陰影。天真和平的原子帶來了電力,但代價卻遠高於人類的原本預測,更帶來了如三哩島、車諾比、福島等地的核災,讓人不禁質疑,究竟人類能否真正馴化控制核電科技。確實,人類上了月球漫步,但在那個瞬間的感動之後,大眾對於太空探索的興趣迅速消失殆盡。花了那麼多的錢,到底是為了什麼?
阿爾文.溫伯格一九六一年的那篇文章中,除了創出「大科學」一詞,也點出當時日益升高的疑慮,質疑大科學對研究、大學和社會造成怎樣不好的影響。他的問題一針見血:大科學那些龐大計劃需要耗費巨額的資金,是否會把原本就稀少的資源吸乾用盡,並且讓科學家分心,不去注意那些與人類生活現況更相關的研究?他寫道:「我覺得,大多數美國人心中的理想社會,會是把重點放在治癒癌症,而不是誰先把太空人送上火星。」
在美國,這些質疑在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初引發對於超導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的討論,原本計劃這部加速器將設於美國德州的沃卡薩哈奇(Waxahachie),功率可能是CERN大強子對撞機的三倍。這項計劃最後是因為地方及預算上的政治紛擾而告終,但大眾對其研究目的所抱持的懷疑,已經讓計劃受到致命傷害。一九九三年,超導超級對撞機遭國會否決,胎死腹中。
大強子對撞機實在太過龐大、複雜又昂貴,讓部分科學家認為這可能已經是國際合作大科學的最後一役。大強子對撞機每次有了發現,都會引發對自然的進一步疑問,而這些疑問又必須有更大、功能更強的對撞機才能回答,就像之前勞倫斯每次打造迴旋加速器,都等於是帶出了打造下一臺迴旋加速器的需求。而正如現有的大強子對撞機,如果真要打造下一台,也必然需要許多國家合力才可能成真。但要讓這麼多國家同心協力,一起研究著一般人會覺得抽象到難以理解的議題,絕非易事。
厄尼斯特.勞倫斯從未表示這樣的疑慮。他的目標就是要解決羅伯特.歐本海默所說「研究自然的問題」,而且勞倫斯的職涯也確實完成了這項目標。他讓我們得要承受後續的影響,但這並不會抹滅他的成就。只是這也確實讓我們覺得,有必要追溯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而這整個故事,要先從小科學世界裡幾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談起。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原文 Michael Hiltzi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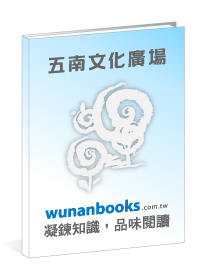 |
$ 514 ~ 585 | 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
作者:麥可.西爾吉克(Michael Hiltzik) 出版社:左岸-木馬文化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大科學:從經濟大蕭條到冷戰,軍工複合體的誕生
從原子彈到核能發電,從太空設備到網際網路,
「大科學」的追尋成就了科學?還是毀壞了科學?
普立茲獎記者揭露一段政治與科學交織的歷史。
張國暉(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
專文推薦
科學專業審定
劉怡維(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林敏聰(台大物理系特聘教授 / 科技部政務次長)
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與「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主編)
蔡榮峰(國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員)
顏擇雅(雅言文化發行人)
劉怡維(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
推薦
這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從原子彈到登月計劃,從探測太陽系外的宇宙,到深入微觀尺度的原子,這些都是「大科學」的產物,至今引導著產官學界的合作。
「大」,不是一個誇張的形容詞,而是特指一九三○年代開始,科學界從人員編制、經費投入、儀器尺寸等各方面,皆往鉅型化發展的趨勢。
居禮夫人時代的科學,往往由一位科學家,搭配兩、三位助理進行,到一九三○年代之後,一個實驗室可能包括數十名科學家,甚至成長為上千名專家的社群;實驗設備從小到可以放在「掌上」或「腿上」,大型化到好幾棟建築物才能容納得下,甚至巨大到變成「地景」的一部分;經費也不再是一所大學能夠承擔,而是需要傾國家之力,再加上工、商業界的巨頭。
是誰創造了新的合作模式?是誰開始追求「大」儀器?答案是,厄尼斯特・勞倫斯(Ernest Lawrence)。
他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也是迴旋加速器的最初奠基者。他顛覆了科學家的傳統形象,發展出經營管理者的領導才能,還不拘領域,廣納技術人員。他在經濟大蕭條時代贏得資源,更讓「大科學」在二次世界大戰(加入曼哈頓計劃),以及戰後隨之而來的韓戰和冷戰裡,成為科學界、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新典範。
在「大科學」新典範下,政府(特別是軍事單位)成為經費最大來源,工商業也逐漸影響學術界。科學家如何反省自身角色的改變?科學還是單純追求自然界真相嗎?還是科學界也需要從商業競爭當中,謀取自身利益?對「大科學」的追尋,究竟成就了科學,還是毀壞了科學?科學家如何成為政治裡的科學家?政治圈又如何因為科學社群的介入而改變?
無論是褒是貶,勞倫斯創造了我們身處的世界,大科學是我們的進行式。
@厄尼斯特・勞倫斯的時代
厄尼斯特・勞倫斯能夠在經濟大蕭條時代,說服研究基金會(例如:洛克斐勒基金會)投入鉅資,也能夠招募各方而來的人員,打破學科界線,打造勞倫斯風格的實驗室,不論是工程師或技術人員,只要有才能,都能在他的實驗室找到一席之地。最後,這樣的實驗團隊,還在世界各地複製,從美東到歐洲,都可以看到勞倫斯將迴旋加速器帶到世界各地的影子。他認為,與其視科學儀器為機密,不如幫助各實驗室打造迴旋加速器,加速讓高能物理的版圖變成科學界的常規。
勞倫斯啟動的迴旋加速器知識王國,不到二十年,加速器從11英吋進展到184英寸,用巨大的儀器探索微觀粒子的奧秘。在經濟大蕭條的時代,勞倫斯有能力說服金主,投入鉅資。接著在二戰時,勞倫斯加入著名的「曼哈頓計劃」,與各座山頭合作,研發原子彈,打造軍工複合體的雛形。戰後,美蘇和平對峙的冷戰時代,依然能持續獲得軍方贊助,成為軍備賽局裡關鍵性的毀滅力量。
@厄尼斯特・勞倫斯的爭議,以及他與歐本海默
核子工業除了引發道德難題,讓世人思考投注武器研發的正當性,核子力量也應用於醫界放射性療法(與他弟弟合作),和工業界的核能發電。究竟「大科學」本身即有為了取得軍方資源,而內建的不道德性?或者,「大科學」因為軍方介入而具備有利的發展條件,當轉移到其他領域,例如:網際網路(Internet),能創造出未來的榮景。
勞倫斯是貢獻卓著的科學家,也是極具爭議性的人物。他所開啟的迴旋加速器研究,每次有了新發現,都會引發新一輪的疑問,而這些疑問又必須有更大、功能更強的機器才能回答。這種不斷掠取更多資源的追尋,讓人質疑:為何不去專注與人類生活更相關的科學研究?
另外,他在冷戰「麥卡錫主義」狂潮侵害美國學術自由的時候,並沒有挺身捍衛。他也因為熟知募款技巧,而在冷戰時期,不斷規劃出更大的計畫;他相信計畫夠大,才夠有吸引力。他還在各方試圖推動「禁核試」的浪潮中,持續追尋核子武器的研發,選擇成為物理學界的少數方。
一般人提到核子工業(原子彈),多會聯想到歐本海默。歐本海默最有名的,是以人道關懷,說出「後悔身為科學家卻製造出殺人武器」的一番話。勞倫斯卻支持核試,他認為,只有繼續核試,人類才有可能有「乾淨」的核彈,不論這個主張是樂觀的天真,或是政治說詞。兩位不同立場的人原先是好友,只是歐本海默為人所知,勞倫斯卻被逐漸遺忘。本書即是為了打開我們的另一隻眼,看見故事的另一半。
歐本海默雖受人敬重,但,是勞倫斯,他所創新的實驗室合作模式,改變了科學的內涵,以及科學和國家、產業界之間的關係。當因爲各界質疑,使得軍方逐漸淡出科學事業,商界和產業界填補了這樣的空間,成為下一波矽谷產業的推手。
得獎與推薦記錄
這是一個史詩級的故事,伴隨著人類的悲劇和人類的勝利,作者以其專業,完成了一部傑作!——Richard Rhodes,歷史學家,曾獲普立茲獎
一反過去從歐本海默的視野來談原子彈的主流敘事,作者從故事的另一個主角、也就是厄尼斯特・勞倫斯的角度,讓我們重新省思這段科學的追尋,並特別描繪人類歷史從「小科學」走到「大科學」的轉變。——George Dyson,科學與技術史學家
愛因斯坦獨自坐在伯恩的專利局,就提出了改變世界的相對論。對比當代,許多基礎研究卻都仰賴龐大的預算、眾多的人員和精密的儀器。我們的科學是如何變成「大科學」?作者從科學社群內部,刻畫了這一關鍵轉變。——Mario Livio,天文物理學家
作者簡介:
麥可.西爾吉克Michael Hiltzik
記者,專長為財經、商業、公共政策領域,曾榮獲普立茲新聞獎、羅布傑出商業財經新聞獎(Gerald Loeb Award)。出版過的書籍,與胡佛水壩、新政、美國鐵路建設等主題相關,例如:《Colossus : Hoover Dam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century》、《The New Deal: A Modern History》、《Iron Empires: Robber Barons, Railroad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譯者簡介:
林俊宏,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喜好電影、音樂、閱讀、閒晃,覺得把話講清楚比什麼都重要。譯有《人類大歷史》、《人類大命運》、《21世紀的21堂課》等。
章節試閱
【引言】 創造與毀滅
二○一二年七月四日,兩個國際科學團隊宣布,靠著大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這種地球上數一數二複雜的研究儀器,他們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這種基本粒子。自從一九六四年以來,認定希格斯場是宇宙一切物質質量的來源,而希格斯玻色子正是由於這套假設,於是成為物理學界近半世紀以來孜孜不倦搜尋的目標。然而,要有LHC才能找到希格斯玻色子。
大強子對撞機的建造者暨擁有者是歐洲核子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研究發現的宣布儀式也...
二○一二年七月四日,兩個國際科學團隊宣布,靠著大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這種地球上數一數二複雜的研究儀器,他們發現了「希格斯玻色子」這種基本粒子。自從一九六四年以來,認定希格斯場是宇宙一切物質質量的來源,而希格斯玻色子正是由於這套假設,於是成為物理學界近半世紀以來孜孜不倦搜尋的目標。然而,要有LHC才能找到希格斯玻色子。
大強子對撞機的建造者暨擁有者是歐洲核子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CERN),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研究發現的宣布儀式也...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引言 創造與毀滅
第一部分 那臺機器
第一章 英雄時代
第二章 南達科塔州的男孩
第三章 「我要出名了」
第四章 墊片和封蠟
第五章 歐本海默
第二部分 放射實驗室
第六章 氘核事件
第七章 迴旋加速器共和國
第八章 約翰.勞倫斯的老鼠
第九章 桂冠
第十章 盧米斯先生
第三部分 原子彈
第十一章 「厄尼斯特,準備好了嗎?」
第十二章 跑道形電磁分離器
第十三章 橡樹嶺
第十四章 三位一體之路
第十五章 戰後的幸運
第十六章 誓詞與忠誠
第十七章 氫彈陰影
第十八章 利弗摩爾...
第一部分 那臺機器
第一章 英雄時代
第二章 南達科塔州的男孩
第三章 「我要出名了」
第四章 墊片和封蠟
第五章 歐本海默
第二部分 放射實驗室
第六章 氘核事件
第七章 迴旋加速器共和國
第八章 約翰.勞倫斯的老鼠
第九章 桂冠
第十章 盧米斯先生
第三部分 原子彈
第十一章 「厄尼斯特,準備好了嗎?」
第十二章 跑道形電磁分離器
第十三章 橡樹嶺
第十四章 三位一體之路
第十五章 戰後的幸運
第十六章 誓詞與忠誠
第十七章 氫彈陰影
第十八章 利弗摩爾...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