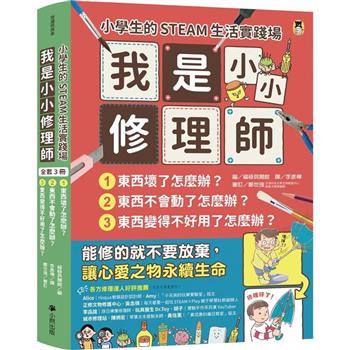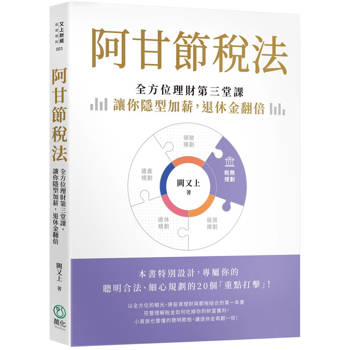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原文 pablo nerud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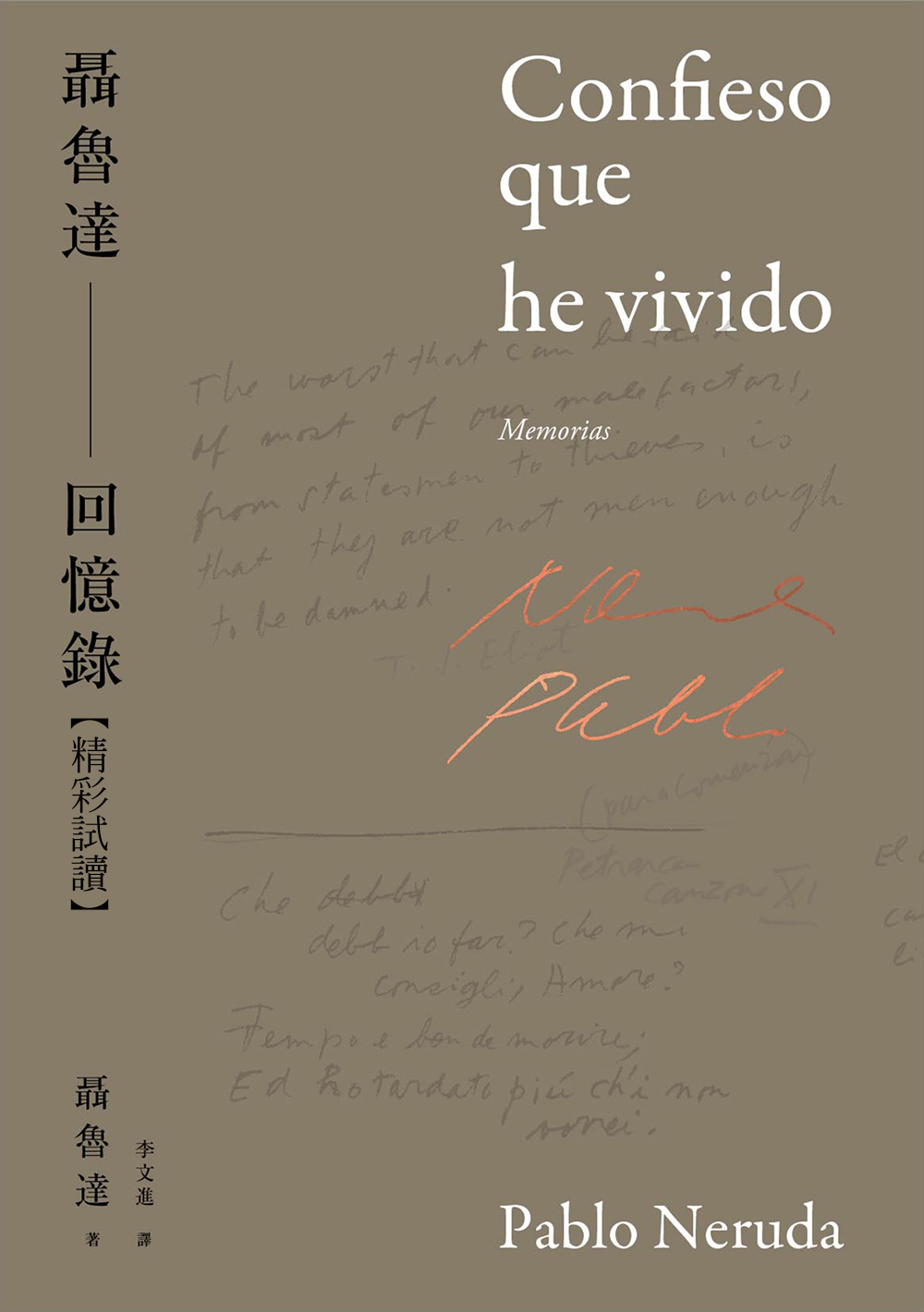 |
$ 0 ~ 738 | 聶魯達回憶錄【精彩試讀】 (電子書)
作者:原文 Pablo Nerud / 譯者:李文進 出版社:蓋亞 出版日期:2020-10-17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 初版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一年,聶魯達的健康亮起了紅燈,於是他開始著手回憶錄的寫作。一直到臨終前,他都還在整理這部回憶錄。
他生前最後的時刻,正逢智利政治局勢的大變局。作為反對獨裁政權的名人,他的屋宅遭到監控毀損,遺孀瑪蒂爾德在他死後費盡心力,才得以委內瑞拉外交郵袋,將這部回憶錄從智利救出。
在這本親筆撰寫的回憶錄中,從少年時期娓娓道來,關於詩歌與愛情,關於政治與時代,不但包含了不同時期作品的重錄,涵蓋他反思過往的再創作作品,他豐富的經歷,也讓回憶錄中處處可見那時代最光采奪目的人們。
多年來聶魯達基金會持續整理遺稿,不斷補充新的篇章,收錄珍貴照片、手稿。䌓體中文版取得「西班牙文最新版」正式授權,由塞維亞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李文進自西文直譯,收錄內容甚至比最新的英文版本更完整豐富,不但是聶魯達個人抒情式的自傳,也是最齊全的聶魯達文集。
本書特色
詩歌不會徒勞地吟唱。
智利國寶詩人、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聶魯達
抒情式的自傳回憶錄,首度正式授權繁體中文版!
瑞典學院稱他為「為受害者寫作的詩人」,
馬奎斯説:凡他觸摸的東西,都會變成詩歌,
在馬埃斯特拉山脈的夜裡,切格瓦拉讀著他的詩給游擊隊員聽⋯⋯
★ 聶魯達基金會正式授權
★ 「西班牙文最新版」西語直譯
★ 收錄內容最豐富的聶魯達文集。
作者簡介
巴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
巴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 1904-1973)是智利的國寶詩人、外交官、政治家。
從十三歲詩作初次登載於報紙上,十六歲以巴布羅.聶魯達作為筆名發表作品以來,詩歌是他終身志業。二十三歲時,受聘成為智利的外交領事,正式進入外交與政治領域,派駐到許多國家,也曾因政治立場兩度展開流亡生活。
一九五零年,他和畢卡索同獲世界和平獎;一九七一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瑞典學院稱他是「為受害者寫作的詩人」,他的《二十首情詩與一首絕望之歌》,是全球最受歡迎,同時也出版和翻譯版本最多的詩集之一。
譯者簡介
李文進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西班牙文學博士,譯有小說《Nada什麼都沒有》、《突然死亡》、《探戈歌手》、傳記《馬奎斯的一生》(西語部份)、藝術專輯《2002台北書年展——世界劇場》(序言和創作簡介六篇)、電影《艋舺》(中文字幕西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