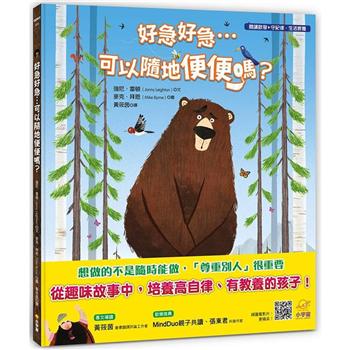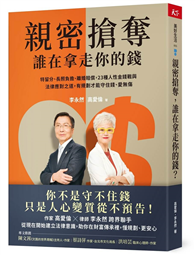〈自我魔術方塊〉
叩叩
——逃跑也沒有用,他們總是追上來找我。不管我去哪裡,就算躲在深處也一
樣。快點。要逃跑才行。要快點跑才行。前往向西延伸的奇異庭園。
「我不認識四五○九……不是,我不認識那個女人,只有在二手拍賣社團裡交易過相框而已。因為商品有瑕疵,她百般挑剔,我就乾脆賠償給她。就只有這樣,我連她的名字也是到現在才知道的。」
「但是她在失蹤前一個小時打了十次電話給你,你卻一次也沒有接。」
刑警斜睨著我的臉,目光銳利。他想讓我開口說話,但我真的一無所知,無可奉告。她和我是透過一個二手拍賣社團聯繫上的,買賣時是初次見面,接著她要求賠償時又見了第二次,就這樣。直到今天接到刑警的通知為止,我只記得她手機號碼的末四碼是四五○九,我完全沒有必要為她的失蹤負責。她打了十通電話我都沒接,那是因為當時我在陽臺上工作,手機調成震動模式、放在房間的沙發上,所以根本不知道。
「我們知道,我也知道徐異園先生的職業,還有你和李知英小姐為何見面。」
刑警語帶壓迫地說出我的名字,然後把一個閃閃發光、有著吊飾的粉紅色手機放在我面前。從手機螢幕上可以看到一面牆,用我做的相框裝飾得密密麻麻,那是我家的客廳。失蹤的那個女人雖然有進入我家,但我不知道她有拍照。
「哇,這整面牆好像一個大相框。」
第一次見面時,她把手伸到客廳牆壁上,一一輕撫著相框說。
「不過你為什麼不拍照,而只是製作相框呢?」
她突然轉過頭來,鼻子瞬間彷彿要碰到一直跟在她後面的我。
「因為……我是為了藝術而創造藝術。」
我往後退了一步說。她大步靠過來,像是想用鼻子碰觸我的下巴,抬頭邊看邊問。
「那是什麼意思?」
「一般人只把照片當作藝術,裝載照片的相框被認為只是附屬品。但同一張照
片,會隨著裝入不同相框而顯現出不同價值。所以我不拍照,而是做相框……」
她攬住我住後退的腰,然後將鼻子貼在我胸口呼哧呼哧的。
「你說得太長了。」
她像小狗般的親暱行為既讓人慌張又忍不住莞爾。她解開我的腰帶,褲子滑落
碰到腳背。我告訴刑警這件事,是因為她的手機裡存有我睡著的照片。
「但那真的就是全部了。又不是說只睡過一次,就算認識那個人吧?」
一覺醒來,她就站在我眼前看著我。她指著我上傳到網路上的桌上型粉紅色相框,付了指定金額後就離開我家。現在回想起來,在來我家前、約在咖啡店見面時,說不定她就在我喝的飲料裡放了不明藥粉,所以我才會大白天就和首次見面的女人在一起時睡著。
刑警不聽我的辯解陳述,只是指著那女人手機裡的照片。我疲憊地嚥下近乎乾涸的唾沫,刑警又給我看手機螢幕。螢幕上,陶瓷娃娃碎片散落一地,照片底下寫著簡短的文字:不滿意的話,隨時都可以打碎,就像不聽話就折斷脖子的玩偶。相框工房作家語錄。看到李知英在個人臉書上的貼文,我很氣憤,我從沒說過那樣的話,而且怎麼想,那種話都不會對初次見面想買相框的女人訴說。
「徐異園先生,還是請你仔細想想,會不會是喝醉所以不記得了……」
刑警看著我,一邊的嘴角上揚露出微妙的笑容,表情讓人感到不舒服。我沒有說話。接著他又把手機貼到我眼前,螢幕中有我入睡的臉。照片縮小,周圍出現了空瓶子。天啊,我沒有和那個女人喝酒啊。
「徐作家,這樣也無話可說嗎?」
她一定趁我睡著的時候,刻意擺了空瓶拍照的,她計畫好的,為了讓我被當成犯人。我激動地越講越快,但刑警只是看著別處掏掏耳朵,然後不情不願地說:
「徐作家,你是不是有酒精性失智症啊?喝醉了就不記得發過酒瘋。」
「不……沒有……」
我張口結舌,刑警壓低聲音說:
「你喝酒的習慣我全知道。你和李知英一起去酒吧,喝了雞尾酒後,打碎酒杯飆髒話,對吧?把你拖出來的年輕老闆全都記得,聽說你還是頭撞到地面才清醒過來,還東張西望地問發生了什麼事。監視器已經確認過了……像你這種人很多,喝了酒就不知道自己變成什麼樣子,典型的酒精性失智患者。喝了酒而興奮地揮拳頭,酒醒後又哭著問為什麼自己會在派出所。就像從凶猛的老虎,變成溫順的羔羊,你們都是這種會突然性情大變的人。」
雖然不想露出驚慌神色,但我能感覺到臉上的僵硬,刑警們喜歡挖苦人的可憎醜話是事實。我的腦海一點也沒儲存喝醉時的記憶,但是喝酒前和酒醒後的情況卻留在記憶的膠捲裡。門與門是確定的,只是門與門之間的空間被燒燬了,所以必須想起和她在喝酒前和酒醒後的事。但我的記憶目錄中沒有那些,只能不斷主張自己沒有與她喝酒。
據說酒精性失智症越嚴重,會連喝酒前後的狀況也很難想起來。
刑警一口否定我的主張,大聲地說:
「我說作家啊,現在案件的大框架就是這個,李知英和你見了兩次面,然後就突然不見了。框架固定了,那中間應該怎麼填滿呢?因為李知英不聽你的話,所以你就折斷李知英的脖子,然後遺棄,不是嗎?或者是你製作的藝術品出了點問題,她要求退費,你很生氣所以把她殺了?就像砸相框那樣,把李知英也給砸了嗎?」
我說不出話來。眼前這個人不是刑警,根本是小說家,我真心想跟他說,他可以認真考慮轉行。刑警癟著嘴笑,彷彿我什麼話都不用說他全知道,接著像搖晃潘多拉的盒子般,拿著粉紅色手機在我眼前晃,低聲說: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隨時都可以來找我,不過,說不定我會先找上你。」
***
回家後,我再次回顧了我和她之間的時間軸。不過才一個禮拜,一個禮拜而已,以及見了兩次面,然後她失蹤了,我被當成嫌疑人到警察局去說明,這些事接連發生的時間不過才七天而已。
我在未接來電裡的號碼尋找,原本以電話號碼末四碼為四五○九存在的她,現在被我存下成了「李知英」,同時通訊軟體kakao talk的朋友目錄中,也自動出現她的名字。我進入連結的個人臉書,看到她的照片,嚇了一跳。披著白色夾克的她,肩上披散長直髮,怎麼看都覺得陌生。初次見面的那天,她是一頭齊耳垂的短鬈髮;第二次見面時則將頭髮高高挽起。穿著是什麼,我想不起來了,而除了這些,並沒有留下其他特徵。
但相較於在臉書上的照片,她本人明顯感覺比較放鬆。我所見到的李知英像是拿父母的錢上學、網路不離身的女孩。當然她並未那樣介紹自己,只是給我的印象是如此。然而手機螢幕中的李知英,是一身洗練裝扮、表情泰然自若的年輕上班族,而照片上傳的日期和我們初次見面的日子相同。難道她來見我時戴了假髮嗎?
不對,她在臉書上的長直髮也可能是假髮。
「有些人喝著夢幻湧泉噴出的水而活,對那些的人來說,現在猶如漆黑一片。」
彷彿有根細長的竹籤斜斜貫穿我的頭,我想起了李知英的聲音。在某段對話的結尾,她看著密密麻麻、掛滿相框的牆壁這麼說,沒有照片的相框就像沒有瞳孔的眼睛。我腦中浮現只有眼白的人,問她會不會太怪了,她搖搖頭。因為什麼都看不見,所以反而更加自由。瞳孔只會展現外面的東西,是屈從外界暴力的走狗。
那時我不知不覺抓起稜角分明的相框碎片,貼近她的脖子,說著那些話的她,既可愛同時也令人憎惡。她的話準確說出我的心聲,這讓我感到迷惑和怪異。若是她看著我的眼睛,我會道歉並放下框架碎片,但她卻一副服從似的表情閉上了眼。那一瞬間,她為什麼會那麼美麗?閉上眼的她,那模樣無法從我瞳孔抹去,就只能用眼皮遮住。我把嘴貼到她的脖子上,同時手變得無力,握著的框架掉落在地發出聲響。
我並不覺得可惜,因為只為打破而做的相框還有很多。比起四角方方正正的相框,我更喜歡雕刻品、繪畫和照片都裝不進去的模具。在破裂的瞬間,身體微微顫抖,我經常抓起相框扔出去,只為了感受那種顫抖。我在客廳地板鋪上地墊,遮住被撞擊出的凹洞,然後再鋪一層鬆軟的地毯,以免踩到碎片割傷腳。
我承認,當她對著我的臉發出「啊、啊」的喘息,或是像歌曲導入般的聲音時,我感受到砸碎相框時的顫抖。但是用這些事來把我和她的失蹤牽扯在一起,根本是無稽之談。
翻看她的臉書,照片中的她給我一種莫名的違和感。仔細看照片邊緣,似乎是
把相框裡的照片翻拍上傳,視窗裡隱約露出不同顏色和紋理的邊框。我噗哧一笑,邊框裡的邊框、框架裡的框架?
我再度想起跟我談論什麼案件框架和骨架的刑警,那一臉嘲諷的樣子。他分明是個不負責任的小說家,只用粗略的大框架,竟編出那麼荒誕的故事,不,那根本就是捏造出來的故事。因為不想再發揮想像力,所以把故事像麵團般隨便揉成一團就往我身上推。那個麵團已經壞了,害我的身體和生活都沾滿了霉味和惡臭。他把責任推給了我,逼我用壞麵團,做出某種像樣的成品。
當然,我只知道填補李知英失蹤框架的內容,就是我和她的失蹤沒有關係。為了找出證據,我更加速瀏覽李知英的臉書照片,畢竟與她莫名其妙有牽扯還不夠,還要消除因她失蹤而冠上的污名。我瞇起眼睛繼續看下去,她的臉書裡也有純文字的貼文。
我們談論了夢境、圍繞在四周的層與幕,在無數分裂的階層中,我們到底在什麼東西的懷抱裡呢?我問。作家說,我們在某人的相框裡,不管怎麼掙扎也跳不出去。他把照相框亂摔到地上,然後也給了我一個,要我如法炮製。相框撞擊地板破碎時發出的聲音還不錯。他說,在破碎的瞬間會產生快感,就像脫離了某人制定的框架,可以暫時喘一口氣。
我們摔壞了幾十個相框,他要我在碎片上面走。光腳嗎?我問。他點點頭。
他抓住我的臂膀扶我起來,我把涼鞋脫在他家玄關,所以真的是光著腳。我說我不要。他拾起一塊碎片說,我啊,不太喜歡人家看到我的作品就說漂亮,那只是無數感嘆詞中的一個。漂亮,說完就忘了不是嗎。他抓住我的肩膀,拿近末端尖銳的相框碎片。如果用這個插在身上留下疤痕的話,會一輩子記住吧,嵌在肉上的模具碎片。碎片的尖端頂著我的脖子,從頸部冒出的雞皮疙瘩一下傳遍全身。我走就是了。我說。
我的額頭皺起來。究竟是有什麼妄想症,才會寫下這種胡說八道的故事?手機裡留下我和我家的照片,在與萬人共享的臉書上,上傳了影射我的奇怪故事,讓我因此受到懷疑。刑警肯定也看過這些文字,才會編出失蹤的李知英像相框一樣粉碎的說法。李知英,毫無疑問一定是為了把我塑造成讓她失蹤的犯人,接近我都是有計畫的,如果不是那樣,就不會出現那麼多不利於我的虛假證據。我緊咬的下巴因憤怒而瑟瑟發抖,我再仔細查看她的臉書。以現實為題材的虛假世界,不,是以假亂真,企圖蠶食現實的卑怯陰謀。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原文 seol hea-wo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7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 149 ~ 315 | 自我魔術方塊 (電子書)
作者:原文 Seol Hea-Wo / 譯者:馮燕珠 出版社:奇幻基地 出版日期:2021-04-2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7 則評論 7 則評論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自我魔術方塊
細膩的心理描寫與反轉,
讓人無法移開目光的致命吸引力與洞察力。
「仁川文化財團,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支援事業」入選作品
★Yes24網路書店讀者評選星等9.5/10分
★2019年「仁川文化財團,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支援事業」入選作品
★短篇〈Clean Code〉獲得《Mystery》季刊2017年冬季號「推薦新人獎」
★短篇〈轉角〉獲得2012年「無等日報(무등일보)新春文藝獎」
▶專文推薦
|陳慶德(文化研究者,《他人即地獄》作者)
|喬齊安(推理評論家、百萬部落客)
▶驚豔推薦
|冬陽(推理評論人)
|何敬堯(奇幻作家,《妖怪臺灣》作者)
|陳栢青(作家)
|提子墨(作家、英國與加拿大犯罪作家協會PA會員)
|黃羅(推理讀書人)
(以上按姓名筆畫排序)
/
self cube,由六個面組成的立方體,如果都以未知的面構成,會是怎樣的世界?
以及,我……又會是誰?
/
我計畫完成一個世界。
為了讓身為主角的他,關閉所有連結,只能有一面敞開以單獨的本體生活,我要給他一個魔術方塊。拼對了一塊就更想再繼續,一個內裝迷宮、能自行變換密碼、改變形狀、獨一無二的魔術方塊,也就是名叫「自我」的魔術方塊。
一個女子失蹤了,曾與她見過面的一名男子成為最有嫌疑的人。
涉有重嫌的男子極力否認,而一直看著這一切的被害人雙胞胎姊姊、警察及心理醫師,將該如何找出真相?
七篇各具特色的故事,無法預測、設定精巧的文句美學,
將最幽微、不欲人知的人性撕扯至極致,
直到蓋上最後一頁前,都讓你感到靈魂冷卻又刺激,一刻不能失神。
/
▶各界好評及讀者迴響
「《自我魔術方塊》集結了七樁仿若怪談、黑暗扭曲的故事,不經意地窺見人皮面具底下的張牙舞爪,生猛異常。它有那麼點返祖,回到推理小說強調的理性邏輯之前,叫人不自在的怪誕恐怖緩緩纏上身,甩脫不掉又夾帶強烈的生活寫實,的確夠勁。」——冬陽(推理評論人)
「本書是一座試煉人性的修羅場,也是善惡的終極考驗,小說家以不同凡響的筆法,描繪出殘酷與救贖的一線之隔。」——何敬堯(奇幻作家,《妖怪臺灣》作者)
「誰?在哪?何時?發生什麼事?南韓新生代推理小說家薛惠元,以讓人屏息以待、步罡踏斗的結局,像把利刃刺向讀者,挑戰人們閱讀快感。」——陳慶德(文化研究者,《他人即地獄》作者)
「如果你熱愛懸疑反轉的結局,《自我魔術方塊》中七篇風格迥異的短篇小說,將一次帶給你七種震撼腦細胞的驚悚反轉。」——提子墨(作家、英國與加拿大犯罪作家協會PA會員)
「本書猶如主打韓式料理的驚奇劇場,內含驚悚、恐怖、懸疑、推理,以及黑色幽默等七篇故事,令人不禁一篇接一篇地大快朵頤!」——黃羅(推理讀書人)
「作者用充滿驚異感的視線和情感,致力將不可思議的世界形象化的意志令我驚訝。我認為,作者選擇懸疑小說這一題材的動機,在於意志的體現。在人們不以為然、或理所當然的事實背後,存在著充滿驚奇的未知和真相,不僅是懸疑類型作家的認知,更是一般本格文學作家的認知。薛惠元把一般的東西以懸疑謎團的方式活性化。」——田英泰(文學評論家,中央大學名譽教授)
「《自我魔術方塊》是一部毫無保留地展現懸疑小說魅力的作品集。無法預測的設定和壓倒性的速度、擊中要害的精巧文章美學,在闔上最後一頁之前,一刻也不能掉以輕心。薛惠元的小說真正驚人的力量,是讓人在最後被喚醒,原來『生活也是一種夢境』。她的作品內藏精心安排的懸疑緊張和別具意義的反擊,是韓國文學的獨特成就,也可說是懸疑推理小說的新紀元。」——房玄錫 (小說家,中央大學教授)
「懸疑驚悚小說中間隱藏的伏筆固然重要,但反轉的結局才是最吸引人的。本書中〈自動魔術方塊〉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反轉,完全和我想像的不一樣,讓我讀得非常過癮。」——讀者skdjaak31
「這本書雖然是推理驚悚小說,但並不侷限於一種類型,跨越多種體裁組成,各有各的特色與個性,讓人讀起來似乎不覺得枯燥乏味,非常獨特。」——讀者okk36
「偶然拿起書翻開,再回過神來已經看到最後了。在小說中出現許多讓人意想不到的內容,只能說作者真是太強大了!」——讀者kdh4067qq
「作者對心理學及人性的精神世界深入著墨,以破格的設定、衝擊性的反轉及流暢的敍述能力貫穿每一篇故事,讓人看了大呼過癮又覺得故事就這樣結束有點可惜。期待作者的下一部新作品。」——讀者ghs744
「新穎的內容及角色設定,作者用帶有魅力的筆法講述他們經歷的心靈故事,在閱讀的同時似乎也隨之在故事裡走了一回,讓人意想不到的鋪陳不同於一般小說感覺頗有新意。」——讀者7eisbar
「強烈的心理描寫、社會批判的素材、獨特的文字力、緊湊的鋪陳等,內容隱含了對韓國人的生活和社會的批判,偶而還夾雜了一點黑色幽默,是一本非常特別的小說。」——讀者heena0521
「很少短篇小說能讓人看得如此投入,緊湊的故事情節和奇特的想像力,在閱讀中根本無法將視線從字裡行間移開視線,卓越的心理描寫能力和到處都有意想不到的轉折令人驚奇。」——讀者sene001
「看這本書有一種走訪奇幻國度的感覺,翻開書頁後進入的七個意想不到的國度,讓人想越走越深入。打開書頁大門目睹七種不同的『惡』,這世上沒有所謂的『正常』。作者不可思議的想像力讓這部小說集深具魅力。」——讀者kaketz0703
作者簡介:
薛惠元Seol Hea-Won
大學主修文學創作,2012年以短篇作品〈轉角〉獲得「無等日報(무등일보)新春文藝獎」後,正式進入文壇。短篇作品〈Clean Code〉獲得《Mystery》季刊2017年冬季號「推薦新人獎」,並以本部短篇小說集獲得2019年「仁川文化財團,韓國文化藝術委員會支援事業」入選作品。目前為「韓國推理作家協會」會員。
譯者簡介:
馮燕珠
新聞系畢業,曾任職記者、公關、企劃。辭去工作隻身赴韓進修,回國後踏入翻譯界。譯有《飛機雲》、《破果》、《外面是夏天》、《我是遺物整理師》等。
工作聯繫:yenchu18@gmail.com
章節試閱
〈自我魔術方塊〉
叩叩
——逃跑也沒有用,他們總是追上來找我。不管我去哪裡,就算躲在深處也一
樣。快點。要逃跑才行。要快點跑才行。前往向西延伸的奇異庭園。
「我不認識四五○九……不是,我不認識那個女人,只有在二手拍賣社團裡交易過相框而已。因為商品有瑕疵,她百般挑剔,我就乾脆賠償給她。就只有這樣,我連她的名字也是到現在才知道的。」
「但是她在失蹤前一個小時打了十次電話給你,你卻一次也沒有接。」
刑警斜睨著我的臉,目光銳利。他想讓我開口說話,但我真的一無所知,無可奉告。她和我是透過一個二手拍賣社團...
叩叩
——逃跑也沒有用,他們總是追上來找我。不管我去哪裡,就算躲在深處也一
樣。快點。要逃跑才行。要快點跑才行。前往向西延伸的奇異庭園。
「我不認識四五○九……不是,我不認識那個女人,只有在二手拍賣社團裡交易過相框而已。因為商品有瑕疵,她百般挑剔,我就乾脆賠償給她。就只有這樣,我連她的名字也是到現在才知道的。」
「但是她在失蹤前一個小時打了十次電話給你,你卻一次也沒有接。」
刑警斜睨著我的臉,目光銳利。他想讓我開口說話,但我真的一無所知,無可奉告。她和我是透過一個二手拍賣社團...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驚奇又驚奇 by 田英泰(韓國文學評論家,中央大學名譽教授)
推薦序:誰?哪裡?何時?發生什麼事了? by 陳慶德(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推薦序:眼花撩亂的七巧板魔術 by 喬齊安(Heero,推理評論家、百萬部落客)
Clean Code
轉角
閱覽室使用守則
自我魔術方塊
自動販賣機倉庫
墨非的詭計
月光
誌謝
推薦序:誰?哪裡?何時?發生什麼事了? by 陳慶德(逢甲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推薦序:眼花撩亂的七巧板魔術 by 喬齊安(Heero,推理評論家、百萬部落客)
Clean Code
轉角
閱覽室使用守則
自我魔術方塊
自動販賣機倉庫
墨非的詭計
月光
誌謝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 |||
|
|

 2021/04/22
2021/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