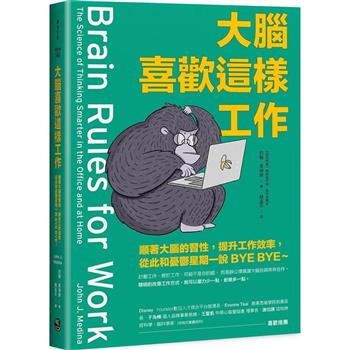身為國家任命的法醫專家,我的團隊經常接獲請求,協助調查分屍案件。即使屍塊沒有散落在兩個不同行政區,這種案件本身就已經非常複雜,但我們在二○○九年時就接獲了這樣一起屍塊分散在兩郡的案件。
警方起初之所以接獲這起可疑的死亡事件,是因為有人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鄉間小路旁發現藏在塑膠袋中的人類左腿和左足。由於遺體非常新鮮,乾淨俐落地從髖關節切除,警方認為可能是鄰近醫院的手術解剖廢棄物。警方立刻聯繫區域內的所有醫院,確認手術後焚化廢棄物的過程是否出現任何異常跡象,但所有院方都堅決表示屍塊並非來自於他們。在比對基因資料庫之後,也找不到任何符合資料。遭到遺棄的肢體明顯屬於一位成年的高加索男性。雖然我們可以透過腿部長度推斷死者身高,但僅靠腿部所能提供的有限資訊,我們也找不到符合當地或英國失蹤人員管制局紀錄的資料。
七天之後,只剩下手肘至手腕處的左前臂出現了,同樣包在塑膠袋中,發現地點是另外一條公路旁的水溝,距離左小腿遭到丟棄的地點二十英里。左前臂的基因比對和左小腿基因相符。又過了兩天,一位來自萊斯特郡(Leicestershire)的農夫,驚慌失措地帶著一顆被丟棄在他乳牛牧場的人頭出現。由於負責調查人頭的警察單位與先前不同,這個案件並未立刻和先前出現的左小腿和左臂連結起來。萊斯特郡警方一直在尋找一位受到高度關注的女性失蹤者,他們認為死者頭顱可能是她的──然而,雖然頭顱的死亡時間不久,卻因為皮膚和軟體組織已經消失而無法進行臉部辨識,法醫病理學家相信消失的原因可能是遭到動物啃咬。經過我們的分析後,結果顯示死者可能是男性,此外,頭骨和失蹤者照片的比對結果也不相符。
萊斯特郡警方也搜尋了基因資料庫,卻徒勞無功。數天以來,兩個地區的警力各自在管轄區域尋找其他消失的身體部位。接著下一週,自膝蓋切開的右小腿出現在赫特福德郡,用塑膠袋包著藏在旅行日用衣物包中,發現地點則是農村小路的停車場。四天之後,警方終於找到死者的軀幹,軀幹上連著左上臂,一起發現的還有右手臂,但右手掌遭到切除。軀幹和右上臂整個被毛巾包住放入行李箱中,被丟棄至郊區的田野排水管,發現地點一樣是赫特福德郡。
所有屍體部位的基因比對相符,但國家基因資料庫卻查無資料,因此若想建立死者身分,並進一步追查死因和凶手(或凶手們),都非常有挑戰性。雖然腳掌還在,手掌卻已遭到切除,下落不明,由此可見凶手的肢解方式不符合一般的六塊規律。然而屍體的丟棄方式確實吻合常見的肢解動機:減低棄屍難度。由於遺體缺乏手掌,臉部也遭到損毀,代表凶手可能還有額外的防禦動機:掩蓋受害者的身分。
死者遺體散落在如此廣大的地理區域,造成行政管理的紊亂。誰應該負責領導調查行動?發現死者頭部的警察單位?找到第一個身體部位的警察單位?還是擁有最多身體部位的警察單位?這是一個重要的後勤分配問題,必須整合不同的警察單位,共同調查一件重要案件。但之後的事實證明,在我們所見過的兩方警察合作行動中,這是最專業的一次。
露辛娜.哈克曼博士和我一起從蘇格蘭前往南方協助調查。漫長的旅途讓我們有時間長談──倘若奧運舉辦交談比賽,我們一定每次都能替英國贏得金牌。雖然我們在中途繞道前往英格蘭北部地區,協助處理另外一個案件,牽扯到毒品幫派勢力的爭鬥和一具臉部受損的屍體,但我們依然花了許多時間來討論肢解案件。我們所做的假設並不符合警方目前的理論,因此我們必須利用這七個小時的車程仔細梳理,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錯了,就會成為特威德河2以南最笨的兩個呆子。但倘若我們是對的,赫特福德郡和萊斯特郡的警方就要開始積極偵辦了。
我們並不同意警方對凶手犯案手法的假設,因為某些關鍵就是不對勁,而我們是兩個最容易起疑心的中年婦女。我們的第一個疑問是肢解的位置。凶手的肢解模式幾乎完全符合一般肢解行為,但肢解方法相當詭異。從未肢解任何屍體的人──坦白說,大多數的人都沒有相關經驗──最有可能嘗試的切割方式,就是從四肢的長骨開始切開手臂的肱骨和腿部的股骨。鄧迪大學研究中心的研究結果認為,如要肢解屍體,多數人的第一選擇是尖銳的廚房刀具,隨後才會發現這種刀子雖然可以切割皮膚的軟體組織和肌肉,卻不能切斷骨頭後,才會前往工具室或車庫尋找鋸子,通常是木鋸或鋼鋸。而喜歡烹飪的人可能也會考慮使用切骨工具,例如廚房的鋸肉刀或放在外屋的斧頭。但這個案件中的屍體模樣更接近「從關節拆除四肢」,而不是鋸斷,這種情況非常罕見。事實上,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接觸此種案件。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骨頭表面,才能決定凶手到底是使用哪種類型的工具,但能肯定的是此事必有蹊蹺。
第二,凶手處理屍體頭部的方式與其他屍體部位不同。首先,屍體發現的地點位於其他郡縣;其次,屍體頭部未經包裝,也是唯一失去軟體組織的部位。我們不相信法醫病理學家提出的理論,他們認為原因是動物啃咬,但屍體頭部沒有任何由家禽或野生動物啃咬造成的常見齒痕。
犯罪工具痕跡分析(Tool-mark analysis),至少在原則上,是一種非常直觀的分析方式。當兩個物體碰撞後,較為堅硬者可能會在較為柔軟者的表面留下痕跡。舉例而言,如果你用鋸齒麵包刀切割一塊起司,因為麵包刀是較為堅硬的物體,就會在較為柔軟的物體表面,留下多個脊狀痕跡,在這個例子中,起司就是那件柔軟的物體。同樣的道理適用於骨頭。如果骨頭接觸尖銳物體,例如刀子、鋸子或動物牙齒,就會留下能夠辨識的痕跡,而痕跡的樣式可能足以辨識造成傷痕的物體或工具。因此,如果死者頭部的軟體組織消失是因為動物的啃咬進食行為,應該會看見動物牙齒所造成的特殊痕跡,但我們嚴重懷疑這個理論的可能性。
死者頭部已經沒有皮膚和肌肉,眼球、舌頭、口腔底部和耳朵也消失了。如果一隻動物可以如此吞食人類遺體,並且未留下任何痕跡,簡直是神乎其技。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在不同肌肉黏著骨頭的區域找到尖銳刀具的切痕。倘若事實真是如此,除非野生或生活於人類花園的獾類在一夜之間奇蹟進化,變得善於使用人類刀具,否則很明顯地,死者頭部的軟體組織是遭到人類親手移除──而這就需要進一步解釋了。死者頭部被乾淨俐落地從第三頸椎和第四頸椎之間切除,肢解位置也有不尋常的問題。
直到親自檢驗屍體之前,我們閉口不談自己的想法。參加案情簡報會議時,我們也彬彬有禮地聆聽警方提出他們推測的動物啃咬理論。在這種環境中,我和露辛娜非常注意自己的眉毛。有人說過我們的眉毛會說話,如果我們不同意別人的說法,眉毛就會上下擺動,彷彿方向不一的眉毛百葉窗一樣。有一次,我們以專家證人身分出席英格蘭的法院審判時,頻頻聽見檢察官提出令人難以置信的證據。但我們同時也知道自己就坐在陪審團正前方,他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們不得不時刻壓抑眉毛的自然反應,甚至因此覺得額頭開始痛了起來。我和露辛娜在撲克牌桌上表現一定非常糟糕。
我們在會議中隻字未提,並且盡力控制眉毛的反應,直到我們終於進入停屍間,得以近距離檢查屍體。凶手的技巧非常值得注意,他(她)完全切除了死者頭部的組織。我們也在原先預期之處找到刀痕,就位於頭部後方、頭部側邊以及下顎下方。所有的軟體組織早已不復存在;實際上,死者的整張臉都被割除了。
令人驚訝之處不只如此。在檢查遺體其他部位之後,我們發現凶手一次就完美地肢解了死者的手腕,準確地切入腕骨和前臂長骨(橈骨和尺骨)之間的關節。死者的臀部也被切除,從髖關節摘除股骨,而左手肱尺關節切除手法的專業程度讓我們明白,無論凶手是誰,他(她)必定非常熟悉解剖。更重要的是,凶手清楚知道如何解剖人體,也不是第一次肢解屍體。
不使用鋸子、鋸肉刀或其他類型的大型工具進行肢解的案件非常罕見,但這具屍體的每一個部分都清楚地顯示,凶手並未在任何階段使用重型或鋸齒狀的工具,唯一的工具就是一把銳利的刀,而這才需要真正高難度的技巧。就連遺體頭部上,也沒有發現任何切割痕跡。事實上,這種俐落的肢解行為完全像是解剖學家、停屍間工作人員或者外科醫師的手法,才能將髒亂、問題和費力程度降至最低。請原諒我就不在此處分享箇中秘訣了。
露辛娜和我透過許多手勢和眉毛動作暗暗地交流了許多想法。警方也察覺事情不對勁。而我們也察覺了他們的不安,因此在確定相關證據之後,就立刻召開會議發表我們的發現。一如往常地,他們會在一開始反駁我們的觀點(「但是,法醫病理學家認為……」),但在看見無可反駁的證據後,他們就匆忙離開會議室,開始倉促地用行動電話進行聯絡。
我們推論著凶手的可能職業:獸醫?屠夫?外科醫師?狩獵場看守人?法醫病理學家或者解剖學家?應該不是同行的法醫人類學家吧?無論凶手是誰,他(她)的肢解技巧雖然高超,丟棄遺體的能力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除了手掌之外,其他遺體部位很快就被發現了。
被害者的死因非常直接,他在背部遭受一把四英寸長的刀攻擊兩次,其中一次刺穿肺部,不久以後就斷氣身亡。法醫病理學家推估凶手花費了十二個小時完成肢解過程,但我們不同意這項推論。凶手的肢解技巧程度讓我們相信他(她)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所有過程,再用另外一個小時,包裝屍體部位並清理現場。
當法醫人類學家完成分析、拍攝照片,並交出報告之後,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調查結果,除非我們持續注意新聞報紙的報導。因為我們在全國各地工作,不見得與警方保持密切聯絡,但民眾會因為電視犯罪影集時而產生錯誤的印象。有時候正如這個案件,我們沒有收到任何後續通知,直到數個月之後才拿到法院傳票。我們不知道警方找到什麼,也不清楚調查結果,所以我們只能帶著自己發現的證據走入法庭,通常也不清楚案件和證據之間的相關脈絡。
我討厭出庭,在這個冷漠詭異的場所工作,是職業生涯中極具壓力的一環。法庭的規則既非由我們制定,我們也鮮少知道辯護策略。在英國的對抗制法律系統中,其中一方會想證明你是全球頂尖的專家,另一方則希望證明你只是滿口胡言的白痴;我經常體驗這兩種處境,也常在中間受到兩面夾擊。
這個案件在媒體報導中變得相當知名,被稱為「拼圖謀殺案」。警方檢驗了所有遺體部位後,檢驗結果與一名住在倫敦北部的失蹤男性相符,牙醫紀錄也確定了死者身分。警方在死者公寓的臥室、浴室,以及汽車後車廂發現了血跡,但痕跡只有一點點,凶手和共犯──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同時遭到起訴──清理得很乾淨。
檢方以謀殺和其他相關的竊盜和詐欺罪名起訴這對情侶。由於被告共有兩名,代表法庭將進行三次律師詰問,加上檢方可能還會再度詰問。因此,我們必須準備接受四次詰問──真是開心啊!在一座陌生城市中出席陌生的法庭作證,面對一年前處理的案件,沒有任何建議可言,所有的情況加起來只會讓你更緊張。如果有人請你出庭討論證據,你一定會假設他們相信你的證據具備審判價值,但你既不清楚具體內容,也不知道律師或檢察官的問題究竟會引導你完成何種結論。
檢方引導我說出自己的專業資格與與案件相關的證據,一切都很順利,但光是如此就已經用了一個早上,法官決定暫停審判,進入午餐休息時間。這代表你必須離開法庭,消磨一個小時之後,再回到法庭中,接受兩名辯護律師的詰問,這才是正式進行法庭對抗與挑戰出現的時候。而這場坐在證人席上的詰問很可能會延續到第二天,這件事情讓我更緊張,因為我不能在這段時間與任何人討論案情。
第一個辯護律師看起來很迷人,但這永遠是一個警訊。他同意我擁有合格的專業證人能力,希望討論我們的主張:肢解者擁有精細複雜的解剖知識。他告訴我,他的當事人曾是私人健身教練,也擔任夜店保鏢,既沒有任何解剖訓練背景,不曾在肉店工作,也不住在屍體出現的郊區,更不從事郊區戶外活動。被告當然也絕對不是外科醫師、獸醫、解剖學家或法醫人類學家。這樣一來,被告要如何完成我描述的精準解剖,或者具備我推測的專業知識?
在這種時候,你的頸部後方會開始冒出冷汗,緩緩地流至脊椎。你開始思考:我怎麼會犯下如此荒謬的錯誤?你開始反覆懷疑自己,卻始終無法提出其他合理的答案。辯護律師旋即將話題引導至犯案工具。他推論,肢解屍體實際上應該會需要特殊的工具。而我的回答是,在這個案件的手法中,只需要一把尖銳的廚房刀具就夠了,前提是凶手知道如何解剖。
「您說的沒錯,但家庭用的刀具,銳利度並不足以解剖屍體,對嗎?」
回答時,我已經知道自己的說法必然會引起麻煩:「律師先生,恕我直言,我家廚房的刀子就夠銳利了。」
他的反應很快,立刻回應:「請務必提醒我,絕對不要到府上吃晚餐。」法庭響起一陣笑聲,我嚇呆了。我從來沒有在法院審判過程中,看過律師如此幽默的表現,更別提這還是一宗褻瀆屍體和謀殺罪的案件。或許我無須感到如此驚訝,畢竟死亡和幽默是老朋友了,除此之外,在承受數日的耗磨心力後,法庭的出席者反而會感謝律師的幽默一語緩和了現場的緊張情緒。我何其希望能用一句睿智機靈的臺詞反擊,卻沒有勇氣。耍嘴皮子是冒犯律師的最快方法,因此,我聰明地選擇了沉默。
在開庭之前和審判期間,被告和共犯都堅稱自己無罪,但在審判結束之前,他們毫無預警地認罪了。男性被告承認自己謀殺被害人,女友也承認協助犯案、教唆以及妨礙司法正義。凶手的刑期因為肢解行為而有所加重,而因為兇嫌在審判結束之前才認罪以及犯行嚴重,認罪並未幫他減輕刑期。他被判決最低三十六年的有期徒刑。
在判刑不久之前,被告透過對案情發展也相當意外的律師坦承,他還肢解過其他四名男子。警方對於被告的自白非常驚訝,但被告拒絕透露被害人的身分和藏匿屍體的位置等相關細節。
被判刑的男人確實曾受一間夜店的合法聘僱為門口警衛,但他也是一個惡名昭彰的倫敦幫派訓練的「刀手」。如果幫派殺害線民或任何造成麻煩的人,就會在午夜時分將屍體帶到夜店後門,由「刀手」分屍,再將屍塊交給「棄屍人」,他的責任就是處置屍塊,通常會埋葬於艾平森林(Epping Forest)中。本案的凶手宣稱,他就是將受害者的手掌丟棄於艾平森林。
凶手曾在一位資深刀手底下擔任學徒,學習如何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肢解人類屍體。幫派分子在處理屍體上的精細分工,也解釋了為什麼凶手的肢解技巧嫻熟,「棄屍」能力卻相當糟糕。但誰又能想像「分屍」居然會是某個人真正的「職業」呢?誰會在履歷上列出這份工作呢?
我從未如此慶幸自己和露辛娜的想法是對的。凶手切除受害者的臉部軟體組織,就是為了隱藏法醫證據。一開始,兩名共同被告都主張對方才是凶手,並且提出了兩種不同的謀殺方法。只有檢驗死者頭部和頸部的軟體組織才能確定何者所言為真。因此,凶手移除臉部的手法是一種保險,避免他們遭到警方逮捕時被查獲證據。他們相信,如果我們不能證明哪一方說謊,法院就無法定罪。他們最後為何選擇認罪,我們永遠不知道原因。
他們的動機似乎只是財務方面的利益。他們偷走了受害者的身分,變賣他的財產並結清他的銀行帳戶。受害者是一位單純無辜的男人,在凶手走投無路時收留他們,而他們的回報是殺了他並且褻瀆他的屍體。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原文 sue blac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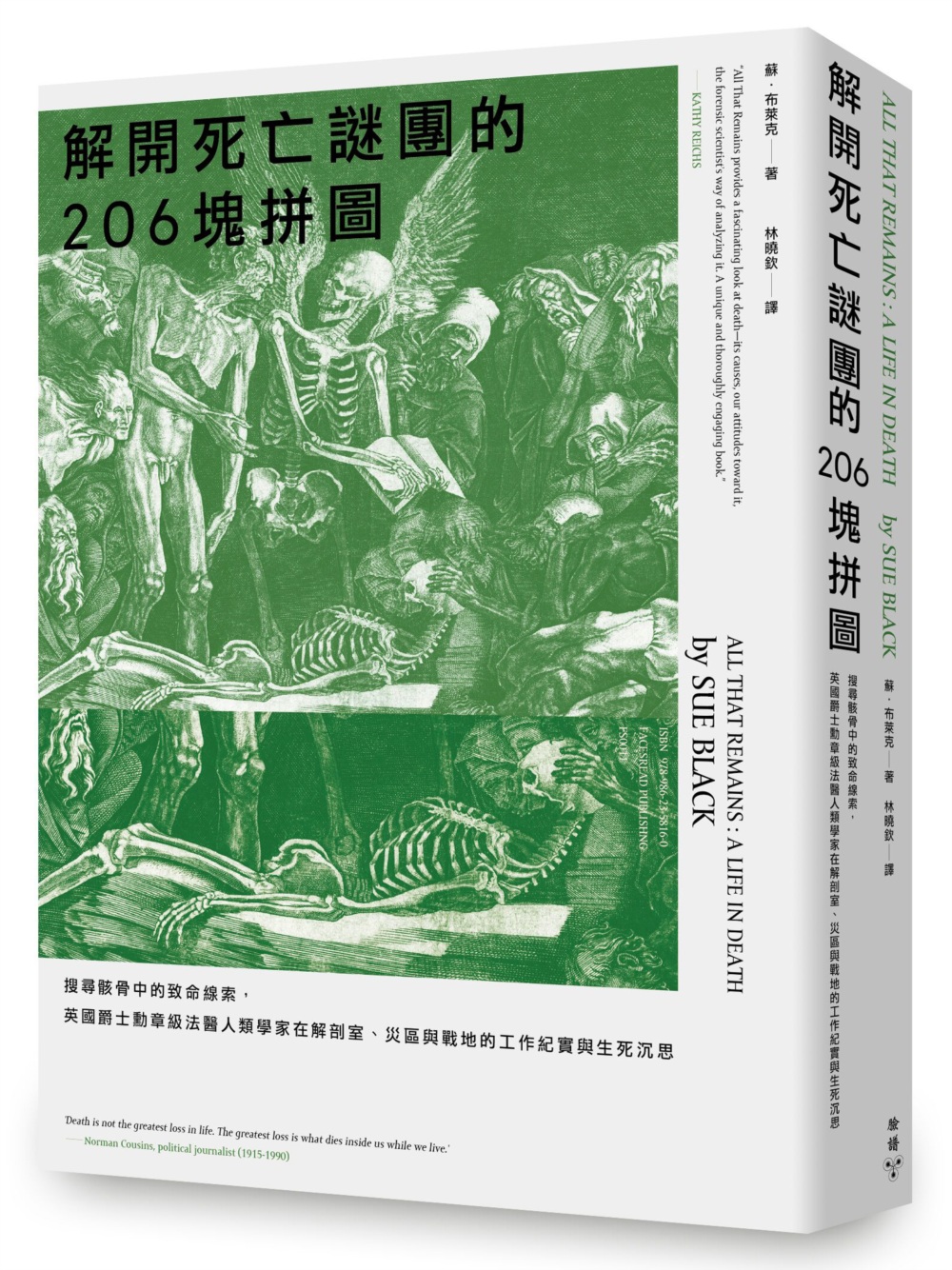 |
$ 190 ~ 378 | 解開死亡謎團的206塊拼圖:搜尋骸骨中的致命線索,英國爵士勳章級法醫人類學家在解剖室、災區與戰地的工作紀實與生死沉思
作者:原文 Sue Blac / 譯者:林曉欽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20-03-1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84頁 / 21 x 14.8 x 2.3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1 則評論 1 則評論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1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解開死亡謎團的206塊拼圖:搜尋骸骨中的致命線索,英國爵士勳章級法醫人類學家在解剖室、災區與戰地的工作紀實與生死沉思
+
揭露罪案真相、鑒證歷史創傷的現代法醫工作實務手記
泰絲.格里森、李.查德、凱絲.萊克斯、薇兒.麥克德米……等暢銷犯罪推理作家同聲推薦!
從手足無措的解剖課學生,到榮獲英國女王授勳的法醫人類學家
火焚、水淹、土埋,都無法讓證據逃過她的顯微鏡
科索沃戰爭、南亞大海嘯、與形形色色的犯罪現場,都是她的鑑識工作空間
屍體經過支解、焚燒等嚴重傷害,或是自然的腐敗分解之後,
只剩下體內的206塊骨骼記錄著死者在生命終點前的遭遇,
負責解讀這些線索的,就是法醫人類學家──
四十年前,一個特立獨行的蘇格蘭女孩在肉舖打工時初次見識了解剖的奧妙,一點也沒有被血腥四溢、骨肉剝離的場面嚇倒;四十年後,她是英國最著名的法醫人類學家──蘇.布萊克。
研究人體骨骸奧祕的歷程帶她走進各式各樣的死亡事件現場,在火災後的灰燼裡篩撈獨居老人的碎骨,在吸滿屍水的床墊上拔起木乃伊化的乾屍,在分屍謀殺案嫌犯的浴室裡尋找細小至極、卻足以左右判決結果的屍骨碎屑。而這些任務之間,還穿插著一段段令人無言以對的插曲:遺骸檢驗報告上以公式推算出的死者身高,因為兩公分的誤差被家屬拒絕接受;關心辦案進度的靈媒,不斷「開示」失蹤人口遺骸的埋葬位置,使得鑑識團隊疲於奔命……
由零碎受損遺骸判斷死者身分及死因的能力,不但讓布萊克成為英國警方的破案幫手,更讓她多次受國際組織之邀,前往戰亂衝突與自然災害後的大規模死傷地區,例如一九九九年剛經過南斯拉夫內戰的科索沃、以及二○○四年南亞海嘯後的印尼,為難以辨識的無名屍體找出身分,撫平家屬的徬徨痛苦,也以鑑識科學的實證手段揭露戰爭中屠殺平民、毀屍滅跡的暴行。
這不只是一部精采度媲美小說的法醫辦案實錄,更是一位聲譽卓越的鑑識科學專家從求學啟蒙到發揮專業的生涯紀實,詳盡地描寫了現今法醫人類學在各種領域的應用,以及從業人員所面對的日常挑戰,豐富的人性關懷也反應在作者對法醫人類學家使命的詮釋:不僅要找出死者為何而亡,更要重建出他/她生前如何而活。
┤好評推薦├
泰絲.格里森:「大多數人都畏懼死亡,但蘇.布萊克讓我們看見,死亡其實是一段充滿驚奇的過程,而且與生命本身密不可分。《解開死亡謎團的206塊拼圖》解密了她與死者為伍亦為友的不凡人生。」
李.查德:「蘇.布萊克寫起生死大事滿是溫柔、毫無贅言,流暢地解析複雜的科學原理。」
凱絲.萊克斯:「本書讓讀者看見死亡的迷人面向──致死的原因、人們面對生命終點的態度,以及鑑識科學家分析死亡的方式。一部獨特且充滿吸引力的作品。」
薇兒.麥克德米:「沒有哪位科學家比布萊克教授更善於溝通表達,《解開死亡謎團的206塊拼圖》是一部混合了回憶錄與論著的獨特之作,帶領我們進入法醫人類學的奇妙世界。」
作者簡介:
蘇.布萊克Sue Black
全球頂尖的解剖學家與法醫人類學家,出身蘇格蘭,曾任教於鄧迪大學及蘭開斯特大學等多所教學及醫學機構,現於布列顛暨愛爾蘭皇家人類學學會擔任會長,因她對法醫人類學的重大貢獻而榮獲英國女王於2016年授予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
除了協助警方鑑識刑案中的遺骸、判定涉案者的骨骼生理特徵,她也曾參與古羅馬遺址考古,並曾遠赴科索沃戰地與南亞大海嘯災區,為罹難者進行身份鑑定。在本業之外,她也為BBC熱門紀錄片影集《歷史懸案》(History Cold Case)擔任主講,對大眾介紹法醫人類學知識。
譯者簡介:
林曉欽
臺灣大學政治碩士,譯作包括《太空的六場葬禮》、《歡迎來到夜谷》、《生活槓桿》等。
章節試閱
身為國家任命的法醫專家,我的團隊經常接獲請求,協助調查分屍案件。即使屍塊沒有散落在兩個不同行政區,這種案件本身就已經非常複雜,但我們在二○○九年時就接獲了這樣一起屍塊分散在兩郡的案件。
警方起初之所以接獲這起可疑的死亡事件,是因為有人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鄉間小路旁發現藏在塑膠袋中的人類左腿和左足。由於遺體非常新鮮,乾淨俐落地從髖關節切除,警方認為可能是鄰近醫院的手術解剖廢棄物。警方立刻聯繫區域內的所有醫院,確認手術後焚化廢棄物的過程是否出現任何異常跡象,但所有院方都堅決表示屍塊並非來自...
警方起初之所以接獲這起可疑的死亡事件,是因為有人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的鄉間小路旁發現藏在塑膠袋中的人類左腿和左足。由於遺體非常新鮮,乾淨俐落地從髖關節切除,警方認為可能是鄰近醫院的手術解剖廢棄物。警方立刻聯繫區域內的所有醫院,確認手術後焚化廢棄物的過程是否出現任何異常跡象,但所有院方都堅決表示屍塊並非來自...
顯示全部內容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