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一個階級的傳記
本書是一個階級的傳記,主角為十九世紀(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的中產階級 (譯註:中產階級、布爾喬亞、中間階層為同義語,作者在本書中交替使用)。我選擇史尼茨勒作為導遊,他是該時代最引人入勝的劇作家與長短篇小說家。為什麼選史尼茨勒?他很難說是最典型的布爾喬亞。在十九世紀,有多不勝數與他同一階級的成員富裕不如他、才智不如他、坦白不如他──神經質不如他,也就是說比他更具代表性。因此,如果「代表性」一詞所指的是「一般」,那史尼茨勒將不勝任導遊之職,因為最不適用於他的形容詞就是「平庸」。然而,從事研究的過程中,我卻發現他具備一些很特別的素質,讓他異乎尋常適合充當我要描繪那個中產階級世界的見證人。他將會出現在接下來的每一章,有時是作為引子稍一出場,有時是全程參與。我發現這個人極為引人好奇(不代表他總是討人喜歡),但單憑這一點,並未讓他夠資格在我企圖探索和了解的那齣包羅廣泛的戲劇裡扮演某種司儀角色。我有更好、更客觀的理由。
史尼茨勒是徹頭徹尾的維也納人。他生於維也納(一八六二年),逝於維也納(一九三一年),除短期到過倫敦、柏林和巴黎,以及在義大利北部度過一些短假以外,一輩子都住在維也納。不過由於具有活躍、銳利的胃納品味,讓他有機會接觸到極其多樣的風格與觀念,而他也克盡職責,數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記錄在日記裡。他具有深入其時代中產階級心靈(包括他自己的)的特殊憑藉。
要言之,他的教養是全方位的:他的人生與作品都在在見證著,人要見多識廣,並不是非要行萬里路不可。心靈是可以接受來自遙遠異地和異代的精神悸動啟發的──史尼茨勒的心靈就是如此。現代的法語和英語文學(含美國文學)都是他的讀物,更不用說的是斯堪地那維亞和俄國重要小說家與劇作家的作品。他對音樂與藝術具有同樣大的容受力。可以說,在他的陪伴下,我遊歷了挪威和義大利、俄國和美國。正如我暗示過的,他是個親切、可信賴和淵博的資訊提供者。
史尼茨勒是十九世紀人,但其生命卻深入到二十世紀。而因為十九世紀乃是二十世紀的孕育者,它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歷史。史尼茨勒藉以架接這兩個世紀的,並不是只有他的肉體生命。人們常常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之間劃下不可跨越的鴻溝。這種說法,固然適用於政治的領域(二十年後那場空前的集體動員和集體屠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種下的果),卻不適用於高等文化的領域。我們常常認為,那些發生在藝術、文學和思想上的激動人心大變動(被統稱為「現代主義」)是二十世紀的產物,但深入探究,就會知道它們是孕育自一九一四年以前(譯註:請讀者注意,作者對十九世紀的「界定」是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一四年)。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這個改變了哲學輪廓的顛覆性思想家為例,儘管他在一八八九年已經發瘋和不再發聲,卻仍然對我們今日的思想世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只是我們多大程度上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祖先餘蔭的其中鮮明一例。
少數藝術家的取樣也許就足以佐證我此說不虛:在戲劇界掀起革命的易卜生(Henrik Ibsen)、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以及繼他們之後的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都是早在一九○○年前就大名鼎鼎(或者說惡名遠播)。另一位他們顯赫的同儕契訶夫(Anton Chekhov)逝世於一九○四年。音樂界方面,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在一九○八年發表他的第二首四重奏,摒棄傳統的調性系統,進入了無人探索過的音樂地帶。最盛名不衰的幾位現代主義小說家──普魯斯特(Proust)、喬哀思(Joyce)、湯瑪斯.曼(Thomas Mann)和漢姆生(Kunt Hamsun)──都是在世紀之交展開他們的事業;當其時,契訶夫已經不只是個戲劇的巨人,而且也聳立為短篇小說的巨人。繪畫方面,學院派畫家早在一九○○年前就經受了來自獨立畫家幾十年的壓力,只能眼睜睜看著叛逆份子人數與影響力有增無已;一連串的極端畫派(印象主義、後印象主義、表現主義,以及德國和奧地利藐視藝術建制的分離主義者)一直都是沙龍藝術家的無情批評者。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逐漸疏遠具象派繪畫若干年後,於一九一○年畫出他的第一張抽象畫。這份名單還可以隨意延伸:不管是在詩歌、建築、都市規劃的領域,一種新的文化正在誕生。這就怪不得世紀之交一個由波納爾(Pierre Bonnard)和維亞爾(Edouard Vuillard)領導的繪畫學派會把他們的團體命名為「那比」(Nabis)──「那比」是希伯來文,意指先知。他們是航向未來的。
史尼茨勒也是如此,他的作品遊走於中產階級可容忍的尺度邊緣,而且不只一次大膽越過之。一八九七年,他寫了一部構思精采而手法機智的喜劇《輪舞》(Reigen)。《輪舞》由幾對情侶的十組情色對話所構成,對話者的其中一方會在下一組對話再次出現,到最後首尾相接,形成一循環。每一幕的高潮都是做愛──當然,這樣的劇情,是離經叛道有如史尼茨勒者都不敢奢望可以搬上舞台的。但這部劇本卻是連出版都有好些年不能出版,至於上演,則是更多年以後的事。然後,在一九○○年,史尼茨勒又創作了眩目程度不亞於《輪舞》的長篇小說《古
斯特少尉》(Lieutenant Gustl),用意識流手法揭示一個年輕氣盛的奧地利少尉輕率挑起一場決鬥後產生的死亡焦慮。
這部小說見證了史尼茨勒的廣泛閱讀:它所使用的那種前衛、繁複的敘事技巧,乃是從法國作家迪瓦爾丹(Edouard Dujardin)的《月桂樹被砍》學來的。對於自己的原創性,史尼茨勒一向相當保守,不認為自己足以與托爾斯泰(Tolstoy)或契訶夫這些不朽大師並駕齊驅。另一方面,他對一些所謂的仁慈批評家的意見也十分氣惱,他們認為史尼茨勒儘管多產,但基本上只是把他最早期劇作的材料──不負責任的獨身漢和通姦戀情──再生利用。史尼茨勒帶著點怒意抗議說,他要比這些批評家所認為的更有想像力、更有創意──一言蔽之是更現代。
他是對的;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有權去問,史尼茨勒的證言是否可以作為我們理解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的有用根據?這個問題預設了一個前提:中產階級是一個可以定義的單一實體。對這個爭論不休的議題,我將會用一整章的篇幅(第一章)去處理。歷史學家已經花了很多年時間與這個問題角力,但到頭來的解決辦法往往是視之為一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史尼茨勒顯然是認定有布爾喬亞這樣的生物存在的。我們將會看到,他對布爾喬亞殊少敬意,而且傾向於把「布爾喬亞」和「無聊乏味」劃上等號。反過來,許多維多利亞時代人一定也會視他的生活方式為偏執古怪,甚至是波希米亞式的。然而,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史尼茨勒都是不折不扣的布爾喬亞,儘管是一個具有高度個人特色的布爾喬亞。有很多事情可以反映出這一點。例如,他順從父命選擇了學醫和行醫;他渴盼自己的情婦都是處女。他也曾經像數以百萬其他布爾喬亞一樣,嘗試阻止自己所愛的女人進入職場。他鄙視一些時空錯亂的貴族式習尚(如決鬥)。他自信具有不拘一格的文化品味,卻無法欣賞荀白克那些無調性的交響曲,也對喬哀思的《尤利西斯》(Ulysses)感到懷疑。他耽於工作,重視隱私。這些都是史尼茨勒的布爾喬亞印記。不過,本書雖以史尼茨勒始,卻非以他而終。正如我說過的,假如本書可以稱為傳記的話,它乃是一個階級的傳記。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與其說是摘要,不如說是綜合。我對維多利亞時代的布爾喬亞發生興趣,是在一九七○年代初,當時,這個歷史課題在史學界相對受到忽略。當然,論十九世紀中產階級的有分量作品還是有的,只不過這個題目並沒有吸引到很多歷史學家注意,而且肯定不是他們最感興趣的項目之一。人們的興趣放在別的地方:婦女史、勞工史、黑人史以及那種自稱為──有一點點裝腔作勢──「新文化史」的研究。自十八世紀的哲學家把歷史的因果性加以世俗化以後(譯註:指不再把歷史事件的成因訴諸超自然的解釋),史學界就會週期性地出現這一類使人興奮的不滿時刻:它們認為既有的歷史研究領域是狹窄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
很多這些不滿都是有獲益的,會引出許多未被提問的問題和未受質疑的答案。但它們同時也製造了混亂,這一點,特別是在兜售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後現代販子入侵史學的領域以後更為嚴重;它們不但未能拓寬歷史學家的視野,反而對大部份歷史學家長久以來的求真精神投以相當不合理的懷疑。在這種一頭熱的氛圍裡,我自己的一套史學方法──一種受精神分析啟迪(只是啟迪,不是淹沒)的文化史──在我看來是適切追隨的方向,而十九世紀的中產階級──有鑑於它普遍受到冷落──則是一個大有可為的課題。我當時並不知道,我的工作最後竟然會有那麼大的修正作用;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純粹是走自己的路,證據把我帶到哪裡,我就走向哪裡。
其成果就是五大冊的著作,我總稱之為《布爾喬亞經驗:維多利亞到弗洛依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八年)。它們所專注的是一些非傳統的課題,如性與愛、侵略性、內心生活、中產階級品味等。儘管我的選題清晰反映出弗洛依德的影響,但我卻小心翼翼,務求不讓我的立論脫離過去的「真實」世界,因為那才是歷史學家的共同家園。換言之,有大量的史實包含在我的書頁裡。它們其中一些會在本書被再次引用;它們太有啟發性了,我捨不得割捨。《布爾喬亞經驗》的讀者也許還會記得以下這些令人難忘的片段:典型的維多利亞人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為了刺激太太的母奶分泌,輕柔而虔誠地為她按摩乳房;十九世紀的美國婦人蘿拉.萊曼(Laura Lyman)以火辣辣的書信挑逗人在遠方的丈夫:「下星期六我會抽乾你的保險箱的,我保證」;義大利統一運動的先驅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因為發現政府官員拆閱他的信件而大發雷霆;前衛詩人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曾經稱許布爾喬亞的藝術品味;德國鋼鐵鉅子克魯伯(Alfred Krupp)推辭了官方把他冊封為貴族的美意。
但這不表示本書只是一部《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性質的讀物,只是前述大部頭之作的濃縮,因為儘管它的厚度不如《布爾喬亞經驗》,結論的分量卻未必有所不如。我引進了相當多的新材料與新課題,其中之一是工作與宗教──儘管它們在《布爾喬亞經驗》裡被討論到,但在本書卻受到更恰如其分的深入檢視。《布爾喬亞經驗》中對維多利亞時代布爾喬亞所作的一些很根本的重新詮釋──他們對性、侵略性、品味、隱私的態度,都會以顯著的分量再次見於本書。即便如此,它們並不是裝到新瓶裡的舊酒。我曾經把它們重新思考了一遍,而且自認為把問題的複雜程度更往前推。
有一點是必須事先聲明的:對於Victorian(維多利亞時代的、維多利亞時代人)這個詞,我採取的是廣義的用法。長久以來,Victorian習慣上都是指英國人──甚至更狹義是指英格蘭人──和他們的品味、道德觀與禮儀。而它的意義從未完全侷限在維多利亞女王主政的時代,因為一般咸信,不管是在維多利亞女王一八三七年登基前還是一九○一年駕崩後,都存在著維多利亞時代人。簡言之,她的名字是被寬鬆地用作十九世紀的同義詞,也就是自拿破崙最終敗北(一八一五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一四年)之間的一百年。但是,還有些維多利亞時代人是活在這個範圍外的。近些年來,研究美國文化史的學者已經把此詞歸化,而我相信,把其涵義進一步擴大是說得通的。但這當然不是說,法國、德國或義大利的「維多利亞時代人」與同時代的英國夥伴一模一樣;因此,本書在致力求「同」之餘,也是「異」的禮讚。儘管如此,我還是深信,不管不同的布爾喬亞之間具有多大差異,他們彼此仍然有著強烈的家族相似性(譯註:family resemblance,哲學家維根斯坦的用語,指家人間那種難以具體界定的五官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正是我使用「維多利亞時代人」一詞時想要強調的。
好吧,現在讓布幕升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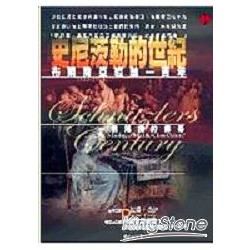
 共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