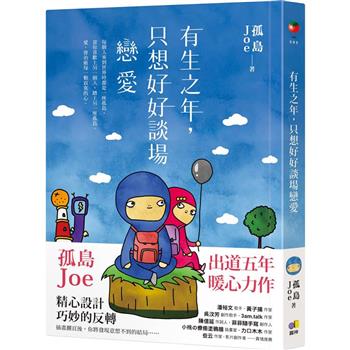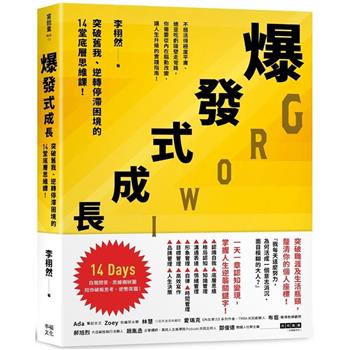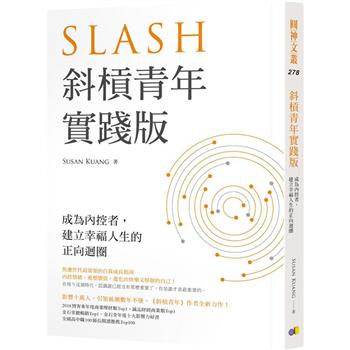得獎紀錄:
2004年龔固爾文學獎.2004法國尚紀沃諾評審獎.波蘭龔固爾文學獎讀高蝶的義大利百年家族傳奇,我彷彿走在我最愛的托斯坎尼小鎮Montepulciano裡的小巷,太陽那麼赤熱,陰影或悲傷也那麼真實,故事充滿想像力和力量,令人難以忘懷!-陳玉慧作者透過史柯塔家族幾代的生命歷程,呈現了二十世紀憂鬱義大利南部的人文風景,封閉、窒息,卻散發著史詩般的真實-徐明松一部史詩般的作品-龔固爾獎評委此書文筆優美,將我們帶入一次夢幻般的旅程,深入我所深愛的那個義大利-龔固爾獎評委羅蘭.高蝶至今最好的小說,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高蝶的寫作深受古希臘詩風影響,自有其一種文筆、一種敘述方式,對簡單的事物挖掘詩意,在平凡的題材裡找出普遍意義。他的語言簡約,敘事則完全像在寫偵探小說,各章一環扣一環,閱讀時只希望趕快知道下一章,恨不得一口氣讀完的小說-名譯家馬振騁。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