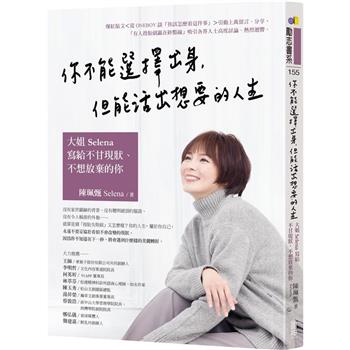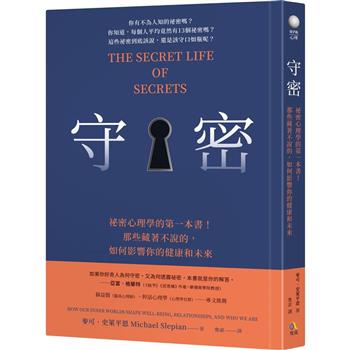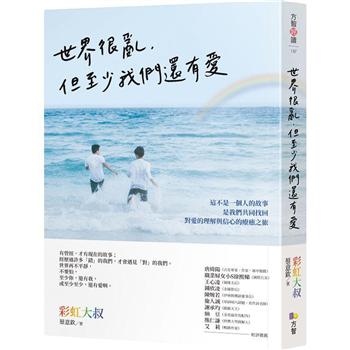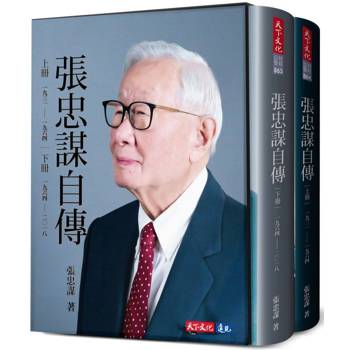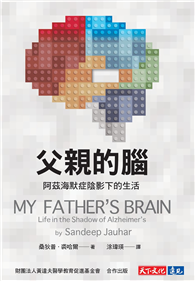不管是怎麼一回事,告別總是艱難的,
無論是要告別想告別的與該告別的。
畢竟那是一種哀悼的工作。
《告別的年代》,串起了三代人的共同回憶,一個家族的歷史,一個種族的集體記憶
大馬的錫埠,三個時空交錯下的杜麗安
媲美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馬康多小鎮、張愛玲孤島時期的上海怨女!
●第一個杜麗安,說: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那個年代。
愛念依舊,而你不是他,你只是另一個人在我心底徘徊不去,深深繾綣的替代品。
杜麗安望著葉望生的肉身,一場遊戲一場夢,思緒在無數個錯錯落落的葉蓮生與葉望生之間兜兜轉轉,像在十幾年的歲月裡往返來回。歲月匆忙,卻讓人感覺恍若前世,恍惚今塵,何以今天再遇見蓮生。而自己已嫁作他人婦,還要牽著懷了葉望生的孽種的繼女。一段等待已經有了幾十年,但人世間的滄海桑田,錫埠的繁盛興衰,國家政治與種族的糾纏不清。這段時間,已經足夠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塵埃落定,化作春泥,以供明日相思。
●●有另一個杜麗安,眾稱「麗姊」,住在五月花的301號房,與「你」相依為命,與一群年華老去的老娼義結金蘭。她出賣自己的肉身,儼然在黑夜暗巷中慈航普渡那些在欲海中浮沉的幽靈。母親死後,五月花風光不再,有一個女人悄悄潛入。204號房內,瑪納的體味;迴旋婉轉的樓梯,母親的體味殘存在空氣中。而你去見了J。
●●●有第三個杜麗安,筆名叫「韶子」,是《告別的年代》的作者,國中畢業生,一個業餘、早慧的小說家,但江湖中人尊稱她為「麗姊」。21歲那年發表了中篇小說《失去右腦的左撇子》,因在國外得獎而備受囑目。引起第四人稱的注意。而杜麗安/麗姊/韶子的英年早逝,留下了一本備受爭論的《告別的年代》。
因此,讀者、報社、評論家、出版社向文壇告急!!請協助尋找:
精裝本,鏽綠色外皮,燙金楷體字,書頁受潮發黃,
沒有扉頁、版權頁、書名頁、出版者、作者,
頁碼從513開始的《告別的年代》
故事從513開始,
你一直以為這是一種正在消失中的歷史語言,一種適合為祖父輩撰寫傳記的文字。
然而從513頁開始的書,讓你感到怪異。你忍不住翻開書的最後一頁……
而這本像磚頭一樣厚重的書,被擱在圖書館裡最低層,而且是最靠牆的,彷彿停放在時光的深處。那角落最惹塵,也最容易被遺留或忽略。
可是現在你覺得它一直沉默地伫候,
為的也許是有一天被你發現──
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花蹤文學獎得主,馬華旅英小說家黎紫書的文學創作轉捩點,萬眾矚目,最受期待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告別的年代》以一部既無開端亦無終結的歷史大書為引子,一個企圖在書中尋找「父親」的青年,展開全書故事的序幕,從此青年身不由己地捲入了時光隧道,在過去與現在間,展開了一場離奇的尋父之旅。
《告別的年代》在「小說中的小說」中,一層一層地開拓出故事的縱深度,展開了真實與虛構、現實與夢幻,個人與家族交織的多方向書寫,以不同質感的語言穿插於不同的時空,編寫出一闕南洋土地上的魔幻寫實之歌。
黎紫書寫活了一個舊時代,那因錫礦開採而繁榮起來的大馬華人市鎮「錫埠」,箇中風土人情,市街景觀,人的欲望流布,愛恨情仇,也再現了中馬華人與香港通俗文化影響的深刻關聯。
不同時空的故事與人物被「大書」串聯起來,充滿尋覓、躲藏與發現,蘊涵了21世紀華人作家與華文書寫的流離的哀愁與生根的意志。
黎紫書以同姓名但不同人物的三位女主角,作為本書情節鋪陳及其創意形式,小說的後設創作架構、文學隱喻與政治暗喻、老練的說故事技巧,可視為近年來華文長篇小說的一大佳作。
他們一致推薦
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
宇文正(知名作家,聯合報副刊主任)
張貴興(知名作家)
張錦忠(中山大學)
陳大為(知名作家,台北大學)
黃錦樹(知名作家,暨南國際大學)
楊照(知名作家)
董啟章(知名作家)
詹宏志(PChome Online董事長)
蔣韻(知名作家)
鄭樹森(美國加州大學榮休教授)
駱以軍(知名作家)
鍾怡雯(知名作家,元智大學)
書評推薦
這是紫書對自己的挑戰,也是對「長篇」和想像力的挑戰。那些落日般的歲月,挾帶著詭譎如基因密碼與血色般起死回生的新鮮,撲面而來。於是,我看到了文字後面作者那一雙不同尋常的、超越了年齡和時光的奇異的眼睛。──蔣韻(知名作家)
在文學條件異常貧瘠的馬華文壇,不管從什麼角度看,黎紫書都是個奇蹟。在馬華文壇,她之崛起是因為她以二十餘歲之齡、在短時間內連續獲得國內外(尤其是馬來西亞與台灣)的文學大獎(尤其是花蹤文學獎與聯合報文學獎)。……這種傳奇性是確實的,可能也是自有馬華文學以來最大的傳奇。顯然她在文學上具有非凡的天分,也許曾在創作上下了不少功夫。從她已發表的作品來看,她對當代中文小說(不論是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留台)的技術與風格是嫻熟的、對人性的曲折隱微,也有相當深入的洞察。──黃錦樹(知名作家,暨南國際大學)
《告別的年代》這樣的一部「大書」(不是就字數而言,而是就立意而言),而又用了虛實互涉(或曰後設小說)的手法,讓書中人物都在追求、閱讀和合寫一部同樣稱為《告別的年代》的「大書」,似乎就是把馬華文學的整個歷史,以《告別的年代》這部既屬虛構也屬實體的長篇小說建構起來,並加以承載。饒有意思的是,小說中多次提到,這部傳說中的《告別的年代》很可能被置放於圖書館一個偏僻的書架的「最低層」、「最靠牆」的位置。「那個角落最惹塵,也最容易被遺忘或忽略。」黎紫書所想像的馬華文學,不得不採取這樣的「邊緣」位置,以被忽略或遺忘但卻終有一日會被重新發現的姿態,以一部包羅萬有、虛實兼容的「大書」,去見證自身在時光中的存在和不滅。──董啟章(知名作家)
《告別的年代》是一本發問之書。它也嘗試提出答案,但答案總是多於一個,而且沒有終極對錯。重要的還是問題本身,也即是為甚麼要問這樣的問題,和為甚麼要這樣地問。
馬華女性書寫第一人──鄭樹森(美國加州大學榮休教授)
黎紫書筆下那個「宛然的昔時」,像老屋水池裡的太湖石、金魚、佈灰的袋蓮、波光閃閃的倒影曲徑迷宮。流年自壼嘴傾出,輕手輕腳,無煙火氣,背後的筆力卻讓我懍畏。我覺得這本小說,或可視作某種失傳小說技藝的活生生復現,華麗的戲台從不可能的虛空被洶湧創造出來。作為讀者,我覺得無比幸福;作為同代華文小說創作者,我覺得她是屈指可數,頂級的,恐怖的對手。──駱以軍(知名作家)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