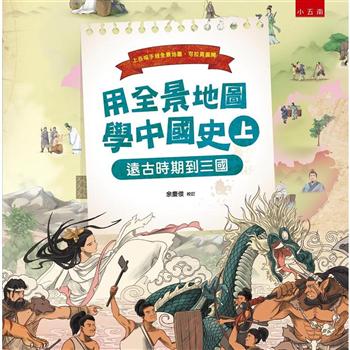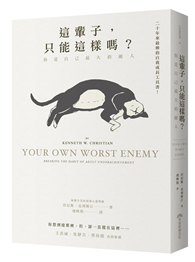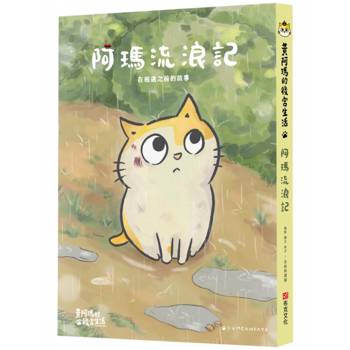《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過渡空間的死亡與重生 /周仁宇
……………
關於死亡母親對過渡空間的摧殘,以及過渡空間如何在重創之後重生,《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是我所知最好的描述。我純粹以一個讀者的身份,以感謝的心情,珍惜小說家所帶來的感動和理解。精神分析和嬰兒研究都沒能說得這麼明白動人。
從大學二年級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活著幾乎只想到死。在那之間雖然迎接了二十歲的生日,但那個刻度並沒有任何意義。那些日子,對他來說,覺得斷絕自己的生命是比任何事情都自然而合理的。......
他在那個時期以一個夢遊症者,或一個還沒發覺自己已經死掉的死者般活著。太陽升起就醒來,刷牙,穿上手邊的衣服,便搭車去大學,在課堂上記筆記。像被強風吹襲的人緊緊抱住路燈柱子那樣,他只是依眼前的時間表行動而已。如果沒事他和誰都不開口,回到一個人獨居的房間坐在地上,靠著牆壁,反覆想著死......
不去想到死時,則完全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想並不是多難的事。既不看報紙,也不聽音樂,連性慾也沒感覺到。世間所發生的事,對他都沒有任何意義......
......清潔也是他所緊抱著的柱子之一。洗衣服、洗澡、刷牙。對吃的事情幾乎毫不在乎......到了該睡覺的時間,就像吃藥般喝下一小玻璃杯威士忌......當時的他沒做過一次夢。就算做了,那些只要一浮現,就會從無處攀手的光溜溜意識斜坡往虛無的領域滑落下去。
多崎作會那樣強烈地被死所吸引的契機非常明顯。就是他長久以來親密交往的四個朋友,有一天斷然告訴他,我們都不想再看到你......
這是書的開頭,多崎作因為被抛棄而失去生命的動力。事情發生在多崎作大學二年級暑假,他像平常那樣,一放暑假回到名古屋立刻打電話到四個朋友家裡,但四個人都外出了。於是他分別留了話就一個人到街上散步看電影打發時間,彷彿沒和他們在一起就沒有意義似的。晚餐後以及第二天再打電話也都不在,還感到接電話的人想趕快掛斷,作覺得自己像是「惡質特殊病原菌的帶原者似的」,是不是自己「發生了某種不適當的、不受歡迎的事。」但「那到底是什麼樣的事呢?......怎麼想都想不到。」當然想不到!他繼續打電話,相信會有反應。結果藍仔打電話來沒有開場白就說「抱歉,請你別再打電話到我們每個人的家了。」作問:「嘿,到底發生了什麼?」藍仔說:「問你自己呀。」並且,作「從中些微可以聽出悲哀和憤怒的顫抖。但那也是一瞬之間的事。在作想起該說的話之前電話已經斷了。」
在一段靜止臉孔實驗的影片中,母親在研究者的安排下先和孩子玩了一陣子,然後在某一刻突然面無表情。嬰兒先是出現驚訝的神色,接著便開始重覆剛才玩時的一切,微笑,拍手,指向遠方,伸手討抱,擠眉弄眼彷彿試著找回失去的歡樂和溫暖。此時母親依然面無表情,嬰兒繼續邊比手劃腳邊哭閙尖叫。然後他似乎放棄了,開始看著並把玩自己的手,再看向別處,似乎不願再目睹悲劇也像是在另尋出路。但接下來他又再度試著向母親伸出雙手,但沒用,不管怎樣都沒用。終於,他轉過頭去崩潰大哭。就在此時,靜止臉孔結束,母親又變回原本那個活生生的人,安慰,說話,充滿情感的踫觸。影片裡,嬰兒在幾秒內就破涕為笑,毫不記恨的樣子。當然如果臉孔靜止得更久,結局很可能會不一樣。實驗的最初設計者發展心理學家特羅尼克說,情境可以好、壞、或醜惡。「好」指的是我們平常和孩子的互動,「壞」是不好但孩子可以承受,「醜惡」則是完全不給孩子任何機會修復。實驗裡看不到醜惡,因為這樣的實驗違反道德。
但我們沒有力量像操作實驗那樣控制人生,醜惡終究會發生,臉孔終究有可能靜止很長的時間,長到彷彿已經變成了雕像。這時,孩子會做什麼呢?就像多崎作掙扎著問:「到底怎麼了?你告訴我啊!到底怎麼了?」但藍仔沒有回答就掛了電話。葛林說孩子接下來會「退灌注」。在意識上,孩子會告訴自己:「如果你不愛我那我也不愛你了」。但這只是欺騙自己,只是意識上的報復,在孩子自己所知有限的無意識裡,灌注仍然維持著。換句話說,孩子心裡仍然偷偷愛著媽媽,那個變成雕像的媽媽。於是失去生命力的母親在孩子心裡變成一個像墓碑般的實體,盤據著原本能夠生成發展各種人生可能的過渡空間,拒絕任何東西進來。於是孩子無法真正有愛也無法真正享樂,一切的愛都被冰凍在死亡母親身上。葛林說得直接而恐怖:「愛在母親墳塋上」。
在死亡母親情結,以及對母親的空白哀悼背後,我們看到瘋狂的熱情,在其中,母親一直是這個瘋狂熱情的客體,使得對她的哀悼不可能發生......主體整個結構的目的在於一個基本的幻想:要去滋養那個死去的母親,要去維持她永恆不朽。
接下來,孩子會不知不覺地認同母親(讓自己的形象變成母親的形象)。當我們失去某人時,最徹底的抵抗就是變成那人,以為如此便再也不會失去她。所以佛洛伊德才說,「自我特質是被放棄的客體灌注的沈積,它承載了那些客體選擇的歷史」。
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是所有曾經被我們愛過之人的集合。這原本是一件相當自然的事,但如果認同的對象是死亡母親的話,就是另一回事了。
所有這些葛林所稱的第一波防衛:試圖修復、退灌注、認同,都是為了挽救或避免承認母親的愛已經不再存在的事實。但這些仍然不夠。當然不夠,而且永遠不會足夠,因為「記憶或許可以掩蓋,但歷史卻不能改變」。
各種顏色的焦慮
於是,孩子發動第二波防衛:恨意、性興奮以及秩序。前兩者就像兩根圖釘,釘住以秩序為基礎的理智架構的布,蓋住第一波防衛在心裡留下的冰冷核芯。或者更精確地說,那是一個白色的墓室。那不是沒有顏色的過渡空間,而是一個被白色焦慮充滿、佔據心靈並不斷汲取能量的實體。孩子最終會對此產生恨意。於是,白色焦慮便被層層黑色焦慮重重地蓋上。診療室裡,因為恨意極為明顯,因此許多受克萊恩啟發的治療師持續地詮釋恨意攻擊。
葛林對克萊恩學派的痛恨極為有名,鋪天蓋地的強烈批判宛如咒罵。他說這樣的追逐永遠到不了最根本的冰冷核芯,這只是強迫個案臣服,只會導向愚笨和無聊。我無意評判誰對誰錯,但在他的氣急敗壞裡,我可以感受到他急於想提醒我們:世界不純然由恨意組成。
關於治療者該做什麼,葛林是這樣說的:不要沈默,那只會惡化空白哀悼的移情並讓分析沈入死寂無聊;也不要直接侵入潛意識幻想或對攻擊做有系統的詮釋,那不會有用。他建議我們想辦法讓自己持續活著、對病人保持興趣、被病人喚醒、溝通其聯想、持續意識到病人在說什麼。葛林不斷強調兩件事:第一,支撐幻滅的能力取決於病人覺得分析師如何愛他;第二,不要過於暴力地詮釋病人的防衛。換句話說,不要像克萊恩,要像溫尼考特。當然,對自信滿滿的葛林來說,溫尼考特也不是沒有缺點,他說他忽略了性幻想的重要性。
我不知道村上春樹有沒有讀過葛林或溫尼考特,但《沒有色彩的多崎作》這本小說簡直就像是死亡母親情結以及過渡空間的案例報告似的。很可惜,雖然《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在一週內賣出了一百萬冊,且於兩年內譯成二十個語言,但死於 2012年 的葛林剛好錯過了隔年才出版的小說,死於1971年的溫尼考特當然更不用說。不過,他們三人說的故事幾乎完全一樣,唯一的差別在於《沒有色彩的多崎作》是一本國小學生也能從中獲得感動的書,並且很有可能是村上唯一能夠當成床邊故事的小說。即使父母們把性和暴力的內容全都跳過,他們還是能從孩子臉上的表情確認某種深遠的人類共感。但村上其他的書(像《挪威的森林》或《1Q84》)在跳過性、死亡與暴力的段落之後,故事就完全無法理解了。
在推薦本書時,我得事先警告讀者兩件事。第一,它未必適合當兒童讀物,我之所以說它是很好的床邊故事,是因為父母親知道該在何時跳過什麼,然後用可以理解承受的方式將書介紹給孩子。第二,當你念太有吸引力的小說給孩子聽時,你得有心理準備,他們不會容許你只把它當床邊小說,因為睡前絕對唸不完,所以隔天早餐要念,然後晚餐也要念,任何有可能的時候你都必須念。《沒有色彩的多崎作》便是這樣的一本書。
請大家容許我不依小說的鋪排,只簡要說明故事的開始與結局。多崎作和四個好友在高中時代形成一個調和存在的團體,只要五人在一起就覺得什麼都對。但高中時代過去,而對於自己的人生,作一直都想建造車站。不是火車,是車站,一個空間,一個可以扺達、出發或歇息的空間。於是畢業後不得不自己一人去東京讀書。但只要一放假,作便會盡快回到名古屋與其他人會合。除了作之外其他四人的名字裡都有顏色:赤松慶(紅仔)、青海悅夫(藍仔)、白根柚木(白妞)、黑埜恵里(黑妞)。
脆弱而美麗的白根柚木有一天突然像是被惡靈附身似地失去了生命力,並且不知為何告訴其他人自己被多崎作強暴了。雖然沒人相信,但黑埜恵里認為白妞那時已瀕臨崩潰,所以她只能把多崎作給切開。在故事的最後,黑妞對作說:
我覺得真是委屈作君你了,我很清楚自己對你做了很殘忍的舉動......不過,以我來說首先必須讓柚子恢復正常才行。在那個時間點,那是對我來說的最優先事項。那孩子正面臨可能失去生命的嚴重問題,需要我幫忙。只能讓你一個人想辦法在暗夜的海裡自己游上岸。而且我想如果是你的話應該可以辦到。你具有那樣的強度。
雖然黑妞沒有錯,多崎作的確有這樣的強度,但在故事的一開頭,作為讀者的我們未必有這個信心。並且,關於為何發生以及發生了什麼,所有人都不知道。讀者、多崎作、治療師、個案都處在未知當中。
當沙羅(作交往的女性,書中除了作之外唯一名字裡也沒有顏色的人)質問作難道不想知道發生那樣的事的原因嗎?作說: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家這樣斷然拒絕。而且那對象又是向來比誰都信任的,像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般熟悉又親近的四個好朋友。在提到尋找原因,或修正誤解之前,我首先就受到極大的打擊。到無法好好站起來的地步。覺得自己心中好像有什麼斷掉了似的。
沙羅說如果是她就會「一直追究原因到自己能接受為止」。多崎作說:
我沒那麼堅強......我想我一定很害怕看到那個。無論真相是什麼樣的東西,我都不覺得那會讓我得救。不知道為什麼,但我有類似這樣的確信。
於是多崎作回到東京,閉起眼睛,塞起耳朵。在無意識裡如葛林描述的那樣,用秩序的布蓋住那個他自己也不曉得的冰冷核芯,然後用性興奮和恨意把布牢牢釘住。
以一個夢遊症者,或一個還沒發覺自己已經死掉的死者般活著。太陽升起就醒來,刷牙,穿上手邊的衣服,便搭車去大學,在課堂上記筆記。像被強風吹襲的人緊緊抱住路燈柱子那樣,他只是依眼前的時間表行動而已。如果沒事他和誰都不開口,回到一個人獨居的房間坐在地上,靠著牆壁,反覆想著死。
直到一個被強烈嫉妒折騰的夢。在夢中,作
非常強烈地需要一個女人......她可以把肉體和心分離......如果是這其中的哪一個我可以給你,她對作說。肉體或心。但你不能兩樣都得到。所以現在我要你在這裡選一個。因為另一個要給別人,她說。但作要的卻是她的全部。不可以把哪一半交給別的男人,那是他實在無法忍受的事。如果這樣的話他兩邊都不要。他想說。卻無法說。他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
那時候作所感覺到的,是整個身體被誰的巨大雙手緊緊勒住般激烈疼痛。肌肉破裂、骨頭吶喊。而這時,所有的細胞都像快被曬乾了般激烈乾渴。全身因憤怒而顫抖。為了她的一半必須讓給誰的事而憤怒。那憤怒化為濃濃的液體,從身體的髓被滴滴榨出來。肺化為一對狂暴的風箱,心臟像油門被踩到底的引擎般提高轉速。並將亢奮的黑暗血液送到身體的末端。他在全身巨大的震動中驚醒。這就是所謂的嫉妒啊…...
當作醒悟到這就是嫉妒,醒悟到這是世上最絕望的牢獄時,他告別了與死的虛無面對面過了五個月的黑暗日子。這段描述裡,幾乎包含了葛林深邃的精神分析語彚裡的所有元素。與其猜村上是否讀過葛林,不如說這一切為所有直立人所共有。無常的人生裡,孩子可以突然被無法理解地丟下,然後用退灌注和認同來扺抗白色焦慮,用秩序、性興奮以及黑色恨意來掩蓋原本被稱為過渡空間但現在卻塞滿死亡氣息的墓室。
如果孩子夠幸運,有一位不過度沈默或武斷且能一直維持對孩子興趣的治療師的話,他或許可以透過原初場景的性幻想重新找回生命的活力。沙羅便有成為治療師的能力。
「被你擁抱著時,我可以感覺到你好像在某個別的地方似的。在稍微離開我們正在擁抱的地方。你非常溫柔,感覺非常美好,可是卻......」
「我真不明白。」他說。「我在那之間一直只想著妳。」......
「......雖然如此,你的腦子裡還是有別的什麼東西在裡面。至少有那種類似隔閡的感觸。那或許只有女性才會知道的東西。不管怎麼樣,我想讓你知道的是,對我來說這種關係沒辦法長久繼續。就算喜歡你也不行。我的個性是比看起來更貪心更率直的。如果我跟你往後還要繼續認真交往的話,我不想讓那什麼夾在中間。那不明底細的什麼。你明白我說的意思嗎?」......
「那是因為我心裡有問題?」
「對。你心裡藏有某種問題。那可能是比你自己所想的還要根深柢固的東西。不過只要你有那意願,我想問題一定可以解決。就像修理發現問題的車站一樣,只是為了這個就必須......」
「因此我有必要再去見那四個人一次,跟他們談談。妳想說的是這件事嗎?」她點點頭。「......從正面面對過去。不是去看自己想看的東西,而是去看不得不看的東西喔。如果不這樣的話,你會繼續抱著那沉重的包袱,度過往後的人生,所以告訴我四個朋友的名字。讓我先去快速調查看看,這些人現在正在什麼地方,做著什麼。」
就像地海巫師裡,當未來的大法師格得走投無路時,他的師父歐吉安對他說的話:「你要轉身......若是你繼續向前,繼續逃,不管你跑去哪裡,都會遇到危險和邪惡,因為那黑影駕馭著你,選擇你前進的路途。所以,必須換你來選擇。你必須主動去追尋那追尋你的東西。你必須主動搜索那搜索你的黑影。」
面對現實需要勇氣
接下來就是多崎作如何慢慢一步一步地去把事實找出來。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我們也常如此,這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從未知的黑暗裡找出答案。或者說找到全部的自己,包括那些因為難以承受以致曾經必須被遺忘的自己。表面上的故事是多崎作與他的朋友們的故事,但我覺得或許所有的人物:作、沙羅、黑妞、白妞、藍仔、紅仔、灰田、綠川,全都是我們的一部份。就像蘇利文說的:「我們擁有多少人際關係,就有多少個自我」,但在錯覺中,這些部分的自我以極和諧的狀態存在著,直到受到內在或外在的衝擊,使得某些部分必須要被壓制。
發現真實的世界並找回自我的過程並不容易,關於這點,比昂說得很好:
敢於覺察我們身處之宇宙的事實需要勇氣。那個宇宙未必令人愉快而我們可能想離開,如果無法離開,如果我們的肌肉沒在運作,或如果逃離或引退並不恰當,我們可以退縮進其他型式的逃避:去睡覺、意識不到我們不想意識到的宇宙或變得無知、理想化。「逃避」是一個基本的療癒......
葛林說孩子寧可供養死亡母親,永久讓他屍身防腐。就算我們有幸在分析過程裡成功理解冰冷核芯,注入生命,個案仍會把他所得的生命全部用來養育死者。每當個案似乎逐漸放下對死亡母親的執著,開始有自己的人生,總是突然又退回原點,彷彿死亡母親拒絕再死第二次。
頗受溫尼考特影響的博拉斯曾經發表過一個動人的案例。A在建築公司當技師2年,離職6個月後因為許多困惑而尋求分析。他每到新的工作環境,老闆都覺得他大有前途,但一陣子以後就會開始出問題。此時只要老闆給A一點刺激,他就會找回動力。但情況周而復始,直到老闆終於不得不接受他的請辭。同樣,在診療室內A常變得很沒活力,但分析師只要詢問,他就會暫時活過來。分析師發現並告訴A:「我覺得你每次都引我到很有意義的路上......然後再加以挫敗......你的回憶似乎是成癮的,像在為失落的電池充電」。A讓身邊的每個人都經歷他受過的創傷:母親突然失去活力,並且不論怎麼修復最後終歸徒勞。
某天,A走進診療室坐下,目不轉睛靜默地看著分析師五分鐘,直到分析師說「哎呀」A回說「哎呀」。然後分析師說「你想到了什麼?」心想A或許聽錯了。但A以平板空洞的回音說「你想到了什麼?」分析師說「抱歉」,A也說「抱歉」。分析師問了一個問題,A重覆。於是分析師只好說「你一直在重覆我的話」,A回說「你一直在重覆我的話」。到這裡分析師終於再也不知如何繼續,沈默到快結束前才盲目地說了一些話。博拉斯說這是死亡的溝通經驗:「他在我面前,但關係的靈魂滅絕,我完全無法理解。」
透過不知不覺中的認同,A在某種意義上真的成了死亡母親。分析師也不得不扮演起那個一直以來困惑挫折恐懼的A。藉此,A假裝她還活著。當然,這些事在診療室中發生之初,分析師根本不知道死亡母親之事,A也所知有限。必須要等到很久很久,在不斷的堅持與奮戰之後,他們才有機會一起在移情與回憶裡慢慢撿拾拼湊曾經發生的悲劇,以及那個悲劇如何在A的人生中不斷重演的故事。在那之前,我們總是在分析裡身處黑暗,不知自己是否正在前進,是否方向正確,就算知道,也永遠無法確定這是隧道或山洞,是否終有出口,終有走到世界另一頭的可能。當然,如果夠幸運的話,最後會看到前方洞口的光,然後向著它前進,直到走進一片新天地。如果夠幸運的話。
假若冰雪中你在南橫公路上由西向東前進,你會看到這條公路如何讓偉大的中央山脈天崩地裂地流了數十年的鮮血,你會看到森林的新舊傷口。如果不被落石擊中,你會在海拔2,772 公尺的高處揮別隔著拉庫音溪與你遙遙相望的南二段與玉山群峰,在塔關山和關山嶺山間的一個小小鞍部,走進刺穿中央山脈骨骼與水脈的大關山隧道。然後你會逐漸進入幾近純粹的黑暗之中,在冷冽的積水和寒風中前行。直到轉過一個大彎,看到前方微小但刺眼的亮光。此時你會知道2009年莫拉克颱風後的大規模岩層崩坍和土石掩埋已經暫時被怪手清走。但樂於知道隧道已被打通的你也會在光芒閃耀中,突然發現頭頂一條一條垂直而下的尖銳冰柱,任何一根掉落都有可能在這短短615 公尺的隧道裡奪走性命。走出洞口,你會看到從向陽山頂垂直落下一千公尺的崩壁直達新武呂溪的源頭,以及從那裡開始似乎無止無盡往太平洋而去的溪谷。大規模的苦難依然俯拾即是,從 1972 年以來就沒有斷過,但你知道自己至少已經走入陽光的眷顧裡。在分析的黑暗路程中,我們同樣永遠無法透徹地知道自己面臨的是什麼樣的危險。或許有人會以某種充滿道德的口吻說:這樣還進行分析不是太過違反倫理嗎?就像常有人指責人們明知危險還去登山一樣。但有誰能說自己活在世上完全知道自己的處境和危險呢?我們會因此宣稱明知世界充滿危險還硬要活著是件違反倫理的事嗎?我們太常為了怕死,而不敢真正的活著。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周仁宇等的圖書 |
 |
$ 200 ~ 315 | 心的顏色和森林的歌: 村上春樹與精神分析
作者:蔡榮裕/林建國/單瑜/楊明敏/劉佳昌/盧志彬/周仁宇 出版社: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1-01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8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心的顏色和森林的歌:村上春樹與精神分析
關鍵特色
★透過國內專業精神科醫師與外文系教授角度,破解村上春樹小說裡荒
誕人生剪影。
★結合醫學、文學觀點,用新穎方式帶您重新看見村上春樹故事裡的人生風景。
內容說明
愛情早已遠離的挪威森林,
世界末日裡被獸運走的心,
充滿騙人表象的1Q84,
以及做為容器卻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這一連串村上春樹的療傷述說,為沈重的生命指涉了什麼出路?
幾位精神科醫師與外文系教授,透過佛洛伊德、溫尼考特、葛林等精神分析名家的觀點,將村上春樹筆下的人物與情節拆解又重構,以種種想像,走進小說幽暗密林的深處。
「或許每本小說都得要有自己的結局,
就好像每個人的夢想只能由自己去完成那樣。
但就算每本小說都有了結局,
小說家仍然必須不斷地寫,
療傷不是一次就完成的事。
分析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分析師和個案還願意冒險的話,
他們就得要繼續不斷地在黑暗中前進。」
周仁宇<過渡空間的死亡與重生>
作者簡介:
作者 蔡榮裕
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資深心理治療督導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兼執行委員會委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推廣和運用委員會主委
作者 林建國
紐約羅徹斯特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榮譽會員
作者 單 瑜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士
精神科醫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作者 楊明敏
法國第七大學精神病理與精神分析博士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直屬精神分析師
台大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
作者 劉佳昌
倫敦大學學院(UCL)理論精神分析研究碩士
精神科主治醫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前理事長
作者 盧志彬
精神科醫師
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
作者 周仁宇
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
兒童精神科醫師
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師
TOP
章節試閱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過渡空間的死亡與重生 /周仁宇
……………
關於死亡母親對過渡空間的摧殘,以及過渡空間如何在重創之後重生,《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是我所知最好的描述。我純粹以一個讀者的身份,以感謝的心情,珍惜小說家所帶來的感動和理解。精神分析和嬰兒研究都沒能說得這麼明白動人。
從大學二年級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活著幾乎只想到死。在那之間雖然迎接了二十歲的生日,但那個刻度並沒有任何意義。那些日子,對他來說,覺得斷絕自己的生命是比任何事情都自然而合理的。......
他在那個時...
……………
關於死亡母親對過渡空間的摧殘,以及過渡空間如何在重創之後重生,《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是我所知最好的描述。我純粹以一個讀者的身份,以感謝的心情,珍惜小說家所帶來的感動和理解。精神分析和嬰兒研究都沒能說得這麼明白動人。
從大學二年級的七月,到第二年的一月,多崎作活著幾乎只想到死。在那之間雖然迎接了二十歲的生日,但那個刻度並沒有任何意義。那些日子,對他來說,覺得斷絕自己的生命是比任何事情都自然而合理的。......
他在那個時...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精神分析和小說相互美麗對方看不見的地方 /蔡榮裕
這是2015年11月7日,在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址所舉辦的精神分析運用的活動,讓文學和精神分析之間嘗試產生交流的起點,這是一條長路,這場活動只是起點。
這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一是偉大文學家卡謬的生日,他的《異鄉人》和《城堡》,是我在大學時代喜愛的作者,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代下的禁制,這些小說好像能窺見一些希望和了解,甚至暫時接受現況的小說。坦白說,這是很奇怪的感覺,現實體制下的禁忌,反而是培養想要看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的心情。
這...
這是2015年11月7日,在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址所舉辦的精神分析運用的活動,讓文學和精神分析之間嘗試產生交流的起點,這是一條長路,這場活動只是起點。
這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一是偉大文學家卡謬的生日,他的《異鄉人》和《城堡》,是我在大學時代喜愛的作者,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代下的禁制,這些小說好像能窺見一些希望和了解,甚至暫時接受現況的小說。坦白說,這是很奇怪的感覺,現實體制下的禁忌,反而是培養想要看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的心情。
這...
»看全部
TOP
目錄
【 起步 】精神分析和小說相互美麗對方看不見的地方/ 蔡榮裕
第⼀人稱愛與死/ 林建國
《挪威的森林》當我們討論愛情,我們討論的是什麼?/單瑜
「 村上春樹、佛洛伊德與音樂」然而你戀愛了!被佔據到八月/楊明敏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心」和「我」的奇幻旅程/劉佳昌
《1Q84》 通往兩個月亮的潛意識世界/盧志彬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過渡空間的死亡與重生/ 周仁宇
第⼀人稱愛與死/ 林建國
《挪威的森林》當我們討論愛情,我們討論的是什麼?/單瑜
「 村上春樹、佛洛伊德與音樂」然而你戀愛了!被佔據到八月/楊明敏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心」和「我」的奇幻旅程/劉佳昌
《1Q84》 通往兩個月亮的潛意識世界/盧志彬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 過渡空間的死亡與重生/ 周仁宇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蔡榮裕、林建國、單瑜、楊明敏、劉佳昌、盧志彬、周仁宇等
- 出版社: 無境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11-01 ISBN/ISSN:978986929723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25開(14.5*21) cm
- 類別: 中文書> 心理勵志> 心理學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