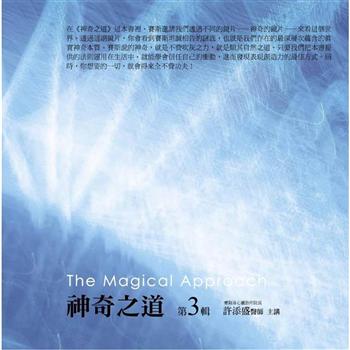提姆.波頓的古怪陰鬱+格林童話的天真殘酷
視覺映像滿溢的傷痕之書
當你殺我時,拿走了我的一切。
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小孩。
你一定連我的寬恕也要嗎?
等我跑回村子,所有東西都不見了。十幾個工人將所有回憶都裝上卡車,正準備開走。「喂!喂!」我追在他們後面大叫:「你們要把那些東西帶去哪裡?」但他們不停。所有房子前面,散著一堆堆的誓言和承諾,全都破成了碎片。我怎麼看得見那些東西的,我無法告訴你。
我抓住他們的肩膀,懇求他們。他們打了個寒顫,用手比畫十字,嘴裡喃喃念起咒語。這些人是農民,很迷信的。但除此之外,他們沒有任何反應。這時我才了解到,我死了,我已經死了。但為什麼我沒有到來世去呢?
傳來一聲劃破夜空的刺耳聲響。
我抬頭。看見渾圓的滿月正從天空往下掉。
在美長銷15年,首次出版便引起各方注目
2012年改編歌劇躍上紐約舞台
諾貝爾文學獎柯慈盛讚為「獨創性超乎尋常之作」
靈感源自於猶太人種族大屠殺的這部作品,作者喬瑟夫.史奇貝以出乎意料的敘事角度,結合了幻想與現實,大膽、獨特、睿智,創造出絕無僅有的奇異氛圍,在生與死的夾縫中,窺見世界背面的蒼白風景。彷如死靈鬼聲朗誦的床邊故事,輕舐死者消逝後、生者心中留下的沉默空缺。
「在猶太人的思維裡,我們被教導將發生在自身上的所有一切視為祝福,無論是好事或壞事。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無論如何,我希望這本小說是一本祝福之書。」透過這本作品,我們看到一位想像力、機智和天賦過人的作家的誕生。喬瑟夫.史奇貝以洞察力和人性光輝,喚起對二十世紀那個最黑暗年代的記憶。
得獎記錄
★美國藝術文學院 羅森塔爾基金獎
★德克薩斯文學協會 特納首作獎
★每月一書俱樂部首選好書
★《出版人周刊》、法國《世界報》、亞馬遜網站 年度最佳書籍
作者簡介
喬瑟夫.史奇貝Joseph Skibell
出生於美國德州拉巴克,已出版三本小說作品《月亮上的祝福》、《The English Disease》與《A Curable Romantic》,揉合歷史與奇幻元素的寫作風格,是文壇上獨特而迷離的說故事嗓音。
於各文學期刊發表過多篇短篇故事,創作的劇本也曾在美國各地的劇院上演。《月亮上的祝福》其中一個篇章曾發表在《故事雜誌》(Story Magazine)上,並獲得短篇小說的首獎。史奇貝曾獲米契納(James A. Michener)獎學金,於德州大學作家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Center for Writers)獲得藝術碩士學位;現於威斯康辛大學執教,並入選該校1996至1997年的小說類名人堂。
譯者簡介
殷麗君
輔大法文系畢業,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英、法文專職譯者,譯有《味覺樂園》、《藝術創意365天》、《巴黎人的巴黎》、《超奢華愛情》、《少年邁爾斯的海》、《五歲時,我殺了自己》等書。Email:yinli@mail2000.com.t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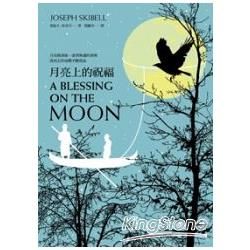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