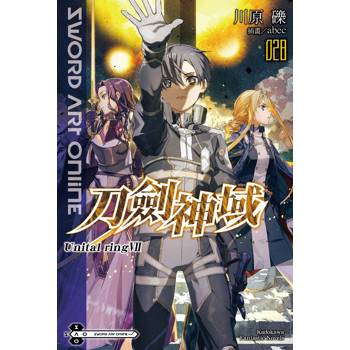洪席耶在當代哲學界享譽盛名,其論述在國內學術界也被廣泛引用,2009年11月,他曾應邀前來臺灣,在中山大學、臺北藝術大學、交通大學及中研院等學術機構,針對其美學與政治學思想從事理論的展演與發展發表演說,專題講座除「何謂美學?」、「政治、民主與現前」、「虛構之政治」外,還有「當代藝術與影像政治」。
《影像的宿命》一書則提綱挈領地論述了攝影、電影與當代藝術影像的美學-政治,為21世紀具開發性的重要論述,內容包含:〈影像的宿命〉討論影像再現的問題;〈構句、影像、故事〉討論書寫與影像之間功能連結的關係;〈文本中的繪畫〉專注文字與繪畫影像在藝術概念之認同上的關係;〈設計的表面〉則討論設計的影像中,圖像與文字的共構關係;〈如果存在著不可再現〉則關注集中營屠殺的再現問題,討論現代與後現代之後對於「不可再現」的指稱。
作者簡介:
賈克.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1940-)
法國哲學家、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榮譽教授,前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主任。
1965年與阿圖塞合著《讀資本論》(Lire le Capital), 1980年代以研究「哲學教育」、「歷史性」及「詩學提問」著稱,1990年代則專注於美學-政治的研究,提出「歧論」(Mésentente)。之後陸續發表《影像的宿命》(Le Destin des images,2003年)、《美學中的不適》(Malaise dans l'esthétique,2004年)、《民主之恨》(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2005年)、《獲解放的觀眾》(Le Spectateur émancipé,2008)等。論述主要涉及文學、電影與政治等哲學思考,被譽為當代美學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譯者簡介:
黃建宏
巴黎第八大學哲學所美學組博士,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助理教授。獲臺北第一屆數位藝術評論獎首獎。從事影像相關研究,同時書寫關於電影、當代藝術、表演藝術與文化的評論,並持續翻譯法國當代理論,如德勒茲、布希亞與洪席耶等人的著作。
著有《一種獨立論述》;譯有《電影I:運動-影像》、《電影II:時間-影像》;合譯有《波灣戰爭不曾發生》、《獨特物件:建築與哲學的對話》、《侯孝賢》。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馬拉梅曾說「現代不屑想像」。於是,詩人、畫家、劇作家或工程師紛紛致力於形式與行動的結合,來取代現實與影像這老舊的二分法,生命也因此發生革命。
我們所處的當代不再相信革命,而是回到過去重新歌頌影像的祭儀:畫布上的崇高閃光、攝影或圖徵的刺點。影像變成它者的感性現身:文字變成肉身,或不可再現之神的標記。
洪席耶利用影像的複雜組成且異質的本性,來對立於上述兩種視野。這些影像既不是拷貝也不是直接現身,而是獨特的操作,對於可見、可述與可思的重新分配。就像書中所探究的高達的「影像-構句」,是一個默片鏡頭、一張屠殺猶太人的影像,以及一段哲學家論述的疊加。這本著作分析了一些不為人知的連結,它們貫穿詩的象徵主義與工業設計、十九世紀小說與集中營的見證,或當代藝術的裝置。
透過這樣的方式也將影像從神學的陰影中解放出來,讓它們得以進行詩意的創作、貫徹其政治作為。
* * * * * * *
在洪席耶的脈絡下,藝術與政治有深刻的雙面性關連:一則,藝術可能因為遵循當代規範性美學制域而強化了同時代的政治共識;再則,藝術可能受到時代政治衝動之牽引而挑戰既有美學制域,透過各種操作重新分配其細節布署,而打開一些空間,讓不可見者得以出現。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都說明了洪席耶所強調的藝術與政治之共屬時代性感受結構,以及其重組此布署邏輯之可能。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劉紀蕙
《影像的宿命》這本書跨越於三大駭人的宇宙圖書館中:高達的影像宇宙、德勒茲的電影宇宙,以及洪席耶靈活穿梭二者並一再交融當代藝術的「影像-構句」宇宙。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副教授 楊凱麟
洪席耶自身哲學的構成涵蓋了多重的哲學特質:浪漫主義的詩性辯證法、尼采的詩性表現法、早年阿圖塞的政治學、傅柯的考古學、德勒茲的逃逸路線;其著作就如同不斷挪移的游擊/牧,穿越過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教育學、社會學、文學、精神分析、電影、攝影與當代藝術,而集中在「美學-政治」的複合課題上。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建宏
名人推薦:馬拉梅曾說「現代不屑想像」。於是,詩人、畫家、劇作家或工程師紛紛致力於形式與行動的結合,來取代現實與影像這老舊的二分法,生命也因此發生革命。
我們所處的當代不再相信革命,而是回到過去重新歌頌影像的祭儀:畫布上的崇高閃光、攝影或圖徵的刺點。影像變成它者的感性現身:文字變成肉身,或不可再現之神的標記。
洪席耶利用影像的複雜組成且異質的本性,來對立於上述兩種視野。這些影像既不是拷貝也不是直接現身,而是獨特的操作,對於可見、可述與可思的重新分配。就像書中所探究的高達的「影像-構句」,是一個默片鏡...
目錄
推薦序
制域與空隙:洪席耶論藝術與政治之雙面性|劉紀蕙
思考跨域,跨域思考|楊凱麟
導論
影像如何被辨識為二十一世紀的徵候?|黃建宏 24
壹、影像的宿命
影像的異類性
影像、相似、典型-相似
從一個影像性制域到另一個
影像終結是我們的過往
裸現影像、明現影像、蛻現影像
貳、字句、影像、故事
沒有共同指標?
影像構句與大並置群
管家、猶太小孩與教授
辯證性蒙太奇與象徵性蒙太奇
參、文本中的繪畫
肆、設計的表面
伍、假使存在不可再現
再現所意味的
反再現所意味的
非人性的再現
不可再現的思辨性曲張
人名索引
推薦序
制域與空隙:洪席耶論藝術與政治之雙面性|劉紀蕙
思考跨域,跨域思考|楊凱麟
導論
影像如何被辨識為二十一世紀的徵候?|黃建宏 24
壹、影像的宿命
影像的異類性
影像、相似、典型-相似
從一個影像性制域到另一個
影像終結是我們的過往
裸現影像、明現影像、蛻現影像
貳、字句、影像、故事
沒有共同指標?
影像構句與大並置群
管家、猶太小孩與教授
辯證性蒙太奇與象徵性蒙太奇
參、文本中的繪畫
肆、設計的表面
伍、假使存在不可再現
再現所意味的
反再現所意味的
非人性的再現
不可再現的思...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