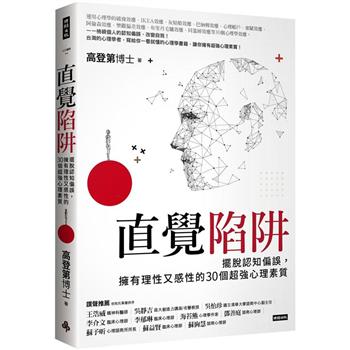改編電影將由《王冠》女星克萊兒‧芙伊主演、《新世紀福爾摩斯》班尼迪克‧康柏拜區製片
一再逃離過往、又忍不住轉身奔向回憶,
血液裡流淌著候鳥般的飄泊難安、心中對於愛與自由的渴望無可妥協,
唯有到過世界盡頭,才能知道自己該何去何從……
★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好書小說類冠軍(不分類亞軍)
★入選《時代雜誌》2020年百大必讀書單
★《出版者週刊》2020年度十大好書
★《圖書館期刊》2020年最佳文學小說
★《洛杉磯時報》年度好書
★美國獨立書店聯盟IndieNext選書
山女孩─Kit│作家─許菁芳│演員、作家─連俞涵│小說家─陳又津│演員、作家─鄧九雲│演員、導演─簡嫚書
──好評推薦
▍故事簡介
北極燕鷗是世界上遷徙時間最長的候鳥,會在一年內從北極一直飛到南極,然後再度北返,如此一生的累積飛行路程可長達地球到月球間來回距離的三倍。人類尚未完全了解這種鳥類獨特的季節性遷移原理,牠們就已瀕臨滅絕,只剩下稀少的一群孤單地堅持著每年的遷徙。
專門研究北極燕鷗的鳥類學家法蘭妮,身上彷彿也流著候鳥躁動不安的血液,每在一個地方定下來,就忍不住開始準備下一次的流浪;而這份飄盪的欲望也讓她如同瀕危的鳥兒般愈來愈孤獨,儘管她渴望愛與歸屬感,但似乎總是無法留在所愛的人身邊──
童年,與她相依為命的母親警告她絕不能離開石牆包圍的家鄉小鎮,自己卻先不告而別地失蹤。
少女時期,收養她的祖母內心慈愛,嚴厲頑固的表現卻迫使她放棄第二個家、遠走高飛。
成年之後,帶領她走上生態研究之路的摯愛丈夫尼爾給予她無盡的溫柔與耐心,試圖留住總是想要無預警遠行的她,願意為她等待守候,只要她能承諾最後會回家。
但如今的法蘭妮仍舊孑然一身,處處掩匿自己的行蹤,為了觀測地球上最後一群北極燕鷗的遷徙而來到格陵蘭。她計劃跟隨這群燕鷗前往南極洲,卻沒有正規的探勘隊伍和船隻,只能說服漁船「薩加尼號」的船員私下載她同行。原本船員對她排斥而懷疑,在並肩度過一次次航海危機、藉由她與燕鷗的帶領而發現魚群之後,才終於接納她作為船上的一份子。
然而,隨著「薩加尼號」的航線更加遠離文明世界,法蘭妮的祕密即將在孤絕的冰海上揭露──究竟是什麼樣的過往,讓親愛之人一一從她身邊消失,留下她隨著候鳥飛行的軌跡,不斷逃離人群、逃向世界的盡頭?而追著燕鷗抵達荒無人煙的極地終點之後,她的生命又將何去何從?
▍各界佳評
「女主角的逃離其實是追尋,同樣的,她的追尋也是逃離。
交錯懸疑的時間線,織出了一個淒美詩意的故事。我們能窺見她在面對易碎與衰敗的世界,卻以有別於對自我宿命的過度悲觀,用與之強烈對比的勇敢與堅毅,奔向瀕危的北極燕鷗,那都是因為來自於心底深處,對愛崇高的信任。
在這日漸崩塌的世界,這部小說於陰暗洶湧的灰色海面上,為我們從厚厚的雲層中灑下幾縷希望的聖光。它教導我們要以愛學會愛,要鼓起勇氣,航行到比過去更遠的地方。」──山女孩Kit
「一個全然獨特又優美的故事,以一名令人目不轉睛又著迷神往的女主角為核心。能將這部傑出的小說搬上銀幕,我無比榮幸且興奮。」──克萊兒‧芙伊
「《候鳥的女兒》優美且揪心,是一部獨樹一格的小說,出自一位才華洋溢的作家手筆。」──艾蜜莉‧孟德爾(《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作者)
「令人驚奇且屏息,書頁中蘊藏著希望,撫慰著我們所處的不安年代。麥康納吉的文字力量深刻入骨。」──拉娜‧普瑞斯考(《齊瓦哥醫生的祕密信差》作者)
「這本小說魔力迷人,卻不是安全無害的童話故事。夏洛特‧麥康納吉駕馭了能讓我們的靈魂熱烈燃燒的狂野魔法,《候鳥的女兒》是一本我全心推薦的作品。」──潔若汀‧布魯克絲(《禁忌祈禱書》作者)
「這部小說的美麗與傷感之處,在於其中毫無荒謬虛假,讀來真實、感人、哀傷又切身……這是一個關於哀悼的故事,一段關於痛苦的私密敘事,也憑弔著氣候變遷之下無可計數的生態傷逝。」──《華盛頓郵報》
「一部藝高膽大的小說,故事中的旅程即使劃下句點,仍會在讀者心中縈繞不去。」──《紐約時報》
「一部令人心痛的淒美作品,也貼近目前的世界時局。書中對於悲傷的描繪充滿衝擊力,特別是對於生活在這個災變連連的世界上,廣泛而幽微的悲傷。」──《衛報》
「麥康納吉逐漸拼湊出神祕主角的真實樣貌,為這個瀕臨崩潰、被和她一樣破碎的世界所掏空的女子畫下了肖像。《候鳥的女兒》為我們開了一扇窗,展示了離現在並不遙遠的陰暗未來。麥康納吉既讓我們理解大自然能夠如何治癒人心,也強調了保護自然環境的迫切性。」──《時代雜誌》
「《候鳥的女兒》講述一名女子遠赴世界盡頭,她追尋自我的同時,也在追隨一群可能是全球碩果僅存的北極燕鷗,一種每年都在南北兩極之間遷徙的候鳥。這個故事關乎愛、冒險、氣候變遷,也探討了一個逃離自己過往、卻又忍不住奔向回憶的人,將會何去何從。法蘭妮跑遍了整個世界,你會一頁接一頁逐漸了解她為何不曾停下腳步。這部小說的步調安排絕佳,坦率、真實、清晰的筆調,讀來幾乎像真實人生的回憶錄。」──亞馬遜網路書店編輯推薦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夏洛特.麥康納吉的圖書 |
 |
$ 270 ~ 360 | 候鳥的女兒【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夏洛特.麥康納伊 出版社:臉譜文化 出版日期:2022-05-14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1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候鳥的女兒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夏洛特‧麥康納吉Charlotte McConaghy
從小熱愛閱讀與幻想,自十七歲起就在澳洲陸續出版了八部科幻、奇幻及青少年小說。為了加強磨練敘事技藝,她進入澳洲影視廣播學院(Australian Film Television and Radio School)修讀編劇碩士學位,其間所學習的故事架構、角色塑造、主題發展等寫作技巧,不但讓她以改編自己早期奇幻小說《怒火》(Fury,暫譯)的劇本贏得澳洲編劇工會獎,更幫助她寫下她的第一部主流文學小說作品《候鳥的女兒》;書中融入她對氣候變遷與物種滅絕的深刻關切,卻全無恐嚇與說教成分,反而藉由人物心理描寫將女主角的生命故事和自然的殘酷與絕美互相交織,營造出動人的感染力。本書成功為她贏得英、美書市的肯定,除了登上各大暢銷排行榜,也獲《時代雜誌》、《出版者週刊》、《圖書館期刊》、《洛杉磯時報》等重要書評媒體選為年度好書。
如同書中主角法蘭妮一般,麥康納吉也曾度過頻繁搬遷的年少時期,目前則定居於雪梨,與伴侶育有一子。
作者個人網站:https://www.charlottemcconaghy.com/
譯者簡介
李雅玲
自由譯者,臺大中文系畢,曾任出版社主編,譯有《改變世界的100瓶葡萄酒》、《紳士的風格》、《人體標本師》、《殺人現場直播》。賜教信箱:artemisylee@gmail.com
夏洛特‧麥康納吉Charlotte McConaghy
從小熱愛閱讀與幻想,自十七歲起就在澳洲陸續出版了八部科幻、奇幻及青少年小說。為了加強磨練敘事技藝,她進入澳洲影視廣播學院(Australian Film Television and Radio School)修讀編劇碩士學位,其間所學習的故事架構、角色塑造、主題發展等寫作技巧,不但讓她以改編自己早期奇幻小說《怒火》(Fury,暫譯)的劇本贏得澳洲編劇工會獎,更幫助她寫下她的第一部主流文學小說作品《候鳥的女兒》;書中融入她對氣候變遷與物種滅絕的深刻關切,卻全無恐嚇與說教成分,反而藉由人物心理描寫將女主角的生命故事和自然的殘酷與絕美互相交織,營造出動人的感染力。本書成功為她贏得英、美書市的肯定,除了登上各大暢銷排行榜,也獲《時代雜誌》、《出版者週刊》、《圖書館期刊》、《洛杉磯時報》等重要書評媒體選為年度好書。
如同書中主角法蘭妮一般,麥康納吉也曾度過頻繁搬遷的年少時期,目前則定居於雪梨,與伴侶育有一子。
作者個人網站:https://www.charlottemcconaghy.com/
譯者簡介
李雅玲
自由譯者,臺大中文系畢,曾任出版社主編,譯有《改變世界的100瓶葡萄酒》、《紳士的風格》、《人體標本師》、《殺人現場直播》。賜教信箱:artemisyle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