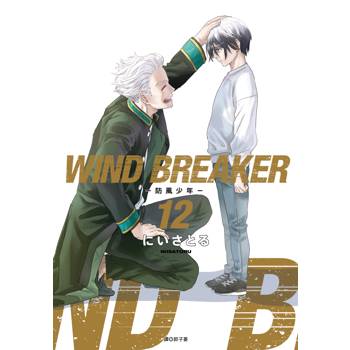處處埋雷的冒險太要命,沒驚喜的日子太無趣。
江郎才盡、奧母不應,文枯思竭的大作家
只好重返最迷人也最危險的──夢.書.之.城……
★ 驚動全球15國、轟動2百萬書迷的《夢書之城》續集大作!
★ 強勢攻占德國排行榜冠軍!
★ 近50幅珍貴插畫,過癮到大聲尖笑的閱讀冒險!
請注意:
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危險著作!
距離上次書鄉市的探險,轉眼又過兩百年。期間,傳說雕龍戲爾得袞斯特一直宅在詩龍堡,儘管功成名就,奧母卻已離他越來越遠。
一天,江郎才盡的雕龍接到長達十頁的神秘信函,開頭寫著:「故事就是從這裡開始。」但接下來的內容乏善可陳,看得他百無聊賴。接著,雕龍猛然察覺,整個故事遣詞用字和自己如出一轍。而信件最後的「影皇還活著!」更讓他差點噎死。他親眼目睹影皇被火吞噬,怎麼可能還活著?兩百年前的記憶瞬間甦醒,雕龍決定重返夢書之城,查明原因。
回到書鄉市的他,映入眼簾的是全新的城市,卻讓雕龍心生鄉愁,亟欲找回兩百年前的舊模樣。幸好,他遇見了久違的老友,帶領他見識目眩神迷的偶戲,並安排他觀看一齣神秘兮兮的隱形劇,未料竟把他帶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夢書迷宮!
然後,故事從這裡再度展開……
◆關於「傳說雕龍」戲爾得袞斯特
查莫寧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由瓦爾特.莫爾斯譯成德文,並繪製插畫。當他888歲的詩藝教父丹斯洛過世時,他只是個77歲的文藝青年,因為一份珍貴手稿,踏上書鄉市,被這座城市深深吸引,卻也陷入無邊無際的地底世界,展開一段生死冒險。後來他將這段冒險寫成書,成為家喻戶曉、出門需要偽裝的大作家。
作者簡介
瓦爾特.莫爾斯(Walter Moers)
德國著名的插畫家和電影劇作家。曾榮獲「德國格林文學獎」,為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他瘋狂的想像力令人大為讚嘆,被媒體喻為「文學界的麥可.傑克遜」。
2004年在德國出版的《夢書之城》,構想源自他流連舊書店的心得,超水準的幽默想像與精采設定,讓愛書人如獲至寶,一路暢快閱讀。本書長踞暢銷榜達42週,並在全球締造驚人的銷售成績,書迷紛紛期盼夢書的相關著作。2011年秋天,《夢書迷宮》即將上市的消息公布後,造成轟動的預購熱潮,一舉衝上德國暢銷榜冠軍,愛書人紛紛以「你看夢書了沒?」為問候語,更勝前一波的夢書熱。
書中所創的「查莫寧世界」,在全球已擁有2,000,000書迷。故事充滿創造力、流暢易讀且高潮不斷;他親製精采插畫,書中角色構想創意十足,專有的夢書詞彙在讀者間廣為流傳,甚至給予至少值得10顆星的評價。
譯者簡介
蔡慈皙
從事翻譯與德語教學。譯有《擁有九頂假髮的女孩》(圓神)《像心理學家一樣思考》等書。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