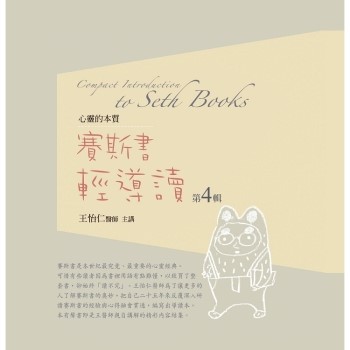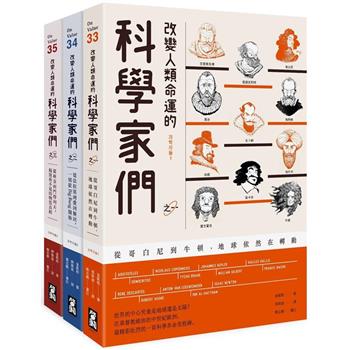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大豐FYNN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5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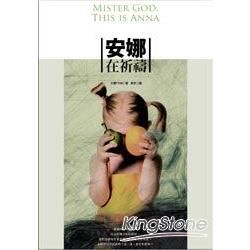 |
$ 45 ~ 225 | 安娜在祈禱【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大豐(FYNN) / 譯者:薛芙/譯 出版社: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05-0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248頁  5 則評論 5 則評論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安娜在祈禱
這是一個找到愛與生命的真實故事
讀者票選"世紀最鼓舞人心"的書,排名超越《小王子》!
與《星期二的最後十四堂課》並列最具影響力選書!
全球總銷售超過2,000,000冊
朱衛茵、李家同、林書煒、紅膠囊聯合推薦
「要分辨一個人和一位天使是很容易的。天使是無形的,而人是有形的。」
這是六歲的安娜對大豐說的話。
他們相遇在一個寒冷的夜晚,他以為自己撿回一隻流浪貓般的可憐蟲。
但安娜卻像火山爆發驚人的能量,像小詩人、園丁,像無形的天使,
兩人跨越年齡的差距,從哲學、科學、從影子、鏡子、數字、黑暗、光亮,
一起辯論一起對話,一起發現生命的答案。
安娜純真地問,生命最大的奇蹟是什麼?信任是什麼?永恆呢……
安娜認真地說,人可以孤獨,但不能悲觀。
聽見安娜專心與上帝先生的祈禱,我們也會像大豐一樣,
慢慢打開自己長期封閉的心靈之鎖,
在絕望的時刻,觸碰創造者的活潑光芒,而欣喜若狂……
作者簡介:
大豐(FYNN)
《安娜在祈禱》是他唯一的一本著作。
倫敦東區孕育出來的他,人高馬大,孔武有力,
但也有一種強烈的女性細膩與體貼。
他創造了「安娜」,也將「真理是什麼?」的答案給了我們。
他的文筆散發亮眼的特質,深具洞察人性的能力,
不受學院派或專業意識形態的干擾,在悲天憫人的胸懷中,
發揮其驚人的原創價值。
◎【特刊】 美好的奇蹟,早就為你預備好了,只是你尚未發現而已……
商品資料
- 作者: 大豐FYNN 譯者: 薛芙
- 出版社: 大田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5-05-01 ISBN/ISSN:9574558312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英美文學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
|

 2006/09/12
2006/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