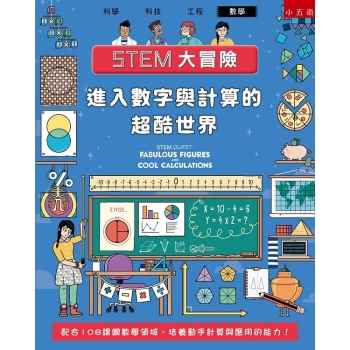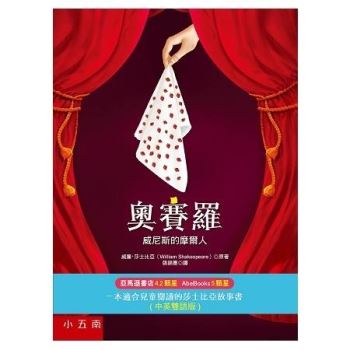前言
女人的故事李子玉
近年來我忽然愛上了寫作這回事,正好賦閒在家,沒事找事做,於是寫了這本小書。十多年來一直在保險公司做事,平素接觸的客戶多,交往的過程往往是:初則純粹在商言商,生意做成之後就變了朋友,其中不乏投緣的,更是無話不談,自然成了知心好友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交了許多女性朋友,當然也有男性的,但能夠說貼心話的,似乎同性的又較異性的為多。
人海萬花筒,各人頭上一片天。《香港屋簷下》是六十年代中聯公司的一部粤語電影,說的是人間悲歡離合的故事。我的這些女朋友們不也大多都是香港人海中的細碎花粒,都各自頂著一片青天,她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蹟,無不感人肺腑,令我一掬同情之淚。偏偏自身又是個極之感性的人,對於她們的不幸遭遇,聽後藏在心裡,總讓我有種忿忿不平的感覺。以往還未開始寫作之時,這種心靈的疙瘩感是無法去除的,於是越積越多,到後來倒有了麻木的傾向。可能是疙瘩的細胞堵住了我的心靈,我成了個不易哭泣的女人。
記得千禧後的一個秋天,我抑鬱症初癒,決定把多年患此病的經過及克服患病的心得公諸於世,遂與丈夫李歐梵合力寫成了《過平常日子》。從此,我涸竭多年的心田又得到了滋潤,原來呆滯的情緒再次躍動了起來,淤塞已久的細胞也暢通無阻地感到喜怒哀樂了。在平常的日子裡,我每能被當時幸福的感覺逗得流下淚來。晚上和丈夫在家欣賞影碟時,看到悲苦片段,往往忍不住淚流滿臉,累得丈夫在旁亂了手腳,連忙勸慰說:「老婆,這是假的,快不要哭。」
二〇〇三年夏天,我媽媽經歷久病之後去世了。她臨終前,我們曾經有過好幾次的真情對話,懺悔的言辭像一道激盪的清流,沖走了積存在彼此心中的愧疚沙石子,回家後我還把它寫成一篇篇的文章,記下我所見所想。到了她離我而去之時,我的心湖竟是澄靜如鏡。面對著一張張原稿紙,我把我所思所想的話語,一一記下來,平時不善用說話來表達的東西,都能藉著筆端盡情傾吐出來。沒想到我對媽媽的複雜感情也挑起我的創作慾望,不知不覺之間,竟然也為她寫了不少文章,加上我對外婆的回憶,幾乎可以出另一本書了。
我認為寫作是最好的心理治療。我畢竟是個有年紀的人,人生路上遇過的人著實不少,尤其是女性,我總可以用感同身受的心情去了解她們的處境,也就編成了一篇篇的故事。這些事蹟大多是真正發生過的,但為了尊重個人隱私的原則,把姓名都改換了,卻不失其真實性;也有幾個故事是我根據真人真事變造出來的小說。
英國著名文學家莎士比亞有這樣一句名言:「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我以他這句話作為這本書的引入,卻又改為一個問句;而書名則改為《女人,你的名字是強者。》。故意在這兩句用上對應的用意十分明顯,我不想替書裡的五十二位女性定位誰強誰弱,把定奪權留給讀者好了。我只希望讀者願意給我幾個鐘頭的功夫,聽聽我說肚子裡傾倒出來的「古仔」,並以「暖酒聽炎涼,冷眼參風月」的態度來聽,情緒就不至於受故事中人的悲慘遭遇所影響。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丈夫歐梵給我的鼓勵,更幫助我文章的校對工作,也費心給我提供修辭的意見;還有友人季進教授和歐梵的博士生陳曉婷,為我把故事輸入電腦去,我在此致以由衷的感激。
小序
李歐梵
數年前子玉寫的這篇前言,沒有提到一件最近發生的事:約在三年前,她的抑鬱症又再次復發了,而且與前不同,似乎是一種焦慮症。本以為這一次是小問題,看了醫生可以很快治癒,沒想到斷斷續續、時好時壞,竟然拖了三年之久。我想盡各種辦法幫助她,似乎都歸無效,不料她自己找到了一個自我紓解的方法:大概一個多月前,子玉突然從書房走到客廳,手裡拿著一個卷宗,裡面夾著一大堆寫得密密麻麻的稿紙,亂七八糟,放在一起,一邊略帶興奮地說:「我找到了不少文章,都是以前寫的,連我也不記得了,都是些短篇的故事,你先看看,說不定有讀者喜歡?」我看她的面色,稍帶紅潤,語氣也有點和往常不同。
我翻看這些文稿,發現幾乎篇篇字跡清晰,顯然是修改重抄過的,雖然有幾篇需要一點「加工」。於是我鼓勵她繼續寫下去,不料她靈感如泉湧,一發不可收拾,每天不停地寫,寫完了就拿來給我看,並迫著我修改。子玉寫作有一個怪癖,寫完了自己從來不看一遍,她說這是她的「自動寫作」。藉此抑鬱症復原時期,我不敢和她爭辯,不過還是提醒她: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任何作家像她這樣的寫法!據我所知,大多數的作家,譬如我的老同學白先勇,往往為了找到文章的語氣和敘事方式,不惜修改十數次之多。她哪裡肯聽,依然我行我素,每天從早寫到晚,我又擔心她的眼睛剛做過割白內障的手術,需要休息,勸她不要寫太多,她更是當作耳邊風。我發現自己也自相矛盾,一方面鼓勵她寫,另一方面又怕她寫多了傷了眼睛,還是隨她去吧,至少可以把寫作當作一種自我治療。她最近寫的三十多篇小說,就是在這個特殊的心理環境下寫出來的。我刪去了內容稍嫌隱晦的幾篇,剛好湊成五十篇。
子玉的文章——小說也好,散文也好——都是和日常生活有關,寫的都是身邊瑣事。此次她把自己的生活退居次位,而把她認識的女性朋友的人生經驗放在前台,書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有受苦受難的經歷。然而,受盡了人生的折磨之後,她們最後還是活過來了,所以,到底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還是強者?答案自明。
子玉小說中的女人都是以結婚為歸屬,遇人是否不淑成了慣常的主題,很少提到當今女性主義理論所揭櫫的個體獨立和顛覆男性霸權,雖然字裡行間,不時流露出對中國女性千年來所受的壓迫和壓抑的忿忿不平。這不是什麼驚人的道理,但經由子玉娓娓道來,連我這個大男人也禁不住感動。她的行文和敘事方式自成一體,靈感來自她讀過的大量晚清小說和看過的粵劇,她的語言既不是五四式的白話,也不是北京官話,而是廣東式的文白夾雜的語體文,至少這是我的看法(見附錄)。因此在修正她的文字的時候不敢多作潤飾,盡量保留她原來的行文方式,保持原汁原味,不能炒得太熟,甚至鼓勵她用章回小說式的標題,讀來別開生面。
子玉的文章基本上樸實無華,修辭幾乎沒有任何修飾,這種風格成了她的「商標」,她以前出版的兩本書:《細味人生——食物的往事追憶》和《憂鬱病,就是這樣》可以作為代表。作為她的第一個讀者(而且是男性讀者)我不能以自己的學術理論來「檢驗」子玉的寫作技巧。她是一個業餘作家,寫作是她的興趣,不是她的職業,她再三對我說,她寫作既不為名、也不為利,而是為了對自己有個交代。因此和她談什麼敘事角度、文體結構、描述細節等等技巧,似乎都與她無關。我曾經和她約法三章:她是我的妻子,不是我的學生,我們夫妻平等,我完全尊重她的「主體性」,所以不願向她灌輸文學理論和小說技巧,反正她聽而不聞,依然我行我素。
作為子玉的親人,我當然偏心,也很擔心。停頓多年後,如今她重操寫作的舊業,並且是在抑鬱症尚未痊癒的心情下寫的,能否維持當年的文風和水準?
以上的「小序」是我的交代,作為子玉「前言」的補記,我知道她自己絕對不會這樣寫的。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