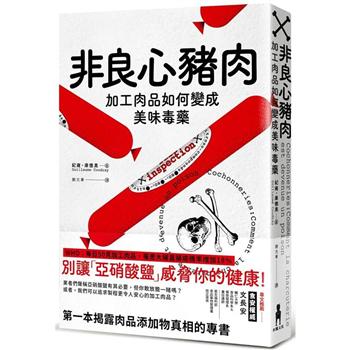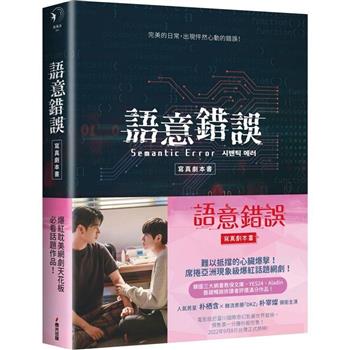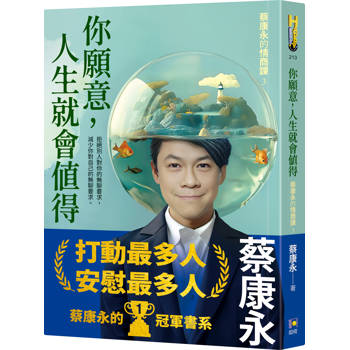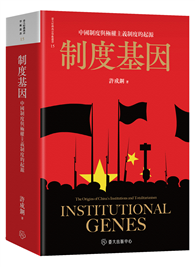第七十四章 遊船舊夢
十日後,一行人抵達金陵。
同濟陽的熱情淳樸不同,與潤都的沉重蕭瑟也不一樣,金陵城溫柔而多情,如嬌美風雅的娘子,沾染了幾分粉紅薄色。晴光盈盈,朝日風流,吳儂軟語裡,滿耳笙歌,是真正的人間富貴鄉。
林雙鶴一到此處便走不動路了,看著街道上走過的嬌軟娘子稱讚道:「這才是神仙窟,難怪人們總說,一入金陵便不想離開了。」
禾晏:「……你先前在濟陽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的。」
林雙鶴一展扇子,「禾兄,我只是入鄉隨俗而已。」
禾晏:「……」
真是好一個入鄉隨俗。
到了金陵,自然該與金陵應天府的巡撫打聲招呼,燕賀帶來的兵馬不方便在城內肆意走動。應天府那頭早已接到燕賀一行人至的消息,是以燕賀先去應天府裡接應,好將兵馬安頓下來。
應天府外,侍衛早已等候在外,有安排好的人去安置兵馬,禾晏本來也該隨著王霸他們,一道站在「兵馬」的隊伍中。奈何林雙鶴拍了拍她的肩:「妳如今是陛下親封的武安郎了,不是白身,當然該與我們一起,正好教妳見見官場世面。」
禾晏無言以對,正想問肖玨,燕賀瞥了她一眼,也跟著開口:「說的不錯,既然有官職在身,就跟著我們罷。」
燕賀這樣眼高於頂,十分不好相處的人,偏偏對禾晏另眼相待,旁人都有些詫異,禾晏卻心知肚明,這多虧了自己在燕賀面前將「禾如非」貶得一無是處,讓他覺得自己是世上難得的知音。
眾人邁進屋裡,正堂裡坐著一人,穿著巡撫的官袍,見他們進來,那人起身,巡撫生的很年輕,身材消瘦,五官清秀中帶著幾分堅毅之色,看起來不像是巡撫,反而像是國子監念書的學生。他站起身來,先是對著燕賀行禮,「燕將軍」,隨即目光落在肖玨身上,立刻面露驚訝之色,只是這驚訝稍縱即逝,很快便成為怔忪。
禾晏心中亦是吃驚,她沒想到,竟會在這裡遇到楊銘之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巧合,一個肖玨、一個林雙鶴、一個燕賀、一個楊銘之,賢昌館裡的同窗,這裡竟然遇著了四個!未免太過不可思議,不過……
禾晏抬眸,偷偷看身側的肖玨一眼,當年念書的時候,肖玨不是與楊銘之最要好麼?
禾晏少時得肖玨暗中相助,但明面上,與肖玨實在算不得親厚。當時肖玨亦有自己的好友,林雙鶴算一個,楊銘之就是另一個。比起林雙鶴這樣不務正業,只知玩樂的公子來說,楊銘之顯得正經多了。
楊銘之的父親楊大人乃觀文殿學士,楊銘之大抵是因著父親的關係,年少時才華橫溢。不過他身體不好,隔三差五頭疼腦熱,因此武科也是一塌糊塗。不過先生或是別的少年並不會因此而嘲笑他。在文科上,楊銘之實在是厲害極了。據說五歲時便能出口成章,八歲時就能與大魏名士論經。禾晏進賢昌館的時候,楊銘之已經很有名了,他的策論和詩文最好,還寫得一手好字,很令禾晏羨慕。他的性情也很溫柔,不比林雙鶴跳脫,也不如肖玨淡漠,柔和的恰到好處。
若說賢昌館中,燕賀總是在武科上與肖玨一較高下,那麼楊銘之便是能與肖玨的文科旗鼓相當的對手。與他溫柔的性情不同,楊銘之的詩文和策論總是帶著幾分銳氣和鋒利,可見他內心激傲。他還喜歡抨擊時事,興致來了,寫的文章連朝廷都敢罵,每每被先生責罵,但禾晏能看得出來,先生們是欣賞他的。
少年時的禾晏一直以為,楊銘之這樣的天才,入仕是必然的,一旦入仕,絕對會在大魏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不過她投軍後,便沒聽到楊銘之的消息,萬萬沒想到,今日會在這裡見到了,也萬萬沒想到,楊銘之竟然成了金陵的巡撫。他沒有留在朔京?這是為何?而肖玨看見他的神情亦是淡漠,這很奇怪。
當年肖玨與楊銘之的關係,就如與林雙鶴的關係一般。而眼下見面,卻生疏得彷彿陌生人。
發現這一點的不只禾晏,還有燕賀。燕賀道:「哎,這不是銘之兄嗎?你如今怎麼在這裡做巡撫?」
燕賀也不知道?看來這些年,楊銘之過得很低調。
楊銘之回過神,對燕賀笑道:「陰差陽錯罷了。」
「肖懷瑾,這可是你過去的好友,你怎麼如此冷淡?」燕賀的目光在他們二人身上一轉,「你們吵架了?」
他這話問的輕鬆,彷彿仍是少年時,卻讓楊銘之臉色微變。
「要敘舊日後再敘,現在又不是敘舊的時候。」林雙鶴適時的插進來,將話頭帶走,「那個,楊……大人,我們如今要在金陵停兩日,麻煩替我們安置一下。燕賀的兵馬你看著辦吧,歇兩日我們就回京了。」
林雙鶴的態度也很奇怪,肖玨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但林雙鶴可是個人精。可瞧他眼下對楊銘之的態度,卻有些刻意的劃清關係,再不見當時的親切。
楚昭自不必提了,早已看出其中暗流,饒是燕賀再心大,也意識到不對。這一回,他總算沒有直接說出來,安靜的閉了嘴。
楊銘之的笑容有些僵硬:「自然,房間都已經收拾出來,等下就叫人帶你們過去。」
林雙鶴一合扇子:「多謝楊大人。」
不多時,來了幾個婢子,領著禾晏他們去住的地方。住的地方不在巡撫府上,在秦淮河畔不遠處的一處宅子,許是楊銘之名下,屋子已經收拾的乾乾淨淨,房間倒是剛好,一人一間。
楚昭也得了一間。
他這一路上,倒是沒有與禾晏說過太多話。顯得沉默而安靜,不知道在想什麼,這倒是省了禾晏的事。肖玨也並未和他發生爭執,暫且相安無事。
禾晏住的屋子本是最偏僻的那間,這一行人中,她官職最小,這麼安排無可厚非。偏偏林雙鶴跳出來,對她道:「禾兄!我方才瞧見住的屋子裡有螞蟻,我害怕,能不能與妳換一間?」
禾晏:「……」
她道:「都在一處,你的房間有,我的房間也會有。」
「可是我單單只怕我房間的螞蟻。」他回答的很妙。
聽到他們對話的燕賀皺了皺眉:「林雙鶴,你有病啊?」
「正是,」林雙鶴笑咪咪地問:「你有藥嗎?」
燕賀拂袖而去。
一邊的楚昭若有所思地看了禾晏一眼,搖頭笑笑,隨應香走進自己的房間。
禾晏瞪著面前笑得開懷的林雙鶴。林雙鶴打什麼鬼主意,她一眼就看出來了。林雙鶴那間屋子,恰好在肖玨隔壁!他這不是將自己往肖玨身邊推,天知道她才下定決心要離肖玨遠一點。
她抬眸,恰好看見肖玨側過頭來,清凌凌的一瞥,一時無話。
林雙鶴道:「就這麼說定了,禾兄,我走了。」他飛快地抱著自己的包袱衝進禾晏原本的屋子,禾晏沒辦法,只能硬著頭皮走進林雙鶴的房間。
關上門,禾晏鬆了口氣。明知道這裡不是涼州衛,兩個房間裡也沒有一撬就開的中門,竟覺出些緊張來。她在心裡暗暗唾罵自己一聲,在濟陽城的時候,崔越之府上,連一間房都睡過,有什麼可緊張的,如今還隔著一堵牆,難不成會飛不成?
思及此,便稍稍放鬆了些。
只是心中到底是念著方才肖玨與楊銘之見面的不尋常之處,有些奇怪。過了一會兒,又溜出門去,見四下無人,就敲響了林雙鶴的房門。
林雙鶴打著呵欠來開門,一看是禾晏,立刻緊緊抓住門框,「禾兄,說話算話,咱們已經換了屋子,決不能換回來。我死也不會出去的。」
他還以為禾晏是要來換回屋子的。
禾晏無奈道:「我不是來換屋子的,我是有事來問你。」
「那就更不可以了,」林雙鶴正色開口,「我是正人君子,我們孤男寡……男,要是落在有些人眼中,豈不是出大事了?」
他這亂七八糟說的都是什麼?
禾晏懶得理他,一掌將他推進屋,自己跟了進去,隨手關上門。
林雙鶴被禾晏一掌推到椅子上,順勢雙手捂住前胸,振振有詞,「禾妹妹,朋友妻不可戲,我不是那種人。」
「我問的是楊銘之。」禾晏打斷他的話。
林雙鶴一愣,隨即大驚失色,「妳看上楊銘之?」
這人心裡怎麼只有情情愛愛,禾晏深吸口氣,「不是我看上他,我是想問問你,那位楊大人和都督之間是否出了什麼事。先前聽燕將軍說,楊大人是都督的好友,可我方才在外頭瞧著,他們二人的情狀,實在不像是好友的模樣。」
一口氣說完,林雙鶴總算明白禾晏的來意。他先是呆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坐直身子,向來開懷的臉上露出愁容,嘆了口氣,道:「妳發現了啊。」
禾晏問:「可是他們之間出了什麼事?」
「其實,我與燕南光、懷瑾和楊銘之是同窗。」林雙鶴放下手中的扇子,端起旁邊的茶壺,倒了一杯茶遞給禾晏,又倒了一杯給自己。他盯著茶盞中的茶水,回憶起從前,聲音輕飄飄的:「燕南光跟鬥雞似的,成日跟這個比那個比,與我們不熟。當年我和懷瑾、楊銘之最要好。說起來,楊銘之和懷瑾,應當比我和懷瑾更親近一些。」
他面上並未有半分妒忌不滿之色,只笑道:「畢竟我文武都不成,與懷瑾只能說說誰家姑娘長的俏,哪家酒樓菜更新。楊銘之和懷瑾能說的,總是比我多一些。楊銘之身體不好,少時還被人暗中說過娘娘腔,後來懷瑾帶著他一起後,就沒人敢這麼說了。」
這些禾晏都知道,她那時還心想,有才華的人總是與有才華的人諸多相似,肖玨與楊銘之同樣出色,難怪能成為摯友。
「後來呢?」她問。
「後來……」林雙鶴低下頭,目光漸漸悵然起來。
肖家出事那一年,朝中局勢很緊張。肖仲武死了,還擔上鳴水一戰指揮不力的罪名,肖家傾覆在即,朝中徐相的勢力越發倡狂。賢昌館裡的學子們,雖然都是出自高官富戶,但這個風口浪尖,誰也不敢為肖家說話。
林雙鶴除外。
他們家在宮中行醫,林清潭和林牧又不管前朝之事,林雙鶴更無入仕打算。得知肖家出事,林雙鶴央求父親和祖父在皇上面前替肖仲武說些好話。林牧也真的說了,他那一手女子醫科出神入化,人又圓滑,後宮諸多娘娘都與他關係不錯。林牧挑了幾位娘娘在陛下面前吹了幾日枕邊風,也不提肖仲武的事,只說肖家兩位公子可憐,都是少年英才,偏偏府中出事。
陛下也是個憐才之人,耳根子又軟,吹著吹著,便真覺得肖璟與肖玨可憐,鳴水一戰之罪,只論肖仲武,不連累肖家人。
但僅僅是這樣,還不夠。
南府兵的兵權還沒有收回來,縱然陛下如今念著舊情不發落肖家其他人,可沒了兵權的肖家就如沒了兵器保護的肥肉,只要旁人想,都能上來啃一口,更不是徐相的對手。陛下的仁慈只會隨著肖仲武死去的時間越長而越來越淡,想奪回兵權,只能當下下手,晚了就不行了。
而滿朝文武,除了肖仲武曾經的舊部以及沈御史,無人敢開口。
肖玨在賢昌館,摯友只有兩位。一位是林雙鶴,一位是楊銘之。林雙鶴央求自己的父親為肖玨說話,楊銘之的父親楊大人,那位觀文殿學士,曾是陛下欽點的狀元郎,文宣帝很喜歡他。若是楊大人說話,陛下未必不會聽。
肖玨請楊銘之幫忙。
林雙鶴至今還記得楊銘之當時說的話,他滿眼都是焦急,拍了拍肖玨的肩,道:「我一定說動父親在朝堂上為肖將軍說情。請陛下澈查鳴水一戰的內情,懷瑾,你放心,我和林兄會一直陪著你。」
他文文弱弱,說的話卻擲地有聲,林雙鶴從未懷疑過楊銘之那一刻的真心。想來肖玨也是。於是他們等著楊銘之的消息。
一日、兩日、三日……楊銘之沒有來賢昌館,問先生,只說是病了。
林雙鶴與肖玨懷疑楊銘之是出不了府,或是被家中關起來,並未懷疑過其他。於是商量一番,兩人便扮作小廝混進楊府,找到楊銘之。
彼時,楊銘之正在屋子裡練字。
沒有門鎖,沒有軟禁,甚至沒有生病。他看起來與從前一般無二,甚至因為在家裡不比學堂辛苦,氣色都好了一些。
「銘之,」林雙鶴訝然地看著他,「你怎麼不去學館?我和懷瑾還以為你出事了。」
楊銘之起身,看向他們,準確的說,是看向肖玨,沒有說話。
倒是肖玨明白了什麼,開口道:「你父親……」
「抱歉,」不等肖玨說完,楊銘之便打斷他的話,「之前答應你的事,我食言了。我父親不能替肖將軍說話。」
「為什麼啊?」林雙鶴急了,「不是說好了嗎?」
「無事。」開口的是肖玨,他垂眸道:「此事是我強人所難,你無需道歉。」
林雙鶴不吭聲,他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求一句話有多難。本不該怪楊銘之的,只是希望寄託越大,失望也更讓人難以承受。
禾晏看向面前的人,不解地問道:「因為此事,都督和楊巡撫決裂了嗎?可也許楊巡撫並非沒有為此事努力過,只是因為楊學士不肯鬆口,所以才沒能成功。」
她不太相信楊銘之是冷血無情的人,因為楊銘之待人和氣善良,當初在賢昌館的時候,禾晏接受的善意不算多,楊銘之絕對算一個。而且詩文和策論飛揚激蕩的人,應當內心尤其仗義熱情。
林雙鶴沒有立刻回答她的話,只是沉默,過了一會兒,他才道:「我當日也是這樣想的,可能楊銘之有些苦衷。」
「然後呢?」
「然後我們臨走時,楊銘之說了一句話。」他的聲音有些不平,眼前又浮現起當年的影子。
楊銘之叫住正要離開的兩人,道:「懷瑾,你有沒有想過,其實鳴水一戰,也許並沒有什麼內情,本就是肖將軍的原因?」
肖玨已經走到門口,聞言回過頭來,少年神情平靜,輪廓漂亮的像是一幅畫,他沒有說話,只是走到楊銘之身邊,一拳揍了過去。
「那一拳真狠啊,」林雙鶴「嘶」了一聲,又有些幸災樂禍,「楊銘之身子不好,被揍得在床上躺了半月,楊大人氣的要死,差點上摺子,最後不知怎麼的又沒上,可能是看懷瑾可憐吧。」
「不過這也沒什麼用,」林雙鶴嘆息一聲,「那之後不久,懷瑾就自己進宮請命了,帶著三千人去了虢城,一戰成名。」
禾晏沒料到楊銘之與肖玨之間,還有這麼一段。聽林雙鶴說完,也思忖了好一陣子。
誠然楊銘之最後說的那句話太過傷人。但無緣無故的,怎會如此?不幫就是不幫,何必這樣往人心口捅刀。且楊銘之原先的性子,不至於這樣尖酸刻薄。禾晏都這樣想了,身為楊銘之曾經好友的肖玨,不該沒想到這一點。
禾晏問:「那之後呢?都督就沒有再和楊大人往來了麼?這其中有沒有什麼誤會?」
林雙鶴搖了搖頭:「懷瑾自帶兵去虢城後,回京的日子很少。不過楊銘之嘛,在懷瑾走後不久,也不再在賢昌館進學。原本以他的才華,我還以為要考狀元留任朔京,以他爹的關係和他自己的本事,這也不難。不過自那以後,他像是銷聲匿跡了。大家兄弟一場,懷瑾的事,的確是他做得不對,我後來也不再與他往來,因此,不知金陵城的巡撫,何時變成了他。」
這兄弟幾人,看來眼下是真的分道揚鑣了,禾晏心中想著。
正在這時,外頭傳來敲門聲,伴隨著燕賀不耐煩的催促:「林雙鶴,開門!」
林雙鶴起身,一打開門,就看見燕賀站在門口,林雙鶴微笑:「燕將軍,請問這麼晚了,來找我何事?」
燕賀正要說話,一轉眼瞧見屋子裡的禾晏,狐疑道:「他怎麼在你屋裡?」
「我來看看這裡有沒有螞蟻。」禾晏道:「如果有,好為林兄驅走。」
「對對對,」林雙鶴正色道:「她是我請來驅螞蟻的,你可不要胡亂懷疑我與他的關係。」
「什麼亂七八糟的,」燕賀皺了皺眉,「趕緊換衣服跟我們走。」
「去哪兒?」林雙鶴莫名其妙。
燕賀輕咳一聲:「我找人告訴楊銘之,今夜要去秦淮河遊船,他一個地方巡撫,自然該為我們準備款待,你趕緊換身衣裳,同肖懷瑾說一聲。」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女將星:古裝大戲《錦月如歌》原作小說(卷六)的圖書 |
 |
$ 292 | 女將星:古裝大戲《錦月如歌》原作小說(卷六)
作者:千山茶客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24-11-13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女將星:古裝大戲《錦月如歌》原作小說(卷六)
成為侯爺,居然還被皇帝賜婚!
禾晏的身分危機拉警報!!
★瀟湘書院大神級作者 千山茶客 超越自我之作!
★古裝大戲《錦月如歌》原作小說!
──《護心》周也、《雲之羽》丞磊 領銜主演!
禾晏與肖玨一行人啟程前往京城,
途經金陵,遇到了年少時的故人。
遊花仙子素手輕彈,掀起當年少年學子們的熱血回憶,
也掀起了關於「禾如非」的祕密……
華原一戰,飛鴻將軍禾如非慘勝,親信副將皆戰死。
唯有禾晏知道,那些親信是隨她一路征戰,最了解她的人
──也是最先察覺飛鴻將軍異樣之人。
禾如非此舉,是在滅口……
中秋宮宴,禾晏入宮面聖,
沒想到一朝功勳加身,皇帝竟加封她為侯爵!
這時,宴席上有人站了出來,揭發她的女兒身──
★《女將星》全八卷,陸續出版,敬請期待──
作者簡介:
千山茶客
閱文集團,瀟湘書院大神級作者。
文筆大氣中含有細膩情感,筆下角色鮮明,劇情跌宕,廣受讀者喜愛。
代表作:《嫡嫁千金》、《將門嫡女》、《女將星(網路名:重生之女將星)》。
章節試閱
第七十四章 遊船舊夢
十日後,一行人抵達金陵。
同濟陽的熱情淳樸不同,與潤都的沉重蕭瑟也不一樣,金陵城溫柔而多情,如嬌美風雅的娘子,沾染了幾分粉紅薄色。晴光盈盈,朝日風流,吳儂軟語裡,滿耳笙歌,是真正的人間富貴鄉。
林雙鶴一到此處便走不動路了,看著街道上走過的嬌軟娘子稱讚道:「這才是神仙窟,難怪人們總說,一入金陵便不想離開了。」
禾晏:「……你先前在濟陽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的。」
林雙鶴一展扇子,「禾兄,我只是入鄉隨俗而已。」
禾晏:「……」
真是好一個入鄉隨俗。
到了金陵,自然該與金陵應天府的巡撫...
十日後,一行人抵達金陵。
同濟陽的熱情淳樸不同,與潤都的沉重蕭瑟也不一樣,金陵城溫柔而多情,如嬌美風雅的娘子,沾染了幾分粉紅薄色。晴光盈盈,朝日風流,吳儂軟語裡,滿耳笙歌,是真正的人間富貴鄉。
林雙鶴一到此處便走不動路了,看著街道上走過的嬌軟娘子稱讚道:「這才是神仙窟,難怪人們總說,一入金陵便不想離開了。」
禾晏:「……你先前在濟陽的時候也是這麼說的。」
林雙鶴一展扇子,「禾兄,我只是入鄉隨俗而已。」
禾晏:「……」
真是好一個入鄉隨俗。
到了金陵,自然該與金陵應天府的巡撫...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七十四章 遊船舊夢
第七十五章 遊花仙子
第七十六章 今日良宴會
第七十七章 回家
第七十八章 見雲生
第七十九章 進宮
第八十章 意中人
第八十一章 轟動
第八十二章 玉華寺
第八十三章 遇襲
第七十五章 遊花仙子
第七十六章 今日良宴會
第七十七章 回家
第七十八章 見雲生
第七十九章 進宮
第八十章 意中人
第八十一章 轟動
第八十二章 玉華寺
第八十三章 遇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