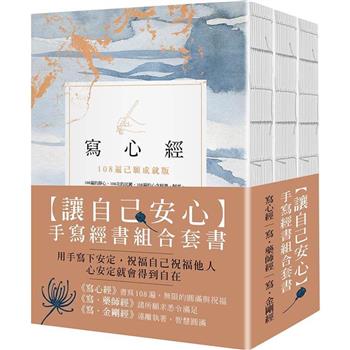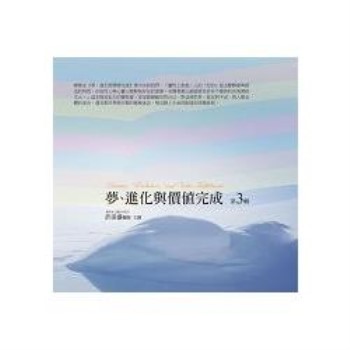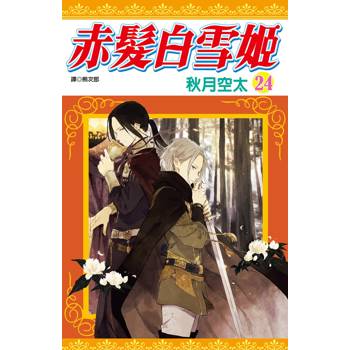【內文摘錄之一】
﹝仁宗的面紗﹞
西元一○四四~一○四五年之間,是宋、遼、西夏三國的國運分水嶺,同時也是宋朝進入黃金時段的破曉時分。
這個黃金時段的生成,就源於宋仁宗的決斷。從這些決斷,和其產生的後果,能隱約看到他三十五年的生命裡,隱藏得非常深的能力和個性。同時,這個黃金時段裡沉浮著太多的明星,中華五千年文臣的代表、儒家的大成者,都在這個時段裡產生。
按說是星光璀璨,無與倫比,也的確在歷史的長河中佔有絕對的制高點,就連在評書演義中,這些人都是出鏡率最高的。但是真正看清楚他們之後,很多眼鏡片就會摔滿一地。
宋仁宗今年三十五歲了,十三歲之前隱藏在他父親宋真宗的影子裡,二十四歲以前又被他養母劉娥徹底籠罩,好不容易親政了,又有超級多的大臣、君子、小人來搞事,滿天下一直在折騰,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反而出鏡率少得驚人。
歷代史書和學者們就給他送上了很多的頭銜──懦弱、懶惰、昏庸甚至好色。那麼他又是怎麼從一次次的內外動亂、財權糾紛、黨爭幫派裡存活下來的呢?每一次都平安度過,是他天生就戴著玉皇大帝給的不死金牌?
開玩笑,一次不死是偶然,兩次不死是幸運,三次不死就只能承認他是超人,不管他的內褲有沒有穿在外面。何況他還每次都做到了不動聲色,讓各方各面的蘋果自動掉到他的手裡來。
趙禎的不作為行為在慶曆新政中已經交代得很清楚了,到了遼、夏戰爭時達到了一個眾臣皆驚的程度。非常令人髮指,幾乎所有知道內情的人都對他很抓狂。
戰爭爆發在那年的十月份,就在爆發的前夕,他答應了李元昊的求和。而且條件還對宋朝非常的苛刻。
議和的內容簡直太不對等了,就算答應,也不能這樣賠本!
何況這是大好時機,為什麼不聯合遼國狠狠地痛打西夏,往大方向說很可能讓李元昊亡國滅種,徹底乾淨,小一些也能讓党項人元氣大傷,回覆到原始社會,重新全族變土匪。那是多麼解恨又理想。
但趙禎居然狼狽到了僅次於割地的賠款狀態,真是懦弱加可恥,搞什麼嘛,昏頭到白癡!我想大家都抱有這個看法吧?
那麼不妨換一種思維方式,假設趙禎突然英明神武,至少精明強悍,他抓住了這個機會。要麼在同一時間出兵党項,配合耶律宗真的軍事行動,要麼不答應李元昊的求和,耗下去,等更好的條款。
考慮下結果。出兵打仗,應該會勝利,李元昊畢竟不是鐵木真或者完顏阿骨打那樣的大角色,輸了,甚至本人都死翹翹,這個結果對宋朝好嗎?
兩個結果。
一、遼國從此獨大,至少恢復宋、遼對峙。以耶律宗真佔便宜不要命的性格,加上這次滅國級的大勝,再考慮到這人之前就對宋朝的瓦橋關土地發生過濃厚興趣。信不信下一個打擊目標就是宋朝?
二、李元昊死,西夏亡。這很好,党項人會不會絕種呢?那片土地上會不會再出現個李繼遷?那個幽靈一樣的党項影子再四處飄蕩起來,想想那是連宋太宗趙光義都搞不定的人物,讓趙禎怎麼才能安枕無憂?
所以出兵打仗沒有半點好處,何況還不見得必勝。
再說耗下去等更好的條款。這事兒看上去半點錯都沒有,不過稍微合計一下,就會發現是個豬腦袋才會想出的蠢招數。
請問你等什麼?
過了這個時段,李元昊無論是輸是贏,都不會再繃緊對宋朝的關係。輸了一了百了,死人不需要和平,不死的話也落寞了,徹底當土匪去,直接就是個搶,還囉嗦什麼?贏了,我連遼國都不放在眼裡,你宋朝算什麼東西?
那時的條件,說不定會更苛刻呢!
所以看似不作為,其實時機拿捏得妙到毫巔,並且從根子上斷絕了西夏和遼國對宋朝再次動武的理由。其實多簡單,對於宋朝來說,這兩個蠻族鄰居是地道的惡鄰,又窮又橫的主兒。他們的東西,宋朝半點都不希罕,根本沒有搶和計較的必要。
如果要說有感興趣的東西,只有一樣──燕雲十六州。得到這個,才真正有意義。除了這點之外,一切免談。
好了,綜上所述,趙禎的對外策略已經分析完成。大家覺得怎樣?我們再回頭研究一下他在慶曆新政時期的表現,看看不動聲色的背後,有著怎樣的智慧和打算。
他最為人所詬病的一點,和外戰方面一樣。麻木得就像那不是他的國家、他的子民一樣。簡直是放任著君子們去表現,再隨便小人們來掐架,一概不聞不問,徹底隱身。直到危及到了他的皇位時,他才動用了點權力,讓君子們發寒。
千年間有無數人要問,你既然大張旗鼓地要新政,為什麼又撒手不管,讓君子們四面楚歌,變得灰頭土臉?這不僅是拿范仲淹等人涮著玩,更是拿宋朝的前途開玩笑!
那麼我們再換個思維想事,讓趙禎牢牢地站在君子們一邊,歐陽修他們說什麼,他就做什麼,那樣的局面會怎樣呢?
「進賢臣」,好,君子們都擁到身邊來。這些人天天嘰嘰歪歪地說三道四,核心內容就是皇帝坐穩了別動,我們怎樣指揮你就怎樣辦事,對,是個木偶就正確了。至於君子們的表現嘛,進奏院事件中,和歐陽修主動狠揍御史台,都表現得很清楚了。
好鬥、無節制,連起碼的倫常概念都沒有。這樣的君子要來幹什麼?尤其是針對國家具體難題時,根本拿不出有效的解決辦法。
而這些事情,都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表現出來的。從新政開始到范仲淹外放,不過才八個月而已。歷代史書都在埋怨、嘲諷趙禎的始亂終棄,但為什麼就不看看新政者本身是什麼貨色呢?
好玩的是,繼續換角度思考。這些人之所以敢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原形畢露,無所顧忌,是因為什麼呢?如果換成是李世民那樣的皇帝,就算有這個心,也沒這個膽吧。呵呵,這就要拜趙禎的不作為所賜了,就是要讓你們表現,為什麼要壓制呢?那樣得花多少時間才能看清楚你們!
至於在黨爭中仁宗的立場,為什麼要支持「小人」們,把君子們定性為黨派呢?那可怪不了趙禎,是歐陽修的文筆太偉大,每當讀到他的傳世大作《朋黨論》歐陽大才子說得再美妙,那也還是朋黨,有了這東西,就會形成勢力,有了勢力,就會和皇帝爭權。尤其是這幫人已經在強迫著皇帝「退小人」了,並且還把小人一一指出。
這樣的人為什麼要支持?
何況政治鬥爭就像荒原上的生存法則,您得去鬥。這麼偉大的賢人君子如果連幾個小人都搞不定,我怎能放心把萬里江山交給你們去管?
所以聽之任之,是這時最好的管理手段。事實也證明,趙禎從來都沒有失去對局勢的掌控力。並且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所謂的新政,對這個本來立意就不高明的改革事件,趙禎的處理結果是那麼的讓人稱道。如果稍微懂點歷史的話。
自古以來,關於改革有一個顛仆不破的真理──「改革,興旺;不改,漸亡;模稜兩可,亂。」
查遍史書,改革徹底的國家,經過陣痛之後,都會煥然一新,得到重生的機會。比如戰國時的秦、趙等國;不改,一以貫之的國家,好比各個朝代裡都有過的某一超長時段,如清朝的康熙、乾隆年間,所謂的盛世一直延續下去,儘量求穩,求溫和,但留給下一代的都是超級爛的大攤子,根本沒法收拾。
但這還不是最壞的,最可怕的就是最後的五個字。
模稜兩可,亂。
這個例子不必去別的朝代裡找,二十年後的宋朝就是最大的經典。到時再細說。現在要強調的是,趙禎屬於第二類,見勢不妙,立即收手,不玩了…
【內文摘錄之二】
﹝生得奸詐死成笑話﹞
宋慶曆八年正月十五日那天出了件事,事發地點在西夏的都城興慶府,主角是當地國王李元昊。
那天是花燈節,李元昊正在享受生活。回顧歷史,這時在他的周圍,無論是世仇吐蕃,近鄰回鶻,上級宋朝,還是主人遼國,都已經成了他的手下敗將。十多年了,他把一個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都變成了他的豐功偉績。
這樣的成就,考慮到之前党項人的家底,真是驚世駭俗。這裡要說句公道話,他就是這一階段的戰神,不管過程怎樣,不管成果如何,他決戰決勝,把党項人這一種族的地位,拔升到了歷史的最高點。
於是就享樂吧。
在這方面他的品味還是比較遊牧的,他沒有多花什麼錢來裝修房間,當然,這個愛好太燒銀子,以西夏這時的家底,別說宋朝的頂級建築,如玉清昭應宮這種他修不起,就連五代十一國時,南唐、南漢的那些宮殿,也不是他能夢想的。
他喜歡騎著馬,帶著帳篷,和自己心愛的女人到處遊獵。
這個女人就是不方便在皇宮裡出現的沒藏氏。時光流轉,溫柔纏綿,在出事這年的前一年,西元一○四七年的二月六日,他們終於有了愛情的結晶。
一個嬰兒誕生在一條叫兩岔河的岸邊,是個男孩兒。李元昊給他起名叫「寧令兩岔」。寧令,是党項語裡歡喜的意思;兩岔,是因地起名,誰讓他生在了這裡。當時誰也沒有留意這個男孩兒對西夏意味著什麼,對李元昊本人的命運會有怎樣的影響。
只不過是個孩子嘛……
但要看這是誰的孩子,並且同類相忌,李元昊還有別的孩子!簡短地說,他生過五個兒子,種種原因,包括他自己親手殺掉的二個,最後只存活了一個,就是野利氏所生的太子寧令哥。寧令哥的命運,以他的婚禮為分界線,之前無與倫比的幸福,之後暗無天日的灰色。
他的老婆變成他的「母后」,他的皇位也有了新的人選,就連他媽媽的地位都開始動搖,從前的衛慕氏就是最好的例子,無恩愛即無一切,連性命都可能保不住,還談什麼將來?
種種苦悶,寧令哥心神不定,各種各樣的想法在他心底裡升起,但無論哪一種,都沒有這個人帶給他的震撼。一個微妙的小人物出場,就是這個人,讓這件事變得兇險詭秘。
他叫沒藏訛龐,是兩岔的舅舅,沒藏氏的哥哥。同時也是西夏當時的國相。重要的位置,尷尬的身分,他有和寧令哥一樣不安的理由,誰知道會不會有別的女人跳出來,比他的妹妹更加漂亮,成為李元昊的第九個春天呢?
每個春天都可以孕育出種子,兩岔不會是第一個,更不會是最後一個,李元昊才剛剛四十出頭,一切還都是未知數。他的地位,他妹妹的地位,有什麼辦法能徹底鞏固呢?
這是個問題,沒藏訛龐想了很久,一個很大膽、很奇妙的構思逐漸生成。越想越妙,只要能達到第一個目標,那麼整件事的結果,無論怎樣都對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關鍵點在兩個人,李元昊和寧令哥,這兩人只要死了一個,對他都會很有利。但細想,裡面有很大的分別。
一、寧令哥死了。那麼至少兩岔的太子位置暫時成立,就算以後還有三岔、四岔直到N岔,都要十多年之後,才能變成麻煩。
簡言之,寧令哥死,會解燃眉之急。
二、李元昊死。這事兒就有點棘手。不是說西夏國勢會劇烈動盪,連帶著周邊的宋朝、遼國,甚至吐蕃都可能起兵報復,而是說,李元昊突然死亡,留下了寧令哥,兩岔會有機會嗎?
精密計算,成算不大。雖然野利族的勢力大不如前了,但絕對不是沒藏氏一個沒名分的女人,再加上他這個國舅牌的相爺可以比的。
所以李元昊可以死,但決不能留下寧令哥!只有達到了這個目標,兩岔和他才能是終極受益者。那麼繼續想,怎樣才能讓這個想法變成現實?難道要讓寧令哥去殺李元昊?
……腦子裡突然蹦出來這個念頭,一瞬間沒藏訛龐被自己嚇得毛骨悚然。怎麼想出來的,讓兒子殺老爸?倒不是說殺不得,草原上這事很多,聽說漢人們也很喜歡搞這套。只是第一道關就不好過,試問寧令哥不殺怎麼辦?稍微有點大腦就能看出來,這是為他人做嫁裳,對兩岔有利。
算計一番之後,沒藏訛龐得出結論,只管去和寧令哥提,別怕任何風險。甚至最理想的結果,就是寧令哥去告發他,那樣是達到目標的最快捷徑。
懷著這樣的成算,他找到了寧令哥。之後發生的事,其實不能去怪這位太子有多腦殘,的確很好笑,沒藏訛龐一說他就答應了。至於為什麼,一來是他的年齡。兩年前他才結婚,在盛行早婚的古代,他能有幾歲?二來是他的恐懼。
而不是傳統史書裡強調的憤怒。
老婆被搶,媽媽失寵,地位動搖,無論哪一點的確都讓他怒火中燒,但如果只是這樣,就能讓他怒到提刀去砍他老爸,那他應該比李元昊還李元昊,真是太有性格了。怎麼還能等到這時還不動手?真正的原因是他恐慌又無助。這點最要命,他怕,就像等死的犯人那樣,眼睜睜地等著失去一切。這時沒藏訛龐出現,帶給了他唯一的希望,再失去,就徹底完蛋了。
時間來到正月初一,那天李元昊在興慶府皇宮的正殿上接受朝拜,傳說當時紅日初升,但是暗淡無光,就像一塊血紅色的雲團虛浮在天空。朝臣一片驚恐,這是大凶之兆。但李元昊不介意,平生作惡多端,殺人無數,天陰了就當是上天拉窗簾,有什麼大不了的?
他繼續威風,繼續享樂,直到正月十五元宵節這一天,達到了狂歡的最高峰。他沒意識到有半點的危險向他靠近,事實上也絕對沒法事先察覺什麼。因為兇手居然是皇太子寧令哥本人。
元宵節之夜,李元昊喝得大醉。醉眼迷離中,他向後宮走去,那是他的私密天堂,從沒有任何外人能夠進去。
這就造成了兩個事實,他身邊沒有護衛,寧令哥不是外人。他的親生兒子突然出現,拔劍就砍了過去。李元昊完全是憑著多年的戰場本能閃了一下,可惜真是喝多了,百分之九十的腦袋都躲開了,唯獨他堅強挺拔的鼻子礙事,被寧令哥一劍削了下來。
瞬間血流滿面,劇痛中李元昊猛然清醒,他滿殿亂跑,躲避危險。但危險比他跑得還快,寧令哥瞬間就消失了。
他真的只是個孩子,看見父親滿身滿臉的血,立即就嚇慌了。他犯了第二個錯誤,這比他起心殺父還不可原諒。都見血了,再怎麼樣也得當場殺死吧!
沒辦法,年輕,可以蠢到無極限。
他直接跑去找沒藏訛龐,也不管是不是完成了合約。這回一路順暢,狂奔到國相家。沒藏訛龐很滿意,前面說過,只要寧令哥動手了,就至少有十多年的好日子過。還等什麼,他立即動手把末路王子抓住,衝進皇宮護駕,百忙中把寧令哥的媽媽野利氏也抓住,據說是第一時間全殺掉。至於為什麼這樣大膽,一來是忠心發作,無法抑制;二來殺人無罪,這是叛徒;三來李元昊已經挺不住了,他殘存的最後一點理智僅夠做出一個決定。
這時的李元昊可以贏得我們的尊重,想想整個鼻子被削掉,那都是軟組織,血是止不住的。大腦瞬間就缺氧迷亂,在這種沒法克制的疼痛昏迷中,他都清醒地意識到了最嚴重的問題。
自己必死,誰來接替他?他的國家,他的拓拔族由誰來保障安全?
僅存的兩個兒子,一個是殺父兇手,一個又實在太小,腦海裡做最後的掙扎,一定要想出個人來!他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委哥寧令。這個弟弟沒什麼才能,但至少是個成年人,不會讓拓拔族的皇權旁落。
這是李元昊的遺願,這一時刻,讓人想起了他的祖父李繼遷。同樣是死於劇疼,同樣的擔憂身後事,但李元昊在這方面就沒法達成願望。
果然,李元昊拖了一夜,沒見到第二天的太陽。他死後沒藏訛龐以國相的權力,加寧令兩岔的唯一皇子身分,竊奪了西夏大權。從此這個國家就進入了一個噩夢般的循環。幾乎每一屆的國王都長不大,國家大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時間都掌握在皇太后、皇后、外戚的手裡。
李元昊的直系後嗣們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究其原因,可以精確歸納為兩個字─「人品」。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如果這是宋史(捌)宋朝開始變樣了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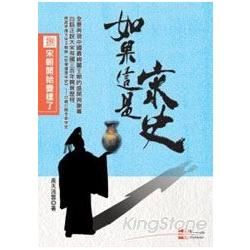 |
$ 213 ~ 250 | 如果這是宋史(8):宋朝開始變樣了
作者:高天流雲 出版社: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0-07-05 語言:繁體/中文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如果這是宋史(8):宋朝開始變樣了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說,他若能選擇中國一個朝代生活,他選擇宋
朝。
在宋朝,只有北宋仁宗時期,其繁華富庶、平安幸福,堪稱歷代之
最。
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18位皇帝中執政最長的一人。
宋仁宗死時,開封城內軍民百姓罷市同悲,數日不絕,連乞丐和小孩
兒都買了紙錢到皇宮門前焚燒痛哭,他們哭的不只是一個封建皇帝,更是
一個人情味十足的父親兄長。就連遼國皇帝都珍藏他的遺相,“奉其御
容如祖宗“!
仁宗童年是個不知身在苦難中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親生母親是誰,
連她死時都沒能及身相見,成了他一生的至痛。
他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繁華幸福中,貴為有史以來最富足王朝裡最繁
華時期的帝王,盡管手裡的錢不計其數,卻從不敢亂花一文錢,沒像他
的父祖那樣,興建過哪個超級宮殿,連某次宮廷內宴,膳房獻上幾隻螃
蟹,他得手知一隻螃蟹一千錢,即無法下箸,怒斥太奢侈。
可惜,他終究走了,宋朝開始變樣了…
作者簡介:
高天流雲
‧本名劉羽權,中國瀋陽人。
章節試閱
【內文摘錄之一】
﹝仁宗的面紗﹞
西元一○四四~一○四五年之間,是宋、遼、西夏三國的國運分水嶺,同時也是宋朝進入黃金時段的破曉時分。
這個黃金時段的生成,就源於宋仁宗的決斷。從這些決斷,和其產生的後果,能隱約看到他三十五年的生命裡,隱藏得非常深的能力和個性。同時,這個黃金時段裡沉浮著太多的明星,中華五千年文臣的代表、儒家的大成者,都在這個時段裡產生。
按說是星光璀璨,無與倫比,也的確在歷史的長河中佔有絕對的制高點,就連在評書演義中,這些人都是出鏡率最高的。但是真正看清楚他們之後,很多眼鏡片就...
﹝仁宗的面紗﹞
西元一○四四~一○四五年之間,是宋、遼、西夏三國的國運分水嶺,同時也是宋朝進入黃金時段的破曉時分。
這個黃金時段的生成,就源於宋仁宗的決斷。從這些決斷,和其產生的後果,能隱約看到他三十五年的生命裡,隱藏得非常深的能力和個性。同時,這個黃金時段裡沉浮著太多的明星,中華五千年文臣的代表、儒家的大成者,都在這個時段裡產生。
按說是星光璀璨,無與倫比,也的確在歷史的長河中佔有絕對的制高點,就連在評書演義中,這些人都是出鏡率最高的。但是真正看清楚他們之後,很多眼鏡片就...
»看全部
目錄
【目 錄】
第一章 仁宗的面紗…………………
第二章 生得奸詐死成笑話…………
第三章 花燈節之夜…………………
第四章 正版包青天…………………
第五章 鬼面崑崙關…………………
第六章 狄青升官記…………………
第七章 朕就是挺張貴妃……………
第八章 妙不可言的災難……………
第九章 狄青之死……………………
第十章 蘇老爹,慘、慘、慘!……
第十一章 蘇東坡風光進京…………
第十二章 四十五年無太子…………
第十三章 不識賤人真面目…………
第十四章 唯此一仁宗………………
第一章 仁宗的面紗…………………
第二章 生得奸詐死成笑話…………
第三章 花燈節之夜…………………
第四章 正版包青天…………………
第五章 鬼面崑崙關…………………
第六章 狄青升官記…………………
第七章 朕就是挺張貴妃……………
第八章 妙不可言的災難……………
第九章 狄青之死……………………
第十章 蘇老爹,慘、慘、慘!……
第十一章 蘇東坡風光進京…………
第十二章 四十五年無太子…………
第十三章 不識賤人真面目…………
第十四章 唯此一仁宗………………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高天流雲
- 出版社: 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0-07-05 ISBN/ISSN:978986622302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8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