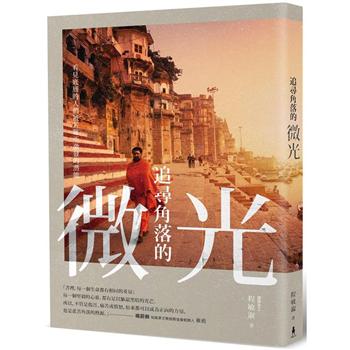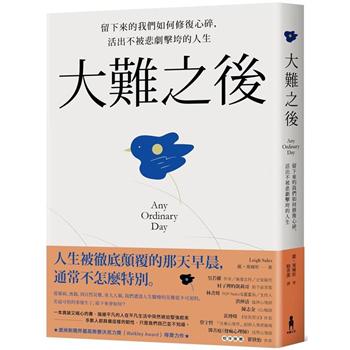﹝西夏孵化記﹞
西元一○三三年,幾乎是李元昊的災年,一樣的父親去世,獨掌國政,他卻沒有感到半分快樂。
從他登上党項之王的寶座時開始,他的榮耀就被兩條枷鎖壓得死死的──党項酋長的身分得由契丹人允許、宋朝人也允許,才能確認生效。
契丹人還好說,怎麼講都是他名義上的外婆家,何況党項人世代相傳,契丹人神勇無敵,很習慣拿党項人的腦袋當球踢。於是問題就出在了宋朝人的身上,因為他們是那樣的富足、那樣的軟弱,還有那樣繁文縟節,超級囉唆。
比如說,李德明去世,得有使者來,李元昊即位,仍然派來了使者。而且來了就是大爺,這些人捧著張黃絹,面朝南站著,念念有詞,唧唧歪歪,不管你聽不聽得懂,都得跪好了低著頭去聽!
奇恥大辱!李元昊都快氣瘋了,党項人世世代代竟然這樣尊敬自己的仇人!想當年爺爺是怎麼死的,想想宋朝的太宗皇帝是多麼的殘忍苛毒,我為什麼要在自己的宮殿裡低眉折腰?但是更屈辱的是,他居然真的就給宋朝的一片黃絹跪下了…
當宋使的宣讀剛剛結束,李元昊就突然跳了起來,向所有人叫道──如此國家,尚屈膝於人,此先王之大錯也!
相信那時的宋使楊告等人一定大驚失色,在宋朝,無論誰也不敢說自己的老爹半個錯字,但這個李元昊竟然這樣的大逆不道,當眾指責他的老爸。但更刺激的在後面,屈辱怎麼來的再怎麼回去,李元昊給他們準備了個特別的宴會。
酒席很普通,音響太特別。楊告等人和党項貴族們在大殿上吃飯,殿後邊一直叮噹亂響,冷兵器時代的成年男人一聽都清楚,那是在鍛造兵器。
事情很明顯,李元昊在挑釁,而且他不惜決裂。
事情也真的是這樣發展的,李元昊怒不可遏,他越想越衝動,跳過了宋朝使者,直接找宋朝皇帝的麻煩——拒不使用宋朝年號,而且質問,你們為什麼要用「明道」二字?不知道我的父親叫什麼嗎?是「李德明」,漢人們連避諱都不懂了?
就在李元昊血貫瞳人,殺性難遏的時候,漢人已經越過千山萬水來到了他身邊,就在興州城裡展開了對他的空前的蔑視和冒犯。
手下人緊急報告,不好了,有兩個漢人在酒樓裡喝得大醉,在牆上亂寫亂畫,其中就有您的名字在裡面。李元昊有點頭暈,避諱,宋朝人是真的不知道避諱是怎麼回事了嗎?他偉大的父親的名字被褻瀆了,現在居然連他的名字也被惡搞。
成了漢人醉鬼取笑的玩物!還等什麼,給我把他們抓來!
片刻之後,兩個錦衣峨冠的傢伙被綁了過來,身上都另穿了一件由麻線精心編製的背心,被捆翻作一團。但就是這樣,這兩個漢人仍然面不改色,神色囂張。這時李元昊已經知道了酒樓的牆上寫了什麼,乃是八個大字──「張元、吳昊來此飲酒。」
……倒也不是特殊的可恨,但是「元、昊」二字俱在,難道會有人身在興州,卻不知党項新王的名號?李元昊大叫,為何敢冒犯我的名字?
卻不料這兩個漢人一笑:「你連自己姓什麼都不在乎,又何必在意名字?」
輕飄飄的一句話,正中李元昊的命脈,這正是他的心事。他姓什麼?李,還是趙?他是什麼人,唐,還是宋?都不對,他乃是堂堂鮮卑後嗣,「衣皮毛、執弓矢,自在於天地之間」,與漢人何干?與「元昊」二字何干?
他立即上前親手解開繩索,待二人如上賓,之後毫無隱瞞,和這兩個漢人互相吐露心事。就在這一刻,他完成了中華五千年歷史中,從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被犬戎部落擊破沒落開始,直到滿清入關,甚至日寇侵略都必備的一個先決條件,即得到「漢奸」。
張元和吳昊,就像明末的洪承疇、范文程等人一樣,是教導異族人怎樣侵略本民族的導師。
他和張元、吳昊聊了幾次之後,某一天突然閃亮登場——真的是光華奪目,精光耀眼,所有党項人看到了一個超級大禿瓢。李元昊原先烏黑濃密的頭髮都不見了,他剃了個大光頭(超獨特,是個雪山式禿頭,四邊還留有些許的頭髮),而且還穿了耳孔,戴上了一對超重的大耳環。
然後他全方位地展示自己,接著下令,全體党項人以我為模樣,三天之內必須剃光了頭,並且戴耳環,特別強調必須是重的。如若不然,殺頭,全家全族可以由任何人隨意地去殺頭!
第一件事「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
眾所周知,滿清人入關之後,就是用這一招來扭曲漢人的心靈,從最根本處把一個種族的鬥志和尊嚴給毀滅的。想想那是怎樣的屈辱,又是多麼的惡毒,但那總歸是人民外部鬥爭,怎麼搞都沒有約束。但李元昊是在自己民族內部折騰啊,他為什麼?
理由很輝煌,因為他是鮮卑人的子孫,偉大的鮮卑祖先們一律都是禿頭,我們復古一下有什麼不好?或許鮮卑人久違的強悍就會覺醒,像五胡亂中原時那樣成功地虐待漢人,不是件超爽的事情嗎?
第二件事,換服裝。
伴隨著李元昊的禿頭出現的,是他的一身新衣衫。只見他上身穿雪白顏色的緊身窄衫,(下身怎樣史料未載,估計他也得穿點什麼)頭戴一頂紅裡氈冠,冠頂後還垂著一條紅色的結綬。紅白相襯,鮮豔華貴。
自此這就是党項王族的制式服裝。
接下來規定文官要戴襆頭、著靴,穿紫色或者紅色的衣服…;武將按官位高低,戴金帖起去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等各色帽子,衣服一律是紫色襴衫…。
平民們只准穿青或者綠的衣服,顏色雜了就殺頭。這樣的效果就非常好,只要李元昊登高一望,立即就能看到自己的國家裡誰是誰,只要不是色盲就絕對不誤事。
前兩件事像小丑,第三件就絕對的非同小可了。李元昊創制了党項文字。
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很清楚,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夠流傳千古,哪怕早已滅亡,都能在歷史長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要有自己的文字。其中的對比就像漢人和匈奴、突厥之間的區別。試想能與漢、唐兩代爭勝數十百年之久的民族,會沒有他們光輝燦爛的歷史嗎?那其間隱藏著漢武帝和天可汗的敵人。但轉眼即逝,就算留下些模糊的傳說,也不被史學家承認。
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文字。
李元昊排除了重重困難,不經過自然衍化,就硬生生地創制出了一種全新的文字。
以上種種,李元昊走過了多種多樣的秀場之後,終於想起要做些實事。他把党項官場的職稱和職權規範了一下,從宏觀上來看,他照搬了遼國官制,細處著眼,他仍然複製了大宋。
做完了這些,李元昊的目光開始向南望過去,多麼肥、又多麼軟的宋朝啊,我現在既成功地梳理了內部,又手握一支常勝不敗,在十年之間擊破吐蕃、回鶻,兼併整個河西走廊的軍隊,還等什麼?宋朝乃至遼國都早已腐朽,現在是党項人的天下!
但是他的謀士們卻集體對他叫停,這裡要提一下他們的名字,算上剛來的張元、吳昊,還有六人,其中除了嵬名守一個党項人之外,全都是漢人。他們叫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這批「漢人」面露微笑,在党項人的鐵血本性之外,又塗抹了一層詭秘難言的暗色。
李元昊的狡詐兇狠被提升到了雄才偉略的高度。
﹝史上最隆重……離婚﹞
西元一○三三年就這樣過去了,對党項人而言,他們有了自己的年號、新衣服、新名字、新文字等等等…
時間還在對宋朝仁慈,仍然給了他們準備的時間,但是回到開封,就會驚奇地發現,偉大的仁宗皇帝在短短八個月的時間裡就做出一個奇蹟。你沒法不佩服他,皇宮裡最大的地震已經發生,居然是──廢皇后。
皇后姓郭,她是已故劉太后親選的,為的就是抵擋絕色美女對兒子的誘惑,那麼她本人的容貌也就可想而知了。更糟糕的是,她出身於武將世家,本性就粗糙了點,而且在十年的夫妻生活中向婆婆劉娥的作風看齊(要命,妳為何學後期的劉娥,不學剛開始時的川妹子啊),不僅面對丈夫時是冰山美人,就連整個後宮都被她凍住了。
有她在,趙禎就別想去親近別的女人。
結果她就嚴重地妨礙了趙禎在後劉娥時代的幸福生活,具體的表現就是──皇后親自打人了,給了皇帝一巴掌。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話說趙禎陷在了溫柔鄉裡,該鄉有兩位最著名的美女,一位姓尚、一位姓楊,相親相愛的程度都達到了夜不歸營的程度,這實在讓人很心煩,於是皇后陛下怒了,她忘了中華民族老祖宗周朝對女士們訂下的「生存七戒」,犯了就會被趕出家門的,其中之一就是「妒忌」。
當年十二月份,某一個寒冷的冬天裡,那一天皇帝正和兩位美人促膝長談,漸入佳境,結果郭皇后突然駕臨,目的很明確,就是敗興加攪局,我冷清,你們也別想快活。按說這已經是第N次了,以往都會遂她的意,不歡而散。但是這一次她絕對沒料到長久的壓抑已經質變,突然間爆發,不可收拾。
一向很乖的尚美人居然開口說話了,而且語帶諷刺(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震驚加憤怒,不管是不是皇后,一個妻子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被情敵所侮辱!一瞬間郭大將軍的基因本性發作,郭皇后忍無可忍,撲過去就是一個大巴掌。
可是仇恨敵不過愛心,她的速度明顯慢於她的丈夫,仁宗陛下護花心切整個身體都擋了過去,結果這個巴掌,就打在了從沒有任何人抽過的脖子上……仁宗大怒!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個蠢女人,新仇舊恨,尚妹妹、楊妹妹,還有從前的王妹妹、張美人,一個個好夢都被她攪了局擋了道兒,現在太后死了,她仍然不讓朕順心!
廢了她!
當天他怒氣沖沖出宮去,直接去了政事堂,把自己的脖子展示給宰相看,那上面還留著郭皇后撓出來的爪痕。
「你看怎麼辦?」趙禎在憤怒中還沒忘原則,皇后的廢立是僅次於皇帝即位、皇太子確立的頭項大事,不是他一個人就能說了算的。百官的意見,尤其是宰相的意見才更關鍵。
只見該宰相看了又看,再看,然後召來內侍副都知閻文應,仔細詢問了事發經過,之後清晰地回答——廢了她。
郭皇后的命運就這樣被確定,因為這位宰相姓呂,叫呂夷簡。
呂夷簡十月份就官復原職。其中的奧妙很簡單,半年的時間足以讓皇帝知道當年他曾經為陛下的生母盡過怎樣的忠心了。美中不足的是他取代的是副相張士遜,首相的位置上坐著德高望重,重如泰山的李迪。
實在是搬不動他,近十年來的政治迫害,再加上仁宗老師的身分,於公於私都讓李迪變成了一個悲劇性、悲壯感的政治符號,是忠臣、正臣的代名詞。
為什麼在仁宗怒氣沖沖趕到政事堂時,裡面值班的人為什麼是呂夷簡,而不是李迪?
如果是道德隆重的李老夫子的話,百分之二百的,這件事的進程和結果就會有天壤之別。
事到臨頭,趙禎突然又有些猶豫,畢竟那是他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妻子,而且他是「仁」宗,性格中真的有太多的不忍。但呂夷簡明確地說出了自己支持廢皇后的理由:「東漢的光武皇帝,那是中興漢室的一代明主,他就曾經廢掉自己的皇后,理由不過當時的郭皇后口出怨言、心有不滿(怨懟)。何況您的郭皇后居然打傷您的脖子?」
言之確鑿,罪證俱在,怒火再一次從趙禎的心裡升騰。而且更重要的,「仁」宗性格裡的另一面也被觸動──但凡心慈手軟,優柔寡斷之人,最怕的就是面對毫不含糊、態度強硬的說客。基本上都會屈服。
下一步呂夷簡已經越過了廢不廢的問題,直接去構思廢了之後,怎樣確保廢之有效。關鍵點就是御史台和知諫院。
這兩個職能重疊的衙門在宋朝的作用就是幫著皇帝制約臣子,其中的意涵就是制約宰相。
本著和平年代雞毛蒜皮都要敲打一番的原則,這次廢皇后簡直就是逼著他們發狂。基本上可以肯定,命令頒佈之時,就是亂蜂螯頭之日。
但是,呂夷簡想出了三條應付之道:
第一,抬出了儒家之正理,男就是封建年代的女子七出之律。
而我們的郭皇后,她至少已經犯兩條:妒忌,還有無子。
第二,就完全是政治上、官場上的工作技巧。呂夷簡第一時間以書面的方式通報有關部門(先敕有司),不得接受御史台、知諫院的奏章公文,讓他們有話沒地方說,統統地憋死。
第三,就比較另類。他替郭皇后想出了一個「體面」的下臺理由。以仁宗皇帝的身分發出了一道詔書,「廢后」的理由變成了皇后引咎辭職的聲明書。書上說,皇后發現自己十年都沒能生出孩子,真是太慚愧了,於是自動讓賢。
如此這般,一切就緒,只等第二天早朝,看看是皇帝加宰相的頂級組合強大,還是宋朝的言官大老爺們無敵。
暴風雨如期來臨,廢后詔書就像一聲令槍,所有的台諫官都一哆嗦,但緊跟著就血貫瞳人,火花四射。不必號召,更不必準備,從跪聽詔書的那一刻起,所有的人都動了起來。
言官們群情激憤,但稍微聚集了一下就又都散開了。程序第一步,回家各自寫稿子。身為法律風紀的糾正維護者,做任何事都要依著規矩來。
於是他們就撞上了第一堵牆。文采飛揚、正氣凜然的稿子交上去了好多天,一點回音都沒有。
接下來,言官們從家門裡走了出來,一個個穿戴整齊,全套朝服,目標金鑾寶殿。程序之二,言官有權力要求和皇帝面談。
他們又撞上了第二堵牆。只見偌大的紫禁城,金釘朱戶的大殿門,居然叫破了嗓子都沒人回應。怪事吧,誰能想像全國最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宮門前,居然就這樣聚了一大堆人大呼小叫,但就是沒人制止,絕對的死氣活樣,躺倒挨錘,只求著你們有火就發,發完走人。
怎樣,這就是呂夷簡臨時想出來的應對絕招──家裡沒人。你們總不會破門而入吧!但他想錯了,門,神聖無比、顯赫無比的金殿之門,在那天真的被人敲了起來!是孔道輔,他抓起殿門上的銅環用力拍擊,大叫道:「皇后被廢,奈何不聽台諫入言?」
這下子皇宮之中再也不能保持沈默,是做皇帝耶,起碼的尊嚴和制度總得留一點吧?不一會兒,有太監開門傳令。皇帝說了,請大家去政事堂,有事找宰相去說。
畫面切換到政事堂,值班的仍然是呂夷簡。李迪老夫子還是不知去向。各位言官終於看到一個活人了,火力空前密集,七嘴八舌,一開始就把問題上升到了最高的程度──宰相大人,請問你有爹和娘嗎?
啊?呂夷簡瞬間癡呆,搞什麼?就算再經驗豐富,天賦異稟,他也沒料到各位言官老大的開篇詞居然是這個……
「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這就是當年言官們的原話,意思很明確,你爹和你娘吵架了說要離婚,難道你當兒子的拍手贊成?
孔道輔和范仲淹質問呂夷簡:「你對陛下所說過的話,不過就是引用東漢光武皇帝曾經廢掉自己的皇后這件事,對不對?但那是光武皇帝一生的污點,是他失德的地方,你想讓我們的皇帝有樣學樣,跟他一起錯?尤其是從那事兒以後,歷代所有廢過皇后的皇帝都是昏君(自余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聖上應該去學習堯、舜的品德,你為什麼要誤導陛下去效法昏君?」
牙尖嘴利,而且善於定罪。所有曾經廢過皇后的皇帝,都是昏君。這事就比較讓人頭昏,難道說當了皇帝之後,一個封建時代男人的最基本權力——換老婆——就已經失去了?皇后只要當選就一定是終身制,無論做了什麼都無責任、無處罰?
肯定有千言萬語的反駁,但呂夷簡選擇了沈默,甚至是認輸。他恭恭敬敬地向眾位言官大老施禮(拱立),說出了超級窩囊的一句話:「請諸君明天早朝時親自向聖上講明此事。」他迴避了,話裡話外的意思居然是這事我辦錯了,已經沒能力再搞,拜託你們明天去皇帝那裡善後。
一時間言官們有點不適應,這就算結束了?不會吧,爭論才剛開始…當天各位言官得出的結論也就是,只要明天上朝把少不更事的小皇帝也說服,那麼就大功告成。於是他們氣勢洶洶而來,得意揚揚離去,滿足啊,一個奇蹟已經創造了──鬥倒宰相;另一個奇蹟就要產生──教訓皇帝,還有比這更充實的人生嗎?
多、麼、的、神、奇、啊──!
但怎麼就不想想,如果萬一呂夷簡不是個衙內廢物呢?那麼這樣的軟弱就一定是個陷阱。果然好戲上演,他們前腳才走,呂夷簡馬上就和皇帝單線溝通,傳達了他的一句話:「陛下,台諫官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應予貶逐。」
哈哈,報應瞬間臨頭。這時就應該重播一下呂夷簡剛才貌似很矬的嘴臉了,看看當時言官們是多麼地能言善道並且博學多才,但有什麼用呢?以為這是在課堂上,誰說得有理聽誰的?開玩笑,那是李迪老先生的風格,想當年機關槍一樣把周邊所有的高官都突突地掃了一陣,結果自動下野,後悔不及。但這是呂夷簡,他從不跟任何人多廢話。
要做就做到狠,讓你們連後悔的時間都沒有!…
﹝韓、范悲愴交響曲﹞
時光流逝,西元一○四一年的二月轉眼就到了,突然間傳來警報,西夏方面在折姜會區域集結軍隊,經天都山侵入了宋朝邊界,目標直指涇原路的渭州,領兵人是皇帝李元昊本人。
韓琦馬上趕往鎮戎軍。這個行動意味著他迎頭攔住了李元昊,把自身處於最前沿。因為鎮戎軍的身後才是渭州城。在這裡他緊急召回了任福,把鎮戎軍裡所有的精銳都交給了他,再招募一萬八千名義勇,唯恐戰力不夠,又把涇原帥司裡的各路名將,如王珪、武英、朱觀、桑懌還有參軍事耿傅,統統都派出去配合他。全體出動,但要注意,目的卻不是迎戰。
韓琦並不是一個狂熱的激戰派,他始終都很清醒。他命令任福等人從鎮戎軍出發,先向正西方行軍,第一站懷遠寨,然後轉向南,也就是向自身的腹地前進,到得勝砦,最後的目標是羊牧隆城,這樣就基本上與西夏軍隊的侵犯態勢平行,決不做抵抗或者交戰,那是我韓琦本人的任務。你們要時刻隱蔽自己,隱身敵軍之後。
倉促之間,韓琦為這次戰役立下了一個盡可能穩妥,但又殺機四伏的佈局。把自身處於最前線,來鼓舞本方的鬥志,以己方之險城,如鎮戎軍來消耗西夏軍隊的銳氣,再安排任福等全部機動力量遊走在戰鬥的邊緣,在外線等待機會。從開始就為最後勝利的一擊隱藏了實力。
這一路上,每隔四十餘里,就有一處軍寨接應你們,無論是物質,還是休息,或者據兵防守的據點,都隨處可見。可以說立於不敗之地。你們要一直等待,直到李元昊攻城不克,筋疲力盡時,才是你們出戰的時候。那時就算不會全勝,也必定讓西夏人狼狽不堪。
任福出戰,熱血沸騰,夜屠白豹城的兇狠仍然讓他興奮,他率領幾千騎兵,以桑懌為前鋒,殺向懷遠寨,這一天是二月十日。
第二天,二月十一日時,他到達了懷遠寨,就在這裡,他得知了一個最新戰報。附近的張家堡正發生激戰,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劉肅和西夏人遇上了。一個大戰役中的小消息,卻成了整個勝負的轉捩點。任福做出了一個勇將的選擇,他聞訊即戰,想都沒想就率軍衝了上去。
把韓琦寫成書面文件的軍令扔到了腦後,那上面清晰地寫著——「……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如果你不聽命令,沒按照我事先安排的方式去作戰,就算勝利了,我也砍你的頭!
而任福的使命是隱藏,是等待,是遊走於外線,可不是第一時間地殺向敵人。但戰鬥開始了,任福所部是宋軍最精銳的部隊,殺到之後砍瓜切菜一樣地獲勝,西夏人扔下幾百具屍體,還有牛馬駱駝開始逃命,任福下令追擊。
這又是一個勇敢的決定,戰而勝之,窮追不捨,他們居然一口氣追逐了三天。三天之後,人困馬乏,他們在行軍中帶的口糧都不夠了。歷代史書寫到這裡,都要嘲笑一下任福的好勝以及短視。追擊也是戰鬥,連口糧都成問題,難道還想打勝仗嗎?但有兩個問題他們都忽略了。
第一,之所以一直追下去,是因為這股西夏逃兵的逃跑方向,與韓琦原定的遊走路線暗合。任福是既追擊又趕路,方向都是羊牧隆城,反正都要走,為何不殺敵?
第二,這一路上就像韓琦所安排的那樣,每隔四十多里路就有軍寨接應。軍糧本是不成問題的,之所以會餓肚子,那是殺敵心切,沒顧上吃!
這怎麼能成為任福莽撞、幼稚的失敗理由?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二月的十三日晚,任福命令全軍停下,必須休整了,當時的地點是羊牧隆城的東南方數十里外的一片灘塗地,名叫好水川。
這一夜,任福是在平靜和期待中度過的。說平靜,前方就是羊牧隆城,主帥指示的位置就要到達。他的友軍也增援到位,朱觀和武英就屯紮在附近的龍落川,與好水川只隔一個山頭,相距五里。還有羊牧隆城,那裡有勇將王珪,上一次在鎮戎軍城下痛擊西夏軍隊的悍將,更是他的得力臂助。
他派出的探子回報,前方一直逃命的敵軍已經跑不動了,人數也變得更少。針對這種形勢,他派人到龍落川聯絡朱觀、武英,相約明早會兵,一起追擊,吃掉這股敗兵。再去王珪那裡休整,任務殺敵兩不誤,堪稱完美無缺。
第二天,二月十四日終於來臨。任福全軍早起,出六盤山沿好水川向羊牧隆城前進。這時另一方向朱觀、武英部也拔營而起,兩軍基本平行,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內會合,為的是儘量快速行軍,去追擊西夏人。一路疾行,前鋒桑懌經籠竿城北追到了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
就在這裡,他發現路中央擺放著五、六個很奇怪的東西。是木盒子,每個都不太大,但裡邊傳出了翅膀屈伸還有鳴叫的聲音。他立即就停了下來,這是戰場,是允許耍詐,越詐越高明的地方。這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時出現在這裡,到底有什麼古怪?
他傳令全軍停止,通知主將來親自觀看。任福來了,他也覺得奇怪,但扔在一邊繼續前進更不妥。那麼打開吧,一瞬間之後,幾百隻鴿子騰空而起,響亮的鴿哨聲響遍山谷。中計了!宋軍每個人都想到,這是軍鴿,幾百隻鴿哨足以相比戰鼓,傳遞消息。
那一天,飛越的翅膀越飛越高,鴿哨聲漸漸升入高空,變得遼遠悠揚。地面上大群的西夏軍隊湧了出來,一眼望不到邊,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親自帶隊的人馬,又是十多萬人,又是上次三川口之戰的格局,兩萬餘宋兵在本土境內面對近十倍的敵人。
中計的一瞬間,不知任福想到了什麼。是明白之前追殺的敵軍是誘餌,他恃勇前進,其實是自陷死地?還是說,能想到更深一層,為什麼這麼龐大的敵軍一直行進到鎮戎軍與渭州之間的六盤山附近,進入宋朝涇原路腹地了,還一點都不知情?
不可能有答案,前鋒桑懌已經率軍衝了上去,那是在儘量爭取時間,讓他能佈置軍隊,結陣自保。哪還有時間想東想西?戰場在瞬間沸騰,桑懌的前鋒部隊顯得那麼孤單,就像用一隻木盆來阻擋洶湧而來的洪水,西夏人淹沒了他們,繼續衝向了後面的任福部隊。
激戰開始,從最初宋軍就陷入了絕對的劣勢,他們甚至連列陣的時間都沒有(福陣未成列),就遭受衝擊。任福的形勢比一年前的劉平還要惡劣,一馬平川的山谷地,中間沒有任何阻礙,連那條作為緩衝地的冰河都沒有。他唯一的辦法就是親自衝鋒,連他的兒子任懷亮在戰鬥中落馬都無暇顧及。
就算這樣,也只是在拖延著最後覆滅的時間。從上午辰時到正午的午時,兩個時辰四個小時之後,宋軍終於崩潰。任福在敗軍中想到了唯一的一個解救辦法,他命令桑懌和自己的兒子帶隊衝向一座高山,據險而守,希望能多挺一陣,或許會有轉機。
但是匆忙之間,他忘了一件事,西夏人是比他先到戰場的!如果是埋伏,那麼僅僅只有對面的伏兵嗎?宋軍衝向高山,突然間在山頭上樹起了西夏人的軍旗,向左指,左邊的伏兵起,向右指,右邊的伏兵起,居高臨下,向爬到半山腰的宋軍壓了下來……
任福在山下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兒子和桑懌墜崖而死,大批的士兵更是死傷無數。敗局己定,這時一個叫劉進的親信小校對他說,將軍,你快單獨逃走吧(勸福自免),或許還來得及。任福百感交集,逃,還要單獨逃,在這樣的生死場上,怎能是一個「人」的選擇?
「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這是任福說的最後一句話。然後他挺身決鬥,身中十箭,面受兩傷,最後一槍從他的左頰刺入,咽喉被刺斷而死。
任福所部全軍覆沒,戰鬥卻更轉激烈,五里之外的姚家川成為新的焦點。朱觀、武英部行軍到這裡,幾乎與任福同時被西夏人伏擊。
西夏人大軍合圍,再沒有半點僥倖的機會!戰鬥從任福覆滅的午時開始,直到午後三點到五點的申時,又兩個多時辰過去,先是武英重傷,再是東邊陣地的步兵崩潰,宋軍的陣地終於鬆散了……最後的時刻到來,一個戰士、一個宋朝人的本質在這時顯露。
軍隊裡有一位文官名叫耿傅,本職是慶州的通判,這時是任福軍中的參軍。危急中,武英把他拉到身邊,勸他立即逃跑。但耿傅沈默,不回答。武英急了,對他說──英乃武人,兵敗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
話說完,武英立即後悔,耿傅是位文官,但更是一位勇士。他仍然沒有說話,反而挺身向前,指揮士卒繼續抵抗。但西夏兵潮水一樣湧來,轉眼間他死在了亂軍叢中。
當天好水川沒有生還者,姚家川最後只逃出了朱觀和一千多個士兵。這時戰場薄暮,天色將晚,西夏人漸漸退去,縱目所見,宋軍屍橫遍野,短短一天之間宋軍涇原路帥司中的名將們損失殆盡,任福、桑懌、武英、趙律、耿傅、訾斌、李簡、王慶、李禹亨、劉鈞等兩百餘名將校無一生還,士兵陣亡過萬,比前一戰三川口時還要慘烈……這還不包括王珪和他的四千五百名士兵。
好水川之戰,英烈無數,最忠勇頑強的人是王珪。他和主戰場裡的所有人都不同,因為他本不必戰死在這裡。
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將,五里之外的好水川發生激戰,他立即帶兵殺了出來。但趕到時西夏人陣勢己成,鐵桶般把任福所部圍在當中。王珪只能隱約地看到宋軍的將旗沒倒,他瘋狂衝擊,要殺進去把任福救出來。但人山人海,四千多人面對十萬之眾,要怎樣才能殺進重圍?
幾次衝擊,沒有效果,王珪的部下們有的膽怯了,猶豫著不敢前進。王珪立即把他們軍前斬首,以激勵士氣。但悲哀的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他的勇氣。終究是血肉之軀,絕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沒有鬥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馬。
當年的那些士兵們或許都鬆了口氣吧,王將軍終於也放棄戰鬥了。卻看見他在震天動地的喊殺聲中向東方跪了下去——「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報耳!」
王珪上馬再戰,衝進了西夏軍中。他獨自擊殺數百人,手中的鐵鞭被打得彎曲,手掌破裂,鮮血滿手,但仍然死戰不退。戰馬被射倒了三匹,換馬再戰,無論如何都決不逃跑。他最後的結局和郭遵一樣,死於亂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於宋朝而言,無論將士們怎樣英勇,敵軍怎樣眾多,好水川之戰畢竟是完敗。但看過程,再看看結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慘勝…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如果這是宋史(陸)眾將官.西北望.射天狼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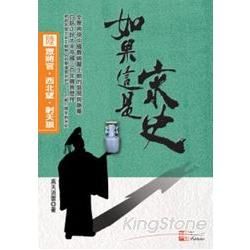 |
$ 238 ~ 280 | 如果這是宋史--(陸)眾將官?西北望?射天狼
作者:高天流雲 出版社:知本家 出版日期:2009-11-1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64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如果這是宋史(6):眾將官‧西北望‧射天狼
換一個角度看歷史,本書告訴讀者一個不一樣的宋朝:
‧這個王朝也有強悍的一面
略懂歷史的人幾乎都根深柢固地認為宋朝是脆弱的。西夏李元昊繼承王位後,由最初的挑釁到後來一次次的挑戰,宋朝名臣遍佈、武將羅列,血洗的戰場,留下宋軍忠貞苦鬥的歷史,漢人的史官忽略、貶低了這一切,蒙古人修宋史時,卻沒有抹煞宋軍在各戰場諸般功績。
‧這是數千年來最風雅的時代,文臣的權力連皇帝也頭疼
"仁宗養士,三代受益"!宋朝三百多年的歷史中,最
耀眼的「天聖進士集團」就出現在仁宗主政時,並為英宗、神
宗二朝培育了才俊。這集團中包括:歐陽修、韓琦、范仲淹、
宋庠、文彥博、包拯、富弼…等。各個都是鐵錚錚的漢子,因
此就算是九五至尊的皇帝也不可快意行事,仁宗朝的"廢后"
事件,充分地展現了眾文臣給了皇帝極大的壓力!
作者簡介:
高天流雲
‧本名劉羽權,中國瀋陽人。
章節試閱
﹝西夏孵化記﹞西元一○三三年,幾乎是李元昊的災年,一樣的父親去世,獨掌國政,他卻沒有感到半分快樂。從他登上党項之王的寶座時開始,他的榮耀就被兩條枷鎖壓得死死的──党項酋長的身分得由契丹人允許、宋朝人也允許,才能確認生效。契丹人還好說,怎麼講都是他名義上的外婆家,何況党項人世代相傳,契丹人神勇無敵,很習慣拿党項人的腦袋當球踢。於是問題就出在了宋朝人的身上,因為他們是那樣的富足、那樣的軟弱,還有那樣繁文縟節,超級囉唆。比如說,李德明去世,得有使者來,李元昊即位,仍然派來了使者。而且來了就是大爺,這些...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高天流雲
- 出版社: 知本家 出版日期:2009-11-09 ISBN/ISSN:978986731593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中國古典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