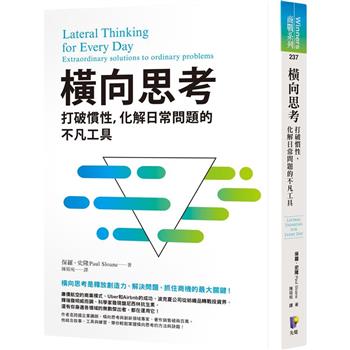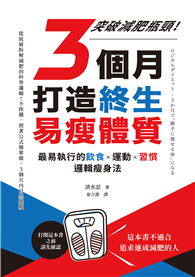序章‧催命契約
我相信等價交易的法則,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要獲得,便先懂得犧性。
誰不想出人頭地?誰不想衣食無憂?誰不想咬著金鎖匙出世?
但我可以怎樣?出身清貧之家,自小已經吃不夠、穿不暖。不想被人白眼,立心發奮讀書,付出比人多十倍努力去工作,但換來的,是無論如何努力、無論如何無私的付出,渴望賺得人緣、渴望賺得機會,最終擺出勝利者姿態的總不是我。
一次又一次為他人作嫁衣裳,一次又一次靠邊站地替人家高興,儘管臉上仍掛著輕鬆自若、彬彬有禮的笑容,嘴裡笑著說「不介意、沒相干」,心裡不斷說服自己絕對沒有懷才不遇這回事,但事實總歸事實,身邊的嘴臉告訴我,「沒用鬼、廢物」才是我的寫照。
一切,都只因我的出身不夠好,在所謂自由民主的社會下,早已被貼上不公平的標籤,自由民主個屁,根本充斥著階級性的醜陋歧視。
我忍受夠了!真的受夠了……
過往的我根本不會去想、不會去問、不……不會抱怨為什麼人家跟自己一樣考得留學資格,但硬只有我因為家境清貧被迫放棄機會。更不會抱怨為什麼辛辛苦苦考進專上學院取得優異成績畢業,就只因證書上印著不是一級學府的名銜,令我的名字在公司升職輪候排名榜上總是墊底。
是的,我從來都逆來順受。
直至那天,陰差陽錯下我聽到最要好的同事在茶水間跟上司說的一番話,我終於明白,自己的單純、愚昧簡直令人作嘔。
「誰叫他出身不好,能力高又如何?」這句話每一字每一語都深深地烙在心坎裡。
對……我是不識時務,不懂像人家一樣賣口乖、托大腿,更沒有多餘錢供上司吃喝消費。甚至,我還蠢得像盲頭烏蠅一樣學人去投資炒股,最終全副身家敗倒在八吋螢幕裡那一串串不能理解的數字和折線圖上。
但可以怎樣?連家人都說我是個沒出息的書呆子,你說……我還可以怎樣?
「你還有愛情吧!」
什麼?愛情?你說……你說我還有愛情?
別在我傷口上灑鹽吧!你看,我這顆自尊心已被撕裂得七零八落,你……你根本不會明白。
而我卻清楚得很,愛情是一場比現實更殘酷的遊戲,更是一場金錢角力的淘汰戰,海誓山盟也得要有溫飽……不!不只溫飽,還要有更多更多的享樂、禮物供應才成。
偏激?你嚐過給人家流著淚兒對你說:「我很愛你,但你給不了我經濟上的安全感,所以我無奈地要離開你。」然後多少個晚上,你自憐、自責,晚晚醉倒街頭,最後在某年某月某日某街頭,你再巧遇她,但她已不是你認識的舊情人。
眼前深深刺激視覺細胞的,是一部尊貴的寶馬跑車、一個LV手袋、一身Gucci 時裝,我不知那些是不是什麼闊太常掛嘴邊的限量版,但有一樣可以肯定,就是她們身邊確確實實都站著一個風度翩翩、有財有勢的年青才俊。
我還可以怨什麼?我有資格去怨嗎?
腦海中,她們那帶著媚態的拜金表情,對我簡直是最狠毒的恥笑,不止一次,是數次,分手的對話內容雖不盡相同,但其實始終還是一句:「你很窮!你配不起我!省點吧!」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我心裡仍然有恨,但恨的已經不再是她們,我恨自己出身不好,恨自已條件不夠,甚至,我恨老天爺連後天運氣也不給我,要我注定做一個窮人。
什麼莫欺少年窮……我說終須窮到褲穿窿,既然不曾擁有過什麼,未來亦不屬於我,我還在這世上幹什麼?我不要再受人白眼,不要貧死街頭,不要……我不要……
我清楚記得,在三支烈酒加一打啤酒的交叉化學作用下,那晚頭很痛,痛得我離魂似的,就在思緒最混亂,混亂得瀕臨崩潰的那晚,我終於緊緊抓著人生中唯一的機會。
那晚,半個身子已懸在七層樓高的唐樓天台外,只差一步就能踏上黃泉彼岸,突然間,不知哪裡飛來的一張看似破破落落的紙,令我失去平衡,二分之一的機會下把我推出鬼門關,跌落在天台的簷蓬上。
一陣暈眩後,我執起那張平白害我死不去的契約,終於發現,它不是契約……是契約,一張足以改變我一生的契約,它不單拯救我的生命,還挽救我的事業,就只需要一個簽名,便把我經年的不幸驅走。
「嘻嘻……來吧!」我記得,那把陰沉而帶誘惑的笑聲是如何吸引著我。
那是一個開始,到今天看來亦預告著終結。
「我當年有什麼錯?只要可以換回尊嚴、做個富翁,少少犧牲算得什麼?這是法則……是法則啊!這是等價交易的一部份,是契約的一部份。」我頹然地說,渾然不覺手上的煙已燒至盡頭,薰灼著手指的皮膚。
不知是否極泰來,還是那一紙契約的魔力,自那晚起,我便開始十年大運,數年間,我由一個店務助理,晉升為經理、分區經理,其後意外地得到一筆資金,再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名設計師佐敦,成功開拓一個以年青少女為主打的國際時裝品牌,數年間成為最年輕的上市公司老闆,更賺得人生第一個一億。
這陣子的好運要擋也擋不著,除了名譽、地位、金錢,我還巧取豪奪了有美艷親王之稱的亞洲影后藍鈴的芳心,一年後在數百萬電視觀眾的艷羨目光見證下娶得美人歸,作為一個男人,有車、有樓、有錢、有面、有女人,我夫復何求。
當一切都順風順水之時,我以為這才是開始,現在才是翻開人生最輝煌的第一章,殊不知,上天根本有心作弄我,太殘忍……對我太殘忍了。
我不會忘記那一天。
※※※※※※※※※※※※※
我記得,是恩庭三歲生日的那天,我跟太太早約好替愛女舉辦神秘生日會,而作為億萬富翁的我,這簡直是舉手之勞。
「有錢,還有什麼事辦不到?」這是我常掛嘴邊的一句話。
但沒想到,那刻,有錢根本毫無意思。
當晚八時,我坐上價值百萬的賓士房車,沿著慣常的路線駛回近郊的大屋,沒記錯的話,半小時前,我還跟太太通過電話,當時一切還安好的。
「是的,一切還是安好……」
我記得,離大屋還有不遠的路程,我享受一個人駕車的樂趣,而車速一直保持每小時七十公里,相信再過十五分鐘,就可以親親我那寶貝女兒。
想著想著,我不期然望向擋風玻璃左上方的月亮,今晚的月亮紅得帶點血褐色似的,望著、望著,腦海裡好像有些零碎的影像慢慢浮現,我好像忘記了些什麼,但又完全記不起……
「嗶嗶嗶……嗶嗶嗶……」車內的電話響起,我知道是誰打來的,因為只有我的太太才享有撥入這個車內直線電話的權利。
「喂……」
「嗄嗄……」
「喂……誰啊?是藍鈴嗎?」
「嗄嗄……嗄……萬家……救……咔……」還未弄清楚是什麼一回事前,電話已經掛斷了。
我好像隱約聽到自己的名字,還有「救」……但「救」什麼?莫非……不會的,我早請了三個保鏢長駐大屋保護妻女,根本不可能出事的。
車駛入大屋前的花園,我隨手關掉引擎,下車後望著大屋,一切看來都安然無恙,只是比平日靜,一點人聲、風聲、昆蟲聲也沒有。
「噠噠……噠噠噠……」
沿著花園的小徑走,我開始感到奇怪,雖然我說過今晚替愛女辦神秘生日會,但並沒下命令叫屋內的傭人全躲起來,可是由下車一直走到大屋門前,我完全沒遇上一個傭人。
「咔!」門鎖開了。
屋內漆黑一片,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詭異氣氛,好像……好像自我踏進屋內的第一步開始,我就與屋外的世界隔絕了,雖然眼前的一步一景、擺設都為我所熟悉,但心裡湧起的一陣疏離感,令我對眼前的種種都變得恍似陌生……好像全不屬於我。
不屬於我?為什麼不屬於我?這裡所有東西都是我辛辛苦苦賺回來的!有什麼可能不屬於我?
「吱吱……」
走過昏暗的走廊,我感覺被導引著走到二樓的尾房,那裡是愛女的睡房,我好像被什麼吸引著,又好像有什麼正期待著與我相遇……
站在房門外,我感到一陣濃烈的絕望感從門隙間滲透出來,一瞬間把我整個人籠罩,我的手不斷顫抖,但我知道,無論如何也要走進去。
「軋……」一陣刺耳的金屬磨擦聲。
門開了,但不是我打開的,是它徐徐地自動打開的。房內沒有燈光,我只靠窗外一絲微弱的白光辨認眼前的景像,我可以屏住呼吸不發出一點聲響,但不能控制心房劇烈的跳動聲。
房內的世界跟外面又截然不同,除了陌生、窒息的感覺外,這裡的死寂感,就好像整個空間被抽成真空似的,沒有接收到一點聲音,只有一股壓迫力在擠壓著耳膜,甚至身上所有感官細胞。
十數秒的時間,雙眼終於開始適應微弱的光線,我沒有停下,繼續前進,向著愛女睡床的方向走,因為床上隆起的一團東西正吸引著我。
「啪……」我感到肩膀碰到一些東西,而「它」好像正在自轉中。
我起初完全沒有細想那東西究竟是什麼,但焦慮不安的感覺瞬間填滿心頭。
「啊……藍鈴!」
我碰到的是藍鈴一雙冰凍的腿,她就吊在我的上方,一雙帶血絲的眼珠凸出,而舌頭在頸項肌肉的擠壓下長長地吐了出來。
她五官流著的濃血混合著舌頭上的唾液一滴一滴地滴在我的面上,我不記得當時自己究竟是被眼前的恐怖情景嚇得離魂,還是傷心得四肢發軟全身發麻,只知那刻軟癱在地上的我,根本壓根兒不知如何反應。
一個圈、兩個圈、三個圈、四個……五個……
我呆呆的望著藍鈴的屍首不斷逆時針地打轉,同時間,我渾然不覺床上那隆起的東西正朝我蠕動過來。
「沙沙……沙沙……」那東西愈來愈接近我。
終於,隨著一陣刺鼻的血腥味撲向我,我發現了「她」,她不是別人,她是我的愛女恩庭,但直覺告訴我,她不是平日活潑可愛的恩庭。
她究竟是誰?究竟發生什麼事?有誰可以告訴我?
我慌張得不斷後退,而渾身污血的她不斷向我迫近,她沒有像往日般叫我一聲爸爸,矇矓間我看到一件東西,是一張契約,恩庭染血的小手拿著一張似曾相識的契約。
不!不是什麼契約,是它……是那份契約!
我當時不及細想,只鼓起僅餘的力氣衝出這間充斥死亡氣息的大屋,直至登上屋前的賓士房車、發動引擎後,從倒後鏡再看不到那緊纏其後的身影,死亡的感覺才稍稍遠離我。
※※※※※※※※※※※※※
「什麼也沒有了……」我錯亂的思緒回到現在。
我隨手甩開腳下昨天的報章,那大大的標題已經對我判了死刑──「青年才俊發瘋失蹤‧一家十口慘遭滅門」。
我知道外面的警察正追緝著我,而那筆懸紅獎金亦引起黑幫小混混的興趣,但這些皆不足懼,我最怕的只有她……她手上的契約。
對,亦即是不知何時已出現在我眼前的一份染著黏稠稠濃血的契約。
「嘻嘻……嘻……」
契約的主人咬著手指向我笑,但我全然不作理會,只怔怔地望著眼前這份契約,在暗黃的紙質上,我依稀辨認出十五年前我的簽名。
「嘻嘻……嘻……」她一步一步向我走近。
「吼!夠了……」
瀕臨崩潰的我已對她猙獰的樣子感到麻木,因為我已經一無所有,而她要的就是這樣,我知道自己應該要怎麼做。
「是應約的時候,對不?你要的就是這樣。」
我緩緩地站起來,解下襯衫上的領帶,然後走到前方角落的一根粗大鋼筋前,結上一圈,把頭套入圈內,在人世間的最後一秒鐘,我再次把臉別過望著那手執契約的主人。
「……可否,不要難為她?」
說罷,我含恨縱身一躍,頸上肌肉一緊,下顎一鬆,沒帶一點痛苦便逐漸流失知覺。在逐糊的視線裡,我看到那份契約恍似有生命般的再次隨風飄盪,飄過我的跟前,向著露台的方向飄去。
我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向下溜,很輕、很不實在,終於,視線影像停留在那雙紅鞋上。我後悔,但奈何……
「咕嚕!」
「不!不要!」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嬰之契約:靈異出版社的圖書 |
 |
$ 45 ~ 194 | 嬰之契約:靈異出版社
作者:畢名 出版社: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9-06 語言:繁體書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3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嬰之契約:靈異出版社
一場以血脈進行的交易
償還時間——永遠
香港最鬼驚悚王者 畢名
寫破輪迴之卷
它是改變我一生的契約,不單拯救我的生命,還把我經年的不幸驅走。
簽下契約,便能讓你享盡成功滋味
只要支付無限的未來……
靈異檔案○○三:
「青年才俊發瘋失蹤‧一家十口慘遭滅門」
原該就此結束的事件,恐怖的怨念卻持續纏上倖存的人們
永無止盡的世代詛咒,居然來自……
……她梳著一個日本娃娃的髮型,穿著一身華麗的和服和一雙紅色小布鞋……舉起那隻白色的小手指向我,然後露出一個與天真外形格格不入的猙獰笑意……
作者簡介:
畢名
香港七十後驚慄小說作家,青少年創作推動者。歷經人情冷暖、體會人間善惡,立志執筆寫作,於2007至2010年間三度入選「十本好讀‧我最喜愛作家」候選名單,2008年憑《娃娃契約》打入「商務印書館」及「三聯書店」暢銷書榜,奠定香港驚慄小說地位。
2001年創辦青少年創作網站「原創空間」,翌年獲選為港台四大創作網站。曾任兩屆全港微型小說大賽評審,現為香港小說會創會會員。筆下小說世界,建構赤裸裸人性國度,喚醒埋藏內心深處的良知自覺。
著作十七本小說,有驚慄長篇《末殺者》、《沉淪者》、《殺性回歸》、《守護者》、《終結者》、《1414》、《娃娃契約》、《魔眼檔案》,恐怖短篇《恐怖潮》、《恐怖潮II──慘絕人寰》及其他五本科幻愛情合著小說。
官方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bedming
官方部落格:http://blog.yahoo.com/bzone
畢名電郵:bedming@yahoo.com.hk
章節試閱
序章‧催命契約
我相信等價交易的法則,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要獲得,便先懂得犧性。
誰不想出人頭地?誰不想衣食無憂?誰不想咬著金鎖匙出世?
但我可以怎樣?出身清貧之家,自小已經吃不夠、穿不暖。不想被人白眼,立心發奮讀書,付出比人多十倍努力去工作,但換來的,是無論如何努力、無論如何無私的付出,渴望賺得人緣、渴望賺得機會,最終擺出勝利者姿態的總不是我。
一次又一次為他人作嫁衣裳,一次又一次靠邊站地替人家高興,儘管臉上仍掛著輕鬆自若、彬彬有禮的笑容,嘴裡笑著說「不介意、沒相干」,心裡不斷說服自己絕對...
我相信等價交易的法則,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要獲得,便先懂得犧性。
誰不想出人頭地?誰不想衣食無憂?誰不想咬著金鎖匙出世?
但我可以怎樣?出身清貧之家,自小已經吃不夠、穿不暖。不想被人白眼,立心發奮讀書,付出比人多十倍努力去工作,但換來的,是無論如何努力、無論如何無私的付出,渴望賺得人緣、渴望賺得機會,最終擺出勝利者姿態的總不是我。
一次又一次為他人作嫁衣裳,一次又一次靠邊站地替人家高興,儘管臉上仍掛著輕鬆自若、彬彬有禮的笑容,嘴裡笑著說「不介意、沒相干」,心裡不斷說服自己絕對...
»看全部
目錄
序 章‧催命契約
第 一 章‧紅鞋
第 二 章‧作屍林
第 三 章‧蛇精現身
第 四 章‧痛失娃娃
第 五 章‧孽種
第 六 章‧神社
第 七 章‧童年詭夢
第 八 章‧錄影
第 九 章‧血祭檔案
第 十 章‧父女相逢
第十一章‧抉擇
第十二章‧前塵日記
終 章‧如是因,如是果
第 一 章‧紅鞋
第 二 章‧作屍林
第 三 章‧蛇精現身
第 四 章‧痛失娃娃
第 五 章‧孽種
第 六 章‧神社
第 七 章‧童年詭夢
第 八 章‧錄影
第 九 章‧血祭檔案
第 十 章‧父女相逢
第十一章‧抉擇
第十二章‧前塵日記
終 章‧如是因,如是果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畢名
- 出版社: 明日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9-06 ISBN/ISSN:978986290404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驚悚/懸疑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