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貢拜師﹞
正聊得起勁,不知不覺,吃中午飯的時間到了。蘧伯玉吩咐安排了簡單的午飯,招待眾人。
剛吃完飯,外面響起一陣車馬的喧囂聲。門開了,一個英俊瀟灑的年輕人從外面大步流星走進來。
「外公,我來看您了!」
來的年輕人正是蘧伯玉最喜愛的外孫子貢。子貢從幾年前接手了家族的生意,此番剛從吳國販玉回來。
「阿賜,你來得正好!」蘧伯玉叫著子貢的小名。子貢復姓端木,名賜。他的名字是有來歷的:在他出生的時候,母親夢見一個神人在雲端里托著一塊五彩的玉石送來,不久生下子貢,因此取名「賜」。
蘧伯玉招呼著子貢進來,讓他給孔子見禮。「阿賜,這就是我常給你講的魯國的聖人孔仲尼!」
「啊?原來是孔夫子駕到,失禮,失禮!」子貢從蘧伯玉口中聽說孔子的大名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因此,一驚之下,連忙上去磕頭見禮。
「快起來!」
孔子從他一進來,就一直在打量他。只見這個年輕人濃眉大眼,一雙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透著聰明伶俐。加上他是蘧伯玉的外孫,家教淵源、學問和道德自然是錯不了!孔子最喜愛的就是人才,一見子貢這等俊秀之才,鍾愛之情,溢於言表。
子貢起身後,在蘧伯玉的身邊落座,這才有機會認真打量孔子。只見孔子身材高大,面貌奇特,果然與凡夫俗子不同。尤其在他那一顆大腦袋里,不知道蘊藏了多少的智慧與深奧思想。
一瞬間,子貢忽然產生了一種爭強好勝的念頭,要測試一下孔子的學問到底有多深。他靈機一動,從懷裡掏出來一塊用錦帕包裹著的玉石。
「孔夫子請看,這是我從吳地重金收購來的一塊玉璧,叫做『蒼龍之壁』。小小一塊玉璧,竟然價值百金,不也太貴了嗎?」
「哦?」孔子輕輕接過玉璧,在手上觀賞了一會兒,說道,「我對於玉的鑒賞是個外行,不懂得它的市場價值。不過,我聽說,『蒼璧禮天』、『璧圓象日』,古代的人們在春季、秋季都要舉行『出日』和『入日』的祭祀日神的祭禮,用的就是這種玉璧。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無價的啊!」
「為甚麼人們對於玉看得很貴重,而對於珉(一種像玉的美石)卻看得很輕賤?僅僅是因為珉非常多,而玉卻非常稀有嗎?」
「不,君子『貴』玉,是認為玉有『德』!」
「哦?」子貢眼睛一亮,「願聞其詳!」
孔子喝了口茶,靜靜地整理了一下思緒,然後滔滔不絕地講起來。「君子認為,在玉的身上存在著和君子一樣的『德』。玉,內性溫潤,而外表散發出純正的光澤,這叫做『仁』;玉的質地細密而堅實,這叫做『智』;玉的稜角方正,而不傷害到人,這叫做『義』;玉的重量沈重而向下墜,這叫做『禮』;玉的敲擊聲音清脆而悠長,終了就戛然而止,這叫做『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這叫做『忠』;玉的氣質純潔而充滿光華,彷彿長虹貫日,這叫做『天』;玉的精神體現了山川的沈穩與內斂,這叫做『地』;玉制的圭、璋是用於禮儀上的,叫做『德』;因為玉有以上這九種『德』,天下沒有君子不尊重玉的德性,與自身的道德修煉相砥礪的,因此《詩》上說:『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君子能夠像做到像玉一樣擁有如此諸多的德性,就完美了!」
他這一番話,直聽得子貢目瞪口呆,汗水從額頭上涔涔而下。向來自負的子貢,第一次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素日裡外公蘧伯玉總批評他應該在學問之道上多下工夫,他還不服呢!
「哈哈,講得好,講得妙啊!」蘧伯玉雖然愛好收集玉器,藏有不少珍貴玉璧,但從未如孔子這般深思「玉德」,這才知道孔子在這些年里,學問和個人修養,一日千里,已經遠非自己可比。因此,老頭子捋著鬍鬚,哈哈大笑:「仲尼啊仲尼,從今以後, 我該尊你一聲『夫子』了!」
「哪裡,哪裡,不敢,不敢!」
孔子卻知道,自己在學問之道上也許有所超越蘧伯玉,但在治世之道上還要向蘧伯玉多多請教。
二人惺惺相惜一番,時候已經不早,孔子起身告辭。蘧伯玉堅持要輓著孔子的手,親自將他送出門。子貢以晚輩身份執禮,在前面替孔子將馬車趕過來,扶孔子登車安坐。蘧伯玉還在嘮嘮叨叨,囑咐著孔子甚麼,大意是既然來到衛國,就不要急著離開。如果在顏濁鄒那裡住夠了,就乾脆搬來和自己一起住。孔子再三感謝蘧伯玉的好意,二人才戀戀不捨地分開了。
子貢拜入孔門,和孔子探討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商品交換的基本規律:待價而沽。
價,是商品的價格。然而商品的價格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市場行情的漲跌在不斷地變化著。最好的商人,一定在商品的價格處於最高的時候賣出去,在處於最低的時候買進來。在一高一低之間進行交易,就會獲利無數,這就是中國最古老的「貨殖之術」。
子貢無疑是精於此道的,然而老師孔子的一番關於商品價值的論述,卻令他陷入了思索:就拿玉器來說,原來除了自身的產地、質地和紋理,還有內在道德上的附加價值。決定一件玉是否是稀世之物的根本,在於它是否有「德」。這是子貢從未聽說過的。
從這裡開始,子貢才意識到:原來一個好的商人,可以賦予商品以更高的價值;相反,一個不好的商人,卻坐擁稀世之珍而不自知,將其稀裡糊塗地當做尋常之物出售。只有商人自身的道德修養與商品的內在品質相得益彰,才能達到「貨殖之術」的最高境界…
【內文摘錄之二】
﹝子貢出馬﹞
孔子在魯國,得知齊國大兵壓境,知道以魯國的軍事實力,根本不可能獨自抗衡齊國,此事不得不救。
孔子立即將眾弟子召集起來,問眾人:「當今的情勢,已經十分危急。魯國是我們的父母之邦,埋骨之地,決不能眼睜睜看著魯國被齊國吞併。你們說說看,誰有辦法能阻止這場戰爭?」
眾弟子面面相覷,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情。如果沒有能力而硬要逞強,自己的安危姑且不說,造成魯國被齊國吞併的惡果,那可真是千秋罪人了!所以人人都在心裡反復思量,以圖良策。
年輕弟子中,子張是佼佼者。他從前在陳國的時候犯過罪,後來投身到孔子門下,深信孔子的「忠」「信」二字,將這兩個字繡在自己的腰帶上,不管每天走到什麼地方,都能隨時看到。
子張又是一位以勇力著名的弟子,主張一旦國家遇到危難,必須獻出自己的性命報效國家。
因此,子張今日一聽老師問,誰能救魯,他第一個就站了起來,大聲說: 「老師,請讓我去吧!」
「你有什麼辦法?」
「什麼辦法?大不了將我這條命獻出去,去和齊人拼了!」
「齊國有兵車千乘,你一條命,怎麼夠用?就是被碾成肉醬,也無濟於事,不過白白送死而已!」
子張被孔子這一番批評,臉漲得通紅,卻啞口無言,只能喘著粗氣坐下來,似乎頗為不服。
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是子石:「老師,讓我去!」
「哦?你有什麼辦法?」
「齊國的國政,不過在陳恒一人手中而已。弟子願意冒死去見陳恒,當面將其擊殺。陳恒一死,齊國必然退兵。」
「陳氏在齊國,羽翼早成,陳恒不過是他們族中的一個代表人物而已。陳恒死了,還有其他人。你總不能把陳氏一族都給滅了吧?何況還有國氏、高氏,他們一樣會挑起事端,來攻打我們。」
「這……」子石也啞口無言,只能默默地坐下了。
一時間,眾人都沉默著,屋子裡的空氣幾乎要令人窒息。孔子將目光投向了一直端坐凝思的子貢。
如果說,眾弟子中,有一個人能解決此問題,那麼也只有子貢了。當日在流浪途中,各自言志,子貢就提出自己的志向,是在魯國、齊國、吳國等交戰的時候,於兩軍陣前,以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令雙方化干戈為玉帛。如今,正該是子貢施展身手,兌現自己諾言的時候!
其實,子貢也知道,作為孔門的三大弟子,子路不在魯國,顏回體弱多病,此時此刻,只有自己能擔當大任。他所以不肯先發表看法,只不過是要給年輕的師弟以鍛煉和考驗的機會罷了!
見老師將目光投向自己,子貢不慌不忙地站起來:「老師,讓我去試一試吧!」
「好!」
孔子對前面的子張和子石,都詳細詢問他們有什麼化解危機之道。對於子貢,卻不聞不問,只說了一個「好」字。
而子貢呢,也沒有多作解釋。一得到老師的點頭允許,子貢立即一言不發,匆匆起身離去了。
子貢走後,眾弟子都奇怪地問孔子:「老師為什麼不問一問端木師兄,看他究竟有何良策?大夥也好出出主意。」
「不可,不可。」孔子卻神秘地微笑著搖了搖頭,「阿賜用什麼方法,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只要相信他就好了。」
對於老師孔子的這份信任,子貢自然不能不報以行動。當天夜裡,他就輕車簡從,奔向汶水。
經過一日一夜的急馳,子貢來到汶水。這一日一夜中,他將自己面見陳恒的說辭,想了無數遍。
雖然是兩國交戰在即,畢竟是孔子門下高足,子貢的聲名連陳恒也有所而聞。陳恒猜到子貢前來,必定是為魯國做說客而來,因此吩咐在軍帳內外設立了刀斧手,袒露胸背,手執刀斧,殺氣騰騰。
子貢一見這等陣勢,不過是微微一笑。他跟隨老師周遊列國,幾次遇險,那場面比這可危險多了。
因此,一入軍帳,見到陳恒,他立即冷笑道:「相國這陣勢,是對待來幫助相國之人的應有之禮嗎?」
「哦?你是來幫助我的?」陳恒一聽,疑惑不已,「難道你不是為魯國做說客而來?」
「誰說我是來替魯國做說客的?」子貢道,「我在魯國,接受的不過是季氏的俸祿,並未受魯侯之恩。再說了,我是個生意人。實不相瞞,我此次來見相國,是因為有一筆大生意要和相國談。」
「你是來和我談生意的?」
「正是。」子貢點頭道,「天下之人,為利而來,也為利而往。如果不是為了一個‘利’字,誰肯冒著刀斧之危,箭矢之險,在這戰事一觸即發的緊要關頭,跑到兩軍陣前來送死!」
「那倒是。」陳恒不由同意了他的說法。「可是我和先生,有什麼生意可談?」
「這就是我說要來幫助相國的原因。」子貢第一步目的,是先瓦解對方的高度戒備心理。出其不意攻陷了陳恒的心理防線,目的已經達到。於是他開始實施自己的第二步計畫,直指陳恒要害:
「相國這次來,不是真的要攻打魯國吧?」
「當然是真的。」陳恒信誓旦旦地道,「我在大王面前許了諾,此次不把魯國滅掉,絕不返回!」
「話雖如此,但我卻知道,相國的真正目標,一定不是魯國。」
「哦?何以見得?」
「顯而易見,魯國是『難伐之國』。沒有誰會傻到白白犧牲自己的兵力,去攻打一個『難伐之國』。」
「魯國有何難伐?」
「魯國的城牆矮小,國君昏庸,大臣無能,三軍將士,很久都沒有實際操練過,這就叫『難伐』。」
「那什麼叫做『易伐』?」
「像吳國那樣,城牆又高又厚,兵甲鋒利無比,君明臣賢,兵士作戰不知道畏懼,這就叫『易伐』。」
「這…豈非顛倒了麼?」陳恒更加糊塗了。不過,他畢竟是個聰明人,領悟到其中必有玄機。
「既然先生是來談生意的,就是朋友,不是敵人。來人呀,撤去刀斧,擺設宴席,給先生壓驚!」
等刀斧撤去,酒宴擺上,只剩下陳恒和子貢二人。陳恒才小聲問道:「不知道先生此來,以何教我?」
「我聽說:『憂在外者攻其弱,憂在內者攻其強』,這句話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在國內有憂患,對外用兵就要選擇強大的對手;如果在國外有憂患,用兵就要選擇弱小的對手。」子貢壓低了聲音說道,「如今,我所瞭解到的情況,是相國在齊國的內部,名義上是一國之相,其實處處被國、高二氏所掣肘,其情勢如同水火不能相容,這就叫做『憂在內』。相國自然也想到了,挾國君以令諸卿,令國、高二氏率兵出征。可是相國卻選擇了一個錯誤的對象──魯國。像魯國這麼弱小的國家,難道還值得齊國的大兵一擊嗎?如果國、高一戰而勝,那麼這份功勞就是國、高二氏的,跟相國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回去之後,恃功而傲,不是更將相國不放在眼中嗎?」
「啊?!」這個結局,的確是陳恒所沒有想到的,一下子,臉色大變,額頭上的汗水涔涔而下。
「所以說,正確的做法,不是來攻打魯國這樣的弱國,而是要去攻打吳國那樣的強國。和吳國作戰,其結果一定是失敗。國、高即使竭盡全力,也無法從和吳國的作戰中全身而退。到時候,心腹之患在外被吳國牽制,削弱實力,而相國在國內,就可以隨心所欲,難道這不是相國所想要的最好結果嗎?」
「先生說的實在太合我的心意了!」陳恒一下子被子貢說穿了內心最深處的秘密,不由臉上微紅。不過因為喝了酒的關係,看不出來怎樣。他警惕地看著四周,小聲對子貢道:「我的這點兒小小心事,既然已經被先生悉數洞知,還望先生替我保守秘密,不要被無關緊要之人知曉。」
「相國放心,我是個生意人,只知道對生意有利的事情,我就去做;對生意無利的事情,就不做。」
「對了,」陳恒聽他一口一個生意人,這才想起來他所說的『大生意』,問道,「你究竟和我談什麼生意?」
「很簡單。」子貢這才將底牌托出,「我要相國去告訴國、高二位將軍,就說得到可靠情報,說吳國聽說齊國進攻魯國,即將發兵來救。齊、吳之仇,甚於魯國。正可趁機以逸待勞,先敗吳國,再取魯國。這樣一來,幾萬大軍在這汶水彈丸之地,糧草用度必然巨大。我嘛,就在這糧草用度的供應上,做一點文章。這裡面的利潤,按照我做生意的規矩,相國六成,我四成!」
「不,我不需要那麼多。」陳恒一聽,立即擺手,「先生六成,我四成!」
「我的規矩是寧可生意不做,規矩不能破壞。如果相國不接受你六我四的分成,那就是壞了規矩!」
「既然如此,我拿出兩成,用作先生去吳國遊說的一應開銷,如何?」陳恒雖然貪財,卻並不糊塗。
「好,就這麼定了!」子貢的目的,就是要將齊國的軍隊暫時穩住,拖延在齊、魯兩國的邊境上,為自己贏得喘息之機。所謂生意云云,不過是他用以『釣』陳恒的『魚餌』。如今二人達成協議,目的達到,子貢立即動身,風塵僕僕地趕往吳國。陳恒則按照子貢教導的那樣,放出風去,只說吳國援軍將至,吩咐國、高二位將軍,不可輕舉妄動,單等吳軍一到,先敗吳軍,再取魯國。國、高二人不知是計,信以為真,果然匆忙去籌備了。陳恒則悠然回國,獨掌朝政去了。
【內文摘錄之三】
﹝陶朱公與子貢﹞
一轉眼,子貢在定陶授徒講學,已經三年了。三年之中,拜在子貢門下學習「商學」的,不計其數。
三年中,定陶的商業亦大為發展。因為這裡的商風純正,依靠一個「信」字聲名遠播,很多地方的商人都專程趕來這裡,一方面是跟子貢學習商業之道,一方面是依靠這裡的市場獲利。
然而,子貢又畢竟不是老師孔子,是個純粹以教書育人為至樂的聖人。子貢自己也不喜歡在一個地方長久地待下去。他年輕的時候跟隨孔子周遊列國,如今過了天命之年,忽然又起了去天下走一走、看一看的念頭。
於是,三年一滿,子貢立即宣佈關閉了講壇,讓自己的弟子們各自去從事商業經營的實踐...
子貢一回到自己府上,很快,眾弟子就趕來問候,各自彙報這三年來的經商成就,所思所悟。
一切都和子貢預料的一樣。眾弟子經過商業實踐,在商業之學上的學問進境,無不是一日千里。但也有一個令子貢想不到的消息:所有的弟子都提到一個人,他自稱「陶朱公」,是一個異常強勁的競爭對手。
「陶朱公?」
子貢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也不知道對方是怎樣的一個人。「你們說說,他是如何經商的?」
於是,眾弟子將自己所遭遇到的「陶朱公」一講,此人果然經營有方,生財有道,更重要的是,此人善於在市場競爭中使用謀略,而且對市場行情的預測異常準確,經常在這一年,就已經預知了下一年的市場情況,從而早作準備,一旦出現了商機,就毫不猶豫地出手,大賺一筆。
更令人稱奇的是,「陶朱公」並不將這些賺來的錢用於個人揮霍。相反,他的生活異常儉樸,從他的吃穿用度上,根本看不出來他是一個大商人。他為人低調,行事神秘,卻因為經常救濟窮苦之人,而深得百姓擁戴。以前人們經常口稱「端木公」是他們的大恩人,如今卻變成了「陶朱公」。子貢的弟子中有不服氣的,上門去和「陶朱公」辯論,卻無不灰頭土臉,大敗而歸。
子貢一聽,這個「陶朱公」竟然是如此莫測高深的一個人,頓時來了興趣。他暗想:「莫非此人是一位隱士?和我與老師周遊列國,所見到的那些隱士一樣?我倒要親自去會一會此人!」
子貢爭強好勝,這個毛病,孔子曾經批評過他很多次,可是子貢卻始終改不了。不過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如果真正遇到比自己有學問的人,就會心悅誠服地讚賞對方,以對方為師。可是,當今之世,能夠在學問之道上令子貢折服,能夠有資格擔當得起子貢老師的,又有幾人?
第二天,子貢迫不及待,在幾個弟子的引領下,來到了這位「陶朱公」的府上。這位「陶朱公」在定陶城外,購買了上千畝的山林,背山面水,將畜牧和水殖結合在一起,是一位實業家。
聽說子貢來訪,「陶朱公」不敢怠慢,親自出來迎接。二人一見面,就互相打量起對方來。
子貢眼中所見的這位「陶朱公」,衣著平常,頭髮微微有些花白,不過身材高大,腰背挺得筆直。子貢看人,先看人的眼睛。然而目光對接,卻從對方的目光裡,看不到任何的鋒芒。那種淡泊,那種內斂,仿佛大海一樣深不可測。只有經歷過人生的大風大浪,才能如此淡定!
而這位「陶朱公」,顯然也對子貢大感興趣。他顯然早聽說過子貢的大名,對子貢的所作所為,耳熟能詳。
「哎呀,原來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端木公!」他上來熱情洋溢地打著招呼,「早聽說端木公乃孔門第一高士,不但精通禮、樂,更兼自創了一套『商業之學』,蓋世無雙,今日登門,必有教我。」
「哪裡,哪裡,」子貢也謙遜道,「談不上什麼創造,不過多年貨殖經營,有所感悟而已。」
當下,進門之後,在廳堂之上,分賓主坐定。子貢和眾弟子這邊,人才薈萃,濟濟一堂;對面的「陶朱公」,卻只有一個人,看上去有些孤單。不過他似乎並不在乎這些,恭恭敬敬地請教:
「請問端木公,您所創造的『商業之學』,究竟是什麼?」
「很簡單,就是五個字而已:『信、義、智、禮、仁』。」子貢於是將自己的“商業之學”的內容,又簡單講了一遍。
「嗯,不錯,商以信立,以義取,以智識,以禮約,以仁成,講得實在太好了!」陶朱公頻頻點頭。
「那麼,先生又有何高論?」子貢反問。
「哦,我的商業之道,和端木公的學問不同。勉強說出來,請端木公指點。」陶朱公不像子貢那麼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是平心靜氣,不慌不忙地講出來一套道理:
「和端木公將商分為‘信、義、智、禮、仁’不同,我所認為的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定義的。」
「這個定義,可以歸結為三個字:天、地、人。」
「哦?」
「天,創生萬物,無欲無求。我聽說,『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不溢、不驕、不矜,這是天道的基本規律。」
「不溢,就是永遠保持在不滿盈的狀態。這一點端木公跟隨孔夫子身邊多年,當知道孔夫子曾經推崇一種『敧器』,當裡面的水少的時候,它是傾斜的;當裡面的水多的時候,它也是傾斜的;只有當水不多不少,保持平衡的時候,它才是端正的。對吧?」
「對。」
「所以,這就是天道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要永遠保持在一種不滿溢的狀態,處於虧損的狀態,商業經營將難以為繼;但如果處於滿溢的狀態,過多地積蓄,就變成了掠奪社會上的財富,就會遭到『反噬』。」
「『反噬』?」
「不錯。為什麼我們見到有那麼多的人痛恨商人,一提起商人來就咬牙切齒,斥為『奸商』,就因為他們不懂得,天下財寶,如水一樣流動,不能只停留在一個地方。如果水積蓄多了,必然會衝垮堤壩。到時候,就是想採取挽回的措施,也來不及了。我把這叫做『反噬』。」
「說得好!」
「不驕,是告誡人們,永遠都不要把自己一時的成就當做多麼了不起。沒有人可以單獨去做成一件事情,在你的成功的背後,一定有很多的人為你勞動,為你付出,甚至連上天都在暗中眷顧,賜予你機會。如果你不懂得這些,被愚蠢和自負遮蔽了雙眼,那麼敗亡是遲早的事情。
「對。」
「不矜,就是不貪功。天創造了萬物,卻並沒有因此而去表白自己是多麼有功勞。同樣,即使我們通過自己的勞動,做成了一些事情,創造了一些財富,那也不值得炫耀什麼,要永遠使自己像天一樣,保持一種虛空的狀態,只有這樣才會源源不斷產生新的催動的力量,生生不已。」
「講得太好了!」
「下面我再講一講地。」
「如果說,是天創造和催生了萬物,賦予了萬物以生生不息的力量,那麼地就是這萬物的容器,是這萬物的養育者。地,承載山川河流,草木五穀,給它們提供生長所需要的一切條件。不管是美好的事物,還是醜陋的事物,在它那裡都沒有任何的好惡,沒有任何的偏倚,這叫做『德』。」
「地之德,如果用一個字來概括,可以稱為『節』。天道持盈,損有餘以補不足,使得天下萬物,永遠保持在一個平衡而不滿溢的狀態,這是天的偉大;地德節事,如同水流一樣,水是天下最公正、最無私的。水永遠從高處流向低處,甘於居住天下最低的地方,而沒有任何怨言。水,沒有自己固定的形態,可以為涓涓細流,也可以為滔滔江河,可以滋潤禾苗,也可以摧毀山谷。水並不堅持什麼,並不表白什麼,然而卻讓天下萬物都能得到它所提供的『利』。」
「所以說,商之道,即是天道;商之德,即是地德,也可以叫做水德。士農工商,皆秉此德,天下就太平了!」
「下面我再說一說人。」
「人,是天和地共同作用,孕育而成的生命,是天下萬物的主宰。人,能根據天時,知道如何採取行動,也知道根據地德,如何使用自己的能力。人,懂得趨利,也懂得避害,這叫做『定』。」
「如何來做到『定』?就需要對天下事物發展,有一個明確而清晰的預測,可以在事情剛發生的時候,看出它最後的結局。也就是說,我們在秋天糧食豐收的時候,要想到來年春天的饑荒;在冬天乾旱寒冷的時候,要想到第二年夏天的洪水肆虐,從而修築堤壩,開挖溝渠,以作準備。」
「具體到商業經營上來說,這就叫做『積貯』。怎麼去做呢?當市場出現低迷的時候,就低價、大量吃進貨物;當市場高漲的時候,就高價、迅速地拋出貨物。因為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於賤;當賤到極點的時候,就會返於貴,所以說,要做到貴到極點時,貨物全部賣出去,視同糞土;當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當做珠寶一樣不要被競爭對手搶去,這叫『物極必反』…」
陶朱公還在繼續闡述他的關於『天地人』的商業之道,可是子貢卻已經聽不到了。子貢的頭腦中,正在浮現出當日老師給他講過的,去見老子的一幕:當時,孔子已經博學多識,可是,在老子面前,孔子卻發現自己的那一套學問,和對方根本沒法比,因此感歎老子『猶龍』也!
如今,子貢的感覺,這個「陶朱公」也好像「龍」一樣,見首不見尾,可是,子貢又堅信,這麼一個才智非凡的當世賢才,一定不會是無名之輩! 「陶朱公」一定不是他的真名,那麼,他會是誰呢?
這天,論道結束後,時候不早,「陶朱公」早吩咐準備了酒席,並且在酒席上,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叫出來,與子貢相見。
這兩個兒子姓范,卻並不姓「陶」正是從這一個「范」字上,子貢忽然領悟了什麼。
「哎呀,原來你就是…」
「噓——」
「陶朱公」卻止住了他,等眾人酒酣之際,「陶朱公」悄悄地將子貢喚離席上,進了裡面的密室。
「哈,我道『陶朱公』究竟是何方大賢?原來卻是那個幫助勾踐滅了吳國、功成身退的范大將軍!」
子貢一進入密室,立即揭穿了「陶朱公」就是范蠡的秘密。范蠡笑著承認,上前給子貢深施一禮:
「在下所以不用真名示人,實在有難言之隱,請端木公見諒!」
「當然,我能理解。」子貢道,「我不久前剛去過會稽,見過勾踐,他可是對你思念得緊哪!」
「是思念得緊,還是不放心得緊?」范蠡苦苦一笑,「我如果遲走一步,只怕就和文種兄一樣的下場!」...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孔子最會賺錢的學生:端木子貢 儒商祖師的圖書 |
 |
$ 298 ~ 350 | 孔子最會賺錢的學生:端木子貢 儒商祖師
作者:安之忠,林鋒 出版社: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4-07-14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84頁 / 14.85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端木
端木姓為中國複姓,此姓相當得古老,自東周時期便有了。據元和姓纂記載,端木一姓的祖宗為孔子弟子端木賜,系出於衞國。端木姓分布相當的廣,但後來大多改姓為端姓、木姓、沐姓,故今日已不多見。
據《端木氏家譜》《祖德性譜》載:鬻熊生二子,長子熊麗,次子端木。端木生典,典以父名為姓,名端木典,這是端木得姓之始祖。其後幾世斷紀。西周末,有端木典後裔端木舒,仍仕於周,隨周平王東遷。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孔子最會賺錢的學生:端木子貢 儒商祖師
孔子門下七十二賢人,端木子貢並非最得意之人,卻一定是最圓滿之人。
子貢出生於衛國君子世家,從小立志要做一名「君子」。
商人,是唯利是圖的「小人」,所關心的是利益;「君子」所關心的卻是
道德修養。那麼,有沒有一條中間的調和道路呢?子貢在外公蘧伯玉那裡沒有找到答案。帶著這個問題,他做了孔子的一名學生。
孔子其他的學生,或者「謀糧」從政以走仕途,如冉有;或者「謀道」
從學以增益道德,如嚴回;或者單純為了忠誠於孔子、和孔子的師生之誼以作陪伴,如子路...每個人都各有目的,但只有子貢的目的最與眾不同:他
要從孔子這裡學習和領悟儒學的最高之道──「仁」的精髓,並且將其借
鑒,用來改造「商」,最終提升「商」...
子貢創造性地完成了「儒」與「商」的結合,提出「義利合一」,並且開啟了「儒商」先河。
作者簡介:
安之忠
‧著名企業家,文學愛好者。
‧貴州雙龍集團創始人。
‧現任中國商業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民營企業家協會副會長、貴州省
商會副會長等。
林 鋒
‧作家、曾就讀魯迅文學院創作專業。
‧作品以長篇歷史小說為主,代表作有《蒼狼秘史》(全三部)、《曹雪芹家族》(上中下)、《鄭芝龍海商傳奇》等。
章節試閱
﹝子貢拜師﹞
正聊得起勁,不知不覺,吃中午飯的時間到了。蘧伯玉吩咐安排了簡單的午飯,招待眾人。
剛吃完飯,外面響起一陣車馬的喧囂聲。門開了,一個英俊瀟灑的年輕人從外面大步流星走進來。
「外公,我來看您了!」
來的年輕人正是蘧伯玉最喜愛的外孫子貢。子貢從幾年前接手了家族的生意,此番剛從吳國販玉回來。
「阿賜,你來得正好!」蘧伯玉叫著子貢的小名。子貢復姓端木,名賜。他的名字是有來歷的:在他出生的時候,母親夢見一個神人在雲端里托著一塊五彩的玉石送來,不久生下子貢,因此取名「賜」。
...
正聊得起勁,不知不覺,吃中午飯的時間到了。蘧伯玉吩咐安排了簡單的午飯,招待眾人。
剛吃完飯,外面響起一陣車馬的喧囂聲。門開了,一個英俊瀟灑的年輕人從外面大步流星走進來。
「外公,我來看您了!」
來的年輕人正是蘧伯玉最喜愛的外孫子貢。子貢從幾年前接手了家族的生意,此番剛從吳國販玉回來。
「阿賜,你來得正好!」蘧伯玉叫著子貢的小名。子貢復姓端木,名賜。他的名字是有來歷的:在他出生的時候,母親夢見一個神人在雲端里托著一塊五彩的玉石送來,不久生下子貢,因此取名「賜」。
...
»看全部
目錄
第1章 孔子適衛 005
第2章 子貢拜師 025
第3章 風波陡起 065
第4章 匡蒲之難 065
第5章 刀劍之盟 091
第 6 章 子貢觀禮 118
第 7 章 顛沛流離 137
第 8 章 喪家之犬 154
第 9 章 陳蔡絕糧 175
第10 章 孔子歸魯 197
第11 章 子貢出馬 217
第12 章 三寸不爛 235
第13 章 孔子之死 250
第 14 章 守喪歲月 267
第15 章 父子入齊 283
第16 章 義利之分 303
第17 章 天命有歸 319
第18 章 定陶授徒 331
第19 章 範蠡論道 347
第 20 章 子貢卒齊 366 ...
第2章 子貢拜師 025
第3章 風波陡起 065
第4章 匡蒲之難 065
第5章 刀劍之盟 091
第 6 章 子貢觀禮 118
第 7 章 顛沛流離 137
第 8 章 喪家之犬 154
第 9 章 陳蔡絕糧 175
第10 章 孔子歸魯 197
第11 章 子貢出馬 217
第12 章 三寸不爛 235
第13 章 孔子之死 250
第 14 章 守喪歲月 267
第15 章 父子入齊 283
第16 章 義利之分 303
第17 章 天命有歸 319
第18 章 定陶授徒 331
第19 章 範蠡論道 347
第 20 章 子貢卒齊 366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安之忠、林鋒
- 出版社: 知本家 出版日期:2014-07-16 ISBN/ISSN:978986622355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4頁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中國哲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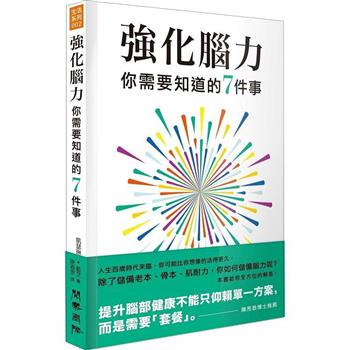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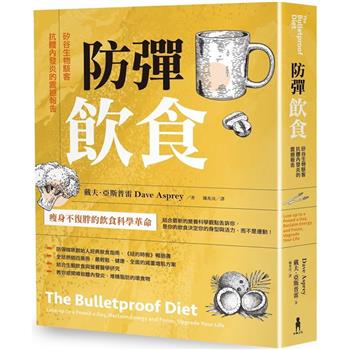





![114年超好用大法官釋字+憲法訴訟裁判(含精選題庫)[警察特考] 114年超好用大法官釋字+憲法訴訟裁判(含精選題庫)[警察特考]](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184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