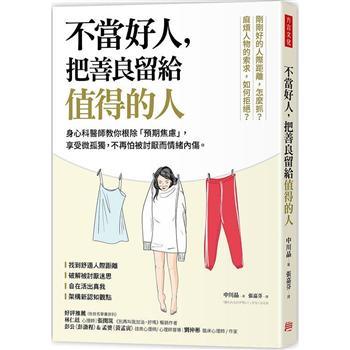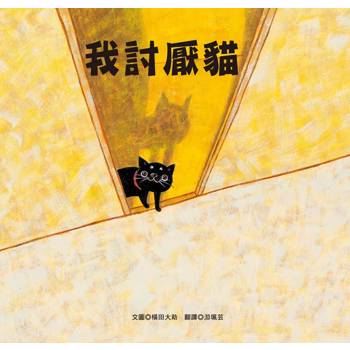《孫中山新探》為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先生“近代史研究六種”之一, 收錄了楊先生多年來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論文、學術札記、演講報告與訪談錄。由於領導辛亥革命、創建民國是孫中山一生的最大業績,有關文章一併收錄於此。所論多與時賢不同,故稱新探。
研究本國歷史只能從本國的歷史實際出發,而不能從先驗的、既定的原則出發,更不能生吞活剝地搬用或變相搬用外國歷史和基於其上的結論。本書提出了若干新看法,如近代中國新型知識份子與“共和知識份子”的形成;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共和知識份子”;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與兩次“倒孫風潮”的成因;辛亥革命勝利迅速、代價很小,其失敗的主因在於財政困難,而非通常所謂“資產階級軟弱性”;等等。都與史學界長期流行的說法不同。這些看法均基於中國歷史實際,其中部分觀點受過經典作家啟發,非離經叛道之論,而是實事求是、認真獨立思考的結果。
學術的發展、進步、繁榮有賴於百家爭鳴,《孫中山新探》以扎實的史料、求真的精神、卓然的創見,展示出楊先生治史的學術風貌,意在為爭鳴之助,推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孫中山新探的圖書 |
 |
$ 504 ~ 760 | 孫中山新探
作者:楊天石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2-27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孫中山
 孫中山,名孫文,幼名帝象,譜名德明,字明德、載之,號逸仙、日新。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2936,故稱孫中山,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祖籍廣東東莞。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與革命家,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和締造者,亦是三民主義的提出者和倡導者。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與開拓者,是辛亥革命的發起者與領導者。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在大中華地區及華人地區被普遍尊稱為「國父」。
孫中山,名孫文,幼名帝象,譜名德明,字明德、載之,號逸仙、日新。流亡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2936,故稱孫中山,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祖籍廣東東莞。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與革命家,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創始人和締造者,亦是三民主義的提出者和倡導者。孫中山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與開拓者,是辛亥革命的發起者與領導者。他對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在大中華地區及華人地區被普遍尊稱為「國父」。 幼年時曾受有關太平天國故事的影響而產生對反清人士的興趣。青年時因中法戰爭的失敗和清朝的腐敗無能而產生反清思想,並決定要以革命的方式改變中國。:52。1894年11月24日,孫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52。1895年,興中會發動乙未廣州起義:53。1905年,在日本東京組成中國同盟會,孫被推為總理:2936;確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並提出三民主義學說:2936。1911年12月29日,被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推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未經過南北政府一致同意),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就職,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2936。1919年,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2936。1940年4月,國民政府明令尊稱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國民黨永久保留其於黨內的「總理」職銜。中國共產黨尊其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2936。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孫中山新探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楊天石
1936年出生於江蘇興化。1955年畢業於無錫市第一中學。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顧問、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中華書畫家》雜誌顧問、上海《世紀》雜誌顧問、廣東《同舟共進》雜誌編委。中央文史研究館34卷本叢書《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副主編之一。曾任中國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為《中國文化詞典》副主編之一。
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民國史、國民黨史。合著有《中國通史》第12冊,《中華民國史》第1卷、第6卷等。個人著作有《楊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揭開民國史真相》(7卷本)、《楊天石文集》、《尋求歷史的謎底:近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近代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朱熹及其哲學》、《朱熹》、《朱熹:孔子之後第一儒》、《王陽明》、《泰州學派》、《南社史三種》、《半新半舊齋詩選》、《橫生斜長集》等。主編有《〈百年潮〉精品系列》(12卷)、《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4卷)等。
參與寫作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獲國家圖書獎榮譽獎。個人著作《尋求歷史的謎底》獲國家教委所屬高校出版社及北京市優秀學術著作獎。《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1輯獲全國31家媒體及圖書評論家協會十大圖書獎以及香港十大好書獎,第2輯獲南方讀書節最受讀者關注的歷史著作獎,第3輯及第4輯獲《亞洲週刊》十大好書獎。楊天石著作所獲的獎勵還有孫中山學術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學術著作獎等。《帝制的終結》獲《新京報》2011年度好書獎,是當年該報獎勵的唯一歷史圖書。
楊天石
1936年出生於江蘇興化。1955年畢業於無錫市第一中學。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顧問、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中華書畫家》雜誌顧問、上海《世紀》雜誌顧問、廣東《同舟共進》雜誌編委。中央文史研究館34卷本叢書《中國地域文化通覽》副主編之一。曾任中國文化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為《中國文化詞典》副主編之一。
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中國近代史、民國史、國民黨史。合著有《中國通史》第12冊,《中華民國史》第1卷、第6卷等。個人著作有《楊天石近代史文存》(5卷本)、《揭開民國史真相》(7卷本)、《楊天石文集》、《尋求歷史的謎底:近代中國的政治與人物》、《近代中國史事鉤沉:海外訪史錄》、《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朱熹及其哲學》、《朱熹》、《朱熹:孔子之後第一儒》、《王陽明》、《泰州學派》、《南社史三種》、《半新半舊齋詩選》、《橫生斜長集》等。主編有《〈百年潮〉精品系列》(12卷)、《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4卷)等。
參與寫作的多卷本《中華民國史》獲國家圖書獎榮譽獎。個人著作《尋求歷史的謎底》獲國家教委所屬高校出版社及北京市優秀學術著作獎。《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第1輯獲全國31家媒體及圖書評論家協會十大圖書獎以及香港十大好書獎,第2輯獲南方讀書節最受讀者關注的歷史著作獎,第3輯及第4輯獲《亞洲週刊》十大好書獎。楊天石著作所獲的獎勵還有孫中山學術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學術著作獎等。《帝制的終結》獲《新京報》2011年度好書獎,是當年該報獎勵的唯一歷史圖書。
目錄
序言/ 王傑 自序/楊天石
第一部分 ——
孫中山思想研究 001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前途——兼論清末民初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批評 002 孫中山與資本主義——2011年11月在新加坡孫中山國際討論會上的報告 022 “取那善果,避那惡果——”略論孫中山對現代文明的辯證態度 037 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40週年 042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及其當代價值——2011年9月24日在國家圖書館
“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上的報告 052 孫中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為用”思想
——答《同舟共進》特約記者葦一 072 孫中山的社會選擇與百年中國的發展道路
——在維也納大學“辛亥革命與20世紀中國”討論會的報告提綱 081 “天下為公”:孫中山的偉大思想遺產
——在海峽兩岸“孫逸仙思想與儒家人文精神”學術研討會的發言 086
孫中山的公僕意識 090
國家統一,孫中山奮鬥的偉大目標 094
第二部分 ——
同盟會和革命黨人的內部矛盾 101
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 102
《龍華會章程》主屬考 133 章太炎與端方關係考析 141 附:朱維錚《致楊天石論章太炎與端方關係函》 154 劉師培舉報章太炎 157 劉師培舉報章太炎引起的風波 160 劉師培舉報章太炎引起的風波的餘波 163 何震揭發章太炎——北美訪報之一 167 《民報》的續刊及其爭論——南洋訪報錄 172
第三部分 ——
辛亥革命研究 191 辛亥革命何以勝利迅速,代價很小? 192 誰領導辛亥革命——在美國哈佛大學辛亥革命百年論壇閉幕式的演講 212 清朝貴族反對根本改革,辛亥革命是“逼”出來的
——2011年3月16日答馬國川 221
第四部分 ——
財政困難與孫中山讓位袁世凱 235 在華經濟利益與辛亥革命時期英國的對華政策 236 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輪船招商局借款
——兼論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與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251
華俄道勝銀行借款案與南京臨時政府危機 267
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 273
第五部分 ——
辛亥革命之後的孫中山 287
為“二次革命”答新浪網記者譚文娟問 288
“真革命黨員”抨擊黃興等人的一份傳單 293
跋鍾鼎與孫中山斷絕關係書——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300
何天炯與孫中山——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309
鄧恢宇與宮崎滔天夫婦——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326
孫中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香港浸會大學、樹仁大學國際討論會的演講 346
第六部分 ——
晚年孫中山 367
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改組 368
關於孫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376
第七部分 ——
檔案、函札所見孫中山 393
犬養毅紀念館所見孫中山手跡——日本岡山訪問所得之一 394
孫中山秘密赴滬時的筆談——讀日本外務省檔案 397
孫中山在1900年——讀日本外務省檔案札記 399
跋孫中山在檀香山的幾次談話——讀日本外務省檔案 406
跋日本政府有關惠州起義的電報——讀日本外務省檔案 415
清政府乞求日本驅逐孫中山 420
孫中山的一次北京未遂之行——讀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段祺瑞函 422
宋嘉樹與孫中山、宋慶齡的婚姻——讀宋嘉樹復孫中山英文函 425
孫中山與田中義一——讀日本山口縣文書館檔案 435
讀孫中山致紐約銀行家佚札 438
新發現的《孫中山致國民黨諸先生函》 443
孫中山致山縣有朋函二通—讀日本山縣有朋文書 445
第八部分 ——
筆談與採訪 449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張磊、陳勝粦、楊天石 450
為孫中山研究質疑答鳳凰網記者張弘問 457
答《孫中山研究口述史》胡波、趙軍問 468
第九部分 ——
附錄 495
辛亥革命(中國大百科全書條目) 496
南洋革命黨人宣佈孫文罪狀傳單 507
請看章炳麟宣佈孫汶罪狀書 514
陶成章《佈告各同志書》 517
第一部分 ——
孫中山思想研究 001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前途——兼論清末民初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批評 002 孫中山與資本主義——2011年11月在新加坡孫中山國際討論會上的報告 022 “取那善果,避那惡果——”略論孫中山對現代文明的辯證態度 037 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40週年 042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及其當代價值——2011年9月24日在國家圖書館
“部級領導幹部歷史文化講座”上的報告 052 孫中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互相為用”思想
——答《同舟共進》特約記者葦一 072 孫中山的社會選擇與百年中國的發展道路
——在維也納大學“辛亥革命與20世紀中國”討論會的報告提綱 081 “天下為公”:孫中山的偉大思想遺產
——在海峽兩岸“孫逸仙思想與儒家人文精神”學術研討會的發言 086
孫中山的公僕意識 090
國家統一,孫中山奮鬥的偉大目標 094
第二部分 ——
同盟會和革命黨人的內部矛盾 101
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 102
《龍華會章程》主屬考 133 章太炎與端方關係考析 141 附:朱維錚《致楊天石論章太炎與端方關係函》 154 劉師培舉報章太炎 157 劉師培舉報章太炎引起的風波 160 劉師培舉報章太炎引起的風波的餘波 163 何震揭發章太炎——北美訪報之一 167 《民報》的續刊及其爭論——南洋訪報錄 172
第三部分 ——
辛亥革命研究 191 辛亥革命何以勝利迅速,代價很小? 192 誰領導辛亥革命——在美國哈佛大學辛亥革命百年論壇閉幕式的演講 212 清朝貴族反對根本改革,辛亥革命是“逼”出來的
——2011年3月16日答馬國川 221
第四部分 ——
財政困難與孫中山讓位袁世凱 235 在華經濟利益與辛亥革命時期英國的對華政策 236 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輪船招商局借款
——兼論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與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251
華俄道勝銀行借款案與南京臨時政府危機 267
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 273
第五部分 ——
辛亥革命之後的孫中山 287
為“二次革命”答新浪網記者譚文娟問 288
“真革命黨員”抨擊黃興等人的一份傳單 293
跋鍾鼎與孫中山斷絕關係書——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300
何天炯與孫中山——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309
鄧恢宇與宮崎滔天夫婦——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326
孫中山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香港浸會大學、樹仁大學國際討論會的演講 346
第六部分 ——
晚年孫中山 367
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改組 368
關於孫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376
第七部分 ——
檔案、函札所見孫中山 393
犬養毅紀念館所見孫中山手跡——日本岡山訪問所得之一 394
孫中山秘密赴滬時的筆談——讀日本外務省檔案 397
孫中山在1900年——讀日本外務省檔案札記 399
跋孫中山在檀香山的幾次談話——讀日本外務省檔案 406
跋日本政府有關惠州起義的電報——讀日本外務省檔案 415
清政府乞求日本驅逐孫中山 420
孫中山的一次北京未遂之行——讀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段祺瑞函 422
宋嘉樹與孫中山、宋慶齡的婚姻——讀宋嘉樹復孫中山英文函 425
孫中山與田中義一——讀日本山口縣文書館檔案 435
讀孫中山致紐約銀行家佚札 438
新發現的《孫中山致國民黨諸先生函》 443
孫中山致山縣有朋函二通—讀日本山縣有朋文書 445
第八部分 ——
筆談與採訪 449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張磊、陳勝粦、楊天石 450
為孫中山研究質疑答鳳凰網記者張弘問 457
答《孫中山研究口述史》胡波、趙軍問 468
第九部分 ——
附錄 495
辛亥革命(中國大百科全書條目) 496
南洋革命黨人宣佈孫文罪狀傳單 507
請看章炳麟宣佈孫汶罪狀書 514
陶成章《佈告各同志書》 517
序
序言
荷雨時節, E 從天降,楊公函囑為其大著《孫中山新探》寫序。驚惶之餘,復信連連求饒。公以本人“長期擔任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是為拙書寫序的非常合適的人選”相勸,經“協商”,則以公獎掖晚輩,扶持後生為慰,權以撰述懷憶或感獲一類的文字應允下來。
楊公著作等身,乃知名的孫中山研究專家。我們於 1978 年在近代史研究所相識,迄今四十餘年。是時,我出道未幾,公正值年富力強。因參加國家“六五”規劃重點項目《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版)的編輯,本人所在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是合作單位,由此,得享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之“近水樓台”,借書、食宿,有幸與公同一棟樓。往事如煙,追憶依然。於孫中山研究領域,楊公有志竟成,其成就之秘訣,可簡括為六個字,曰:勤奮、求真、創見 —這是我粗略的體會,亦為本人受益終身之信條。
勤奮乃成功之基石。近代史所的藏書,勝似寶藏,浩如煙海。楊公的勤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客居近代史所,斷續不下一年半,印象最深刻的,不管是圖書館,還是辦公室(可將舊報借回),都可看到楊公翻閱書報與寫作的身影。記憶猶新者,他對報紙中的廣告頁,翻得特別快,蓋因習慣成自然了。一旦發現心儀的史料,便埋頭抄錄於卡片中(那時無電腦)。每每從他的門口走過,半開的房間總是看到他讀作的神韻,這對我這位初出茅廬的求知者來說,委實是“言傳”不如“身教”了。十多年前,我到北京參加研討,有意重溫舊夢,某星期日,深夜十一時,幾位同仁往所裏走,電梯已關,碰見楊公抱著一大疊書在爬樓梯,七十多歲的學者,以所為家,於夜色蒼茫中負書上行,其勤其奮之形象,深印於我的腦海。聰明出於勤奮,治學呵護冷板,難能可貴啊!楊公幾十年如一日,專心學問,其砥礪之精神,令人感佩有加。
史料有如史學之磐石,亦賴勤奮之功經營。史學即史料學,欠缺史料,史學就會變成空泛的說教;言中有物,論從史出,才是治史之要義。前賢早有言曰,南京大學教授韓儒林先生撰過家喻戶曉之一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楊公堪稱典範,所撰著述,既以史料為基底,又以新見史料見長。以《新探》為例,撇開書刊不論,僅引用的報紙(不含《民報》、《新民叢報》等)就有:《大共和日報》、《獨立週報》、《神州日報》、《申報》、《民聲日報》、《民志日報》、《大漢報》、《大公報》、《民立報》、《民權報》、《天鐸報》(上海)、《民主報》(北京)、《國民公報》、《中華民報》、《燕京時報》、《衡報》、《天義報》、《蘇報》、《少年中國晨報》、《新世紀》、《越鐸日報》、《中興報》、《中國旬報》、《香港華字日報》、《南洋總匯新報》、《星洲晨報》、《廣州民國日報》、《高知新聞》(日本)、《日新報》(加拿大)等三十種,還有《朱希祖日記》(稿本)、陶冶公《無政府主義思想對同盟會的影響》(未刊稿)、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未刊稿,陶冶公原藏)等;翻閱“檔案、函札所見孫中山”一章,不乏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台北“國史館”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宮崎滔天家藏書札、日本山口縣文書館檔案等資料,均為史料中之乾貨!其“上窮碧落下黃泉”之功力,可見一斑。尤須多書一筆的是,書末附錄《孫文罪狀》、《偽〈民報〉檢舉狀》、《佈告同志書》等三份文件,均係同盟會發生“倒孫風潮”的文獻,或發表於當年的海外報紙,或深藏於海外的檔案館,除《偽〈民報〉檢舉狀》外,今天已很難見到。楊公視史料為生命,卻把罕見史料和盤托出供學界共用,嘉惠士林,精神可佩!
史學有獨立的品格,史家有獨特的人格,楊公的“格”定位於求真。舉凡《新探》文字,無時無刻不在展示楊公求真的樣態。關於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楊公認為,孫中山並不將資本主義視為垂死的、沒落、腐朽、應該打倒、消滅的生產方式,也並不將它視為與社會主義格格不能相容的敵對力量,而是仍然視為推進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經濟能力”,主張調和兩者,使之“互相為用”,共同促進人類的文明發展。所謂“互相為用”,那意思是說:
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可以利用社會主義,相互借鑒、相互吸取,人類社會因而得以前進、發展。這是一種充滿辯證思想的遠見卓識。可惜,孫中山並未展開充分論述,但是,人類歷史的發展經已證明並將進一步證實這一認識的偉大意義。楊公對孫中山關於資本主義的把握,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光點。
求真,乃是對實事求是精神的弘揚。關於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楊公指出,孫中山曾對馬克思主義做過批評。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進行過多方面的、嚴厲無情的批判。孫中山也曾嚴厲批判資本主義剝削,批判資本家的缺乏道德,他將馬克思所分析的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手段歸納為三種:一是減少工人的工資,二是延長工人做工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但是,孫中山根據 20 世紀 20 年代的社會現實,對馬克思的有關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以美國福特汽車工廠為例說: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做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做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孫中山認為以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馬克思一點都沒有料到。這其實都是孫中山研究中的前沿問題和最敏感的話題了。
良史,須憑史識,必有“求義”。楊公將“歷史學家要對歷史負責”作為治學的座右銘,道出了良史的心聲。《新探》關於《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輪船招商局借款——兼論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與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一文,一改前人和時人將辛亥革命的失敗簡單地歸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的成說,以事實為基礎,圍繞孫中山的困難問題展開闡述,把孫中山的財政困難講得很清楚,從而拋棄政治概念的套路,到目前為止,仍未見對該文提出的質疑。又,關於
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與兩次“倒孫風潮”的論述,楊文強調既與日本社會黨人內部軟硬兩派的分裂有關,也有同盟會自身的原因等等。舉凡,揚葩吐豔,各極其致,學界遂蒙絕大之受益。
學問的靈魂在於閃光,學術的生命重於創見。業師章開沅先生說:“史魂即史德,用現代話語來表達,就是這個學科固有的獨立品格。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是以史學為志業者必須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史學尋找自己》,《實齋筆記》第 309 頁)應該指出,《新探》主人畢生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箴言作為研究學術的最高理想,努力踐行“獨立的學術人格”,卓然成家,提出了不少創見,如近代中國新型知識份子與“共和知識份子”的形成;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共和知識份子”等。尤其特別指出的是,他強調孫中山指斥近世“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冀望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政權,因此提出,與其說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如更準確地說他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或“平民革命家”。從百家爭鳴的視角說,這是楊公與其他學者的不同見解,堪稱一大創見。
多年以來,學人一直把孫中山定位在資產階級革命家。這無疑牽涉到孫中山階級定性的問題。楊公倡說孫中山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並在《孫中山研究口述史》中列舉了七大依據:
一、於家庭經濟狀況言,孫中山出身貧苦,其兄孫眉雖一度為海外農場主,但因支持革命而毀家紓難,迅速破產且困居於香港的茅草棚,故而,將孫中山劃歸資產階級群體中缺乏充分的理由。二、從孫中山的支持群體(階級基礎)言,並未有多少資產階級在支持他: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多支持立憲派;革命後又多投靠袁世凱。“二次革命”時明確支持孫中山的資產階級寥寥可數;廣東作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又是孫中山故里,但是,廣東的資產階級都是站在孫中山的對立面,擁護孫氏的著實少見。三、從孫中山思想維度看,把孫中山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家好像更沒有道理。在近代革命家中,孫中山最早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痛罵資本主義,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痛罵資本家沒有道德良心、唯利是圖的言論還有很多,而且是最早宣稱中國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老路的人。四、就中國國家制度選擇言,孫中山肯定施行民主共和制度,嚴正指出“英美立憲,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從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上全面批判和否定了西方資本主義,明確提出不能對西方亦步亦趨,要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創建中國民主制度,這是孫中山創造“五權分立”思想及實行五院並立制度的根本原因。五、對待社會主義態度言,孫中山於 1903 年就表達過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將“民生主義”直接和“社會主義”對等翻譯就是直接體現; 1905 年,孫中山在比利時向國際社會黨(第二國際)執行局申請,要求接納他正在組織的政黨,其所彙報的黨綱中稱,要使“工人階級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1915年 11 月,孫中山再次致函國際社會黨執行局,要求提供人才,協助自己將“中國建立成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見,孫中山是中國最早表示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和追求的一位革命家,把這樣一個人說成是資產階級,拿不出道理來。六、就中華民國頒佈的綱領政策看,均未鼓勵發展資本主義。翻查南京臨時政府的命令、條令,並沒有多少是鼓勵資本主義發展。而相比於晚清政府的新政,則是大力扶持資本家,並根據資本家的投資封官封爵,鼓勵發展資本主義。相反,南京臨時政府所頒佈的政策法律頂多是些空洞的發展實業詞語,絕對沒有達到晚清新政的那種高度和力度。所以,相比較之下,把孫中山說成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不對的。七、就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而言,康梁以“保商”為根本追求,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抵抗外資,認為保護資本家是第一要務。康梁派特別是梁啟超,是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和利益代表者。而革命黨則並不如此,革命黨主張社會革命,主張發展國家資本,發展國營企業,這與資產階級價值追求和利益保障明顯有所差距。
創見可以喻為史學的玉石,乃學人智慧的迸發、創新的結晶。楊公此文,初以《孫中山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家》為題,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 2001 年第6 期,後易題為《孫中山應是“平民革命家”》摘要轉載於 2001 年 9 月 17 日《北京日報》。(參見《孫中山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收入《哲人與文士》,見《楊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值此多言一筆者,十年之後,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本人步楊公後塵,於 2011 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平民孫中山》,後記寫道:“孫中山出身平民,一生為了平民,他的三民主義、中華民國、國民革命,都與民字相聯,並為之鞠躬盡瘁⋯⋯他生活於民間,思想營養吸吮於民間,其事業的追隨者來自民間,他是從民間中走出來的偉人。”可謂“無巧不成事”, 2015 年本人赴台灣採訪《孫中山研究口述史》,將拙書贈張玉法先生指謬,先生問是什麼書,答曰《平民孫中山》,先生笑道:“平民孫中山,我要!如是⋯⋯(省略)”,令我頓時聽出了弦外之音!
毋庸諱言,關於孫中山革命性質的理論思考,有如孫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曾經主張“資產階級”說的章開沅先生在 1911 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辭典》序言說:諸如“資產階級”或“國民革命”或“紳士運動”說,“都促使我們對長期以來似乎已經成為定論的‘資產階級革命’說重新加以考察與探究 ⋯⋯ 比如,當時在中國大地上到底有沒有一支明確的社會力量稱得上是資產階級?相應的問題是如何判斷資產階級的形成,形成的條件與標
準是什麼?僅僅從歷史現象作就事論事的簡單答復是無濟於事的,還需從理論上,特別是理論與史事相結合的基礎上,作更為客觀、深入、細緻的探索,才有可能獲致若干比較確切和令人信服的答案。”
祈願“平民”說當有後續,孫中山研究沒有窮期。
謹祝《孫中山新探》問世,一花引來百花開!
王 傑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孫中山研究所所長
自序
本書收我多年來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論文、學術札記、演講報告與訪談錄。由於領導辛亥革命、創建民國是孫中山一生的最大業績,故將相關文章作為重點。所論多與時賢不同,故稱新探。
研究本國歷史只能從本國的歷史實際出發,而不能從先驗的、既定的原則出發,更不能生吞活剝地搬用或變相搬用外國歷史和基於其上的結論。本書提出了若干新看法,如近代中國新型知識份子與“共和知識份子”的形成;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共和知識份子”;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與兩次“倒孫風潮”的成因;辛亥革命勝利迅速、代價很小,其失敗的主因在於財政困難,而非通常所謂“資產階級軟弱性”。等等。都與史學界長期流行的說法不同。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明確表示: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20 頁。)
19 世紀下半葉至 20 世紀,俄羅斯、北美、西歐等地一度流行“平民主義”思潮(Populism)。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依靠平民群眾進行社會改革,將平民化作為政治運作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孫中山明顯地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從創立興中會,投身革命之日起,他就高度推崇“平民”的社會地位,以“平民”的利益和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在上述宣言中,孫中山指出了近世“民權制度”的階級實質:“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因此,他排斥“資產階級”,企圖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政權。這就表明了孫中山的政治理想:空前地擴大國家政權的社會基礎,改變其為資產階級執政,壓迫平民的性質。因此,從這一點,結合他的其他大量言論考察,與其說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如更準確地說他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或“平民革命家”。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起義各省的革命群眾團體和都督府就主張進行北伐,攻佔北京,推翻以滿洲貴族為代表的清朝政權。 1911 年 11 月 15 日,廣東光漢社召集會議,上書都督胡漢民,要求確定“籌兵、籌餉、平胡”之大計。稍後,旅滬各省人士紛紛組織北伐隊,滬軍都督陳其美建議組織北伐聯軍。 10月 5 日,北伐聯合會在上海成立。 12 月 20 日,江浙聯軍召開軍事大會,推舉徐紹楨為北伐總司令官。同月廣東北伐軍第一軍抵達上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於 1912 年 1 月 4 日聲稱“北伐斷不可懈”,命令廣東民軍“宜速進發”,他自己也表示要“親率大兵北伐”。同月 9 日,陸軍部成立,黃興確定計劃,確定兵分六路,共同攻佔北京。同時,孫中山則任命藍天蔚為關外大都督,在東北起事。 1 月 29 日,南京臨時政府各軍在清江浦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北伐。
袁世凱是晚清“新政”中崛起的官僚和武人,本已罷職回鄉。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獨立,清政府惶急無策,於 10 月 30 日以溥儀的名義下詔“罪已”,承認登基以來,“未辦一利民之事”,所有動亂,“皆朕一人之咎”。 11 月 1 日,皇族內閣總辭職,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老謀深算,老奸巨猾,認為清廷大勢已去,對待革命黨人,非單純武力鎮壓所可了結。 12 月 7 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同日,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 9日,十一省革命軍政府公推伍廷芳為總代表,與唐紹儀談判。 12 月 18 日,唐、伍二人在上海英租界舉行會議。 12 月 20 日,英國駐滬總領事會同日、美、德、法、俄等五國總領事向唐、伍二人遞交照會,聲稱他們決心堅持迄今所採取的絕對中立的態度,但戰事繼續進行,將使外國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遭到危險,要求雙方儘快達成協議,停止衝突。此後,英國的財團、銀行不斷向袁世凱提供大額借款,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訓示駐華公使朱爾典,向袁提供“一切外交上的支援”。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袁世凱一面謊報國庫存銀,向清廷施加壓力,聲稱“欲戰,則兵少餉絀;欲和,則君主立憲難保”,一面以甘言誘惑懦弱無助、撫養宣統帝的隆裕太后:“倘議定共和政體,必應優待皇室。”(《紹英日記》(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4、 269—270 頁。) 隆裕太后為袁的甜言蜜語所動。 2 月 3 日,授權袁世凱全權研究宗廟,陵寢,皇室優禮,八旗生計,蒙古、回、藏待遇等問題,做退位打算。
武昌起義後,列強除向中國加派軍艦、兵力外,為了防範革命黨人取用海關稅收, 11 月 7 日,公使團強行決定,將中國海關稅收全部匯解上海,存入滙豐等三家外國銀行,作為償還外債之用。革命黨人沒有對公使團的這一蠻橫決定提出異議,其財政狀況本已十分拮据,此時就更加困窘。臨時政府最艱難的時候,金庫僅存十洋。這種情況,不僅難以支付北伐所需的巨大軍費,甚至難以支付日常的行政管理費用和各部總長們的薪金。為此,孫中山等人不得不想方設法,繼續向外國人借債,以解燃眉之急。 2 月 3 日,孫中山在南京與日本三井物產公司的代表會談,企圖以“租讓滿洲”為代價取得 1000 萬元借款。孫稱:“倘或有幸,此刻能獲得防止軍隊解散之足夠經費,余等即可延緩與袁議和,俟年關過後再進一步籌措資金,而後繼續排袁,仍按原計劃,堅決以武力消除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森恪致益田孝函》( 1912 年 2 月 8 日),日本三井文庫藏。] 孫中山的這段話說明,他不是不想北伐,徹底推翻清廷;也不是對袁世凱心存幻想,而是企圖靠槍桿子說話,以“武力”消除“異端”,斬除“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2 月 8 日,湖南革命黨人譚人鳳致電孫中山,要求“激勵各軍,同時北上”。(《臨時政府公報第 3 號》。)次日再電,堅決反對議和。 11 日,孫中山答稱:“目下籌集軍費最為第一要著。”(《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81 頁。)13 日,再答云:“斷不容以十數省流血構成之民國,變為偽共和之謬制。”(《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91 頁。)
十塊洋元當然無法向北京進軍,更無法維持南京臨時政府的存活。 2 月 11日凌晨 1 時 55 分,與孫中山談判的日方代表急電國內,要求對革命黨人的借款要求“火速給與明確回答”。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認為日本理應享有“滿洲”的一切權益,無須金錢收買,不予回音。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統帝宣佈退位。 13 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對此,當年在孫中山身邊的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回憶說:“孫先生方面既無打倒袁世凱的武器,又無資金”,“不得不含淚同意南北妥協,最終讓位於袁世凱”。 (《シナ革命と孫文の中日联盟》,見嘉治隆一編:《第一人者の言葉》,亞東俱樂部 1961 年版,第 268 頁。)
多年來,人們分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大都籠統、簡單地歸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歷史真相顯示的主因則是:革命黨人面臨巨大的、嚴重的財政困難,借貸無門,不得不被迫妥協。哪一種說法更為真實可信?請讀者自辨。
關於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與兩次“倒孫風潮”,本書認為,既與日本社會黨人內部軟硬兩派的分裂有關,也有同盟會自身的原因。 1901 年,日本建立社會民主黨。 1903 年,幸德秋水組織平民社,宣揚“平民主義、社會主義”,翻譯並出版《共產黨宣言》。 1906 年,日本社會民主黨改名社會黨。 1907 年,日本社會黨分裂為軟硬兩派。硬派以幸德秋水為代表,軟派以片山潛為代表。在東京的中國革命黨人、同盟會員張繼、章炳麟、劉師培、陶成章等與幸德秋水關係密切。 4 月,章炳麟等組織亞洲和親會,它既“反抗帝國主義”,也反對一切“在上之人”,章程規定“無會長、幹事之職,各會員皆有平均利權”。以罷免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為目標的第一次“倒孫風潮”顯然與此相關。同年 8 月 31日,劉師培等成立“社會主義講習會”,宣揚無政府主義,在一系列問題上與孫中山的主張相抗,從而形成一個極“左”的政治派別。
本書的上述看法,均基於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歷史實際。其中部分觀點受過經典作家啟發。例如,“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的看法,受到列寧關於俄國革命中三代知識份子論述的影響;關於辛亥革命領導力量的分析,受到毛澤東關於“五四”運動領導力量相關論述的啟發。凡此種種,均非離經叛道之論,而是實事求是、認真獨立思考的結果。其中《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一文,曾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名義發表於《光明日報》。 2012 年 9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前沿報告》第 11 號,收入拙文《辛亥革命的性質與領導力量》,似可代表該書編者對本人相關觀點的重視。學術的發展、進步、繁榮有賴於百家爭鳴,本人此次不揣譾陋,將有關各文編輯成書,即意在為爭鳴之助,推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本書除個別文章外,過去都已發表過。凡有修改者,均在文後說明;無說明者,則全係發表時的原貌。孫中山一生,反復論述同一問題,筆者多年研究孫中山,或為文,或報告,或接受採訪,也難以完全避免重複。但為不致重複過多,有些文章略去未選,有些則做了刪節。
書後附錄《孫文罪狀》、《偽〈民報〉檢舉狀》、《佈告同志書》等三份文件,均為當年同盟會分裂,發生“倒孫風潮”時的產物,或發表於當年的海外報紙,或深藏於海外的檔案館,除《偽〈民報〉檢舉狀》外,今天已很難見到。為便於讀者和研究者,特加收錄。
謹以此書,獻給偉大的辛亥革命 110 週年。
楊天石
荷雨時節, E 從天降,楊公函囑為其大著《孫中山新探》寫序。驚惶之餘,復信連連求饒。公以本人“長期擔任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是為拙書寫序的非常合適的人選”相勸,經“協商”,則以公獎掖晚輩,扶持後生為慰,權以撰述懷憶或感獲一類的文字應允下來。
楊公著作等身,乃知名的孫中山研究專家。我們於 1978 年在近代史研究所相識,迄今四十餘年。是時,我出道未幾,公正值年富力強。因參加國家“六五”規劃重點項目《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版)的編輯,本人所在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學是合作單位,由此,得享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之“近水樓台”,借書、食宿,有幸與公同一棟樓。往事如煙,追憶依然。於孫中山研究領域,楊公有志竟成,其成就之秘訣,可簡括為六個字,曰:勤奮、求真、創見 —這是我粗略的體會,亦為本人受益終身之信條。
勤奮乃成功之基石。近代史所的藏書,勝似寶藏,浩如煙海。楊公的勤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客居近代史所,斷續不下一年半,印象最深刻的,不管是圖書館,還是辦公室(可將舊報借回),都可看到楊公翻閱書報與寫作的身影。記憶猶新者,他對報紙中的廣告頁,翻得特別快,蓋因習慣成自然了。一旦發現心儀的史料,便埋頭抄錄於卡片中(那時無電腦)。每每從他的門口走過,半開的房間總是看到他讀作的神韻,這對我這位初出茅廬的求知者來說,委實是“言傳”不如“身教”了。十多年前,我到北京參加研討,有意重溫舊夢,某星期日,深夜十一時,幾位同仁往所裏走,電梯已關,碰見楊公抱著一大疊書在爬樓梯,七十多歲的學者,以所為家,於夜色蒼茫中負書上行,其勤其奮之形象,深印於我的腦海。聰明出於勤奮,治學呵護冷板,難能可貴啊!楊公幾十年如一日,專心學問,其砥礪之精神,令人感佩有加。
史料有如史學之磐石,亦賴勤奮之功經營。史學即史料學,欠缺史料,史學就會變成空泛的說教;言中有物,論從史出,才是治史之要義。前賢早有言曰,南京大學教授韓儒林先生撰過家喻戶曉之一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楊公堪稱典範,所撰著述,既以史料為基底,又以新見史料見長。以《新探》為例,撇開書刊不論,僅引用的報紙(不含《民報》、《新民叢報》等)就有:《大共和日報》、《獨立週報》、《神州日報》、《申報》、《民聲日報》、《民志日報》、《大漢報》、《大公報》、《民立報》、《民權報》、《天鐸報》(上海)、《民主報》(北京)、《國民公報》、《中華民報》、《燕京時報》、《衡報》、《天義報》、《蘇報》、《少年中國晨報》、《新世紀》、《越鐸日報》、《中興報》、《中國旬報》、《香港華字日報》、《南洋總匯新報》、《星洲晨報》、《廣州民國日報》、《高知新聞》(日本)、《日新報》(加拿大)等三十種,還有《朱希祖日記》(稿本)、陶冶公《無政府主義思想對同盟會的影響》(未刊稿)、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未刊稿,陶冶公原藏)等;翻閱“檔案、函札所見孫中山”一章,不乏台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檔案、台北“國史館”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宮崎滔天家藏書札、日本山口縣文書館檔案等資料,均為史料中之乾貨!其“上窮碧落下黃泉”之功力,可見一斑。尤須多書一筆的是,書末附錄《孫文罪狀》、《偽〈民報〉檢舉狀》、《佈告同志書》等三份文件,均係同盟會發生“倒孫風潮”的文獻,或發表於當年的海外報紙,或深藏於海外的檔案館,除《偽〈民報〉檢舉狀》外,今天已很難見到。楊公視史料為生命,卻把罕見史料和盤托出供學界共用,嘉惠士林,精神可佩!
史學有獨立的品格,史家有獨特的人格,楊公的“格”定位於求真。舉凡《新探》文字,無時無刻不在展示楊公求真的樣態。關於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楊公認為,孫中山並不將資本主義視為垂死的、沒落、腐朽、應該打倒、消滅的生產方式,也並不將它視為與社會主義格格不能相容的敵對力量,而是仍然視為推進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經濟能力”,主張調和兩者,使之“互相為用”,共同促進人類的文明發展。所謂“互相為用”,那意思是說:
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可以利用社會主義,相互借鑒、相互吸取,人類社會因而得以前進、發展。這是一種充滿辯證思想的遠見卓識。可惜,孫中山並未展開充分論述,但是,人類歷史的發展經已證明並將進一步證實這一認識的偉大意義。楊公對孫中山關於資本主義的把握,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光點。
求真,乃是對實事求是精神的弘揚。關於孫中山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價,楊公指出,孫中山曾對馬克思主義做過批評。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進行過多方面的、嚴厲無情的批判。孫中山也曾嚴厲批判資本主義剝削,批判資本家的缺乏道德,他將馬克思所分析的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手段歸納為三種:一是減少工人的工資,二是延長工人做工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但是,孫中山根據 20 世紀 20 年代的社會現實,對馬克思的有關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見。
他以美國福特汽車工廠為例說: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做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做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孫中山認為以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馬克思一點都沒有料到。這其實都是孫中山研究中的前沿問題和最敏感的話題了。
良史,須憑史識,必有“求義”。楊公將“歷史學家要對歷史負責”作為治學的座右銘,道出了良史的心聲。《新探》關於《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輪船招商局借款——兼論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與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一文,一改前人和時人將辛亥革命的失敗簡單地歸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的成說,以事實為基礎,圍繞孫中山的困難問題展開闡述,把孫中山的財政困難講得很清楚,從而拋棄政治概念的套路,到目前為止,仍未見對該文提出的質疑。又,關於
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與兩次“倒孫風潮”的論述,楊文強調既與日本社會黨人內部軟硬兩派的分裂有關,也有同盟會自身的原因等等。舉凡,揚葩吐豔,各極其致,學界遂蒙絕大之受益。
學問的靈魂在於閃光,學術的生命重於創見。業師章開沅先生說:“史魂即史德,用現代話語來表達,就是這個學科固有的獨立品格。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是以史學為志業者必須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史學尋找自己》,《實齋筆記》第 309 頁)應該指出,《新探》主人畢生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箴言作為研究學術的最高理想,努力踐行“獨立的學術人格”,卓然成家,提出了不少創見,如近代中國新型知識份子與“共和知識份子”的形成;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共和知識份子”等。尤其特別指出的是,他強調孫中山指斥近世“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冀望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政權,因此提出,與其說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如更準確地說他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或“平民革命家”。從百家爭鳴的視角說,這是楊公與其他學者的不同見解,堪稱一大創見。
多年以來,學人一直把孫中山定位在資產階級革命家。這無疑牽涉到孫中山階級定性的問題。楊公倡說孫中山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並在《孫中山研究口述史》中列舉了七大依據:
一、於家庭經濟狀況言,孫中山出身貧苦,其兄孫眉雖一度為海外農場主,但因支持革命而毀家紓難,迅速破產且困居於香港的茅草棚,故而,將孫中山劃歸資產階級群體中缺乏充分的理由。二、從孫中山的支持群體(階級基礎)言,並未有多少資產階級在支持他: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多支持立憲派;革命後又多投靠袁世凱。“二次革命”時明確支持孫中山的資產階級寥寥可數;廣東作為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又是孫中山故里,但是,廣東的資產階級都是站在孫中山的對立面,擁護孫氏的著實少見。三、從孫中山思想維度看,把孫中山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家好像更沒有道理。在近代革命家中,孫中山最早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痛罵資本主義,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辛亥革命後,孫中山痛罵資本家沒有道德良心、唯利是圖的言論還有很多,而且是最早宣稱中國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老路的人。四、就中國國家制度選擇言,孫中山肯定施行民主共和制度,嚴正指出“英美立憲,富人享之,貧者無與焉”,從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上全面批判和否定了西方資本主義,明確提出不能對西方亦步亦趨,要在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創建中國民主制度,這是孫中山創造“五權分立”思想及實行五院並立制度的根本原因。五、對待社會主義態度言,孫中山於 1903 年就表達過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將“民生主義”直接和“社會主義”對等翻譯就是直接體現; 1905 年,孫中山在比利時向國際社會黨(第二國際)執行局申請,要求接納他正在組織的政黨,其所彙報的黨綱中稱,要使“工人階級不必經受被資本家剝削的痛苦”;1915年 11 月,孫中山再次致函國際社會黨執行局,要求提供人才,協助自己將“中國建立成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見,孫中山是中國最早表示對社會主義的嚮往和追求的一位革命家,把這樣一個人說成是資產階級,拿不出道理來。六、就中華民國頒佈的綱領政策看,均未鼓勵發展資本主義。翻查南京臨時政府的命令、條令,並沒有多少是鼓勵資本主義發展。而相比於晚清政府的新政,則是大力扶持資本家,並根據資本家的投資封官封爵,鼓勵發展資本主義。相反,南京臨時政府所頒佈的政策法律頂多是些空洞的發展實業詞語,絕對沒有達到晚清新政的那種高度和力度。所以,相比較之下,把孫中山說成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不對的。七、就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而言,康梁以“保商”為根本追求,主張發展資本主義,抵抗外資,認為保護資本家是第一要務。康梁派特別是梁啟超,是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和利益代表者。而革命黨則並不如此,革命黨主張社會革命,主張發展國家資本,發展國營企業,這與資產階級價值追求和利益保障明顯有所差距。
創見可以喻為史學的玉石,乃學人智慧的迸發、創新的結晶。楊公此文,初以《孫中山不是資產階級革命家》為題,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 2001 年第6 期,後易題為《孫中山應是“平民革命家”》摘要轉載於 2001 年 9 月 17 日《北京日報》。(參見《孫中山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收入《哲人與文士》,見《楊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值此多言一筆者,十年之後,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本人步楊公後塵,於 2011 年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平民孫中山》,後記寫道:“孫中山出身平民,一生為了平民,他的三民主義、中華民國、國民革命,都與民字相聯,並為之鞠躬盡瘁⋯⋯他生活於民間,思想營養吸吮於民間,其事業的追隨者來自民間,他是從民間中走出來的偉人。”可謂“無巧不成事”, 2015 年本人赴台灣採訪《孫中山研究口述史》,將拙書贈張玉法先生指謬,先生問是什麼書,答曰《平民孫中山》,先生笑道:“平民孫中山,我要!如是⋯⋯(省略)”,令我頓時聽出了弦外之音!
毋庸諱言,關於孫中山革命性質的理論思考,有如孫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曾經主張“資產階級”說的章開沅先生在 1911 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辭典》序言說:諸如“資產階級”或“國民革命”或“紳士運動”說,“都促使我們對長期以來似乎已經成為定論的‘資產階級革命’說重新加以考察與探究 ⋯⋯ 比如,當時在中國大地上到底有沒有一支明確的社會力量稱得上是資產階級?相應的問題是如何判斷資產階級的形成,形成的條件與標
準是什麼?僅僅從歷史現象作就事論事的簡單答復是無濟於事的,還需從理論上,特別是理論與史事相結合的基礎上,作更為客觀、深入、細緻的探索,才有可能獲致若干比較確切和令人信服的答案。”
祈願“平民”說當有後續,孫中山研究沒有窮期。
謹祝《孫中山新探》問世,一花引來百花開!
王 傑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原孫中山研究所所長
自序
本書收我多年來關於孫中山的研究論文、學術札記、演講報告與訪談錄。由於領導辛亥革命、創建民國是孫中山一生的最大業績,故將相關文章作為重點。所論多與時賢不同,故稱新探。
研究本國歷史只能從本國的歷史實際出發,而不能從先驗的、既定的原則出發,更不能生吞活剝地搬用或變相搬用外國歷史和基於其上的結論。本書提出了若干新看法,如近代中國新型知識份子與“共和知識份子”的形成;辛亥革命的領導力量是“共和知識份子”;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與兩次“倒孫風潮”的成因;辛亥革命勝利迅速、代價很小,其失敗的主因在於財政困難,而非通常所謂“資產階級軟弱性”。等等。都與史學界長期流行的說法不同。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孫中山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明確表示:
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20 頁。)
19 世紀下半葉至 20 世紀,俄羅斯、北美、西歐等地一度流行“平民主義”思潮(Populism)。強調平民群眾的價值和理想,依靠平民群眾進行社會改革,將平民化作為政治運作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孫中山明顯地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從創立興中會,投身革命之日起,他就高度推崇“平民”的社會地位,以“平民”的利益和代言人的身份自居。在上述宣言中,孫中山指出了近世“民權制度”的階級實質:“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因此,他排斥“資產階級”,企圖建立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國家政權。這就表明了孫中山的政治理想:空前地擴大國家政權的社會基礎,改變其為資產階級執政,壓迫平民的性質。因此,從這一點,結合他的其他大量言論考察,與其說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不如更準確地說他是“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或“平民革命家”。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起義各省的革命群眾團體和都督府就主張進行北伐,攻佔北京,推翻以滿洲貴族為代表的清朝政權。 1911 年 11 月 15 日,廣東光漢社召集會議,上書都督胡漢民,要求確定“籌兵、籌餉、平胡”之大計。稍後,旅滬各省人士紛紛組織北伐隊,滬軍都督陳其美建議組織北伐聯軍。 10月 5 日,北伐聯合會在上海成立。 12 月 20 日,江浙聯軍召開軍事大會,推舉徐紹楨為北伐總司令官。同月廣東北伐軍第一軍抵達上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於 1912 年 1 月 4 日聲稱“北伐斷不可懈”,命令廣東民軍“宜速進發”,他自己也表示要“親率大兵北伐”。同月 9 日,陸軍部成立,黃興確定計劃,確定兵分六路,共同攻佔北京。同時,孫中山則任命藍天蔚為關外大都督,在東北起事。 1 月 29 日,南京臨時政府各軍在清江浦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北伐。
袁世凱是晚清“新政”中崛起的官僚和武人,本已罷職回鄉。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獨立,清政府惶急無策,於 10 月 30 日以溥儀的名義下詔“罪已”,承認登基以來,“未辦一利民之事”,所有動亂,“皆朕一人之咎”。 11 月 1 日,皇族內閣總辭職,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老謀深算,老奸巨猾,認為清廷大勢已去,對待革命黨人,非單純武力鎮壓所可了結。 12 月 7 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議和全權大臣,同日,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南下。 9日,十一省革命軍政府公推伍廷芳為總代表,與唐紹儀談判。 12 月 18 日,唐、伍二人在上海英租界舉行會議。 12 月 20 日,英國駐滬總領事會同日、美、德、法、俄等五國總領事向唐、伍二人遞交照會,聲稱他們決心堅持迄今所採取的絕對中立的態度,但戰事繼續進行,將使外國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遭到危險,要求雙方儘快達成協議,停止衝突。此後,英國的財團、銀行不斷向袁世凱提供大額借款,英國外交大臣格雷訓示駐華公使朱爾典,向袁提供“一切外交上的支援”。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袁世凱一面謊報國庫存銀,向清廷施加壓力,聲稱“欲戰,則兵少餉絀;欲和,則君主立憲難保”,一面以甘言誘惑懦弱無助、撫養宣統帝的隆裕太后:“倘議定共和政體,必應優待皇室。”(《紹英日記》(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4、 269—270 頁。) 隆裕太后為袁的甜言蜜語所動。 2 月 3 日,授權袁世凱全權研究宗廟,陵寢,皇室優禮,八旗生計,蒙古、回、藏待遇等問題,做退位打算。
武昌起義後,列強除向中國加派軍艦、兵力外,為了防範革命黨人取用海關稅收, 11 月 7 日,公使團強行決定,將中國海關稅收全部匯解上海,存入滙豐等三家外國銀行,作為償還外債之用。革命黨人沒有對公使團的這一蠻橫決定提出異議,其財政狀況本已十分拮据,此時就更加困窘。臨時政府最艱難的時候,金庫僅存十洋。這種情況,不僅難以支付北伐所需的巨大軍費,甚至難以支付日常的行政管理費用和各部總長們的薪金。為此,孫中山等人不得不想方設法,繼續向外國人借債,以解燃眉之急。 2 月 3 日,孫中山在南京與日本三井物產公司的代表會談,企圖以“租讓滿洲”為代價取得 1000 萬元借款。孫稱:“倘或有幸,此刻能獲得防止軍隊解散之足夠經費,余等即可延緩與袁議和,俟年關過後再進一步籌措資金,而後繼續排袁,仍按原計劃,堅決以武力消除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森恪致益田孝函》( 1912 年 2 月 8 日),日本三井文庫藏。] 孫中山的這段話說明,他不是不想北伐,徹底推翻清廷;也不是對袁世凱心存幻想,而是企圖靠槍桿子說話,以“武力”消除“異端”,斬除“禍根”,“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2 月 8 日,湖南革命黨人譚人鳳致電孫中山,要求“激勵各軍,同時北上”。(《臨時政府公報第 3 號》。)次日再電,堅決反對議和。 11 日,孫中山答稱:“目下籌集軍費最為第一要著。”(《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81 頁。)13 日,再答云:“斷不容以十數省流血構成之民國,變為偽共和之謬制。”(《孫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91 頁。)
十塊洋元當然無法向北京進軍,更無法維持南京臨時政府的存活。 2 月 11日凌晨 1 時 55 分,與孫中山談判的日方代表急電國內,要求對革命黨人的借款要求“火速給與明確回答”。日本陸軍大臣石本新六認為日本理應享有“滿洲”的一切權益,無須金錢收買,不予回音。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統帝宣佈退位。 13 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對此,當年在孫中山身邊的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回憶說:“孫先生方面既無打倒袁世凱的武器,又無資金”,“不得不含淚同意南北妥協,最終讓位於袁世凱”。 (《シナ革命と孫文の中日联盟》,見嘉治隆一編:《第一人者の言葉》,亞東俱樂部 1961 年版,第 268 頁。)
多年來,人們分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敗,大都籠統、簡單地歸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歷史真相顯示的主因則是:革命黨人面臨巨大的、嚴重的財政困難,借貸無門,不得不被迫妥協。哪一種說法更為真實可信?請讀者自辨。
關於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與兩次“倒孫風潮”,本書認為,既與日本社會黨人內部軟硬兩派的分裂有關,也有同盟會自身的原因。 1901 年,日本建立社會民主黨。 1903 年,幸德秋水組織平民社,宣揚“平民主義、社會主義”,翻譯並出版《共產黨宣言》。 1906 年,日本社會民主黨改名社會黨。 1907 年,日本社會黨分裂為軟硬兩派。硬派以幸德秋水為代表,軟派以片山潛為代表。在東京的中國革命黨人、同盟會員張繼、章炳麟、劉師培、陶成章等與幸德秋水關係密切。 4 月,章炳麟等組織亞洲和親會,它既“反抗帝國主義”,也反對一切“在上之人”,章程規定“無會長、幹事之職,各會員皆有平均利權”。以罷免孫中山的同盟會總理為目標的第一次“倒孫風潮”顯然與此相關。同年 8 月 31日,劉師培等成立“社會主義講習會”,宣揚無政府主義,在一系列問題上與孫中山的主張相抗,從而形成一個極“左”的政治派別。
本書的上述看法,均基於辛亥革命時期的中國歷史實際。其中部分觀點受過經典作家啟發。例如,“平民知識份子革命家”的看法,受到列寧關於俄國革命中三代知識份子論述的影響;關於辛亥革命領導力量的分析,受到毛澤東關於“五四”運動領導力量相關論述的啟發。凡此種種,均非離經叛道之論,而是實事求是、認真獨立思考的結果。其中《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一文,曾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名義發表於《光明日報》。 2012 年 9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前沿報告》第 11 號,收入拙文《辛亥革命的性質與領導力量》,似可代表該書編者對本人相關觀點的重視。學術的發展、進步、繁榮有賴於百家爭鳴,本人此次不揣譾陋,將有關各文編輯成書,即意在為爭鳴之助,推動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本書除個別文章外,過去都已發表過。凡有修改者,均在文後說明;無說明者,則全係發表時的原貌。孫中山一生,反復論述同一問題,筆者多年研究孫中山,或為文,或報告,或接受採訪,也難以完全避免重複。但為不致重複過多,有些文章略去未選,有些則做了刪節。
書後附錄《孫文罪狀》、《偽〈民報〉檢舉狀》、《佈告同志書》等三份文件,均為當年同盟會分裂,發生“倒孫風潮”時的產物,或發表於當年的海外報紙,或深藏於海外的檔案館,除《偽〈民報〉檢舉狀》外,今天已很難見到。為便於讀者和研究者,特加收錄。
謹以此書,獻給偉大的辛亥革命 110 週年。
楊天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