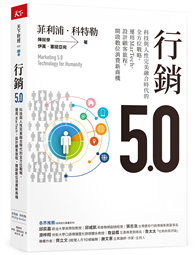「可怕的京都,可怕的祇園祭,可怕的宵山。
我這個外行人不應該獨自到處亂轉的……」
京都新世代作家代表 X 最夢幻繚亂的千年祭典!
心地善良的傻瓜─神隱15年的少女─謎樣的古董店男子
又怪又有趣
森見登美彥開啟想像力的新境地!
宵山──京都祇園祭的前夜。
在這華美幽暗的千年古都裡,祭典的熱鬧彷彿吞沒了整座城市。
兩姊妹在熙攘人群間失散了。年幼的妹妹遇上一群穿紅色浴衣的女孩,嬉笑著帶她奔越大街小巷。煩鬧的人聲裡,妹妹的腳步竟漸漸虛浮,彷彿下一刻就要飛上天去……
而城市的另一角,宵山宛若棲居在這間老宅內。十五年過去了,仍舊彷彿一夜。畫家在萬花筒內見到了那張懷念已久的面孔,微笑著召喚他踏入宵山的迷離中。
頻頻來訪的古董店男子究竟是何來歷?他索討的那樣「不該擁有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前失蹤的少女,與十五年後猝死的老人之間,又有什麼關聯?
本書收錄〈宵山姊妹〉、〈宵山金魚〉、〈宵山劇場〉、〈宵山迴廊〉、〈宵山迷宮〉、〈宵山萬花筒〉六個短篇:
〈宵山姊妹〉
老師明明說了,「下課後要直接回家」。好奇的姊姊為了要去看「螳螂山」,帶著我在大街小巷間亂跑,想不到我們倆竟在人群中走散了。怎麼辦、怎麼辦?
〈宵山金魚〉
乙川的夢想是培養出「超金魚」,興趣則是「放我鴿子」。這一年,他終於允諾帶我見識所謂的「宵山」,卻也照例放了我鴿子,不幸的是,我竟然還誤闖宵山大人的禁地……
〈宵山劇場〉
那一年的學園祭讓我對舞臺設計的熱情就此燃燒殆盡。無所事事、打工度日的我,難以拒絕學長的邀約,加入他莫名其妙但號稱絕對華麗的計畫,卻意外與那瘋狂的女子重逢?!
〈宵山迴廊〉
十五年前的那一夜開始,宵山的影子就此棲居在這座老宅內。而十五年後,畫廊老闆帶來的萬花筒裡,竟出現了我日思夜想的面孔,微笑著呼喚我前去尋找她的芳蹤……
〈宵山迷宮〉
一年前,無人知曉父親為何遠赴鞍馬,並且猝死在半途。一年後,古董店的男子日復一日前來索求某個物品。為什麼母親每天早上都在倉庫裡整理東西?為什麼每天見到我的人卻說是第一次見面?
〈宵山萬花筒〉
我不該放開妹妹的手的。明明那麼膽小,為什麼要跟著陌生的女孩走呢?街角的大和尚說好了要給我養著金魚的氣球,卻帶著我來到神祕的大樓屋頂上……
作者簡介
森見登美彥 Morimi Tomihiko
一九七九年出生於奈良。一九九八年進入京都大學農學系,畢業後進入農學研究所就讀。二○○三年研究所在學期間,以描寫京都大學生日常生活的處女作《太陽之塔》獲日本奇幻小說大獎,驚豔文壇。誰也沒想到一個內向害羞的京都大學高材生,腦中的「宅男狂想」竟能如此生動逗趣,又富有內涵。
二○○七年,以《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一舉拿下第二十屆山本周五郎獎、日本書店大獎第二名,達文西雜誌讀者票選最愛小說第一名。以幽默、擬古的「森見文體」風靡全日本,受到各大書店店員和一般讀者的熱烈推崇。就連日本最毒舌的文學評論家大森望也對他讚譽有加,盛讚:「大傑作!毫無疑問是二○○七年的戀愛小說NO. 1!」
二○○八年,以《有頂天家族》拿下日本書店大獎第三名,奠定暢銷作家地位。
森見登美彥的登場與成功使得日文文學在「寫實」與「幻想架空」等傳統分類之下,又開創另一「打破類型疆界、以閱讀享受至上」的新體裁。
二○○九年七月,日本著名讀書社群網站「閱讀計數器」公布一項調查:「上半年度最多人閱讀的小說」,即由《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堂堂登上冠軍寶座!
森見登美彥可說是日本目前最炙手可熱、最受讀者喜愛的新銳作家!
著有《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狐的故事》、《有頂天家族》、《宵山萬花筒》、《竹林與美女》、《戀文的技術》等。
譯者簡介
劉姿君
畢業於台大農學經濟系,曾於日商公司、出版社任職。現為文字工作者,譯有《最後的兒子》、《地標》、《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為青年設立的讀書俱樂部》、《再見溪谷》等書。


 共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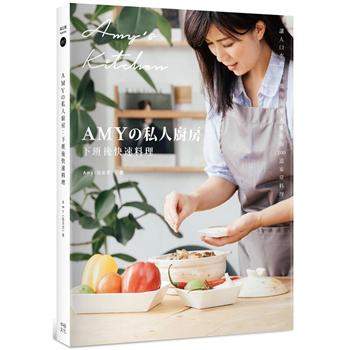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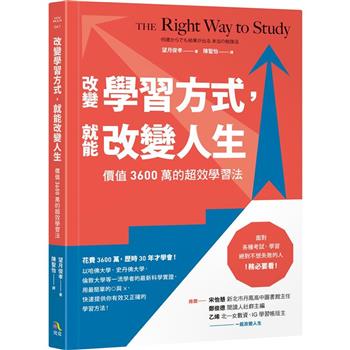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