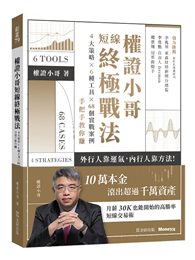我可以跟你們講個偉大藝術家的名字:法蘭茲‧卡夫卡。――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卡夫卡遺稿管理人
首部卡夫卡素描手稿集結,遺落的經典中的經典
捷克VITALIS出版社授權,荷蘭「法蘭茲‧卡夫卡學會」專家編輯考證
卡夫卡說:這些素描是很久以前的、深深烙印在心裡的熱情的痕跡……
卡夫卡曾經夢想當一名偉大的畫家,儘管最終選擇了文學道路
《變形記》的矛盾絕望、《城堡》的漫長等待、《審判》的荒謬無助
透過卡夫卡的畫筆將更加真實
談及法蘭茲‧卡夫卡(1883-1924),我們直覺就會想到他的文學作品。卡夫卡熱愛畫畫這件事則少有人知。
卡夫卡早在小學時期就上過畫畫課,到了大學階段則發展出對繪畫的喜好。大學畢業後不久,儘管曾經受教於某位「二流畫家」,加上中學以來萌生成為作家的野心,但他似乎想過要成為一名藝術家;這個心願使得他在回顧過往時,曾自稱是「一個偉大的素描畫家」,素描帶給他的滿足感遠勝其他一切。而直到過世為止,卡夫卡規律地提筆畫畫,他對美術的興趣,尤其是素描與繪畫,不曾衰退。
他的朋友兼遺稿管理人馬克斯‧布羅德認為,卡夫卡是個擁有「特殊力量且與眾不同的藝術家兼畫家」。幸虧布羅德將卡夫卡幾個不同時期的素描作品留存下來,後人才有幸得見這位文學大師不同的一面――這些畫要不是卡夫卡送給布羅德的,要不就是布羅德從卡夫卡的廢紙簍裡搶救下來的。
本書是卡夫卡的素描首次集結付梓,搜集了迄今可以尋得的卡夫卡繪畫作品共 41 幅;已知但無法取得的素描,也以清單的形式納入本書。書中的素描主題豐富,有人物、街景、旅行印象、白日夢、自畫像等等。每幅作品皆襯以卡夫卡的文字,這些文字內容或許是編者選自卡夫卡的日記、小說、書信,或許是卡夫卡為圖畫親自做的說明。書末亦針對畫作的主題、技法、格式、來源、日期、原作地點做了詳細評註。
贈品簡介
隨書附贈卡夫卡式精美萬用掛卡一張
贈品裝訂在書內,附裁切線,讀者可自行拆下使用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尼爾斯.伯克霍夫的圖書 |
 |
$ 168 ~ 399 | 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
作者:法蘭茲‧卡夫卡,尼爾斯.伯克霍,瑪利耶克.凡多爾斯特(Franz Kafka,Niels Bokhove,Marijke van Dorst) / 譯者:謝靜雯,林宏濤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14-08-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60頁 / 17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9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曾經,有個偉大的素描畫家:卡夫卡和他的41幅塗鴉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法蘭茲‧卡夫卡 Franz Kafka
存在主義代表作家 現代主義文學鼻祖,二十世紀德語文豪。1883年生於布拉格,1924年因肺結核病逝。1906年自卡爾費迪南特大學畢業,獲法學博士學位,後於勞工事故保險局任職。1899年起開始寫作,早期作品皆未予以保留,死時更交代友人將作品全數銷毀,友人未予聽從,三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因而得以傳世。
尼爾斯.伯克霍夫Niels Bokhove
哲學家、教育家、歐洲頗負盛名的卡夫卡研究專家。荷蘭「法蘭茲‧卡夫卡學會」(Nederlandse Franz Kafka-Kring)的創立者,曾擔任卡夫卡研究季刊 Kafka-Katern的主編。
瑪利耶克.凡多爾斯特Marijke van Dorst
教育家,專研藝術與文化領域的諮詢工作。曾擔任荷蘭「法蘭茲‧卡夫卡學會」祕書,主要從事捷克文學的研究。對繪畫也學有專精。
譯者簡介
謝靜雯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英語語言與文化碩士。近期譯作有《筆電愛情》、《當我們談論安妮日記時,我們在談些什麼》、《時光機器與消失的父親》、《沼澤新樂園》等。
翻譯作品集:miataiwan0815.blogspot.tw/
林宏濤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之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正義的理念》、《與卡夫卡對話》等作品。
法蘭茲‧卡夫卡 Franz Kafka
存在主義代表作家 現代主義文學鼻祖,二十世紀德語文豪。1883年生於布拉格,1924年因肺結核病逝。1906年自卡爾費迪南特大學畢業,獲法學博士學位,後於勞工事故保險局任職。1899年起開始寫作,早期作品皆未予以保留,死時更交代友人將作品全數銷毀,友人未予聽從,三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因而得以傳世。
尼爾斯.伯克霍夫Niels Bokhove
哲學家、教育家、歐洲頗負盛名的卡夫卡研究專家。荷蘭「法蘭茲‧卡夫卡學會」(Nederlandse Franz Kafka-Kring)的創立者,曾擔任卡夫卡研究季刊 Kafka-Katern的主編。
瑪利耶克.凡多爾斯特Marijke van Dorst
教育家,專研藝術與文化領域的諮詢工作。曾擔任荷蘭「法蘭茲‧卡夫卡學會」祕書,主要從事捷克文學的研究。對繪畫也學有專精。
譯者簡介
謝靜雯
荷蘭葛洛寧恩大學英語語言與文化碩士。近期譯作有《筆電愛情》、《當我們談論安妮日記時,我們在談些什麼》、《時光機器與消失的父親》、《沼澤新樂園》等。
翻譯作品集:miataiwan0815.blogspot.tw/
林宏濤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德國弗來堡大學博士研究。譯著有:《鈴木大拙禪學入門》、《啟蒙的辯證》、《菁英的反叛》、《詮釋之衝突》、《體會死亡》、《美學理論》、《法學導論》、《愛在流行》、《隱藏之泉》、《神在人間》、《眾生的導師:佛陀》、《南十字星風箏線》、《神話學辭典》、《與改變對話》、《死後的世界》、《正義的理念》、《與卡夫卡對話》等作品。
目錄
卡夫卡和他的素描作品
1.思考者
2.牢籠中的人
3.拄枴杖的男人
4.頭靠在桌上的男人
5.立鏡旁的男人
6.低頭坐著的男子
7.擊劍者
8.奔跑者
9.三位跑者
10.「舞者艾杜朵娃……與兩位提琴手相伴在輕軌列車上」
11.手腳並用行走的男子
12.馬背上的騎師
13.馬車與馬
14.「我的幾個生活場景」
15.沒有胃口
16.「手挽著手散步」
17.「我『正在忙』的事」
18.「日本藝人」
19.雜技演員
20.與神祕生物共處的男人
21.蛇女
22.遊行抗議
23.走路的人影;河流與樹木旁邊的轎子
24.歌德的「史登的花園之屋」
25.鐘塔,可能在奧斯泰諾
26.甘德利亞的教堂與房舍;聖瑪格麗塔的噴泉
27.「那種橋」
28.琉森市,在療養地賭場的賭桌上
29.塔特拉溫泉地,塔特拉別墅的生活景況
30.「請願者跟高貴的贊助人」
31.亞伯拉罕將兒子以撒獻為燔祭
32.桌邊的男子,牆後的老闆娘
33.婦女的頭部和馬的大腿(擬達文西)
34.桌子前面被虐待的男子,以及圍觀者
35.穿著黑色西裝的憂鬱男子
36.狂飲者
37.沒穿褲子在屋頂散步的人
38.等待中的兩個人
39.「奧特拉的午前點心」
40.朵拉‧迪亞芒
41.卡夫卡的母親在看書;自畫像
關於這些素描
卡夫卡:「一個偉大的素描畫家」
一段小插曲
以字母為圖
睡前的畫面想像
卡夫卡的筆
卡夫卡的藝術嗜好
編輯的話
圖文評註
本書提及但無法取得的素描
卡夫卡素描所根據的原始素材
1.思考者
2.牢籠中的人
3.拄枴杖的男人
4.頭靠在桌上的男人
5.立鏡旁的男人
6.低頭坐著的男子
7.擊劍者
8.奔跑者
9.三位跑者
10.「舞者艾杜朵娃……與兩位提琴手相伴在輕軌列車上」
11.手腳並用行走的男子
12.馬背上的騎師
13.馬車與馬
14.「我的幾個生活場景」
15.沒有胃口
16.「手挽著手散步」
17.「我『正在忙』的事」
18.「日本藝人」
19.雜技演員
20.與神祕生物共處的男人
21.蛇女
22.遊行抗議
23.走路的人影;河流與樹木旁邊的轎子
24.歌德的「史登的花園之屋」
25.鐘塔,可能在奧斯泰諾
26.甘德利亞的教堂與房舍;聖瑪格麗塔的噴泉
27.「那種橋」
28.琉森市,在療養地賭場的賭桌上
29.塔特拉溫泉地,塔特拉別墅的生活景況
30.「請願者跟高貴的贊助人」
31.亞伯拉罕將兒子以撒獻為燔祭
32.桌邊的男子,牆後的老闆娘
33.婦女的頭部和馬的大腿(擬達文西)
34.桌子前面被虐待的男子,以及圍觀者
35.穿著黑色西裝的憂鬱男子
36.狂飲者
37.沒穿褲子在屋頂散步的人
38.等待中的兩個人
39.「奧特拉的午前點心」
40.朵拉‧迪亞芒
41.卡夫卡的母親在看書;自畫像
關於這些素描
卡夫卡:「一個偉大的素描畫家」
一段小插曲
以字母為圖
睡前的畫面想像
卡夫卡的筆
卡夫卡的藝術嗜好
編輯的話
圖文評註
本書提及但無法取得的素描
卡夫卡素描所根據的原始素材
序
導讀
耿一偉
遺稿中的遺稿――卡夫卡的圖像書法
“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
――哲學家維根斯坦
卡夫卡在1913年2月11/12日給菲莉絲的情書中,畫了兩張手臂挽在一起的小圖(見本書44頁),隨後他在信中寫道:「妳喜歡我的塗鴉嗎?我曾是個不錯的工匠,妳知道的,但後來我參加學院派的繪畫課程後,碰到一位十分差勁的女性畫家,她幾乎毀了我的天份。想想看,那多可怕!但請耐心期待,過幾天我會寄給妳幾張我的畫,讓妳有些素材可以嘲笑。這些圖畫曾帶給我極大的滿足――那是幾年前――沒有任何事物比得上。」
讓我們先分析這段文字,卡夫卡對自己的素描頗為自信(「妳喜歡我的塗鴉嗎?」),表示自己上還過繪畫課,只是學院派的教育破壞了他對繪畫本有的天份。想像你在追求某個對象,接著你秀出以前彈的吉他錄音,然後說,其實我以前吉他彈得還不錯,都是被別人害的(「想想看,那多可怕!」)――這背後的潛台詞是,我曾有一項非常珍貴的特質,後來被別人毀了,但我想讓你知道我曾有那麼棒過(這有點像在臉書放以前很瘦的照片)。
從這角度來觀察,可以想見卡夫卡在寫給追求對象的情書中,忽然秀出自己的塗鴉技巧時,他幾乎已經是在亮底牌了。這段文字的最後,卡夫卡強調繪畫曾帶給他的滿足(「沒有任何事物比得上」),我們可以猜測,在他還沒有決定走向文學之路前,繪畫也是他人生的一個選項。寫這封信時,卡夫卡剛好三十歲,三十而立的他,已經完成《判決》、《蛻變》與《司爐》等重要作品,他的人生之路已經確定,文學是他的志業。
但在1906-7年左右(「那是幾年前」),他對視覺藝術產生了某種狂熱(「這些圖畫曾帶給我極大的滿足」),一方面是他正受到福樓拜的影響,另一方面是他與一群新生代的捷克畫家有密切往來。福樓拜的《情感教育》是影響卡夫卡極重要的一部小說,作品中大量視覺描述而非內心感受的自然主義文學技巧,可能刺激卡夫卡在文學初期的道路上,轉向繪畫以吸取養分。這有點像宋朝詩人陸遊說的:「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
卡夫卡與捷克畫派「八人組」(Osma)的交往,在本書附錄的〈卡夫卡:一個偉大的素描畫家〉一文中,已有詳盡交代。另一篇〈一段小插曲〉談到卡夫卡原有一張畫要給馬克斯・布羅德的新書當封面的軼事,也是在1907年這段繪畫高峰期。這時候卡夫卡的歲數,大概是25歲,是他於1906年拿到法學博士開始在法院實習的階段(1906-07)。這是剛從學校離開準備就業的年齡,卡夫卡還在尋找人生的目標。而且很明顯,法院工作不會是他喜歡的。如同所有文藝青年一樣,卡夫卡勢必會受到同儕的影響,而且什麼都想做,就是不想當上班族。
二十世紀初,現代繪畫正處於歷史的前期高峰,百家爭鳴,「八人組」受到孟克的表現主義與野獸派的啟發。前者致力於潛意識想像的陰森畫風,對卡夫卡的小說風格有關鍵性的影響。另一位與卡夫卡熟識的表現主義大將庫賓(Alfred Kubin),卡夫卡曾多次在日記中提到他,尤其是在1911年9月底,正好是他要完成《判決》、《蛻變》與《司爐》等作品的前一年。法國學者樂梅爾(Gérard-Georges Lemaire)的《卡夫卡與庫賓》(Kafka et Kubin, 2002)一書,即探討了庫賓畫作與卡夫卡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的關聯性。
卡夫卡的素描多是塗鴉,而且是畫在日記、筆記本或私人信件上,而非文學作品的插圖。換言之,這些作品是獨立的畫作,不是文學的圖解。卡夫卡對繪畫的喜好,可追尋到1903-05年在讀大學的時光,好友馬克斯・布羅德發現他在課堂筆記本的空白處進行塗鴉,而這份嗜好,一直持續到他過世之前的1924年。
這些畫作感覺起來像是文字的變形,如同本書附錄的〈以字母為圖〉所描述的,有些圖可能是K這個字母的變化。總而言之,這些素描多半沒有深度,缺乏陰影,毫無色彩,而是筆畫的筆觸與線條,構成作品的主要特徵。目前可能是唯一一部研究這些素描的專著《卡夫卡的觀看:一位作家的素描》(Le regard de Kafka, dessins d'un écrivain, 2002),法國學者賈克琳・蘇妲卡・貝納哲拉芙(Jacqueline Sudaka-Bénazéraf)提出以書法角度來看待這些作品,讓當代對這些遺稿如何做出詮釋,提供一道曙光。
書法是文字書寫的藝術,筆勢的氣韻生及筆觸,是我們欣賞這些作品的要點。如果以一種圖像書法的角度來看待卡夫卡的素描,首先要留意到的,是他所使用的創作工具,恰似書法一般,是寫作用的筆。由於這些畫作都是出現在書寫過程(不論是筆記、日記或信件),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卡夫卡不太可能有專屬的繪畫用筆,而是直接用正在書寫的筆進行素描。
在中國的水墨畫作中,經常搭配有畫家的題款,表述作畫緣由或感言之類,這些題款往往突破了視覺的內容,以書法的方式與畫作共存。卡夫卡的素描,則恰好是題款的顛倒。在這裡,文字是主要內容,圖畫倒成了一種題款。在水墨當中,圖像表達了一種抽象的意境,不可言傳,題款雖以語言表達,卻非被限制在對圖像的註解,而是帶離我們離開畫作,講述更多關於藝術家本人的訊息。更進一層的顛倒現象,一樣存在卡夫卡的素描當中,以語言論及個人生活的文字是主要內容(再提醒一次,這些都是日記、筆記或信件),位在邊緣的塗鴉反而不可言傳,亦非單純內容的圖解。
現在讓我們回到卡夫卡給菲莉絲畫手臂挽在一起的那封信,在畫圖之前,卡夫卡提到他夢見兩人臂挽臂走在一起(見本書44頁),然後他說:「我就是無法透過文字向妳描述在我夢裡我們是怎麼散步的!」夢中的世界已經超越卡夫卡的文字能力,他只能用圖像的方式來表達(「等等,我用畫的好了。」)同樣的,意境也往往無法以語言表達,你只能看到畫,這幅畫以圖像的方式呈現給你,激發了你的想像力――正如夢境不是用語言,而是用視覺的方式呈現給你一般。(有人作夢是夢到只有對話或文字,而沒有影像的嗎?)
《與卡夫卡對話》作者亞努赫記錄了卡夫卡晚年,有一次曾提到他對自己畫的小人素描的看法(見本書102頁),卡夫卡說:「我想要抓住人物的輪廓,可是他的透視消失點不在紙上,而在我的鉛筆沒有削尖的另一端――在我的心裡!」所以這些小人來自卡夫卡的靈魂深處,他的素描目的不在模仿客觀世界,而是出自心中的一種主觀感覺,我說不出來,找不到文字,只能用塗鴉的方式,透過我的手,去宣洩那種感覺。這就像書法不是記錄外在對象,而是記錄手的動作一樣。而且,他還說這「是個人的表意文字」,不就更肯定了我們用書法來解釋這些素描的觀點嗎?
塗鴉的過程,往往是無意識的,來源與夢很接近,所以卡夫卡對亞努赫說:「(那些小小男人)他們是來自黑暗,為的是要消失在黑暗裡。」接下來這句話最關鍵:「我的塗鴉是不斷重複而失敗的原始巫術的嘗試。」如果這是巫術,是我在進行私人反省的時候才出現的動作,那我在召喚什麼?為什麼這些塗鴉我只願給最親密的自己、情人與好友看?我想把這兩個問題留給讀者思考,開啟與卡夫卡的對話過程。
卡夫卡的素描是他最私密的創作,甚至超越了他的日記與書信,是遺稿中的遺稿。這些遺稿代表他在文學創作之外的另一項熱情,即使這個熱情沒有被適當開展。卡夫卡就像難忘年輕時搞團的上班族,總會不時回到他最初的嗜好,偶爾彈兩下吉他。(「這些素描是很久以前的、深深烙印在心裡的熱情的痕跡。」)
這些素描與卡夫卡的文學寫作之間,亦存在平行關係。我們知道,卡夫卡多數作品都是殘篇,而且有大量短篇或札記,都是未完稿且未考慮出版的,可說是一種文學塗鴉。若以未完成的角度來看,他大多作品都是失敗的。但正是這些不斷失敗的嘗試,不論是文學或繪畫上的,卡夫卡以一種失敗者的獻身,拉近了我們與他的距離,照亮了這些作品。班雅明說:「再也沒什麼事情,比卡夫卡強調自己失敗時的狂熱,更令人難忘。」
卡夫卡的圖像書法源自他對失敗的熱情,那股狂熱就保留在不斷重複的塗鴉筆觸當中,永不燃盡。
本文作者目前為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臺北藝術大學與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曾選編與譯註卡夫卡的《給菲莉絲的情書》
推薦序
施舜翔
卡夫卡的自戀凝視與愛情藝/囈語
卡夫卡的人物素描:思考者、牢籠中的人與饑餓的藝術家
卡夫卡連素描都如此卡夫卡。卡夫卡那噩夢式的現實書寫已被定義為「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文字風格。這邊我們也可以說,這些線條簡單抽象、描繪日常生活場景卻又詭奇變形的素描作品,也非常「卡夫卡式」。
卡夫卡的這四十一幅素描可以大致分為幾類:抽象人物素描(又被稱為「六個小黑人」)、單一地點、生活場景,以及城市小人物。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抽象人物素描。這些素描雖然線條極其簡單,卻透露出卡夫卡最深的哲學思維。我在六個小黑人中,尋到的發現的都是卡夫卡的文字蹤跡。
〈思考者〉中的男人,與其說在進行理性思考,不如說沉思是一個永恆的姿態,沒有終點,就像卡夫卡在寫給菲莉絲的情書中所說的:「連貫、循序漸進的思考對我來說還是完全不可能的。」卡夫卡畫筆下的思考者,是對理性體制下的線性思考,一個最大的挑戰。
而〈牢籠中的人〉則讓我想起卡夫卡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審判》(The Trial),那個被看似理性實則荒謬的法律體制給困住的約瑟夫K。卡夫卡在1920年1月13日的日記中寫下:「囚徒其實是自由之身,他可以參與一切,籠外的一切都逃不過他的注意,他大可以離開牢籠,畢竟柵欄間隔幾公尺遠,根本沒人將他囚禁在內。」這段日記正好呼應了卡夫卡在《審判》中所寫的「法律之門」寓言。在這個寓言中,法律之門大開,鄉下人卻無法進去,守門人對鄉下人說「你現在不能進去」。鄉下人於是在這扇敞開卻無法進入的法律之門前耗盡一生。等到他即將死去前,鄉下人問守門人,為什麼都沒有其他人嘗試進入?守門人表示:「這扇門是專門為你設的,但現在我要將它關上了。」鄉下人然後死去。
鄉下人就是卡夫卡畫筆下的牢籠中的人。鄉下人其實是「自由」的,卻將自己的一生耗在這個操弄著理性語言卻無法讓你進入的荒謬體制中。也就是說,如卡夫卡日記所寫,「他大可以離開牢籠。」鄉下人看法律之門敞開,天真地以為它真允許所有人進入,而他對這個荒謬司法體制的天真信任,也造成了他的死亡。
另一幅讓我想起卡夫卡文字的,是〈沒有胃口〉這幅素描。這幅圖抽象到看不出人形,卻也是這樣的「不見人形」,讓我想起卡夫卡筆下那個找不到喜歡的食物的藝術家。〈饑餓的藝術家〉(A Hunger Artist)是卡夫卡在192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故事寫的是一個以「饑餓」作為展示藝術的藝術家。人們問他為何不進食?他表示自己「找不到喜歡吃的東西」。饑餓的藝術家後來自然是餓死了,臨死前,雙唇卻輕輕噘起,彷彿在向那些殘酷的觀者索吻。
說到底,卡夫卡也跟饑餓的藝術家一樣,終其一生,尋著的只是那一個吻。
卡夫卡的愛情素描:情書、囈語,以及臂挽著臂散步
在這幾幅素描中,有兩幅特別不同,它們在訴說愛情:〈臂挽著臂散步〉。這兩幅圖直接取自卡夫卡寫給菲莉絲的情書。他用畫訴情,用畫勾勒夢境中兩人牽手漫步的模樣,像是以這兩幅線條簡單的素描在對菲莉絲說:其他人都是臂挽著臂散步,而我與妳卻是手牽著手;這是我能夠給你,最與眾不同的愛,以及最親密的溫度。卡夫卡的情書與其說是寫給情人看的,不如說是自己的囈語,即使是後來寫給米蓮娜的情書,卡夫卡永遠像是在自言自語,就像這一幅幅素描一樣。這些囈語是最脆弱也最溫柔的。
1914年,卡夫卡與自己深愛的菲莉絲曾經訂婚,最後這樁婚事卻被臨時取消,卡夫卡也被菲莉絲的家人與好友進行了一次「審判」。(1) 失去了對婚姻體制信任的卡夫卡,寫成了《審判》一書。在1920年寫給米蓮娜的信中,卡夫卡表示:「第一次訂婚已成過往雲煙,第二次訂婚還存在著,但由於對結婚沒有任何指望,因此可以說這份婚約已經死了。」(2) 那些囈語中極其脆弱的溫柔的愛,終究敵不過婚姻體制的冷酷摧殘,還來不及發出聲音就死了。
於是我也重讀了一次《審判》。原來這真的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而故事中那些入侵的強取豪奪的操弄荒謬體制下理性語言的,最終都成為了阻絕了愛的。
原來愛情才是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輕。
卡夫卡的自畫像:自戀、自憐與破碎的鏡像
卡夫卡素描中最使我心疼的,是最後那幅自畫像。他曾在寫給菲莉絲的情書中,附上一張自己的照片。沒有自戀自誇自吹自捧,反而充滿自卑自憐自貶自抑。他說:「我會寄張照片給你,那張照片真叫人反感……總而言之,我只求你不要被這張照片嚇壞。」這個自卑又自憐的男子,跟情書中那個小心翼翼地溫柔囈語的男子,同樣敏感、脆弱、溫柔,害怕卻又迷戀自己最卑微的模樣。
卡夫卡的自畫像不是一種理想鏡像。相反的,那是他自戀又自憐的破碎鏡像。透過自我素描,自我繪畫,他看到了某個殘破不堪的自己。那個被冷酷體制排斥在外的自己,那個被荒謬的理性語言折磨的自己,那個饑餓卻又等待一個溫柔的吻的自己,以及那個,想要在身旁手挽著手的群眾之中,與戀人手牽著手,感受到最親密的溫度的自己。
(1) 請見鍾英彥〈愛情中的孤獨與審判:卡夫卡創作《審判》的情感背景〉。收錄於《審判》。台北:漫步文化,2014年。300-303頁。
(2) 請見法蘭茲˙卡夫卡著。彤雅立、黃鈺娟譯。《給米蓮娜的信:卡夫卡的愛情書簡》。台北:書林,2008年。14頁。卡夫卡此信中的第一次訂婚指的就是菲莉絲,第二次訂婚指的是1919年的戀人茱莉˙沃里契克。
本文作者為《女人迷》與《主場新聞》專欄作家,「後女性的魔鏡夢遊」版主,國立政治大學英國文學碩士
耿一偉
遺稿中的遺稿――卡夫卡的圖像書法
“What can be shown, cannot be said”
――哲學家維根斯坦
卡夫卡在1913年2月11/12日給菲莉絲的情書中,畫了兩張手臂挽在一起的小圖(見本書44頁),隨後他在信中寫道:「妳喜歡我的塗鴉嗎?我曾是個不錯的工匠,妳知道的,但後來我參加學院派的繪畫課程後,碰到一位十分差勁的女性畫家,她幾乎毀了我的天份。想想看,那多可怕!但請耐心期待,過幾天我會寄給妳幾張我的畫,讓妳有些素材可以嘲笑。這些圖畫曾帶給我極大的滿足――那是幾年前――沒有任何事物比得上。」
讓我們先分析這段文字,卡夫卡對自己的素描頗為自信(「妳喜歡我的塗鴉嗎?」),表示自己上還過繪畫課,只是學院派的教育破壞了他對繪畫本有的天份。想像你在追求某個對象,接著你秀出以前彈的吉他錄音,然後說,其實我以前吉他彈得還不錯,都是被別人害的(「想想看,那多可怕!」)――這背後的潛台詞是,我曾有一項非常珍貴的特質,後來被別人毀了,但我想讓你知道我曾有那麼棒過(這有點像在臉書放以前很瘦的照片)。
從這角度來觀察,可以想見卡夫卡在寫給追求對象的情書中,忽然秀出自己的塗鴉技巧時,他幾乎已經是在亮底牌了。這段文字的最後,卡夫卡強調繪畫曾帶給他的滿足(「沒有任何事物比得上」),我們可以猜測,在他還沒有決定走向文學之路前,繪畫也是他人生的一個選項。寫這封信時,卡夫卡剛好三十歲,三十而立的他,已經完成《判決》、《蛻變》與《司爐》等重要作品,他的人生之路已經確定,文學是他的志業。
但在1906-7年左右(「那是幾年前」),他對視覺藝術產生了某種狂熱(「這些圖畫曾帶給我極大的滿足」),一方面是他正受到福樓拜的影響,另一方面是他與一群新生代的捷克畫家有密切往來。福樓拜的《情感教育》是影響卡夫卡極重要的一部小說,作品中大量視覺描述而非內心感受的自然主義文學技巧,可能刺激卡夫卡在文學初期的道路上,轉向繪畫以吸取養分。這有點像宋朝詩人陸遊說的:「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
卡夫卡與捷克畫派「八人組」(Osma)的交往,在本書附錄的〈卡夫卡:一個偉大的素描畫家〉一文中,已有詳盡交代。另一篇〈一段小插曲〉談到卡夫卡原有一張畫要給馬克斯・布羅德的新書當封面的軼事,也是在1907年這段繪畫高峰期。這時候卡夫卡的歲數,大概是25歲,是他於1906年拿到法學博士開始在法院實習的階段(1906-07)。這是剛從學校離開準備就業的年齡,卡夫卡還在尋找人生的目標。而且很明顯,法院工作不會是他喜歡的。如同所有文藝青年一樣,卡夫卡勢必會受到同儕的影響,而且什麼都想做,就是不想當上班族。
二十世紀初,現代繪畫正處於歷史的前期高峰,百家爭鳴,「八人組」受到孟克的表現主義與野獸派的啟發。前者致力於潛意識想像的陰森畫風,對卡夫卡的小說風格有關鍵性的影響。另一位與卡夫卡熟識的表現主義大將庫賓(Alfred Kubin),卡夫卡曾多次在日記中提到他,尤其是在1911年9月底,正好是他要完成《判決》、《蛻變》與《司爐》等作品的前一年。法國學者樂梅爾(Gérard-Georges Lemaire)的《卡夫卡與庫賓》(Kafka et Kubin, 2002)一書,即探討了庫賓畫作與卡夫卡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的關聯性。
卡夫卡的素描多是塗鴉,而且是畫在日記、筆記本或私人信件上,而非文學作品的插圖。換言之,這些作品是獨立的畫作,不是文學的圖解。卡夫卡對繪畫的喜好,可追尋到1903-05年在讀大學的時光,好友馬克斯・布羅德發現他在課堂筆記本的空白處進行塗鴉,而這份嗜好,一直持續到他過世之前的1924年。
這些畫作感覺起來像是文字的變形,如同本書附錄的〈以字母為圖〉所描述的,有些圖可能是K這個字母的變化。總而言之,這些素描多半沒有深度,缺乏陰影,毫無色彩,而是筆畫的筆觸與線條,構成作品的主要特徵。目前可能是唯一一部研究這些素描的專著《卡夫卡的觀看:一位作家的素描》(Le regard de Kafka, dessins d'un écrivain, 2002),法國學者賈克琳・蘇妲卡・貝納哲拉芙(Jacqueline Sudaka-Bénazéraf)提出以書法角度來看待這些作品,讓當代對這些遺稿如何做出詮釋,提供一道曙光。
書法是文字書寫的藝術,筆勢的氣韻生及筆觸,是我們欣賞這些作品的要點。如果以一種圖像書法的角度來看待卡夫卡的素描,首先要留意到的,是他所使用的創作工具,恰似書法一般,是寫作用的筆。由於這些畫作都是出現在書寫過程(不論是筆記、日記或信件),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卡夫卡不太可能有專屬的繪畫用筆,而是直接用正在書寫的筆進行素描。
在中國的水墨畫作中,經常搭配有畫家的題款,表述作畫緣由或感言之類,這些題款往往突破了視覺的內容,以書法的方式與畫作共存。卡夫卡的素描,則恰好是題款的顛倒。在這裡,文字是主要內容,圖畫倒成了一種題款。在水墨當中,圖像表達了一種抽象的意境,不可言傳,題款雖以語言表達,卻非被限制在對圖像的註解,而是帶離我們離開畫作,講述更多關於藝術家本人的訊息。更進一層的顛倒現象,一樣存在卡夫卡的素描當中,以語言論及個人生活的文字是主要內容(再提醒一次,這些都是日記、筆記或信件),位在邊緣的塗鴉反而不可言傳,亦非單純內容的圖解。
現在讓我們回到卡夫卡給菲莉絲畫手臂挽在一起的那封信,在畫圖之前,卡夫卡提到他夢見兩人臂挽臂走在一起(見本書44頁),然後他說:「我就是無法透過文字向妳描述在我夢裡我們是怎麼散步的!」夢中的世界已經超越卡夫卡的文字能力,他只能用圖像的方式來表達(「等等,我用畫的好了。」)同樣的,意境也往往無法以語言表達,你只能看到畫,這幅畫以圖像的方式呈現給你,激發了你的想像力――正如夢境不是用語言,而是用視覺的方式呈現給你一般。(有人作夢是夢到只有對話或文字,而沒有影像的嗎?)
《與卡夫卡對話》作者亞努赫記錄了卡夫卡晚年,有一次曾提到他對自己畫的小人素描的看法(見本書102頁),卡夫卡說:「我想要抓住人物的輪廓,可是他的透視消失點不在紙上,而在我的鉛筆沒有削尖的另一端――在我的心裡!」所以這些小人來自卡夫卡的靈魂深處,他的素描目的不在模仿客觀世界,而是出自心中的一種主觀感覺,我說不出來,找不到文字,只能用塗鴉的方式,透過我的手,去宣洩那種感覺。這就像書法不是記錄外在對象,而是記錄手的動作一樣。而且,他還說這「是個人的表意文字」,不就更肯定了我們用書法來解釋這些素描的觀點嗎?
塗鴉的過程,往往是無意識的,來源與夢很接近,所以卡夫卡對亞努赫說:「(那些小小男人)他們是來自黑暗,為的是要消失在黑暗裡。」接下來這句話最關鍵:「我的塗鴉是不斷重複而失敗的原始巫術的嘗試。」如果這是巫術,是我在進行私人反省的時候才出現的動作,那我在召喚什麼?為什麼這些塗鴉我只願給最親密的自己、情人與好友看?我想把這兩個問題留給讀者思考,開啟與卡夫卡的對話過程。
卡夫卡的素描是他最私密的創作,甚至超越了他的日記與書信,是遺稿中的遺稿。這些遺稿代表他在文學創作之外的另一項熱情,即使這個熱情沒有被適當開展。卡夫卡就像難忘年輕時搞團的上班族,總會不時回到他最初的嗜好,偶爾彈兩下吉他。(「這些素描是很久以前的、深深烙印在心裡的熱情的痕跡。」)
這些素描與卡夫卡的文學寫作之間,亦存在平行關係。我們知道,卡夫卡多數作品都是殘篇,而且有大量短篇或札記,都是未完稿且未考慮出版的,可說是一種文學塗鴉。若以未完成的角度來看,他大多作品都是失敗的。但正是這些不斷失敗的嘗試,不論是文學或繪畫上的,卡夫卡以一種失敗者的獻身,拉近了我們與他的距離,照亮了這些作品。班雅明說:「再也沒什麼事情,比卡夫卡強調自己失敗時的狂熱,更令人難忘。」
卡夫卡的圖像書法源自他對失敗的熱情,那股狂熱就保留在不斷重複的塗鴉筆觸當中,永不燃盡。
本文作者目前為臺北藝術節藝術總監,臺北藝術大學與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助理教授,曾選編與譯註卡夫卡的《給菲莉絲的情書》
推薦序
施舜翔
卡夫卡的自戀凝視與愛情藝/囈語
卡夫卡的人物素描:思考者、牢籠中的人與饑餓的藝術家
卡夫卡連素描都如此卡夫卡。卡夫卡那噩夢式的現實書寫已被定義為「卡夫卡式」(Kafkaesque)的文字風格。這邊我們也可以說,這些線條簡單抽象、描繪日常生活場景卻又詭奇變形的素描作品,也非常「卡夫卡式」。
卡夫卡的這四十一幅素描可以大致分為幾類:抽象人物素描(又被稱為「六個小黑人」)、單一地點、生活場景,以及城市小人物。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抽象人物素描。這些素描雖然線條極其簡單,卻透露出卡夫卡最深的哲學思維。我在六個小黑人中,尋到的發現的都是卡夫卡的文字蹤跡。
〈思考者〉中的男人,與其說在進行理性思考,不如說沉思是一個永恆的姿態,沒有終點,就像卡夫卡在寫給菲莉絲的情書中所說的:「連貫、循序漸進的思考對我來說還是完全不可能的。」卡夫卡畫筆下的思考者,是對理性體制下的線性思考,一個最大的挑戰。
而〈牢籠中的人〉則讓我想起卡夫卡最有名的著作之一《審判》(The Trial),那個被看似理性實則荒謬的法律體制給困住的約瑟夫K。卡夫卡在1920年1月13日的日記中寫下:「囚徒其實是自由之身,他可以參與一切,籠外的一切都逃不過他的注意,他大可以離開牢籠,畢竟柵欄間隔幾公尺遠,根本沒人將他囚禁在內。」這段日記正好呼應了卡夫卡在《審判》中所寫的「法律之門」寓言。在這個寓言中,法律之門大開,鄉下人卻無法進去,守門人對鄉下人說「你現在不能進去」。鄉下人於是在這扇敞開卻無法進入的法律之門前耗盡一生。等到他即將死去前,鄉下人問守門人,為什麼都沒有其他人嘗試進入?守門人表示:「這扇門是專門為你設的,但現在我要將它關上了。」鄉下人然後死去。
鄉下人就是卡夫卡畫筆下的牢籠中的人。鄉下人其實是「自由」的,卻將自己的一生耗在這個操弄著理性語言卻無法讓你進入的荒謬體制中。也就是說,如卡夫卡日記所寫,「他大可以離開牢籠。」鄉下人看法律之門敞開,天真地以為它真允許所有人進入,而他對這個荒謬司法體制的天真信任,也造成了他的死亡。
另一幅讓我想起卡夫卡文字的,是〈沒有胃口〉這幅素描。這幅圖抽象到看不出人形,卻也是這樣的「不見人形」,讓我想起卡夫卡筆下那個找不到喜歡的食物的藝術家。〈饑餓的藝術家〉(A Hunger Artist)是卡夫卡在192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故事寫的是一個以「饑餓」作為展示藝術的藝術家。人們問他為何不進食?他表示自己「找不到喜歡吃的東西」。饑餓的藝術家後來自然是餓死了,臨死前,雙唇卻輕輕噘起,彷彿在向那些殘酷的觀者索吻。
說到底,卡夫卡也跟饑餓的藝術家一樣,終其一生,尋著的只是那一個吻。
卡夫卡的愛情素描:情書、囈語,以及臂挽著臂散步
在這幾幅素描中,有兩幅特別不同,它們在訴說愛情:〈臂挽著臂散步〉。這兩幅圖直接取自卡夫卡寫給菲莉絲的情書。他用畫訴情,用畫勾勒夢境中兩人牽手漫步的模樣,像是以這兩幅線條簡單的素描在對菲莉絲說:其他人都是臂挽著臂散步,而我與妳卻是手牽著手;這是我能夠給你,最與眾不同的愛,以及最親密的溫度。卡夫卡的情書與其說是寫給情人看的,不如說是自己的囈語,即使是後來寫給米蓮娜的情書,卡夫卡永遠像是在自言自語,就像這一幅幅素描一樣。這些囈語是最脆弱也最溫柔的。
1914年,卡夫卡與自己深愛的菲莉絲曾經訂婚,最後這樁婚事卻被臨時取消,卡夫卡也被菲莉絲的家人與好友進行了一次「審判」。(1) 失去了對婚姻體制信任的卡夫卡,寫成了《審判》一書。在1920年寫給米蓮娜的信中,卡夫卡表示:「第一次訂婚已成過往雲煙,第二次訂婚還存在著,但由於對結婚沒有任何指望,因此可以說這份婚約已經死了。」(2) 那些囈語中極其脆弱的溫柔的愛,終究敵不過婚姻體制的冷酷摧殘,還來不及發出聲音就死了。
於是我也重讀了一次《審判》。原來這真的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愛情故事。而故事中那些入侵的強取豪奪的操弄荒謬體制下理性語言的,最終都成為了阻絕了愛的。
原來愛情才是生命中最不能承受之輕。
卡夫卡的自畫像:自戀、自憐與破碎的鏡像
卡夫卡素描中最使我心疼的,是最後那幅自畫像。他曾在寫給菲莉絲的情書中,附上一張自己的照片。沒有自戀自誇自吹自捧,反而充滿自卑自憐自貶自抑。他說:「我會寄張照片給你,那張照片真叫人反感……總而言之,我只求你不要被這張照片嚇壞。」這個自卑又自憐的男子,跟情書中那個小心翼翼地溫柔囈語的男子,同樣敏感、脆弱、溫柔,害怕卻又迷戀自己最卑微的模樣。
卡夫卡的自畫像不是一種理想鏡像。相反的,那是他自戀又自憐的破碎鏡像。透過自我素描,自我繪畫,他看到了某個殘破不堪的自己。那個被冷酷體制排斥在外的自己,那個被荒謬的理性語言折磨的自己,那個饑餓卻又等待一個溫柔的吻的自己,以及那個,想要在身旁手挽著手的群眾之中,與戀人手牽著手,感受到最親密的溫度的自己。
(1) 請見鍾英彥〈愛情中的孤獨與審判:卡夫卡創作《審判》的情感背景〉。收錄於《審判》。台北:漫步文化,2014年。300-303頁。
(2) 請見法蘭茲˙卡夫卡著。彤雅立、黃鈺娟譯。《給米蓮娜的信:卡夫卡的愛情書簡》。台北:書林,2008年。14頁。卡夫卡此信中的第一次訂婚指的就是菲莉絲,第二次訂婚指的是1919年的戀人茱莉˙沃里契克。
本文作者為《女人迷》與《主場新聞》專欄作家,「後女性的魔鏡夢遊」版主,國立政治大學英國文學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