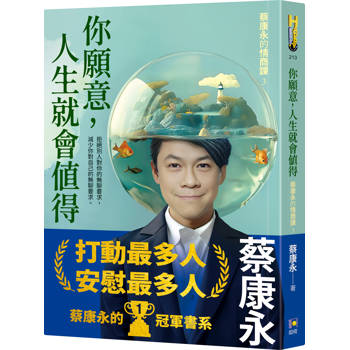名人推薦:
「我愛這本書。其中有一部分是求生者的回憶錄,另一部分則是寫給大自然的情書,而我被它深深吸引。」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茱麗亞‧希爾里茲
「這是一本引人入勝的回憶錄,崔西‧羅斯在描述自己因為隱晦的祕密及被深埋的傷口,而一路走來斑斑傷痕的生命時,表現非常堅毅坦率,在她摯愛的荒野中,我們為她得來不易的自信與平靜的原諒感到欣喜。當你闔上它時,故事仍縈繞你心,久久無法散去。」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瑪麗‧蒙蘿
「在這本勇敢的回憶錄中,崔西‧羅斯具體呈現了──當童年的性侵傷口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惡化時,一定會起作用的脫序行為,最終將迸發成自我毀滅和危險的行為。直到羅斯終於知道真相,進而開始療癒。在說到她的真實故事時,雖然可能讓自己招致責難,但卻有助於療癒其他人。」
──作家 珍寧‧拉特絲
「崔西‧羅斯無畏無懼。她面對了童年時期的黑暗本質,並將它寫成一部回憶錄,它吸引你、讓你心碎,最後對你詠唱。重要的是,你會很高興她活下來寫了這本發人深省以及動容的著作。」
──作家 克萊兒•戴德勒
「這本動人的書充滿大大的悲傷和小小的喜悅。若說要在崔西之外還有其他主角,那就是整個大自然,它包容無限的療癒力和輔引,會讓人深刻體悟及寬容表面上的那些困苦與艱難。」
──美國外展教育理事長兼總裁 約翰‧李德
推薦序:荒野正適花重生
精神科醫師、荒野保護協會解說員 陳俊霖
我國幸由法律的規範,未成年人一旦遭受性侵害,知情的相關工作人員必須通報社會局的力量介入,必要時緊急安置,幫助受害人儘速脫離受虐的環境。這彷彿遙遠的電影情節,二○一一年內政部統計的通報人數達兩千三百四十八人,但根據多年來從事兒童性侵害輔導工作最力的勵馨基金會估計,未報的案件往往多達通報案件的七倍以上。
救援不但是一項人權措施,也是個重要的心理衛生工作。許多研究顯示童年性侵害與長大後出現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傷害等心理衛生議題都有關連。而這類受害者,一則年齡尚輕,二則此類案情在本質上就難以啟齒,即便有幸接受正式的心理治療,要在傳統口談治療中陳述過程或描述情感,總是困難重重。目前縱有沙遊治療、藝術治療等非語言的模式協助療癒,仍往往趕不上陰影在內心擴散的速度。
本書的作者崔西.羅斯(Tracy Ross)就是這樣一位在八歲時受到繼父性侵害的女性。難得她同時具有細膩的省思和文筆,以及回首當年的勇氣,描繪了這件創傷如何在一個小女孩心裏糾纏、發酵、腐爛、又重新昇華的過程。尤其身為加害人的繼父,曾經是帶著她在自然荒野中享受野營和打獵樂趣的好父親,更是她母親在作者生父意外死亡後最大的依靠,而非自始就無惡不赦的暴徒,更讓作者因為年少本就不知如何面對侵犯的困惑,混雜了對繼父愛恨交織的感情,和造成全家幸福破碎的罪疚,如此混雜難理的情緒,就此化為青少年時自我墮落的漩渦。作者在此書中將此切身之痛娓娓道來,是心理衛生工作者學習同理此類案主難得的素材。
隨著作者透過寫作、戲劇來發揮創作的能量,以及投身荒野懷抱進行冒險式的遁走,抑或透過感情、瑜伽、心理治療、精神醫療等方式,她童年的傷痛,彷彿一次次獲得療復,卻又一次次地像海浪般重新捲來。如此真實的起伏,隨著篇章的鋪陳,讓人才鬆了口氣不久,心情又得隨著新的情節下沉。以作者的勇氣和努力,療癒之路竟已如此艱難,在真實世界裏,更多的受害人甚至無法觸及治療資源,其心中的痛楚到底多久多深,更讓人不忍想像。
在作者諸多的療癒嘗試中,有一個深厚的力量卻是來自自然荒野。自然荒野既是她和繼父童年歡樂時光的所在,也是她第一次心靈受創的刀砧,更是她日後流浪、逃避、沉澱、和重新獲得能量的聖堂,最後更成為她自救儀式的祭壇。恐怕真也只有廣闊的自然荒野,才有足夠的能量去承載如此複雜的情感。
事實上,美國的確發展出「荒野治療」(wilderness therapy)與「冒險治療」(adventure therapy)等新的心理工作模式。書中作者打工帶領青少年的基金會,即屬於此種組織,只不過算是手法比較強烈的。國內則有「亞洲體驗教育學會」最積極引進推動冒險輔動,另有如「都市人基金會」等宗教或公益團體,陸續曾引用冒險輔導的方式來幫助受害少女。
崔西雖曾在進行荒野治療的基金會打工幫助其他少年,但她對自己的「荒野治療」,則是一路在生命中點點滴滴地曳進。雖然大部分的人都認同大自然是療傷的好地方,但基於專業的好奇,我努力想體會那一段一段深入荒野的經歷,究竟是如何對作者產生「療效」?是成為她逃離傷心文明社會的避難所?還是讓她走過個體化歷程的神聖空間?尤其在她婚姻分合的緊要關頭,竟相隔千里遇到多年前舊識的一條狗,讓我驚異於榮格(Jung)學說中極具療效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就這樣精準地敲在她命運的轉捩點上。
然而,即便命運之河似乎就此流出坎坷山崖,奔向寬廣平原,未來卻依然一波三折,且待讀者親自讀完全書。
作者來回穿梭在荒野旅行與性侵陰影間的對話,讓全書更同時呼應著生態心理學(ecopsychology)將自然與心靈交織印證的韻味,亦提醒了我們,當代被虐待/濫用(abuse)因而亟待療復(healing)的,又豈只是人類的心靈而已?人類的心靈的確常可從自然荒野中獲得療癒,但正如生態心理學想提醒人類的,若如此深具療癒能量的自然荒野消失了,將不只是生態科學上的浩劫,更會讓人類的心靈永遠地失根。「Green the Mind; Mind the Green.」或許才是人類心靈與荒野大地共同的救贖。
推薦序:重建,始於徹底的崩壞
身心靈領域新銳作家 陳卓君
每個人在成長的路上,可能遭逢過或大或小的考驗、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外在壓力或埋藏在內心的未知陰影,但大部分的人們為了維持日復一日的生活步調,選擇了忽視這些傷痛所帶來的潛在威力。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若不是荒野,我不會活下去》的作者崔西‧羅斯一般,有勇氣揭開傷痛的真實面貌。童年時期被自己最信任的繼父性侵的崔西,透過力求客觀的文字剖析自己的成長過程,細述自己如何從對父親的愛與恨的矛盾情緒中解放,讓這看來永遠無法被原諒的傷害成為自我成長的正面能量。
大部分童年受創的孩童,為了讓自己能夠繼續在家庭中生存,會選擇用自責來合理化遭受到傷害的正當性,尤其是在面對來自親人的傷害,這種「一定是我不好,所以才會有這種懲罰」的念頭更為強烈。在書中,崔西不只一次的提到她對父親的愛,但對於伸出狼爪的父親又有滿滿的怨恨,加上母親刻意漠視崔西的求救,讓她只有用「是我自己不好」的藉口才能解除這種愛恨交織的矛盾壓力。
然而自責的背後,往往深藏著內在價值被忽略的缺憾,為了生存,受創的孩童會尋求其他的替代方式來彌補。崔西用了各種荒唐的叛逆行徑,如吸毒等,藉由自甘墮落的方式麻醉自己,彷彿只有這樣,才能從面對血淋淋的家庭泥沼中掙脫,但越是這樣上癮式的自溺,卻越讓崔西陷入更深的自卑與恐懼──不相信愛,也無法愛人,甚至絕望地想用自我了斷來逃離關於家的桎梏。關於崔西熟悉的生活圈,正快速的崩壞中。
本書之所以打動人心,是因為崔西不只讓人生故事停留在過往傷害和隨之而來的負面後座力,也不讓自己只是沉溺於自憐自艾中,而是用她堅毅的勇氣突破心魔、找出那深藏於心缺憾,用正面的力量去擁抱曾經傷害過她的人。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巧合,曾讓崔西受到傷害的荒野之地,在過了許多年之後,成了她療癒傷痛的重生之地。從大自然的山林中找到力量,拋開外人眼中叛逆、放蕩不羈的偏差生活型態,直搗內心最深處,發現外在的放縱,其實是來自於從來都沒被好好對待的內心傷痛,隨著時間累積成了對抗自我的反撲力量。透過參加戶外營隊接觸原始自然、嘗試為人付出的過程,重新正視自己的傷口,讓心重獲安適。
從崔西身上,我看到了勇於改寫生命故事的毅力。我們不需比較誰的生命中所受的傷痛比較重、比較久,只要那傷痛在你長大成人之後變成吸附所有負面能量與造成身心症的根源,我們都應該鼓起勇氣向自己坦承「我曾經受了傷,我需要修復過去的自己」,而不是不斷用自己的未來複製過去的傷痛,甚至把自己童年的痛帶到自己的下一代。除非能從自身找到愛自己的力量,否則單依靠外在的人、事、物轉移注意力,例如瘋狂工作、不停換伴侶、大肆採購等形而上的宣洩,終究會被捲入過往的黑洞中而無法自拔。
我們或許無法選擇原生家庭,也或許在年幼時無法抵抗大人們對我們的傷害,但是長大後,自己卻是自己生命的唯一主宰。我們都沒有任何藉口把現在所遭遇的不幸歸咎在過去無法改變的事實,而是學習崔西為生命找出路的方式療癒自己,因為每個人都有資格為自己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與快樂。書末,崔西從過往釋放與擁抱當前幸福實例,證明了來自於內心、相信自己、原諒自己的信念,是改寫過去與未來生命的最大力量。
如果,你正處於崩壞中而不自知,或是崩壞後正等待重建自己,希望你能從這本書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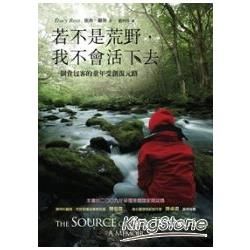
 共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