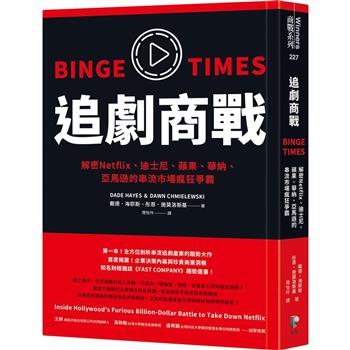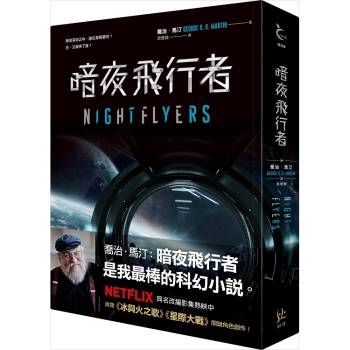細讀東坡,不只為了章句考據與注釋,更是希望了解為什麼他的心靈得到了自由解放, 為什麼他能悲天憫人、超越其身處的時代困境, 千載之下,仍然讓我們欽仰敬佩。讀到他的詩文,如沐春風。
本書收錄了著名學者、作家、書法家鄭培凱教授近年來發表的關於蘇東坡的散文,題材涉及詩書、飲饌、登臨、交遊、為官等,從中可以窺見蘇東坡在不同時期的人生態度與創作特點。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幾度斜暉蘇東坡的圖書 |
 |
$ 296 ~ 396 | 幾度斜暉蘇東坡
作者:鄭培凱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23-01-04 語言:繁體書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4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蘇東坡
 蘇軾,眉州眉山人,北宋時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醫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鐵冠道人。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南宋理學方熾時,加賜諡號文忠,複追贈太師。有《東坡先生大全集》及《東坡樂府》詞集傳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編有《蘇文忠公全集》。
蘇軾,眉州眉山人,北宋時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醫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鐵冠道人。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南宋理學方熾時,加賜諡號文忠,複追贈太師。有《東坡先生大全集》及《東坡樂府》詞集傳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編有《蘇文忠公全集》。 其散文、詩、詞、賦均有成就,且善書法和繪畫,是文學藝術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認韻文散文造詣皆比較傑出的大家。蘇軾的散文為唐宋四家之末,與唐代的古文運動發起者韓愈並稱為「韓潮蘇海」,也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更與父親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蘇軾之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又與陸游並稱「蘇陸」;其詞「以詩入詞」,首開詞壇「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來綺靡的西崑體餘風。後世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惟蘇軾故作豪放,其實清朗;其賦亦頗有名氣,最知名者為貶謫期間借題發揮寫的前後《赤壁賦》。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現其文命題之考試,故當時學者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嚼菜羹」。藝術方面,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北宋四大書法家之首;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並在題畫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政治上,在王安石變法期間,雖贊同政治應該改革,但反對王安石任用的後任呂惠卿及一些政策,招來新黨爪牙李定橫加陷害;後來又因反對「盡廢新法」受到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斥退,終生當不了宰相。在新舊黨爭中兩邊不討好導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雲戲稱為「一肚皮不合時宜」。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書;宋哲宗紹聖復述又加貶謫至儋州;徽宗即位,遇赦北歸時病卒於常州。墓在河南郟縣。
![]()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幾度斜暉蘇東坡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鄭培凱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臺灣大學、新竹清華等校,1998 年到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原任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現任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香港集古學社社長、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台灣逢甲大學特約講座教授。2016年獲頒香港政府榮譽勛章。
著作所涉學術範圍甚廣,以文化意識史、文化審美、經典翻譯及文化變遷與交流為主。近作有《湯顯祖:戲夢人生與文化求索》《多元文化與審美情趣》《歷史人物與文化變遷》《文化審美與藝術鑒賞》《遨遊于藝》等。
鄭培凱
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於紐約州立大學、耶魯大學、佩斯大學、臺灣大學、新竹清華等校,1998 年到香港城市大學創立中國文化中心。原任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現任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香港集古學社社長、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台灣逢甲大學特約講座教授。2016年獲頒香港政府榮譽勛章。
著作所涉學術範圍甚廣,以文化意識史、文化審美、經典翻譯及文化變遷與交流為主。近作有《湯顯祖:戲夢人生與文化求索》《多元文化與審美情趣》《歷史人物與文化變遷》《文化審美與藝術鑒賞》《遨遊于藝》等。
目錄
推薦序(陳萬雄)/4
自序/8
輯一 佳趣
東坡詠西湖/ 18
陌上花開/ 25
從來佳茗似佳人/ 30
白土與擂茶/ 34
蘇軾品泉/ 37
詩詠天下第四水/ 45
蘇東坡黃州種茶/ 49
黃州驚艷/ 52
蘇東坡好酒/ 55
蘇軾吃素不殺生? / 58
蘇東坡祈雨禱晴/ 85
輯二 幽人
雪泥鴻爪/ 106
三過蘇州識閭丘/ 109
三瑞堂「惡」詩/ 121
蘇軾過陳州/ 130
蘇軾的《梅花二首》/ 133
蘇軾謝上表/ 136
黃州幽人蘇東坡/ 143
蘇軾夢迴蘇州/ 146
寒食雨之後/ 153
東坡與誰遊赤壁/ 159
舉報蘇東坡/ 165
蘇東坡判案/ 168
天涯何處無芳草/ 171
輯三 書法
黃庭堅評東坡書法/ 196
蘇軾定惠院書跡/ 212
自序/8
輯一 佳趣
東坡詠西湖/ 18
陌上花開/ 25
從來佳茗似佳人/ 30
白土與擂茶/ 34
蘇軾品泉/ 37
詩詠天下第四水/ 45
蘇東坡黃州種茶/ 49
黃州驚艷/ 52
蘇東坡好酒/ 55
蘇軾吃素不殺生? / 58
蘇東坡祈雨禱晴/ 85
輯二 幽人
雪泥鴻爪/ 106
三過蘇州識閭丘/ 109
三瑞堂「惡」詩/ 121
蘇軾過陳州/ 130
蘇軾的《梅花二首》/ 133
蘇軾謝上表/ 136
黃州幽人蘇東坡/ 143
蘇軾夢迴蘇州/ 146
寒食雨之後/ 153
東坡與誰遊赤壁/ 159
舉報蘇東坡/ 165
蘇東坡判案/ 168
天涯何處無芳草/ 171
輯三 書法
黃庭堅評東坡書法/ 196
蘇軾定惠院書跡/ 212
序
自序
研究蘇東坡的著作,即使不是多如牛毛,也不會少於我們頭頂的三千煩惱絲,那麼,我為什麼還來湊熱鬧呢?自從蘇軾過世,宋代文人就開始搜集與注釋蘇軾的著作,捋清他的生平事跡,記述軼事,收藏書跡拓片,成績斐然。歷經元明清三代,文人墨客崇尚坡仙成風,甚至次韻遙和東坡詩詞,也樹立了東坡作為中華文化傳承的優秀典範。近代學者更以新的文學研究模式,從文學史專業的角度推崇蘇軾,使得蘇軾的文學聲名與地位直追李白杜甫,寖寖乎有並駕齊驅之勢,專著與論文也隨學術升等的要求與日俱增,到了五輛卡車也裝不下的地步了。
其實,我寫這本書,還真不是來湊熱鬧,而是有感而發。從小耳濡目染,背誦了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念奴嬌.大江東去》之後,就念茲在茲,讀其書思其人。雖然只是個人興趣,欣賞東坡文章的灑脫自然,一徑讀來,山河影路,清風朗日,但是,超過一甲子的浸潤與積澱,總還是有些揮之不去的詩情感懷,覺得自己一生經歷的波折起伏,早已在蘇軾詩文中點明道盡。退休之後有了餘暇,經常書寫東坡詩文樂府,在書法筆墨之間追摹其中意蘊,濡墨揮灑的神思想像得以升華,感到別有境界的體會,是體制內學術書寫難以企及的樂趣。2019 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困居香港烏溪沙家中兩年又半,早晚翻閱不同版本的蘇軾詩文,有如闍黎誦經,以期處變不驚,坐看雲起,對東坡心境更加有所體會。期間應海內外報刊所需,寫了長短不一的文字,在此重新匯集編輯,盡量排除餖飣考證的繁瑣論據,也算是讀東坡一甲子的心路歷程。
蘇軾(公元1037 年1 月8 日-1101 年8 月24 日),按照傳統紀年,生於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綜觀蘇軾入仕的生平,大體可以分作四個階段:
風華正茂, 詩情萬丈( 1 0 5 9 - 1 0 7 9 ),二十三到四十三歲
烏臺詩獄, 貶謫黃州( 1 0 7 9 - 1 0 8 5 ),四十三到四十九歲
朝廷重臣, 官場風波( 1 0 8 5 - 1 0 9 4 ),四十九到五十八歲
放逐嶺海,有志未伸(1094-1101),五十八到六十六歲(虛歲)
蘇軾離開四川眉山,進入仕途之後,如脫弦之箭,再也無緣回到家鄉。一生如大江東去,波濤洶湧,在北宋政壇上幾度浮沉,卻總能在萬般挫折之中,昂首前行。貶謫黃州,在烏雲密佈風狂雨暴之際,寫出「一蓑煙雨任平生」這樣的詩句,令人敬佩之餘,也給後人重要的提示,必須直面慘淡人生,而有所體悟與升華。他晚年從海南放歸,在金山寺自題畫像,回顧畢生經歷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調侃之中,對世間所謂功業,有了明澈的觀照,也給後世孜孜名利之徒,提供了一面閱世的明鏡。本書書名《幾度斜暉蘇東坡》,典出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的上闋:「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蘇軾一生寫了340 多首詞,用了 80 种詞牌,《八聲甘州》只寫過這一首。他在元祐六年(1091)離開杭州太守任,告別參寥子的時候,有感一生波濤起伏,希望能安享寧謐的晚年,寫了這闋詞,藉着與參寥子的來往,探討內心深處的詩情感觸與嚮往。然而,東坡老白首忘機,只是渺茫的心願,是曾經滄海之後的美好願望,卻也在內心深處隱約感到,不一定能夠實現。
蘇軾與參寥子交往一生,經歷了早期蘇軾從杭州到徐州、湖州做地方官,到烏臺詩獄、遭貶黃州,從風華正茂的精英,一下子打到社會底層,九死一生。之後召回朝廷,擔任翰林學士,參與朝廷政策的決議,後來又外放杭州、潁州、揚州,一路走來,都有參寥子這個方外知己相隨。甚至到了再次遭貶,流放到嶺南,到海南,參寥子還想去看他,被蘇軾勸阻,才未成行。這首《八聲甘州》寫於蘇軾經歷了烏臺詩獄與黃州貶謫,在離開杭州十五年後,以龍圖閣學士身份擔任杭州太守,在兩年之中,盡忠職守,疏浚西湖,築修蘇堤,解除民瘼。離任之際,告別詩友參寥子,寫出了自己宦場沉浮與知己相伴的心境,本意是想退隱,但有詩讖的意味,好像預知自己晚年要遭遇的苦難。下闋是:「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它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且不管以後的宦途風雨,至少在西湖邊上,春花秋月,山水清雅,詩友知音得以相聚,也是人生難得的際遇。
這首詞時空交疊,情景相融,渾然天成,讀來如行雲流水。上闋寫景,下闋寫情,地點十分明確,是杭州鳳凰山南麓,俯瞰錢塘江的滔滔潮水,可以望到隔江的西興渡口,風光如畫。不禁想起在黃州寫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緬懷的是歷史中三國人物,赤壁鏖兵,在時間的長河中灰飛煙滅。目前在錢塘江邊與參寥子分別,寫的是當下的自我感懷,「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感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美好的光陰歲月像潮水一般流逝,就要和眼前的知己好友分別,天地不語,有情無情,只感到江上幾度餘暉。
「幾度斜暉」的意象,呼應了他貶謫黃州之時,在沙湖道中遇雨,寫《定風波》自勉的心境。身處困厄,依舊要昂首挺胸,不怕風刀霜劍的侵凌。即使感到寒氣的逼迫,也總相信前景光明,「山頭斜照卻相迎」,雖然只是夕陽斜暉,心境明澈,就能「也無風雨也無晴」。到了他貶謫海南,政敵有意置他於死地的時候,他依舊無所畏懼,不忘初心,在回應弟子秦觀的《千秋歲》詞中,倔強地發放夕陽斜暉的光芒,說出「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不管受到任何無情打壓,「舊學終難改」,認定了自己的信念,無改初衷,最多也就是永遠放逐海外,學孔夫子:「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對於《八聲甘州》的深層意蘊,以及蘇軾創作時神思飛揚所涉及的心理狀態,古來有許多揣測與評論,特別是下闋引用「西州路」的典故,導致了眾說紛紜。蘇軾與參寥子相約他年再會,講到「謝公雅志」,說的是晉代謝安身在官場,一直有退隱的「東山之志」,後來卻未隱先死。《晉書》卷七十九,記載謝安突然去世,「雅志未就」:「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一向為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西州路引人發出深沉的悲痛,懷想故人逝世,再也沒有相會之期,傷感慟哭。蘇軾用了這個雅志未酬的典故,就有人認為這是詩人的讖語,暗示自己前途黯淡,或許天不假年,參寥子不必在西州路上為我落淚沾巾。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認為詩讖之說不通,因為蘇東坡告別參寥子以後還活的好好的,十一年以後才逝世:「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雖然胡仔的詩話編寫的不錯,提供了許多理解詩歌的資料,但他在此對詩讖的辯說,未免膠柱鼓瑟,並不能理解蘇軾寫詩創作的心理狀態,也對詩境想像翱翔的下意識聯想,做了生硬的解釋,缺乏慧識。明代張綖《草堂詩餘後集別錄》批評胡仔的說法:「昔人謂坡作此語,疑若不祥,後歷十一載乃薨,世俗所謂成讖者,意不足信。愚謂非也。凡言讖者,謂其無心而先見之也,若坡翁此語,自是有心為之,乃高人曠達之懷,不可以言讖。劉伶嘗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豈真然耶?公在海外示姪詩云:『嗟予潦倒無歸日』,與韓文公藍關示姪湘詩:『好收吾骨瘴江邊』,皆若不祥,而二公竟生還無恙。」張綖的批評,是說蘇軾心胸曠達,毫不在乎生死忌諱,所以,根本不是詩讖。胡仔拿蘇軾後來還活了十一年為據,說此詩並非詩讖,是無的放矢。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也是這個意思,說這首詞「寄伊鬱於豪宕,坡老所以為高」。張綖與陳廷焯認為,蘇軾天性豁達,不在乎談論生死,也就無所謂詩讖不詩讖。然而,這樣的斷語也未免過於討巧,以粗魯的標籤方式來解詩。標榜東坡老高人一等,再拿豪放曠達作為理由,解釋蘇軾面對的生命處境,是以概念替代詩情體會,根本不能觸及蘇軾寫《八聲甘州》的創作心態。說這闋詞是「詩讖」,有一定的道理,不是說他即刻就要面臨謝安的命運,雅志未酬身先死,而是隱約透露了蘇軾長期以來對政局的不滿,對官場體制束縛自由心智的心理挫折,以及一心想要退隱而不得的苦悶。張綖說「凡言讖者,謂其無心而先見之也」,說得沒錯,是感受到了這闋詞想要吐露的心理挫折,只是讓他一深入解釋,就變成辯駁胡仔的說法,高舉坡翁曠達的大旗,不能探測到蘇軾心境的幽微與傷感。
蘇軾與參寥子的交往,我另有長文探討,在此簡單拈出,作為點題,只說明這本小書的寓意,是通過蘇軾的具體生命歷程,探究他潛藏在詩文深處的意識活動,了解他內心情愫的變動。蘇軾的確心胸開闊,瀟灑豁達,但並非永遠歡笑暢意,也有避不開「罣礙恐怖,顛倒夢想」之時。他可以成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是有一定心路歷程的,而他撰寫的詩詞,又最能反映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由表至裡,展示了詩人內心繽紛繁複的心理狀態。所以,「細讀」東坡的目的,並配合他的生活處境,不只是為了章句的考據與注釋,而是希望了解他為什麼成為高人,為什麼心靈得到了自由解放,為什麼人品高尚,悲天憫人,超越他身處的時代困境,千載之下,仍然讓我們欽仰敬佩,讀到他的詩文,如沐春風。本書的出版有點倉促,是為了配合我在香港集古齋「書寫蘇東坡」的書法個展,因此,探討蘇軾生平與詩文意蘊的關係,有不能盡意之憾,只好留待下一部書來彌補了。我要特別感謝好友陳萬雄與趙東曉的鼓勵,更感激中華書局侯明、黎耀強、何宇君諸位大編的提點,才有本書的問世。我在書中呈現的蘇東坡,只是一己之見,有時與坡仙拊掌而談,有時與古人隔空叫陣,總之都是私下的讀書心得。知我罪我,還望坡仙天上有知,諒宥則個。
鄭培凱
研究蘇東坡的著作,即使不是多如牛毛,也不會少於我們頭頂的三千煩惱絲,那麼,我為什麼還來湊熱鬧呢?自從蘇軾過世,宋代文人就開始搜集與注釋蘇軾的著作,捋清他的生平事跡,記述軼事,收藏書跡拓片,成績斐然。歷經元明清三代,文人墨客崇尚坡仙成風,甚至次韻遙和東坡詩詞,也樹立了東坡作為中華文化傳承的優秀典範。近代學者更以新的文學研究模式,從文學史專業的角度推崇蘇軾,使得蘇軾的文學聲名與地位直追李白杜甫,寖寖乎有並駕齊驅之勢,專著與論文也隨學術升等的要求與日俱增,到了五輛卡車也裝不下的地步了。
其實,我寫這本書,還真不是來湊熱鬧,而是有感而發。從小耳濡目染,背誦了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念奴嬌.大江東去》之後,就念茲在茲,讀其書思其人。雖然只是個人興趣,欣賞東坡文章的灑脫自然,一徑讀來,山河影路,清風朗日,但是,超過一甲子的浸潤與積澱,總還是有些揮之不去的詩情感懷,覺得自己一生經歷的波折起伏,早已在蘇軾詩文中點明道盡。退休之後有了餘暇,經常書寫東坡詩文樂府,在書法筆墨之間追摹其中意蘊,濡墨揮灑的神思想像得以升華,感到別有境界的體會,是體制內學術書寫難以企及的樂趣。2019 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困居香港烏溪沙家中兩年又半,早晚翻閱不同版本的蘇軾詩文,有如闍黎誦經,以期處變不驚,坐看雲起,對東坡心境更加有所體會。期間應海內外報刊所需,寫了長短不一的文字,在此重新匯集編輯,盡量排除餖飣考證的繁瑣論據,也算是讀東坡一甲子的心路歷程。
蘇軾(公元1037 年1 月8 日-1101 年8 月24 日),按照傳統紀年,生於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綜觀蘇軾入仕的生平,大體可以分作四個階段:
風華正茂, 詩情萬丈( 1 0 5 9 - 1 0 7 9 ),二十三到四十三歲
烏臺詩獄, 貶謫黃州( 1 0 7 9 - 1 0 8 5 ),四十三到四十九歲
朝廷重臣, 官場風波( 1 0 8 5 - 1 0 9 4 ),四十九到五十八歲
放逐嶺海,有志未伸(1094-1101),五十八到六十六歲(虛歲)
蘇軾離開四川眉山,進入仕途之後,如脫弦之箭,再也無緣回到家鄉。一生如大江東去,波濤洶湧,在北宋政壇上幾度浮沉,卻總能在萬般挫折之中,昂首前行。貶謫黃州,在烏雲密佈風狂雨暴之際,寫出「一蓑煙雨任平生」這樣的詩句,令人敬佩之餘,也給後人重要的提示,必須直面慘淡人生,而有所體悟與升華。他晚年從海南放歸,在金山寺自題畫像,回顧畢生經歷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調侃之中,對世間所謂功業,有了明澈的觀照,也給後世孜孜名利之徒,提供了一面閱世的明鏡。本書書名《幾度斜暉蘇東坡》,典出蘇軾《八聲甘州•寄參寥子》的上闋:「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蘇軾一生寫了340 多首詞,用了 80 种詞牌,《八聲甘州》只寫過這一首。他在元祐六年(1091)離開杭州太守任,告別參寥子的時候,有感一生波濤起伏,希望能安享寧謐的晚年,寫了這闋詞,藉着與參寥子的來往,探討內心深處的詩情感觸與嚮往。然而,東坡老白首忘機,只是渺茫的心願,是曾經滄海之後的美好願望,卻也在內心深處隱約感到,不一定能夠實現。
蘇軾與參寥子交往一生,經歷了早期蘇軾從杭州到徐州、湖州做地方官,到烏臺詩獄、遭貶黃州,從風華正茂的精英,一下子打到社會底層,九死一生。之後召回朝廷,擔任翰林學士,參與朝廷政策的決議,後來又外放杭州、潁州、揚州,一路走來,都有參寥子這個方外知己相隨。甚至到了再次遭貶,流放到嶺南,到海南,參寥子還想去看他,被蘇軾勸阻,才未成行。這首《八聲甘州》寫於蘇軾經歷了烏臺詩獄與黃州貶謫,在離開杭州十五年後,以龍圖閣學士身份擔任杭州太守,在兩年之中,盡忠職守,疏浚西湖,築修蘇堤,解除民瘼。離任之際,告別詩友參寥子,寫出了自己宦場沉浮與知己相伴的心境,本意是想退隱,但有詩讖的意味,好像預知自己晚年要遭遇的苦難。下闋是:「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它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且不管以後的宦途風雨,至少在西湖邊上,春花秋月,山水清雅,詩友知音得以相聚,也是人生難得的際遇。
這首詞時空交疊,情景相融,渾然天成,讀來如行雲流水。上闋寫景,下闋寫情,地點十分明確,是杭州鳳凰山南麓,俯瞰錢塘江的滔滔潮水,可以望到隔江的西興渡口,風光如畫。不禁想起在黃州寫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緬懷的是歷史中三國人物,赤壁鏖兵,在時間的長河中灰飛煙滅。目前在錢塘江邊與參寥子分別,寫的是當下的自我感懷,「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感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美好的光陰歲月像潮水一般流逝,就要和眼前的知己好友分別,天地不語,有情無情,只感到江上幾度餘暉。
「幾度斜暉」的意象,呼應了他貶謫黃州之時,在沙湖道中遇雨,寫《定風波》自勉的心境。身處困厄,依舊要昂首挺胸,不怕風刀霜劍的侵凌。即使感到寒氣的逼迫,也總相信前景光明,「山頭斜照卻相迎」,雖然只是夕陽斜暉,心境明澈,就能「也無風雨也無晴」。到了他貶謫海南,政敵有意置他於死地的時候,他依舊無所畏懼,不忘初心,在回應弟子秦觀的《千秋歲》詞中,倔強地發放夕陽斜暉的光芒,說出「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不管受到任何無情打壓,「舊學終難改」,認定了自己的信念,無改初衷,最多也就是永遠放逐海外,學孔夫子:「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對於《八聲甘州》的深層意蘊,以及蘇軾創作時神思飛揚所涉及的心理狀態,古來有許多揣測與評論,特別是下闋引用「西州路」的典故,導致了眾說紛紜。蘇軾與參寥子相約他年再會,講到「謝公雅志」,說的是晉代謝安身在官場,一直有退隱的「東山之志」,後來卻未隱先死。《晉書》卷七十九,記載謝安突然去世,「雅志未就」:「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一向為謝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西州路引人發出深沉的悲痛,懷想故人逝世,再也沒有相會之期,傷感慟哭。蘇軾用了這個雅志未酬的典故,就有人認為這是詩人的讖語,暗示自己前途黯淡,或許天不假年,參寥子不必在西州路上為我落淚沾巾。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九,認為詩讖之說不通,因為蘇東坡告別參寥子以後還活的好好的,十一年以後才逝世:「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雖然胡仔的詩話編寫的不錯,提供了許多理解詩歌的資料,但他在此對詩讖的辯說,未免膠柱鼓瑟,並不能理解蘇軾寫詩創作的心理狀態,也對詩境想像翱翔的下意識聯想,做了生硬的解釋,缺乏慧識。明代張綖《草堂詩餘後集別錄》批評胡仔的說法:「昔人謂坡作此語,疑若不祥,後歷十一載乃薨,世俗所謂成讖者,意不足信。愚謂非也。凡言讖者,謂其無心而先見之也,若坡翁此語,自是有心為之,乃高人曠達之懷,不可以言讖。劉伶嘗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豈真然耶?公在海外示姪詩云:『嗟予潦倒無歸日』,與韓文公藍關示姪湘詩:『好收吾骨瘴江邊』,皆若不祥,而二公竟生還無恙。」張綖的批評,是說蘇軾心胸曠達,毫不在乎生死忌諱,所以,根本不是詩讖。胡仔拿蘇軾後來還活了十一年為據,說此詩並非詩讖,是無的放矢。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也是這個意思,說這首詞「寄伊鬱於豪宕,坡老所以為高」。張綖與陳廷焯認為,蘇軾天性豁達,不在乎談論生死,也就無所謂詩讖不詩讖。然而,這樣的斷語也未免過於討巧,以粗魯的標籤方式來解詩。標榜東坡老高人一等,再拿豪放曠達作為理由,解釋蘇軾面對的生命處境,是以概念替代詩情體會,根本不能觸及蘇軾寫《八聲甘州》的創作心態。說這闋詞是「詩讖」,有一定的道理,不是說他即刻就要面臨謝安的命運,雅志未酬身先死,而是隱約透露了蘇軾長期以來對政局的不滿,對官場體制束縛自由心智的心理挫折,以及一心想要退隱而不得的苦悶。張綖說「凡言讖者,謂其無心而先見之也」,說得沒錯,是感受到了這闋詞想要吐露的心理挫折,只是讓他一深入解釋,就變成辯駁胡仔的說法,高舉坡翁曠達的大旗,不能探測到蘇軾心境的幽微與傷感。
蘇軾與參寥子的交往,我另有長文探討,在此簡單拈出,作為點題,只說明這本小書的寓意,是通過蘇軾的具體生命歷程,探究他潛藏在詩文深處的意識活動,了解他內心情愫的變動。蘇軾的確心胸開闊,瀟灑豁達,但並非永遠歡笑暢意,也有避不開「罣礙恐怖,顛倒夢想」之時。他可以成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是有一定心路歷程的,而他撰寫的詩詞,又最能反映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由表至裡,展示了詩人內心繽紛繁複的心理狀態。所以,「細讀」東坡的目的,並配合他的生活處境,不只是為了章句的考據與注釋,而是希望了解他為什麼成為高人,為什麼心靈得到了自由解放,為什麼人品高尚,悲天憫人,超越他身處的時代困境,千載之下,仍然讓我們欽仰敬佩,讀到他的詩文,如沐春風。本書的出版有點倉促,是為了配合我在香港集古齋「書寫蘇東坡」的書法個展,因此,探討蘇軾生平與詩文意蘊的關係,有不能盡意之憾,只好留待下一部書來彌補了。我要特別感謝好友陳萬雄與趙東曉的鼓勵,更感激中華書局侯明、黎耀強、何宇君諸位大編的提點,才有本書的問世。我在書中呈現的蘇東坡,只是一己之見,有時與坡仙拊掌而談,有時與古人隔空叫陣,總之都是私下的讀書心得。知我罪我,還望坡仙天上有知,諒宥則個。
鄭培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