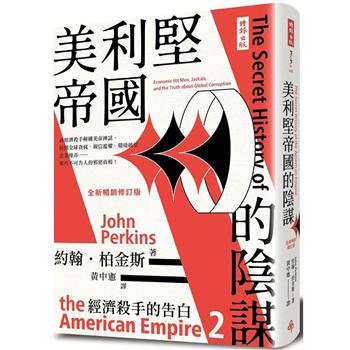推薦序一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理事長 龔尤倩
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為了因應其國內社會經濟動盪、農村人口帶來的壓力,因此積極地推動官營的移民事業,於是花蓮的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官營三移民村陸續存在。首先成立的吉野村,作為日人進駐墾拓農業移民村的先驅,在近代史上已讓世人印象深刻。《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無疑是讓昔日的吉野村多添了一項重要的傳奇!原來,吉野村不只是日本農業移民的先驅,更接納了許多來自台灣宜蘭、桃園、苗栗、新竹等其他地區的島內移民,當年的他們蓬戶甕牖簞食瓢飲,聽說花蓮「卡好賺吃」,舉家遷徙此處尋求生機,或做日本人的佃農、或憑恃勞動技能賣豆腐、採樟、做木材,展開他們的移動探險。經歷了日本殖民、二次大戰期間美軍對花蓮的襲擊、國民政府遷移台灣等一連串因戰事所帶來的時代巨大動盪,在政治歷史的皺褶中,庶民如何身在其中開展勇敢決斷地冒險,他們透過自身的行動孕生出具有主體性選擇的移動敘事。
相應於單一的時代敘事。《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透過故事中訪談的二十餘位主人翁,將1895年至1945年間日本殖民時期,他們的親身經驗透過訪談,讓歷史躍然紙上。書中那貧窮、吃重的農務勞動、挖地瓜、孩子出養送養、男子入贅都是當時農家困窘的生活實況;日治時代,被戰爭動員、殖民者要老百姓推飛機、挖戰壕、挖防空洞、還要背炸彈當敢死隊,成為許多故事主角揮之不去的人生記憶;在殖民政權下,老百姓偷殺豬、偷藏米是老百姓險中求生的伎倆;二戰期間美軍頻頻轟炸日本殖民地的台灣,空襲導致書中多數主人翁小學學業中輟,孩子童稚「不怕機關槍,只怕會挨餓」,旋即又因為家貧投入農務勞動中;日本殖民者離開台灣,老百姓開始佔地佔屋,連繳10年稅金,以便取得土地。而,主人翁口中的日本人有好有壞,有的歧視責罵,也有的深具同理心。傅昌銘的母親殺了家中僅有的雞,擺在桌上,全家卻無人想去動筷,那種面對連綿戰事的無助與無奈的情緒,是老百姓面對戰亂無力回天的絕望。
《來去吉野村》透過了這些耆老的故事,應證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一統的論述,能夠涵蓋所有的故事,也沒有一種言說可以含納所有的歷史事實,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這本紀事中的主角是台灣大歷史書寫中罕見的「缺席他者」,卻是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他者」,他們以身為鏡,補缺了歷史的疏漏與偏執,指認出那個時代的模樣,為我們開展不同的視角與文化模式的歷史質1。
這本書中的主人翁,約莫與我父親是同一世代的人。我的父親龔彩章,在1949年隨著國民黨六十萬軍隊來台。在河南農村的他看見了軍隊到處徵兵捉伕的殘酷,在生死戰亂中,他選擇了不隨命運擺佈而主動從軍;從軍,對他而言,不是甚麼戎馬關山的熱血激昂,只是他當時求生的選擇,怎知就這麼被迫離鄉一甲子,國民黨讓他成了離散者,台灣成了他終老的故鄉。《來去吉野村》一書中的王裕德,在吉野村經驗到了國民黨的軍隊,他說:「來的國軍好像土匪,大家都說是『穿草鞋的來管穿皮鞋的』」。父親當年是在高雄上岸,當年國民黨部隊裡頭一定有很多小兵們如我父親般滿懷著不甘與憤恨的情緒,被迫打那場不知道為誰而打的仗,然後離鄉背井,去到一個耗盡所有可能的想像也無法描繪的地方。就是在這樣的戰事背景下,這些受到影響牽動的幾群百姓在台灣交會,他們命運不同,卻同樣受到「上層爭權,下層顛沛流離」所苦,戰事動盪,世時翻轉,將數百萬老百姓都拋擲向那無垠的天與地。
不同歷史的遭遇與經歷,就會有不同的故事述說與認識,人的身分不會是僵固和穩定的,總會持續隨著歷史政治而產生變化。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時代是「日治」或「日據」之爭,凸顯了台灣社會關於民族記憶與歷史詮釋的重大分歧。書中人物黃菓妹的阿公,參與了號召「驅逐日本,收復台灣」印尼華僑羅福星的抗日活動,父親黃阿書代父背刑,入獄12年,我們只能透過想像,忖思那家族如何詮釋這種壯烈的革命行動;林建智8年內被國民黨調兵6次,只為了「反攻大陸」,到後來卻是無仗可打;他又看見國民黨政府強騙農民的地,忿忿不平讓他對於政治頗有看法,書裡照片中那客廳高掛的「台灣獨立」旗,我猜想就是經歷累積形成了他的政治立場。《來去吉野村》一書,沒機會多對這些豐厚的政治性加以琢磨,我相信,歷史中的人們回觀來時路,應該有著更多值得我們捕捉的睿智。
美國批判心理學家Fred Newman說:「歷史無從失落(Nothing is lost here in history),所有的事情都會消失在社會中,但不會消失在歷史中。2」透過移動者的足跡,我們回歸到歷史之中,了解真正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發生,我們又是誰,我們不論在實體或是在文字中相遇,而共同取回某種歷史的所有權與根源,這無非是最深刻的學習,書中特別摘錄了四位訪談者的心得分享中,都讓我們看見珍貴的應證了。
而花蓮這個後山之地,向來就是多元族群的薈萃之地。百年以來,花蓮已然呈現多重的移民風貌。日本殖民者在花蓮構築日本式的農村,將「原鄉」的樣板移植打造了和風味的吉野村,企圖在南國的土地上,營造那熟悉又似乎那裡有些違和感的氣氛。台灣的閩南客家人,在原鄉生存不易、天災頻仍、土地貧脊的處境下,因應日本殖民者的開墾需求,徒步、搭船來到台灣東部為自己與家族打造一個新的生命機會。而在花蓮,新一代的島內移民則是來自嬰兒潮世代的中產階級,他們帶著鄉村生活的想望,花蓮成為都市人為了尋求田園樂活而移民的天堂。無論是原住民、灣生者、閩客、大陸、東南亞新住民、退休的專技人士等等,這些人民透過在這塊土地上先來後到,也許曾經篳路藍縷,也許遭遇歧視迫害,然而都為兼容並蓄、海納多元的移民文化注入了無窮的生命力。
行動研究強調,人是自己行動的設計者。在我過去二十多年的草根社會運動的肉身實踐中,經驗告訴我,移動者不是無根漂流的無限擴張,也不是自憐式地歷史悲劇的受害者。移動者是勇敢的冒險家與展演家,他們專注在地投入,面對風險,時時打量著怎麼對於自己的發展更好,然後等待或是計畫著迎接那有時罕見的運氣,在歷史情境中實踐自己。但是,移動一定程度又會鞏固了原有的社會矛盾,當通過移動衝破牢籠,勞動積累轉來的洋房華廈,新的牢籠仍舊繼續出現,繼續不斷地遞交給下一代新的任務。《來去吉野村》書中的主人物,走過了胼手胝足辛勞開墾的年代,勤勉成就子孫滿堂的家業。然而,當代的台灣,我們正遭逢一個有別於過去的複雜時局,那挾雜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交錯影響,各種族群與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把許多政治歷史與壓迫的原貌搞得模糊不堪,區域發展嚴重不平等、資本商品拜物教的不斷催眠下,扭曲了質樸的人性與人際關係。怎麼面對時局政治歷史的交疊壓治,從歷史中看待新局,我想是我們讀完《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後所要面對的挑戰吧!
推薦序二
基進教育、解殖教習-從聆聽庶民主體的歷史聲音開始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廉兮
若非王淑娟和參與日治時期的吉野村訪談調查的東華大學同學們,我們將無從得知,在日常生活的吉安小鎮裡,與我們擦身而過的長輩身上,承載著如此厚重與層疊的殖民歷史。庶民並非無聲,只是我們是否願意傾聽。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以行動研究作為方法,將學生帶向社區,透過與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王淑娟的協作,訪談、出版這本書,成為中心第一本協作出版品,意義深遠。2010年,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正式從獨立所轉為今日「教育與潛能開學系碩博班」的結構。王淑娟身為多元所博士生,她鼓勵敦促我參與成立多元文化教育中心。我們在中心一同工作,發展以庶民為主體的教育方法。2015年,她協同太魯閣族中生代共同完成《太魯閣族的另一種鄉愁~花蓮縣吉安鄉太魯閣族人的移動故事》。今年(2017)協同東華大學生,完成《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這兩本書中,花蓮庶民主體的歷史地景,在我們眼前展開。
難能可貴的是,這個歷史是人民為自身的發展、自身的認識而寫,也是寫給願意傾聽庶民聲音、願意不簡化對待我們社會中多重主體的歷史視域的人們,這是一個自內解殖的社會學習過程。多位參與解殖教習的大學生長出了世代接續的歷史感知,張宏婷說:「這些長輩遭逢了台灣歷史上的數個轉捩點、政權、社會經濟的大轉變,那些由他們敘述出、略顯平淡的生存途徑,都是層層疊疊的妥協與適應,到了晚年,這些歷史記憶,多只剩彼此茶餘飯後的憶當年了,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能一起泡茶聊天的老友也愈來愈少,因此,當我們用實際行動告訴他們,你們的經驗是重要的,不單只侷限在這個計畫和地域,更應該被放在更大的格局去詮釋和對話,就像到後來,熟識的長輩都會以他們自己的語言,向新加入、前來串門子的其他人解釋,我們這些小孩為什麼想知道日本時代的事情,以及,為什麼重要:要知道台灣過去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才知道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走。我將這視為這些長輩給予的託付。」而在都市長大的鄧家洋看見:「東部生活實然樸實開闊,在這次計畫裡,讓我更了解花蓮也讓我覺得它實在可愛。這讓我不禁想要將這樣的成長經驗帶回到桃園。透過這種方式嘗試的去理解我所處的人事物。最後,如果從我學到的價值來去看政府的作為。我認為一個地方的偉大不是在於它的新穎,而是在於它如何看待過去。」
同樣面對層疊殖民歷史被執政者簡化對待的香港學者周思中(2010,33頁),分析世代接續、人民團結的意涵,他說:「僅在同一地理及歷史空間共存的個人並不構成世代,更重要的是共同面對同一歷史及社會單位,並投身參與共同的社會困境」。在淑娟與東華大學生投身屬於人民歷史的書寫與聆聽中,我看見在地工作接合探尋社會生活的多種需要、發展多元族群文化的關懷與照顧方法。謝謝本書中每一位與艱難歲月搏鬥的長輩們以身示教,與我們共享在這片土地生活的過往,指引著我們朝向未來。在人民互助共生的家園歷史裡,我們前行有路。
推薦序三
逆勢迎風,步步穩健的行動者-沛然雜陳的島內移民混居聚落
夏林清
王淑娟,做為行動研究學會花蓮工作站的主任,先是落地生根地做著吉安新住民(國際家庭)的服務工作,接著,在對歷史情感探究態度的引領下,竟能在三年中先後完成的兩本書:《太魯閣族的另一種鄉愁~花蓮縣吉安鄉太魯閣族人的移動故事》和《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令我感動!我有幸跟隨著淑娟的努力耕耘,重新認識吉安移民歷史的複雜性與豐富性。
戰爭與貧窮永遠是趨使人們移動到他鄉的力量,《來去吉野村》一書中,繽紛的家的小歷史,如《太魯閣族的另一種鄉愁》一樣,讓我們在花蓮吉安常民生活敘事的小細節裏,看見日本殖民、二戰前後與1949年後國民黨治理的歷史風景的變化。這一方小天地裏,有與日本移民合夥工作的、有與革命者羅福興共同抗日的後裔(苗栗黃家的孫女菓妹)、有衝著蓬萊米香味來的,還有要來就全家族一起來的客家家族!這群7、80歲長者謀生不易與艱困生活的故事,點燃了移民混居的吉野村中,每一家戶的燈火;招贅原來可以是一種雙方協議的有期勞動契約!兄弟南洋當兵去,一回一失蹤!公地放領繳貸款、稅金買肥料後,卻吃不夠!
《來去吉野村》是細碎的常民訪談記事書,沒有輝煌的歷史篇章,也沒有名人軼事,但卻拉開了由1910迄今的百年歷史皺褶,讓小小的一個吉野村的地方常民生活史,開了我們的眼。在閱讀時,情感在細節中與複雜真實相遇,化約的、二分的說法就不會蠱惑與消費掉我們的歷史感;當你看到每一家戶的老照片、群居空間家戶說明圖解、空拍方位圖和掩體壕式樣的圖解說明與實際照片時,讓故事細節帶著你進入一場時空旅行的想像空間吧!
當然,你閱讀這些細細碎碎的文字與圖檔時,很有可能你會難以專注到底,但也就在這來來去去、斷斷續續的閱讀之間,日治時代島內移民,紛然雜陳的生命力與歷史感知的高度,是會萌發於你內心的。
祝福書中的每個家庭,相信王淑娟與工作團隊已於訪談、寫文的過程中,實實在在地參與到歷史中了!
導 讀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花蓮工作站主任 王淑娟
2010年因緣際會我來到花蓮讀書,2012年我落腳吉安鄉西區、設立工作站。2015年,我與10位太魯閣族中生代訪談15位長者3,才瞭解學會座落的吉安西區靠山邊這塊土地豐厚的歷史。也不過是短短一百多年,卻經歷了四種族群的移動,1908年之前為七腳川社傳統領域,日本政府將之滅社,1910年建立吉野移民村清水聚落,1945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令大同部落的太魯閣族集體移住,卻因住不慣平地生活而搬離,再到閩南人的入住。
2014、15年隨著「灣生回家」4書籍的出版、紀錄片上演之際,遠道而來的遊客絡繹不絕,來此地探詢書中日本房子的下落;相較之下,相隔沒多遠的七腳川溪(吉安溪)旁的「七腳川事件紀念碑」卻乏人問津,引不起遊客的駐足。令我感慨為何一個地區的歷史怎麼這麼容易被截取、切割?
再則是,吉安西區留下了吉野移民村棋盤式的耕地、四通八達的水圳灌溉溝渠、完善的公共設施,至今農民仍然受用,若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堪稱具有遠見的農村規劃。當我們領受這些日本人留下來的建設,稱之為「禮物」時,可曾想過這些建設當時為何而建?為誰所用?當年台灣人也曾一同參與?
當吉安鄉這片土地鋪天蓋地只剩下了「灣生」的鄉愁及對日本人水利、田園建設景仰之際,我選擇進入田野,探詢至今仍生活在吉安這一塊土地上,同樣在日治時期來到吉野村周遭開墾的閩南及客家移民。瞭解他們怎麼經驗日本時代?他們跟日本人相處的經驗又是如何?於是,開啟了《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5的探究歷程。
《來去吉野村》一書,主要場景為日治時期在吉野村周遭形成的島內移民聚落。日本吉野移民村,包含宮前、清水及草分三個聚落,島內移民來到吉野村後,因大多靠著當日本人的佃農為生,而就在鄰近形成了或集中、或鬆散的聚集。除三個聚落外,今日之宜昌、南埔等地,在1937年之後均屬吉野庄,亦為今吉安鄉的區域,都是本書所描述長者的主要居住區域。而特別有三位長者黃菓妹、邱梅蘭及林月英,他們的居住地是在花蓮港街∕市,並非在吉野庄,本書也將之納入。其主要原因是,跟每位長者進行訪談時,他們不會一開始就能清晰告知其所遷移落地的區域,當訪談者透過進一步對話越趨清晰的同時,長者的故事已全盤托出。我們站在以文史工作做為社群培力的立場上,與他們來回對話、將故事書寫清晰且出版,對長輩而言是極大的鼓勵;其二,我認為幾位長者的故事,會拓展讀者的歷史感,於是,我將他們寫入書中。黃菓妹是抗日志士的後裔,從她的故事窺見被澆熄的抗日火苗;而林月英是世居阿美族,從中看到皇民化極深的家庭樣貌;而邱梅蘭的先生及父親則分別參與了的今銅門及石壁街、花蓮港等工程,從中看見島內移民參與日治時期工程一景,打破了這些建設是「日本人留下來的禮物」的單薄觀點;更貼切地說是由日本人為主要規劃設計,本島各族群一起參與的工程建設。
本書主要描寫日治時期因為時局變化、家族或個人經濟困局,為了討口飯吃,移動到吉野村的過程及後續在吉野村內的生活。吉野村內由於許多荒地未開墾,戰爭、徵調日本人而致勞力短缺,而帶來了許多工作機會。他們來到吉野村墾地、種米,想當然耳,應該更有米可吃,但在日本大帝國,為擴張領土而發動太平洋戰爭,迫使來到吉野村的島內移民,都經歷了空襲、戰亂的童年,無一倖免。
日本大帝國的面貌,透過兩個故事一覽無遺。一是海鳥仔在1945年17歲時擔任特攻隊的經驗,在七星潭邊背炸彈,等著讓敵軍坦克車碾過,一條命換一輛坦克車的「自殺式」攻擊行徑,其二是顏文徵在1942年15歲時,和哥哥文慶一同到海外當軍屬,日本政府誘之以利,擔任不是志願的志願兵(軍屬),看得更加透徹。所以第一部分,我們將這兩篇故事先行,鋪陳日本大帝國以擴張領土、殖民為目的的時代氛圍。當中,第二個故事主角顏文徵雖非日治時期就來到吉野村,而是1967年才來到吉安的住民,但因為與海鳥仔、林建智、張朝榮等長輩年紀相仿,同樣歷經戰亂,使他們成為能談論歷史經驗的好友,基於社區長輩們共同發展的思考,及我認為文徵的經驗,更能增加讀者對當時徵兵及海外征戰局勢的瞭解,於是,我把他納入書中。而海鳥仔從南埔機場推飛機到今南華山邊的路線,及吉野庄的軍事部署等,都是非常珍貴的口述資料,也是首次公開出版。
本書第二部分,島內移民地景部分,本書詳細地書寫島內移民聚落的地景及家戶圖。或許有些讀者會覺得細碎,不知為何要寫。這部分凸顯兩件事,一是在日治時期的地圖上,吉野村只見日本人居住的宮前、中園、清水、草分的地名,不見島內移民聚落的標示。本書經過兩年的查訪,將島內移民聚落台灣村仔、竹篙厝、清水(今舊村)、牧場、新庄及漆樹下等地,儘可能描述清晰,且繪製家戶圖,這些資料大多是過去文史資料付之闕如的。其二是,從台灣村仔及舊村兩聚落形成的過程,也凸顯了日本人跟台灣人(島內移民)的關係。兩聚落先後從宮前及清水聚落因為文化差異、貧富差距被趕了出來。這組關係中,當然有些雇主與佃農有不錯的情誼,但總體而言,日本移民村是儘可能不讓台灣人靠近的(只能路過,不能東張西望),常因爭相提水而被打、賞巴掌,權力關係的不對等顯露無遺。而從影片或書中看見灣生(或後代)回台灣探望時,所流露的跟這塊土地、人民的情感;或許混雜了時空變遷、對於這塊土地的思念,但當時日本人跟島內移民的日常關係,絕大部分並非如此。
將近兩年的訪談過程,是一個行動研究的過程,亦是訪談者、受訪者相互培力共學的過程。幾位訪談者包括黎南堂熱心地帶路與客語翻譯;東華的學生─宏婷、家瑋、家洋、芃如的參與及與東華大學多元文化中心廉兮老師的合作,都促成了此一探究行動。同學在此吃盡苦頭,聽不懂客語或台語,卻要勉力謄稿,再從謄稿中再整理出故事,但也從中受益。
最辛苦的,莫過於這些長輩了,不厭其煩地跟我們對話,謝錦標先生對旁人說,「王淑娟來找我40次」,張朝榮先生家的客廳更是對我們開放,抱病帶著我們看山邊地景、但永遠面帶笑容。看著幾位長輩海鳥仔、張朝榮、傅昌銘等人,他們80多歲、將近90歲的身影,不下10次騎著機車帶我們察訪地景,我們努力跨越因為身份、世代帶來的距離。在講述歷史中,他們精神抖擻,我們深深感受到他們的能量;在聽歷史故事中,我們中生代、年輕世代獲得滋養!
正當書的訪談出版告一個段落時,如何讓社區年輕世代、新的吉安住民更瞭解歷史的行動才要展開;且我們面對執政者長期因為經費挹助的來源,而在歷史書寫或是歷史建築的布置上偏重單一族群,已造成族群間的矛盾,深感憂心,日治時期閩南、客家為了討生活來到吉野村外圍形成了聚落,不分族群互相協力蓋屋的景象猶在眼前,我們要求主事者注重史實、關照各族群的歷史、促進族群共融的行動正在開展。
過程中非常感謝潘繼道老師、陳鴻圖老師、林茂老師不辭勞苦的審查,郭俊麟老師提供寶貴的GIS資訊及花蓮縣文化局的委員們的寶貴意見。尤其是潘繼道老師,午夜時刻還接受我的諮詢、過程中的有問必答,令人感念在心。此外,葉柏強老師、邱上林老師更將珍藏的照片讓本書使用。由於前輩們的慷慨,才得以讓本書的結構、內容更為完整及可能的錯誤降到最低。
最後要特別感謝花蓮縣文化局連續兩年的支持,尤其是陳淑美局長的深切鼓勵及工作團隊的協助。在「哈日風」興起的當下,願意支持「背道而馳」的田野調查,讓島內移民的聲音可以被聽見,讓過去沒有機會認識字的長輩可以與年輕人交談,讓生命經驗粹鍊出來的知識可以被寫在書裡,如今才得以生產這樣一本庶民的書。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張永照等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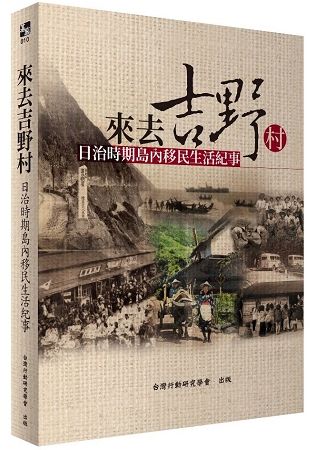 |
$ 270 ~ 396 | 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
作者:張永照等口述;張宏婷等採訪編輯 出版社:耶魯國際文化 出版日期:2018-01-01 語言:繁體書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5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
《來去吉野村》主要描寫日治時期因為時局變化、家族或個人經濟困局,為了討口飯吃,島內移民移動到吉野村(今吉安鄉)的過程及後續在吉野村內的生活。
吉野村內由於許多荒地未開墾,戰爭、徵調日本人而致勞力短缺,而帶來了許多工作機會。本書的主角們來到吉野村墾地、種米,想當然耳,期待的是一個更有米可吃的未來,但在日本大帝國,為擴張領土而發動太平洋戰爭,迫使他們被迫捲入了空襲、戰亂的童年,無一倖免。
本書企圖與《灣生回家》鄉愁式的敘事對話,透過主角們和日本移民生活上相處的經驗,體現日本殖民者及人民的權力與隔離心態。《灣生回家》所流露對這塊土地、人民的情感,或許因時空、距離抹平了衝突的記憶,但當時日人跟島內移民的日常關係,絕大部分並非如此。
而日本帝國主義的面貌,透過海鳥仔當兵時兩次被迫「自殺式」攻擊行徑,看得更加透徹。1945海鳥仔17歲時擔任特攻隊,在七星潭邊背炸彈,等著讓美軍坦克車碾過,一條人命換一輛坦克車,所幸美軍並未上岸。
而書中的許多珍貴史料更是首度公開,包括:海鳥仔從南埔機場推飛機到牧場(今南華)山邊的路線、吉野庄的軍事部署、吉野移民村外圍島內移民聚落家戶圖及島內移民被趕出清水、宮前聚落而形成今舊村、台灣村仔(今太昌)的過程等。
作者簡介:
口述者:張永照、張永龍、張朝榮、張朝發、張清輝、顏文徵、潘秀英、林阿綢、謝錦標、傅昌銘、楊世安、吳芋萱、林建智、徐阿泍、王裕德、彭天榮、王紅緞、劉復振、曾義洪、張春妹、黃菓妹、黃盛坤、邱梅蘭、邱玉蘭、林月英、張寶丹、葉一雄、蔡阿寶、林美玉、田秀鳳、田吉康、陳聰明、陳阿聰、羅添福、徐保雄
採訪編輯群:張宏婷、郭家瑋、鄧家洋、陳芃如、黎南堂、王淑娟
TOP
推薦序
推薦序一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理事長 龔尤倩
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為了因應其國內社會經濟動盪、農村人口帶來的壓力,因此積極地推動官營的移民事業,於是花蓮的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官營三移民村陸續存在。首先成立的吉野村,作為日人進駐墾拓農業移民村的先驅,在近代史上已讓世人印象深刻。《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無疑是讓昔日的吉野村多添了一項重要的傳奇!原來,吉野村不只是日本農業移民的先驅,更接納了許多來自台灣宜蘭、桃園、苗栗、新竹等其他地區的島內移民,當年的他們蓬戶甕牖簞...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理事長 龔尤倩
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為了因應其國內社會經濟動盪、農村人口帶來的壓力,因此積極地推動官營的移民事業,於是花蓮的吉野村、豐田村、林田村,官營三移民村陸續存在。首先成立的吉野村,作為日人進駐墾拓農業移民村的先驅,在近代史上已讓世人印象深刻。《來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生活紀事》,無疑是讓昔日的吉野村多添了一項重要的傳奇!原來,吉野村不只是日本農業移民的先驅,更接納了許多來自台灣宜蘭、桃園、苗栗、新竹等其他地區的島內移民,當年的他們蓬戶甕牖簞...
»看全部
TOP
目錄
局長序 花蓮縣文化局長 陳淑美 3
推薦序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理事長 龔尤倩 5
推薦序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廉兮 11
推薦序 夏林清 13
導 讀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花蓮工作站主任 王淑娟 15
本書常見用詞及地名沿革說明 22
PART1昔日 殘酷的生命故事 25
人命如螞蟻/張永照(海鳥仔) 26
兄弟倆南洋做軍屬/顏文徵 38
→日治時期花蓮港南埔機場、飛機路及吉野庄山邊軍事部署 45
PART2當時 移動的時代背景 53
清朝、日治初期 54
日治時期來到吉野村的島內移民 61
吉野村島內移民地景 64
PART3過程 島...
推薦序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理事長 龔尤倩 5
推薦序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廉兮 11
推薦序 夏林清 13
導 讀 台灣行動研究學會花蓮工作站主任 王淑娟 15
本書常見用詞及地名沿革說明 22
PART1昔日 殘酷的生命故事 25
人命如螞蟻/張永照(海鳥仔) 26
兄弟倆南洋做軍屬/顏文徵 38
→日治時期花蓮港南埔機場、飛機路及吉野庄山邊軍事部署 45
PART2當時 移動的時代背景 53
清朝、日治初期 54
日治時期來到吉野村的島內移民 61
吉野村島內移民地景 64
PART3過程 島...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永照等口述 ; 張宏婷等採訪編輯
- 出版社: 耶魯國際文化 出版日期:2018-01-01 ISBN/ISSN:978986925361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2頁 開數:菊16開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台灣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