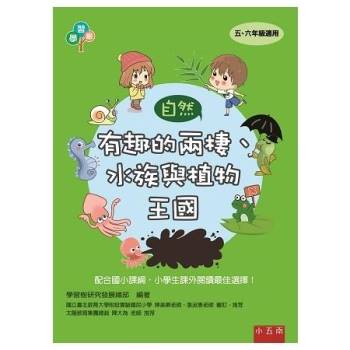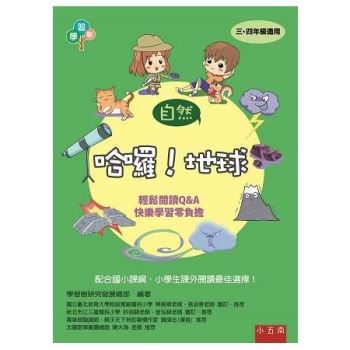Intel、Google、Microsoft 紛紛設立腦機部門,
研發「大腦—電腦—機械介面」新科技。
「阿凡達」、「獵殺代理人」、「火狐狸」、「駭客任務」等電影中,
用腦波操縱機器、甚至控制其他生化軀體的情節,不再是噱頭和幻想。
《念力——讓腦波直接操控機器的新科技‧新世界》
由名列「全球20位最頂尖科學家」的尼可列利斯,親自執筆。
為我們介紹「腦機介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他的心路歷程。
這位巴西國寶級科學家,率領一支國際天才團隊,
以及實驗鼠艾栩、實驗猴貝拉、奧蘿拉、伊朵雅,
進行最尖端、充滿人道關懷的「念力」研究,
已經成功讓猴子運用腦波,去打電玩、去操控數百公里外的機械臂,
甚至遙控半個地球外的機器人在空中漫步!
這是殘障人士的福音,在不久的將來,
無法聽、無法看、無法抓物、不能行走或說話的神經疾病患者,
將可能運用念力,操作各式機電義肢,回復正常的生活與尊嚴。
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也將可能大幅改變:
未來我們只要單用想的,就可以控制家中所有電器的開關,
連上「腦際網路」,不必輸入文字,直接與網友進行意識上的交流。
甚至,頭腦不再受限於我們的身體疆界,
每個人的記憶、心靈,不會隨肉身毀壞而消失……
作者簡介:
尼可列利斯(Miguel Nicolelis)
出生於巴西,創立美國杜克大學神經工程研究中心,
創辦巴西納塔爾國際神經科學研究所。
現任杜克大學狄恩(Anne W. Deane)神經科學講座教授。
論文經常發表於《自然》和《科學》等國際一流學術期刊,
已獲選為法國科學院院士、巴西科學院院士。
2004年《科學人》雜誌挑選為全球最頂尖的20名科學家,
2010年獲頒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先鋒獎,
2011年受教宗本篤十六世冊封為天主教廷科學院院士。
目前的研究計畫之一,是要運用腦機介面,
讓全身癱瘓的兒童,在2014年巴西的世界杯足球賽,
擔任開幕戰的開球嘉賓。
譯者簡介:
楊玉齡
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曾任《牛頓》雜誌副總編輯、《天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目前為自由撰稿人,專事科學書籍翻譯、寫作。著作《肝炎聖戰》(與羅時成合著)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台灣蛇毒傳奇》(與羅時成合著)榮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譯作《生物圈的未來》榮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大自然的獵人》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推薦獎、《雁鵝與勞倫茲》榮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另著有《一代醫人杜聰明》;譯有《基因聖戰》、《大腦開竅手冊》、《奇蹟》、《大腦決策手冊》等數十冊書(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中文版編輯說明
這是一本描寫大腦的能力和潛力的書,也是一本挑戰你大腦的理解力與想像力的書。
作者雖然已名列全球最頂尖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呼聲極高;但是他的研究生涯一路走來,不時在衝撞學術界的傳統認知,不時與神經科學的主流思想牴觸。他研究的主題和方法、他自創的理論,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異端。因此他寫這本書時,可說是把壓抑已久的思緒,全部傾吐出來。他既想對一般讀者娓娓道來,也想對科學界的同儕抒發自己的完整理念。
所以在這本書中,既有精采的實驗室故事、人生故事,也遍布許多學理和科學史。中文版為了方便一般讀者閱讀,特別在某些章節的小標題前面,打上※號,表示這些章節包含比較多的學理或技術細節,一般讀者可略過不細讀。當然,對於想了解「念力」這個主題的完整內涵的讀者,仔細攻讀這些打※號的章節,肯定能讓自己的腦力超越既有的疆界。
本書第1到5章和第7章,大抵在講腦科學研究史上,兩個陣營的對峙(一邊陣營主張腦部有分區,每區專司一種功能;另一邊陣營主張,腦袋就像一支交響樂團,與其拆解開來研究,不如細心聆聽整首交響曲)。作者屬於後者的陣營,在這幾章史實軼事的回顧中,也穿插自己聆聽大腦交響樂的歷程,還有幻肢、靈魂出竅的奇異實驗——見第3章〈虛擬的身體實境〉。
第6章〈解放奧蘿拉的腦〉、第8章〈腦機介面的真實世界之旅〉、第10章〈分享我們的心靈〉介紹腦機介面的種種精采實驗,包括猴子用腦波打電玩、猴子用腦波遙控機器人走路(華裔科學家鄭順威發明的機器人),以及老鼠用腦波指揮另一隻老鼠的「腦對腦介面」實驗構想。
第9章、第11章、第12章,分別從飛船奇人、尼斯湖水怪、巴西足球隊的驚天一擊,切入作者要進一步闡述的念力理論,其中包含台灣赴美科學家林士傑的傑出貢獻。
第13章〈回到星辰〉則是作者對於腦機介面的遠景,縱橫馳騁的想像。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中文版編輯說明
這是一本描寫大腦的能力和潛力的書,也是一本挑戰你大腦的理解力與想像力的書。
作者雖然已名列全球最頂尖的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呼聲極高;但是他的研究生涯一路走來,不時在衝撞學術界的傳統認知,不時與神經科學的主流思想牴觸。他研究的主題和方法、他自創的理論,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異端。因此他寫這本書時,可說是把壓抑已久的思緒,全部傾吐出來。他既想對一般讀者娓娓道來,也想對科學界的同儕抒發自己的完整理念。
所以在這本書中,既有精采的實驗室故事、人生故事,也遍布許多學理和科...
章節試閱
前言 跟著音樂走
—— 聆聽腦細胞集體創作的交響樂
滿溢聲光的第一堂課
當第一串小提琴音,自二樓大理石廳堂湧出,順著樓梯,恣意奔向空無一人的醫學院大樓門口,情境之荒誕,頓時讓我摸不著頭緒。畢竟,一個醫學生在世界上最忙碌的醫院急診室裡操勞到半夜,好不容易偷空小憩之際,怎會料到樂聲大作。然而,這陣樂聲把充滿希望與冒險的生命氣息,緩緩吐進濕悶的仲夏夜中,消弭了我的不安。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我的大腦被那陣琴聲誘惑,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往事,我到現在依然清楚記得那天夜裡,記得那懾人心魄的美妙旋律,如何串成一股熱切的、集體的邀約,聲聲呼喚我,要我追隨那誘人的音樂。我快步爬上樓梯,穿過一條窄窄的長廊,最後來到一間大講堂入口,華格納歌劇「帕西法爾」的序曲,正是從這裡飄出來的。我忍不住跟著樂聲踏進講堂。
然而一眼望去,不禁大失所望,掛著枝形吊燈的諾大講堂,空蕩蕩的,只有一位衣著考究的老先生,顯然正忙著修理一台不知放過多少幻燈片的破舊幻燈機。
巴西聖保羅大學醫學院建於1920年代末,裡頭每一間講堂都是雅致簡約的典範。最前方,是整齊的箱型講台,區隔出教授講課的空間。一張沉甸甸的木桌、一把結實牢靠的椅子、以及一面狹長沉舊的滑動黑板,就是簡樸的教師專屬空間的全部了。學生座位則是往後堆疊,坡度陡峭,讓坐在最後一排的學生,包括我,可在一堂又一堂沒完沒了的課程中,得以避開教授權威的目光。
這時候,老先生(他有一頭近乎平頭的白髮,襯著身上的白袍,倒是挺相稱的)也被我推門而入的聲音嚇了一跳,不過他馬上輕鬆拋來一個地中海式的爽朗笑容。他一邊繼續和幻燈機奮戰,一邊向我揮手示意,彷彿我們是多年老友。而講桌上頭,我有點沮喪的找到了證據,暗示這位隨和的老先生與那天夜裡的音樂會有關:一台唱盤機、兩只看起來頗昂貴的喇叭,以及一疊唱片,封套標示著柏林愛樂交響樂團。
「歡迎光臨!這裡有美酒加乳酪。今晚幻燈機有點問題,但是只要再等一下下,就可以開始。對了,我是提摩艾利亞(Cesar Timo-Iaria)教授。我負責教這門課。」
話才說完,幻燈機便發出一聲金屬巨響,迴盪在講堂中,而幻燈機的亮光也立刻滿溢在前方的銀幕上。我還沒來得及答話,他已經迅速轉換位置,來到幻燈機後方,彷彿身經百戰的將軍站上艦橋去指揮。他熄了吊燈,等待第二首曲子響起之後,便開始興高采烈的放起幻燈片來,那種喜悅,我只有童年在老家街邊踢足球的時候,才親眼見識和體驗過。
我獨自坐在烏七八黑的台下,接受「唐懷瑟」歌聲的催眠,聽它在大廳裡迴旋,一邊觀看一連串與醫學完全不相干的影像,不禁又氣惱又著迷。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在課堂上有這種感覺。
「請問您是教哪一門課?」我問。
「生理學導論,」提摩艾利亞教授看都沒看我一眼。
為了確定自己沒弄錯,我又再仔細看了一下銀幕。和所有醫學生一樣,我在好幾年前就修過生理學導論,然而我怎麼也看不出,眼前這些影像與我學過的生理學有關連。
「怎麼可能?」我追問。
「什麼東西怎麼可能?孩子。」他反問,仍沒正眼瞧我一下。
「這些怎麼可能是生理學導論?您這些幻燈片,我是說,它們的主題,您在展示的只不過是……」
「是什麼?」對於我的不自在,他似乎覺得很好玩,看起來這種反應他見多了。「繼續說。告訴我,你為什麼這樣驚訝。」
這樣的音樂,這樣的影像,加上一名老先生,半夜在空曠的大講堂裡上課。完全沒道理!半困惑、半惱怒,我終於不客氣了。
「你放的片子淨是些星星、銀河。你看,現在又來一張電波望遠鏡。這在幹嘛?這怎麼會是生理學導論?」
「這個嘛,它是開端。一切從這裡開始,從大霹靂到大腦,只不過一百五十億年左右。了不起的旅程,是吧?我會一一解釋。」
我望著一幅又一幅夢境般的影像:閃閃發光的螺旋星系、剛萌芽的星團、喧鬧繽紛的星雲、叛逆的彗星以及爆炸的超新星……都由彷彿專為宇宙眾神所譜的樂曲陪襯下,魚貫登場,一邊聆聽提摩艾利亞教授敘述這一部最後導致人類心智的史詩。
終於,行星誕生了。但大部分都保持荒蕪狀態,沒有生命。可是,在至少一顆行星上,幾十億年前,一場有趣的實驗導引出能夠維持並複製生命的生化與遺傳機制。於是萬物欣欣向榮,奮力求生,始終充滿了希望與啟發,各自踏上完全無法預測、而且十分脆弱的演化之路。
接著,我看到了最早的人類影像。幾百萬年前,他們肩並肩,行走在衣索匹亞阿法沙漠(Afar Desert)的夜空下。然後,就在這一刻,當華格納歌劇裡的唐懷瑟,為了經歷凡世而拒絕永生,終於在維納斯堡獲得自由時,我也經歷到了那一刻:早期人類祖先第一次仰望頭上無盡的星空,心中充滿敬畏,腦中則颳起一場野火般的電風暴,忙著搜索直到今天依然折磨著我們的答案。我終於明白,當那些最早期的世間男女,膽怯又好奇的仰望天空時,一場既漫長又高貴的接力賽業已展開,它串聯起所有人類,來找尋能解釋我們的存在、意識以及周遭一切意義的基本答案。
的確,再沒有比這張幻燈片,更適合做為歷史上科學誕生的象徵了。艦橋上的老將軍,顯然寶刀未老。
唐懷瑟的〈朝聖者合唱〉終曲音符漸漸消逝,宣告了最後一張幻燈片,它佇留在銀幕上,而我倆也靜默了好一會兒。這張幻燈片是人腦的側面影像。幾分鐘後,提摩艾利亞教授打開燈,下了講台,靜靜朝講堂門口走去。在走出講堂前,他回過身子,彷彿要跟我說再見。然而,他說的卻是:「這是人體生理學導論的第一堂課。對了,剛才忘了提,我也教神經生理學高級班,第一堂課的時間是明天晚上。我強烈建議你也來上。」
還沒有從震撼中回復過來的我,只想到一個問題,「我要怎樣才能註冊上這門課呢?」
踏出門口之前,提摩艾利亞教授又笑起來了,對於那晚毫不費力,就招到的這名終生門徒,提出他的第一項建議。
「你只要跟著音樂走,就對了。」
神經元交響曲
過去二十五年來,我經常記起提摩艾利亞教授那牢不可破的信念:在人類心智無盡的努力所產生的副產品中,音樂與科學方法是最令人驚豔的代表。這或許也說明了,為何我決定要終生致力於聆聽另類音樂,聆聽那種由全體大腦細胞一起創作出來的交響樂。
嚴格說,我是系統神經生理學家。至少,我的神經科學同行會這樣界定我在杜克大學神經工程研究中心的實驗團隊的工作。這麼說吧,我們腦袋裡住著上千億個神經細胞,這些細胞伸展出來的神經纖維,形成了各式各樣的神經網路,而系統神經生理學家一輩子都在研究,到底是什麼樣的生理學原理,讓這些神經網路得以運轉。
這些精密的腦神經網路,足以令任何電子產品、電腦或是人造機械相形失色,因為腦神經網路的複雜度與連結性,比起任何電機產品,都超出了好幾個數量級。也因此,每一個腦細胞,也就是神經元(neuron),都能與成百上千個其他神經元,直接接觸與溝通。人腦就是透過這些連結繁密、高度動態的細胞網路(但是它們有一個相當乏味的名字,叫神經迴路),才有辦法執行主要任務:製造大量高度特化的行為,也就是我們常常自豪的通稱為「人性」的東西。
這些精細的神經網路,確實能藉由駕馭大量僅有千分之一伏特的放電,讓我們得以思考、創造、破壞、發現、包庇、溝通、征服、引誘、臣服、愛、恨、快樂、悲傷、團結、自私、自省、以及興奮等等,它們貫穿在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的祖先、乃至所有人類的存在過程中。若非miracle(奇蹟)這個字已經讓其他領域給盜用了去,我相信,這個字眼的專利權應該許給神經科學家,用來報告大腦的神經迴路執行例行工作時,有多麼奇妙。
對於大部分系統神經生理學家(譬如我)來說,最終極的問題在於:到底是什麼樣的生理機制,讓這些神經細胞電流的小爆衝,得以產生全套人類的動作與行為?然而,在尋找這只神經科學聖杯之際,過去兩百多年來的諸多神經科學研究,已經先捲入一場激辯:腦裡有哪些特化區域,負責特定的功能或行為?
功能定域化論者(localizationist)是其中一個極端,他們屬於顱相學之父高爾(Franz Gall, 1758-1828)的傳人,雖然通常不明說,但是他們到現在還深信:不同的腦部功能,是由不同的腦部特定區域產生的。
另一端,也就是我所謂的多工分散論者(distributionist),勢力較小,但人數正在快速增加之中。他們主張:人腦在達成每一項任務時,都是藉由號召散布各處的神經元,來共襄盛舉。
我和這群主張多工分散論的人,提出的理由是:人腦似乎有辦法採用類似民主選舉的生理機制,也就是由腦袋裡散布在各個不同區域的大量神經元共同投票,決定最後的行為產物;儘管個別神經元的決定權都很輕微,而且不是「一人投一票」。
過去這兩百年來,功能定域化論與多工分散論兩個陣營,都選擇了大腦皮質(cortex,大腦的最外層結構,也就是頭骨下方的腦組織),做為這場沒完沒了的神經大辯論的主戰場。這場戰爭的開端,可以回溯到顱相學風行的年代,顱相學家宣稱:他們只需摸觸一個人的頭骨,搜尋能夠反映「特定皮質區不成比例擴大」的頭骨隆起,就有辦法判讀當事人的個性,因為根據他們的學說,我們之所以產生諸如愛情、驕傲、自負、虛榮以及野心等等,都歸因於不同的皮質區。按照顱相學家的說法,每一種人類情感與行為,皆是由特定的大腦皮質區產生的。
雖然高爾和他的偽科學終於被時代淘汰了,但是顱相學的基本架構卻倖存下來,演變成二十世紀神經科學的重要教條之一。大約一百年前,第一代專職研究腦袋的學者,做了一系列讓人眼睛一亮的實驗,領導人物是西班牙的拉蒙卡厚爾(Santiago Ramón y Cajal, 1852-1934)。那些實驗證明,頭腦和其他器官一樣,結構上的基本單位是個別的細胞,也就是神經元。然而,在幾乎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神經元很快又躍升為中樞神經系統在功能上的基本單位。由於神經元教條的地位扶搖直上,再加上法國生理學家布羅卡(Pierre Paul Broca, 1824-1880)於1861年提出一份非常搶眼的觀察報告,發現左前額葉受損的病患,有可能嚴重喪失語言能力以及右半身癱瘓。一時之間,讓多工分散論陣營慌了手腳。
不過,就在多工分散論陣營孤立無援時,薛靈頓(Charles Sherrington, 1857-1952)爵士伸出了援手。薛靈頓指稱,即便是最簡單的人腦功能「脊髓反射動作」,都必須靠大量的神經元與各種不同的神經迴路巧妙合作,才能完成。
嶄新的腦機介面
最近十年雖然沒有出現決定性的發現,但是在這場攸關腦袋和靈魂的戰爭中,多工分散論陣營已經取得了優勢。來自世界各地神經科學實驗室的發現,正逐步推翻功能定域化論模型。在這場群策群力的奮戰中,我在杜克大學的實驗室過去二十年來所做的研究,也有一份貢獻:我們確切證明了,單獨的神經元,不再能視為腦袋的基本功能單位;相反的,相連的神經元集群(neural ensemble)才是腦袋創作思想交響曲的推手。
現在,我們已經有辦法記錄這些神經元合唱團創作的音樂,甚至還有辦法以明確的自主運動行為方式,來重播一小段。而且,我們只不過聆聽幾百個神經元(就腦中上千億個神經元來說,是極小的樣本),就已經開始複製這個流程了,而複雜的思想就是藉由這個流程,即時化為身體的行動。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理,導引了這些神經交響曲的創作與演奏?潛心研究神經迴路的作品長達二十年後,我發現自己不僅在腦袋外面的宇宙,蒐羅到相似的原理(主要是從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更在中樞神經系統的深處,摸索出十條神經生理學原理。我希望找出「腦袋自己的觀點」,讓它自己來表達。我認為,人腦和迷人的宇宙一樣,也是一位深刻理解相對論、善用相對論性質的雕塑家,一位技藝高超的模型鑄造者,能夠把神經元集群的空間與時間,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時空連續體,進而創造出我們稱做「現實」的感官經驗,包括自我存在感。
接下來的十三個章節,我要談的是:未來幾十年間,藉由將「人腦的相對論性(relativistic)觀點」結合「日益精進的聆聽與記錄神經交響曲的技術能力」,神經科學最後一定能夠讓人類,突破目前脆弱的肉體及自我感覺的疆界。
對於這個想像的世界,我還滿有信心的,我的實驗室曾經教導猴子(詳見第6章〈解放奧蘿拉的腦〉),學習使用革命性的神經生理學新典範「腦機介面」(brain-machine interfaces,簡稱BMIs)。我們已藉由腦機介面來證明:猴子可以學會單靠腦袋中的腦電活動(也就是腦波),去指揮外界的人工裝置,例如隔壁房間的機械臂、或是遠在地球另一端的機械腿,讓那些機械裝置依照猴子的自主意向來運作。這些實驗釋出了許多「重新看待頭腦與身體的關聯」的可能性,最終將會徹底改造我們的生活方式。
為了測試不同形式的腦機介面,我們利用一種嶄新的實驗方法,直接即時讀取同一神經迴路裡,數百個神經元的電訊號。發展這項技術的最初用意,是為了測試多工分散論者的觀點:腦袋要執行任何功能,都需要腦中不同區域的神經元集群相互溝通。然而,一旦學會如何聆聽腦袋裡演奏的某些運動神經交響曲,我們決定更進一步,去記錄、去解碼、傳送靈長類大腦皮質裡的運動思想,而且是直接傳送到地球的另一面(從美國傳送到日本)。然後,我們將這些思想轉譯成數位指令,指揮機械裝置做出像人類一樣的動作,雖說該機械最初在設計時,並未具備這樣的人類特徵。
也就在那一刻,我們的腦機介面誤打誤撞的解放了大腦,讓它不再受到身體的束縛,讓它能夠利用虛擬的電動機械裝置,來控制實體世界。換句話說,單單只靠思想,就能控制周遭或遙遠距離外的實體世界。本書將要講述這些實驗的故事,以及它們如何改變我們對大腦功能的理解。
對當今大部分人來說,我們的腦機介面研究造成的影響,主要落在醫學領域。因為打造先進的腦機介面來闡明大腦的複雜運作之後,將能引導發展出神奇的新療法,醫治飽受神經性疾病之苦的患者。這些病患將能透過各種神經義肢技術,讓原本無力的身軀,重拾活動力、感覺和感受。譬如,利用與心律調整器大小相仿的裝置,來採集健康的腦電活動(腦波),然後協調薄如絲綢般的「可穿式機器人」的伸縮運動——這種外型像背心的機器人,細緻程度有如第二層肌膚,但保護力卻不輸給甲蟲的外骨骼。這件外衣不只能支撐起癱瘓者的體重,還能讓先前不能動的身軀,開始漫步、奔跑,再度自由歡暢的探索這個世界。
腦袋不受身體束縛的新世界
然而,腦機介面未來的應用前景,遠遠超過醫療範圍。我相信經過幾個世代後,人們能展現的動作以及能經歷的感官,現代人將難以想像,更別提用言語來形容了。腦機介面可能會徹底改變我們與人造器械的互動方式,以及我們與遠方同類溝通的方式。
如果你想了解這個未來世界可能的樣貌,首先你需要想像,一旦我們腦袋裡的腦波,有管道能在這個世界上自由翱翔,有如今天在你我頭頂上高來高去的無線電波,我們每日從事的例行事務將產生多大的變化!
請各位暫停閱讀這本書,想像這樣的一個世界:世人只需要動用思想,就能使用電腦、駕駛汽車、相互溝通。我們再也不需要大而無當的鍵盤或是液壓方向盤了。甚至,我們再也不需要依靠身體動作或是口語,來表達自己的意圖了。
在這個以腦為中心的新世界裡,這種新取得的神經生理能力,將能讓我們的運動、感知與認知技巧,流暢且毫不費力的擴張到一個新境界:人們的思想可以充分且完美的轉譯成當事人所需要的運動指令,不論是執行奈米工具的微細操作,或是智慧型工業機器人的複雜操作。有朝一日,在這樣的未來世界裡,當你坐在海灘小屋外你最心愛的椅子上,面對你最喜歡的大海,你可能可以很輕鬆的,就和世界各地的三五好友閒話家常——但是你不用忙著打鍵盤或是開口說話,你連一根肌肉都不必動,只要用想的就行了。
如果這還不夠迷人,那麼試想想看,假如能在不離開家的情況下,就能夠親身碰觸到幾百萬公里外的星球表面,那種新奇的探險所帶來的激動之情。你覺得怎樣?
或是更精采的,如果你能接觸到「記憶銀行」裡的資料,隨時下載其中某位祖先的想法,透過他(或她)最私密的印象與鮮明的記憶,來創造一個你和他原本絕無可能分享的邂逅機會。你覺得有沒有意思?
然而,如果真能生活在一個腦袋不受身體束縛的世界,究竟會替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以上這些場景都只能算是略窺一二。
要不了多久,如此奇妙的世界將不再是科幻小說情節。這樣的世界,此時此地,正在你我的面前形成。如果想要沉浸其中,套一句提摩艾利亞教授的話,從下一頁開始,你只要跟著音樂走,就安啦!
前言 跟著音樂走
—— 聆聽腦細胞集體創作的交響樂
滿溢聲光的第一堂課
當第一串小提琴音,自二樓大理石廳堂湧出,順著樓梯,恣意奔向空無一人的醫學院大樓門口,情境之荒誕,頓時讓我摸不著頭緒。畢竟,一個醫學生在世界上最忙碌的醫院急診室裡操勞到半夜,好不容易偷空小憩之際,怎會料到樂聲大作。然而,這陣樂聲把充滿希望與冒險的生命氣息,緩緩吐進濕悶的仲夏夜中,消弭了我的不安。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即使我的大腦被那陣琴聲誘惑,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往事,我到現在依然清楚記得那天夜裡,記得那懾人心魄的美妙旋律,如何串成...
目錄
《念力》目錄
中文版編輯說明 4
前言 跟著音樂走 5
—— 聆聽腦細胞集體創作的交響樂
第1章 思考,是什麼? 15
—— 顛覆你的傳統認知
第2章 腦內風暴的追逐者 35
—— 兩大陣營持續交鋒
第3章 虛擬的身體實境 53
—— 電擊腦袋、幻肢、靈魂出竅
第4章 聆聽大腦交響曲 79
—— 擷取神經元集群的動態織錦
第5章 老鼠如何躲貓貓 101
—— 老鼠觸鬚的妙用
第6章 解放奧蘿拉的腦 133
—— 用念力指揮機械臂
第7章 自我控制 163
—— 回顧初期的腦機介面
第8章 腦機介面的真實世界之旅 185
—— 機器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
第9章 化身飛機的人 203
—— 工具是肉體的延伸
第10章 分享我們的心靈 231
—— 邁向「腦對腦介面」
第11章 腦裡的怪獸 259
—— 腦動力學初探
第12章 用相對論性腦來計算 281
—— 掙脫局限,開啟無限的可能
第13章 回到星辰 303
—— 「腦網」無遠弗屆,永垂不朽
誌謝 328
延伸閱讀 331
《念力》目錄
中文版編輯說明 4
前言 跟著音樂走 5
—— 聆聽腦細胞集體創作的交響樂
第1章 思考,是什麼? 15
—— 顛覆你的傳統認知
第2章 腦內風暴的追逐者 35
—— 兩大陣營持續交鋒
第3章 虛擬的身體實境 53
—— 電擊腦袋、幻肢、靈魂出竅
第4章 聆聽大腦交響曲 79
—— 擷取神經元集群的動態織錦
第5章 老鼠如何躲貓貓 101
—— 老鼠觸鬚的妙用
第6章 解放奧蘿拉的腦 133
—— 用念力指揮機械臂
第7章 自我控制 163
—— 回顧初期的腦機介面
第8章 腦機介面的真實世界之旅 185
—...

 共
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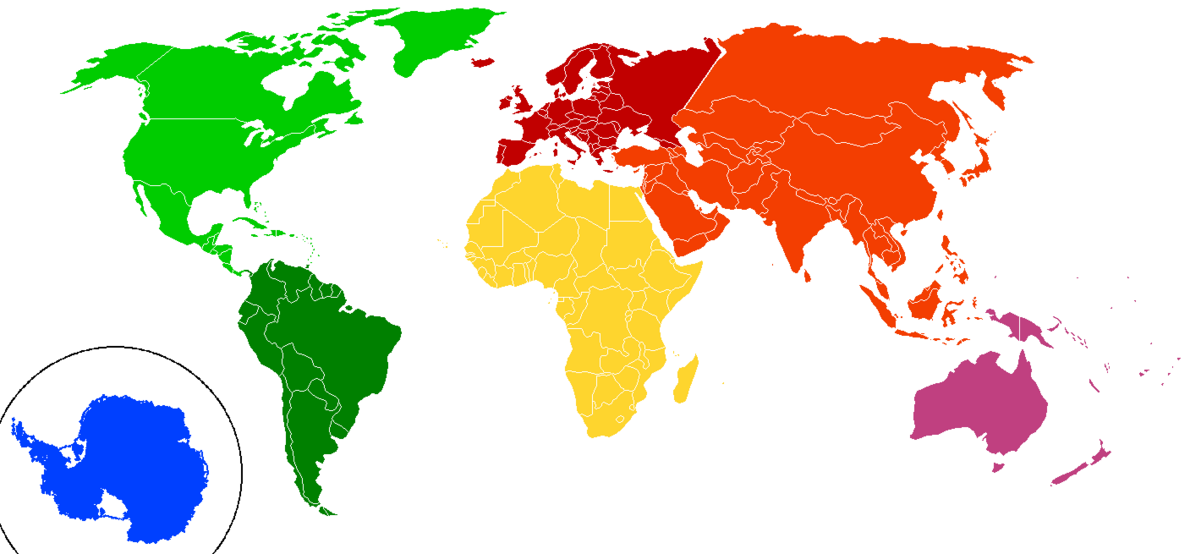 世界一詞在現代社會意為對所有事物的代稱。原本是佛教概念,由「世」和「界」組合而成的世界,即所謂由所有時間空間組成的萬事萬物。
世界一詞在現代社會意為對所有事物的代稱。原本是佛教概念,由「世」和「界」組合而成的世界,即所謂由所有時間空間組成的萬事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