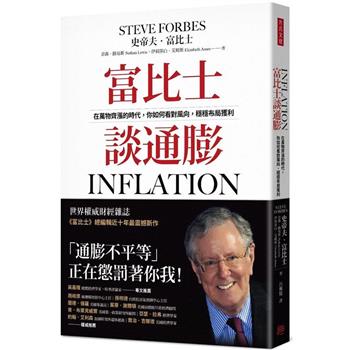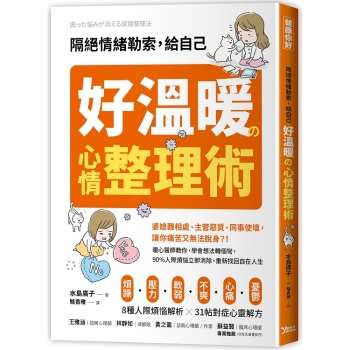慶熹紀事卷一:七寶太監(上+下套書),共二冊,含:
慶熹紀事卷一:七寶太監(上)
慶熹紀事卷一:七寶太監(下)
★榮獲「中國網絡小說好看榜」年度武俠權謀小說桂冠、「小說閱讀榜」年度最值得期待新作
★千萬讀者引頸期盼十六年!武俠迷一生必讀的宮廷權謀大作!
★鳳儀影業、湖南衛視聯手影視化!
比《慶餘年》更隱忍果決的權謀之術,
比《琅琊榜》更快意恩仇的家國情懷!
慶熹紀事 卷一 七寶太監
身世淒離,是他的霜雪心事。
四海清平,是他的烈焰丹心。
風雲開闔,忠賢滅門,他在阿鼻地獄中涅槃重生,卻甘為深宮賤奴,為仇人之子驅使,只願親手撤藩地、平邊患,一竟父志。
慶熹十年,在宮廷中服侍多年的七寶太監,決定留下七名身受他各種技藝的徒弟,告老還鄉。任誰也無法想到,這名深藏不露的老太監,早已經在宮廷之中佈下了兩顆暗棋,即將掀起一股驚濤駭浪……
七寶太監的第六弟子僻邪,繼承了他的衣缽,逐漸在宮廷內面前嶄露頭角,很快得到皇帝的信賴,並委以重任,卻也因此遭人忌諱,引來殺機。他胸懷驚人的秘密與滔天的仇恨,以過人的智慧與武功,周旋於這步步危機,勾心鬥角的宮廷之中……
| FindBook |
|
有 1 項符合
慶熹紀事卷一:七寶太監(上+下套書),共二冊的圖書 |
 |
$ 493 ~ 504 | 慶熹紀事(卷一):七寶太監(上+下套書),共二冊
作者:紅豬俠 出版社: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19-09-11 語言:繁體書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共 2 筆 → 查價格、看圖書介紹
|
|
|
七寶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慶熹紀事卷一:七寶太監(上+下套書),共二冊
|
 七寶鎮是位於上海市閔行區西北部的一個行政建制鎮。
七寶鎮是位於上海市閔行區西北部的一個行政建制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