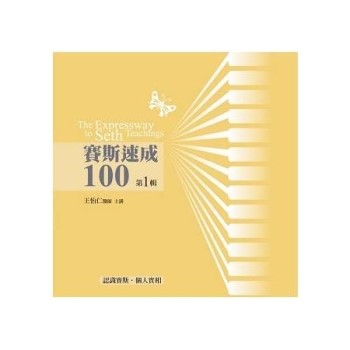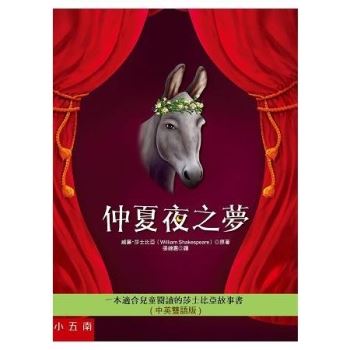幸好有詩,讓秘密都有了翅膀。
《我不懼怕突如的愛》是莊東橋的第二本詩集,也是他飛翔後的低鳴。
封面設計、拍攝:霧室。
作者簡介:
莊東橋,1981年生於臺灣屏東,藝術家、詩人。
近幾年在臺、法兩地舉辦過聯展與個展,寫詩也畫畫。
水花發芽了 les germes en pluie:http://lesgermesenpluie.blogspot.tw/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跋 來自外面的回音──蕭鈞毅
這本詩集就是一個自足的世界。
詩人靜默地與之對話的,是名為「你」的情感集合處 。「你」的身影未曾具體,只存在動作、時態、某支雙人舞裡悄然的承諾、遺憾或是暗夜繁星裡頭。「你」被提取出來,成為了詩人的對立面。所有對「你」的感嘆與召喚,部分來自於重新確認自己的渴望;而另一部分,源自於被時間折損、徒留情感之剩餘,卻再無他人的遙遠之處。
即使知道那裏沒有任何物事,詩人仍然執著地凝視。
直到他看見那裡,有東西正倒映著光。那個世界的物質,是詩人的這個世界的殘餘物:斷了線頭的對話、再也碰觸不到的夢想、已經遠去的人……這些都在「外面」了。
即使只隔著一堵牆、或一扇門,裡外就是兩個世界,依循不同的邏輯運作。是以這樣的段落,就像是詩人側耳薄壁:
不想聽的聲音
你利用時間
雲和雪逐漸遮蔽了整座城堡
更深的傷
像是銀河裡面有一顆星
偷偷將自己藏了起來
隱身並且不作聲
直到你走開
──〈無你之處〉
外面世界的每一處細小規律,都是聲音的微粒,詩人試著傾聽,試著聽見「你」,結果卻是不可避免的時差。
外於他的,因「你」出現而變化,「你」終究不會進到屋裡來,不會進來這裡。而屋裡發生的所有事,都是因「你」而起,卻再也與「你」無關。
該如何理解這樣在詩裡的「內外」之分?出現在許多詩作裡的「家」這個意象,或可理解為分別內部與外部的那一個空間。「家」是什麼?詩人並未明說,它成為概念。一個詩人試圖理解、也試圖被理解的曖昧之處,或是,一個「動詞」。
如這樣一首詩,〈我牽著彩色筆回家〉:
我牽著彩色筆回家
沿路我採集一點點糖粒
回家煮一碗熱奶茶
回家我點起鵝黃色的燈
沿路有風把草削得尖尖
我牽著劃過的線
繞路
沿路回家
煮一杯熱巧克力牛奶
我醒來,看著麵包
我等下應該要打電話
杯子被水沖的聲音
隔壁有一個空間
我專門放空氣
有形有體,我在廚房關起櫃子
木頭和木頭接縫摩擦的聲音
毛毯似的鞋,我的腳在裡面
像一個家
我有些衣服適合烘乾
我適合在床上柔軟一個海
洗手精的香味
雙手有時候擁抱我的臉
整張臉都被蓋住,像窗戶被關起來
我好遼闊,連你都裝得下
家既是概念,同時亦是肉身,肉身其後則是被細緻地串接起來的情感。在這首詩裡,徒具輪廓的「家」,收容了各種動作。彩色筆畫的也非家的形貌,反而更像「繞路/沿路回家」時,不讓自己迷失,或是最後一點面對「你」時盡可能輕鬆的態度。詩作是輕盈的,而話語背後轉喻的內在卻不合比例地沉重。單單將這首詩獨立出來,它可以是彩色的,但與它接楯的卻是整本《我不懼怕突如的愛》,它的聲音與它可能面對的時刻,就不是某個被懸置、在遇到「你」之前(或之後)的明亮畫面。
有內部與外部的分別,隔閡二者的「家」也只能是詩集裡眾多牆壁的集合點。分隔內外的牆面不僅是繪製了家的圖彩,上頭還畫上了一只靜止的沙漏。停滯的時間是這本詩集的美學基礎,「我也想愛一個人」、「我不懼怕突如的愛」、「你不再淨白」、「那時候,也只剩下你了」、「你準備著三十歲後的死亡」,這些時態皆出自於詩題,而詩作本身則浮貼了從這些時態中出發的內在視域,詩人不停地用語言切分出「之前/之後」、「以前/以後」、「突如」或「不再」等時差,讓詩中種種詩人與「你」的雙聲合唱,成為詩人與自己的對話:確立自身的哀愁或快樂,同時又以自己的視線,牢牢地望著那一個空無的,「你」可能存在的地方。
只有從個人的視角出發,才會有「你不再淨白」這樣的判斷。「不再」,作為曾經的對比,詩作中時態恆常的周折扭轉,其後潛藏的是詩人所慾望的是否存在的問題。但我並不認為詩人在詩裡表現的慾望,只由遺憾或劬勞的感嘆組成,這樣的判斷太小看詩人自戀的程度,他不停地回首空無的那一個倒映的光,不停閃爍刺進他的文學視角之中的──是「此曾在」(Ça a été),一個動態的、更積極的時間想像。不會因為單一的詩作將「你」收納於過去,從此只剩回憶──遠不止於此,不在場的「你」同時還伴著詩作裡的內在生命,被懸置在一個時空混亂的癥結點:當詩人回憶,「你」便與現在對比;當詩人期待,他便失去「你」:
你住在這麼裡面,你不是內心
你不是最重要的片刻
你不像跑步時候淋過的雨
不像吹風機
不是為什麼
像一長串討論選擇餐館的對話
像打電話後的反悔
不是情人間的約定
像一張乾淨床單
你坐在上面,你也想要遺忘
──〈你站在這麼遠而且你沒辦法靠近〉
悄悄開啟一個黑夜
這麼深沉地躺在水色的土上
像小鹿般睡著
以至於,星斗為此騰出一段時間
與你說點話
「翠石、山形、在夜中流動的河」
黑鐵般躺在光質的夢境
「圍繞在森林周遭,流星安靜地通過」
沒有任何野草前來打擾
「逃離者點起另一營火,有霧因此而來」
──〈與你說點話〉
「你」被詩人拉進了他慾望的運作邏輯之中,「你」是他所慾望的身分、關係、思想,或單純的存在。當他慾望「你」,他慾望的動作本身就不停地構成在「你」之外的其他慾望。
他想要的,與他所得到的,中間出現了一道落差。他終究沒慾望到他想要的情感、物事、或是「你」,但詩作的內在時間早已成立,不肯再多等詩人片刻:寫詩以前,詩人凝視那個遙遠的空無處;寫完了詩,「你」就在外頭,詩人就在裡頭,縫隙永恆地落在那裏;詩人如果走到屋外,只能夠回首凝視空無處,他終要起步離去(當他寫詩,他就已經開始離去);如果他在屋內,森林、陷阱、隧道、雲、雨水與霧氣,那一層又一層反覆使用的意象,便成為無窗的屋裡最奢侈的想像。
即使奢侈、即使想像,被時間與空間隔出裡外的詩作,我見到的卻是詩人無法避免的偏移。如我上面提到,詩人慾望的「你」將會因為詩作的完成而越離越遠,這些以「你」為目標的詩作,便不可遏止地逸離了它原本可能的目標。
我這樣理解這些詩作中「你/我」、「裡/外」所呈現的運動狀態:當「你」現身,世界靜默;當「你」離去,森林上有星、時間依然湍流、有鹿走過花坡。而詩人只能從外面的聲音變化,得知「你」是否曾經靠近。但彼此永遠碰不到面。
這是徹底的別離,儘管告別並非詩人的目的。但我還是看見了,當界線確立,裡外有別,剩下的就只是峽谷。情感從此停留在不同的時態裡,而詩人說出的話,永遠不會是現在進行式。
最後,世界因此而感傷地自足。
祝福這本詩集。
.有時會提到「他」。對話人稱不同,就要用別的方式來思考。這裡我先以最搶眼的「你」開始。
2.參見詩集裡的畫作,對比詩裡的繁星,莊東橋畫作中的世界觀極簡、少有屋外的景觀。〈萬物再度呼吸〉,那是莊東橋版本的抵達之謎。
蕭鈞毅
現就讀於清大台文所,《秘密讀者》編輯委員其一,得過幾個文學獎。在寫小說與研究之中總覺得日子難過,現正與論文肉搏中。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跋 來自外面的回音──蕭鈞毅
這本詩集就是一個自足的世界。
詩人靜默地與之對話的,是名為「你」的情感集合處 。「你」的身影未曾具體,只存在動作、時態、某支雙人舞裡悄然的承諾、遺憾或是暗夜繁星裡頭。「你」被提取出來,成為了詩人的對立面。所有對「你」的感嘆與召喚,部分來自於重新確認自己的渴望;而另一部分,源自於被時間折損、徒留情感之剩餘,卻再無他人的遙遠之處。
即使知道那裏沒有任何物事,詩人仍然執著地凝視。
直到他看見那裡,有東西正倒映著光。那個世界的物質,是詩人的這個世界的殘餘...
章節試閱
自序
0.
九月,把行李打包好
我想起了地球另一端,我想起
去年的這個時候
一封分手信伴隨著一顆行星來到
揚起的塵土和碎裂的地表
1.
或是在颳起風的時候,我什麼都不說,連落葉掉在地上,我也不說。
擁有一個人,只是一種記憶。
2.
不是離開、逃離、離別或遠離,
而是往那個方向去、在那個國度、另一個地方或是下一個地方。
3.
我的夢是星做的,一到日出就消失。
一到日出,我的夢是海做的。
一到海邊,我的夢就會在浪上
畫出一些圖案
比如說家
比如一頓飯,和妳吃飯。
4.
離別,還有暫別。
這幾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妳變成這樣。
5.
你知道有些時候會心神不寧,像是就要出發到某地,卻連班次時刻都還未查詢。
七月,重生者的季節;而之前活下去的,會趁此時益發茁壯。
6.
我很不安
像是深夜,害怕太過大聲。
7.
驟雨,常聽見內心有這兩個字的回音。
8.
不能,什麼都不可以輕易地碰觸,不可以用靈魂,也不可以用眼淚。
然而忽然間有風吹起,聽說春天早上有陽光,接近傍晚,冷風颳起。
不能輕易地答應了邀約,就把期望投入進去。
不能抓住了什麼,就輕易地整個人攀上。
不能,什麼都不能抓住,不能用手心,也不能用手背。
不能,什麼都不能太輕易地認定。
9.
睡眠是黑夜故意挖出的池塘。
【我也想愛一個人,像你愛我一樣】
我也想愛一個人
像當初的夢想,只是一間房屋
我想今天是不可能了
我也想為一個人而耗費
像那些退後的海
像剛點起的燈正要明亮
我想在一個人臉上留下唇痕
在額頭上留下想念
像是剛開始,所有的星石聚攏在暗處
如果有光倏忽地經過就一擁而上
我也想和你一樣,為了最初好好地愛一個人
不論那人如何衰敗
衰敗是你不計較的
讓雲開在土壤
一群鹿走過有花的坡
我也想有一個家,長在靠近森林那端
我也想愛一個人,像你愛我一樣
可以原諒,可以被原諒
我也想好好地照顧、教導以及陪伴一個人
像你陪著我長大
像剛發芽的溫暖,找到合適的水瓶
我也開始像你一樣,在沉默裡面隱隱存在
原來你不是沒說話,原來我只是不夠專注
【我愛的人會老】
我愛的人會老
我的愛會老
我的老
是愛我的人
送我的
我的懺悔會被赦免
我的歡愉歪斜我的殿堂
我送給摯愛的
是一株破口的百合
我避免談及那個家
我選擇單人床
我的背包是一間臥室
我的皮夾沒有照片
幾分錢和一張車票
我喜愛的花都在山谷
我的蜂巢,我擅長豢養空的蜂巢
我不談死去
經過墓園的列車很快就離站
頭頂上那盞燈輕微地晃
我的內心正視著我剛撇過的頭
我愛的人正在老去
我的鞋底快要磨平耗損
我的懺悔仍被赦免
我的歡愉如同雷聲哭號
我的殿堂啊
愛我的人從裡面摘了一朵無瑕的百合
給我
自序
0.
九月,把行李打包好
我想起了地球另一端,我想起
去年的這個時候
一封分手信伴隨著一顆行星來到
揚起的塵土和碎裂的地表
1.
或是在颳起風的時候,我什麼都不說,連落葉掉在地上,我也不說。
擁有一個人,只是一種記憶。
2.
不是離開、逃離、離別或遠離,
而是往那個方向去、在那個國度、另一個地方或是下一個地方。
3.
我的夢是星做的,一到日出就消失。
一到日出,我的夢是海做的。
一到海邊,我的夢就會在浪上
畫出一些圖案
比如說家
比如一頓...
推薦序
【推薦序一】看什麼都像花 ── 黃浩嘉
做為一個曾經(或許)精壯的成年男子,他已開始面對必然且越來越具體的限制,有些秘密聚在一起,有了質量--他看到自己黑洞的能耐。唯一能消磨黑洞的只有時間;曾經旺盛地趨向於美的他,也將面對時間的消磨,於是他像對待秘密,幫這些黑安上翅膀,像是已有翅膀的愛與幸福。中性而公平地看待那些「黑」需要美感;中性而公平地看待幸福需要深度。他沉穩沉穩地,用詩。我想,他的野心不在詩,更像是要美美的悼念,以示莊重。
悄悄開啟一個黑夜
這麼深沉地躺在水色的土上
像小鹿般睡著
以至於,星斗為此騰出一段時間
與你說點話
「翠石、山形、在夜中流動的河」
黑鐵般躺在光質的夢境
「圍繞在森林週遭,流星安靜地通過」
沒有任何野草前來打擾
「逃離者點起另一營火,有霧因此而來」
--〈與你說點話〉
他的野心不在詩,或許反而好,那讓他不是這麼怕老。適合他的老派,像一個紳士對於美好了然於心。他知道怎麼樣恰當地任性與可愛,在一個成年男子身上,這總是難,總是過猶不及。當他既不暖男也不草食地建構出困境與觀點,他是這麼赤裸,他不怕使你畏懼,只怕你帶著誤解走開。
我想把最無力的,放在那裡
等到該日來到,就會被燒掉
你不好奇我無力的原因,你是力量
你不好奇我的枕邊,突然變冷的原因
我可能在自瀆,可能在自嘲
我可能在脫衣,可能在性愛
我可能忽然醒來,意識忽然清楚
我可能點一根菸,可能禱告
你不好奇我的意識
你不好奇我行為之前,你做了什麼,而我都接受。
--〈甚至我向你要一點快樂〉
像司機習慣了每個客人上車都有要去的地方;廚師習慣了每種生物送來都有適合的菜餚,他在送往迎來之間也有了習慣,進而有了看待這一切的情懷。像是寂寞的人慢慢看什麼都像花。然而你多半無法感覺,這一切如何演變如斯,關於他怎樣老的,這本詩集呈現得十分合宜。所謂合宜,就是你可以選擇要不要知道。他努力地列舉各種情境與選擇,每條岔路你都可能遲疑過,但你不會記得,因為你選好了。
我不談死去
經過墓園的列車很快就離站
頭頂上那盞燈輕微地晃
我的內心正視著我剛撇過的頭
我愛的人正在老去
我的鞋底快要磨平耗損
我的懺悔仍被赦免
我的歡愉如同雷聲哭號
我的殿堂啊
愛我的人從裡面摘了一朵無瑕的百合
給我
--〈我愛的人會老〉
他也畫畫,我曾問過他,為什麼不放畫在詩集的封面,他告訴我「雖然詩是我寫的,畫畫的也是我,但現在沒有把他們湊在一起的理由。」,想來詩是他盡力的另一種方式,畫與詩都是獨特的儀式,一以眺望、一以傾訴。從〈萬物再度呼吸 003〉這幅畫開始,他知道自己會溢散,但不會消逝,往後的詩慢慢地相信、切合「我不懼怕突如的愛」。但不懼怕,並不是單純的勇氣,是更陰性的領悟,這把他變成一個中性的人,這使得他看來顯得成熟而遠慮,而有了本質上的從容。
我看見前面有樹
路旁有花
害怕狼群認出我的腳步
我看見前面有樹
樹上有風在築巢
我害怕野巢
我害怕掉落的蛋
--〈害怕睡前一盞燈〉
他用詩呼喚曾經的你,也用詩找到現在的自己,你看,這是多麼適合世界毀滅後偶然被倖存的你讀到的一本詩集。最後,我個人想跟他說,你是大藝術家,你真心創作的愛無價*。
*節錄自歌曲〈大藝術家〉
對失去最愛的恐懼
你怎麼能只在旁邊
你應該要進來,再進來
進入消失的那一塊
但是我害怕我的
我害怕我的沮喪
你要負責
撐住每一片屋瓦
--〈你不害怕我的沮喪,但是我害怕我的。〉
黃浩嘉(喵球) ︱ 出版過詩集《要不我不要》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畢業。曾在快炒店內場、咖啡店內場工作。無法不去注意路上被壓扁的各種動物屍體;愛洗澡,很會長腳皮。
【推薦序二】王志元
莊東橋又找我寫序,這件事有點奇怪,因為第一本我已經寫過了。本來想拒絕,因為我們之間還是不談詩(這點第一本序也說過了),這麼不長進的事何苦讓人知道兩次?但我最後答應下來,無非還是希望能為他的詩集做點什麼。對我而言,莊東橋的風格在同年紀詩人中相當少見,我仍覺得有必讓多點人讀到。
他的第一本詩集《我們三個》只印了五十本,這件事我唸了很久,覺得非常可惜。但很多事情你無法勉強他,他自有他的腳步。比如說將作品依創作時間順序來集結成冊,這麼老派的方法他還是要做,這種拗執在這次詩集裡也看得見。比如說詩題中的「我」,又或者重複出現的意象,例如森林、宇宙、星、光、水、……他像是偶爾見面的老同學,反覆講著某段回不去的時光。而那個時光,其實只依存著幾個薄弱的記憶點作為證據。只是這本《我不懼怕突如的愛》更不踏實,他講的是一個從不存在的地方。
不存在的「森林」,成了詩人的避難之地。詩行裡並不總是花花草草有霧有雲,偶而會有「現實」侵入,但無論是「一片過於人工的海灘」(〈我想用森林的漆黑來安慰〉);還是「水龍頭的冷水」(〈你聽〉)出現的一瞬,似乎都只是為了加強「森林」的美好。是別過臉去的姿態,以及「刪去法」(我不……)的語句,造就了這本詩集。其實更接近於祈禱吧。「你」的應許與曾在,成了森林美好的基礎;而我只能祈禱或祈求(〈甚至我向你要一點快樂〉)。莊東橋說《我不懼怕突如的愛》是他在2008-2012年間的創作,大概就是他留法期間。我問他,留學時挫折感有這麼重嗎?他回答我:「就是個魯蛇啊。」
相較於《我們三個》裡那個懷抱著小小種子,平和午後的感覺,《我不懼怕突如的愛》對現實幾乎可算是絕望了。他離開眾人,潛入森林裡(〈這一次我沒有離開〉),看見了什麼呢?留法學藝術的他,回到台灣後仍持續著繪畫創作。《我不懼怕突如的愛》最特別的是,莊東橋終於將畫作放了上來。畫會是他別過臉(詩)後望向的所在嗎?森林會在裡面嗎?我看著《家屋之夢005》左上角看似永恆的缺口,不禁想著這個問題。
王志元︱出版過詩集《葬禮》
喜歡觀眾少的棒球比賽,獨奏的爵士樂手,廉價威士忌,和可以反覆背誦的句子。每次酒醒後從棺材裡站起來,就得重新詮釋世界一次。覺得寫詩就像在比黑還深一些的夜裡行走,有些鬼魂向我招手,有些則面無表情,而前方那點火光,究竟還能期盼什麼?
【推薦序一】看什麼都像花 ── 黃浩嘉
做為一個曾經(或許)精壯的成年男子,他已開始面對必然且越來越具體的限制,有些秘密聚在一起,有了質量--他看到自己黑洞的能耐。唯一能消磨黑洞的只有時間;曾經旺盛地趨向於美的他,也將面對時間的消磨,於是他像對待秘密,幫這些黑安上翅膀,像是已有翅膀的愛與幸福。中性而公平地看待那些「黑」需要美感;中性而公平地看待幸福需要深度。他沉穩沉穩地,用詩。我想,他的野心不在詩,更像是要美美的悼念,以示莊重。
悄悄開啟一個黑夜
這麼深沉地躺在水色的土上
像小鹿般睡著
以至於...

 共
共